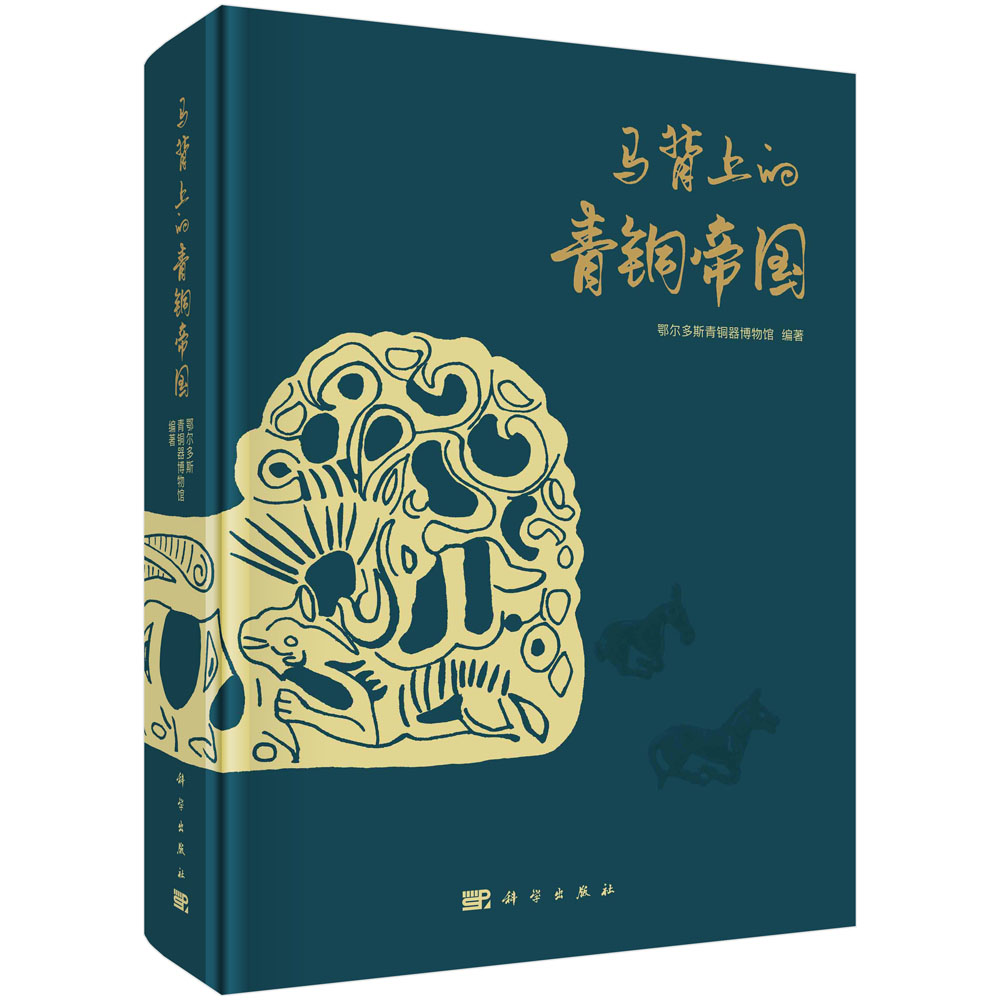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468.00
折扣价: 369.72
折扣购买: 马背上的青铜帝国
ISBN: 9787030678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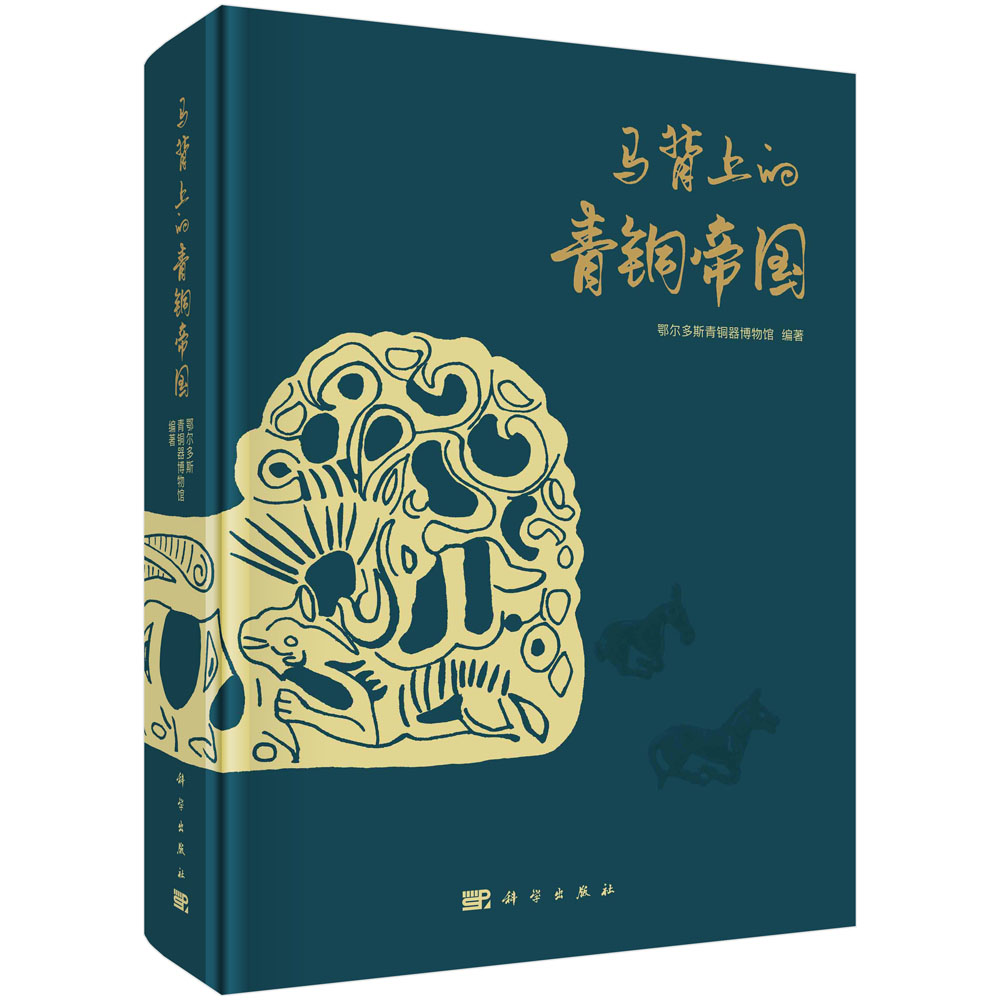
第一章鄂尔多斯与北方系青铜器
一鄂尔多斯地理历史概况
黄河中上游流经一块隆起的高原,这里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属西北黄土高原的最北端,黄河在这里沿高原的西部北上,又向东折,然后顺东部南下,形成一个“几”字形的大回旋,正好置高原于一曲之内(图1-1)。历史上,这里曾有过“河南地”“新秦中”“河套”等称谓,自明朝天顺年间(15 世纪中叶)以来,因蒙古鄂尔多斯部长期驻牧在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这里也被称作“鄂尔多斯”。清朝初期,漠南蒙古归附清廷,鄂尔多斯部被划分为六旗(后增设为七旗),合为一盟,称伊克昭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沿用此名。2001 年4 月,国务院批准撤销伊克昭盟设立地级鄂尔多斯市。鄂尔多(Ordo)为蒙语“宫帐”“宫殿”之意,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曾写作“斡耳朵”或“斡鲁多”等。约从唐代的突厥民族开始,活动在北方草原上的众多游牧民族,便把具有“宫殿” 性质的“大帐”称为“斡耳朵”。鄂尔多斯(Ordos)则是蒙古语中斡耳朵的复数形式,即“众多宫帐”之意。据史料记载,早在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便建有“四大斡耳朵”,为了保卫这些斡耳朵,成吉思汗特意抽调亲信、骨干,组成了一支专司守护之职的贴身卫队,成为蒙古草原上负有特殊使命的组织。成吉思汗逝世后,根据蒙古民族的传统习俗,真身入葬,而将象征成吉思汗灵魂的灵柩、遗像及生前使用的物品等依旧供奉在这些宫帐内,接受人们的四时祭拜,于是这些斡耳朵便成为祭祀成吉思汗的移动陵寝,作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祇”或“奉祀之神”,相伴在蒙古宫廷左右。守护斡耳朵的组织严格按照祖训世代相承,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个组织的子孙日渐繁盛,便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鄂尔多斯遂成为这个专职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部族的族名(图1-2)。
鄂尔多斯市位于北纬37° 35′至40° 51′,东经106° 42′至111° 27′,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西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壤,西北与乌海市毗邻,北与巴彦淖尔市、包头市、托克托县隔河相望,东与清水河县和山西省的偏关县、河曲县以黄河为界,南接陕西省的府谷、神木、榆林、靖边、横山等县。东西长约400 千米,南北宽约340 千米,面积约8.7万平方千米。历史上的鄂尔多斯所泛指的区域要比现今广泛,还应该包括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杭锦后旗、五原县、乌拉特前旗,陕西省的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等县、市、区的部分地区。
鄂尔多斯南部地处黄土高原的最北端,北部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地势由南、北分别向中部隆起,于达拉特旗敖包梁、东胜至杭锦旗四十里梁一线,形成一条高耸而宽阔的分水岭,境内的河流分别向南、北注入黄河干流或支流。鄂尔多斯东部最低处海拔为850 米,西部最高处海拔2149 米,平均海拔1100—1500 米。鄂尔多斯东南部是山峦纵横、沟壑连绵的丘陵地貌,西北部则是一望无垠的荒漠草原,著名的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分别漫漫横亘高原南北,绵延起伏的乌仁都希山脉雄踞西端。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和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导致了鄂尔多斯地区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鄂尔多斯三面环黄河,北有阴山之天险,西有贺兰山做屏障,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图1-1 鄂尔多斯东部黄河图
图1-2 成吉思汗陵全景
由鄂尔多斯向北过黄河越阴山,便进入广袤无垠的蒙古高原;而顺鄂尔多斯南下,便可直达中原腹地;阴山山前又是贯通东西的大通道,因此,鄂尔多斯地区既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的重要通道,又是北方诸族进入中原的跳板。
这里曾经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地,坚硬、古老的岩石默默倾诉着地球混沌初开期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还曾是一片茫茫的大海,三叶虫、海百合等低等生物的石化遗骸,竞相述说着生物进化史的历程和鄂尔多斯古海的腾喧。这里是爬行动物的世界、恐龙家族的王国,漫山遍野、形态各异的恐龙足迹印痕化石,令你目不暇接于“恐龙王国”时代的热闹非凡。这里还是哺乳动物的摇篮,巨犀、大唇犀、披毛犀等早已灭绝了的动物饱经风霜的遗骸上,记录着你急于探寻的一切。
鄂尔多斯地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错带,是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造就了这里多样的生态环境格局,也孕育了这里独特的人类文明进程。
地处鄂尔多斯东南部的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黄土堆积中,蕴含丰富的第四纪古动物化石资源,寓意着这里同样具备远古人类进化、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而近年在准格尔旗南流黄河西岸开展的旧石器考古调查显示,在这里发现距今20 万年以前、甚至更久远古人类的活动行踪,只需假以时日。
距今14 万—7 万年前生活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河套(鄂尔多斯)人”(图1-3),是鄂尔多斯这块古老土地上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也是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智人化石,他们极有可能是中国现代人的直系祖先。作为北方小石器文化系统的使用者,“河套(鄂尔多斯)人”不但奏响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的多彩乐章,而且成为远古时代沟通欧亚大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锋。
大约距今7 万年前,鄂尔多斯地区也进入了地球历史上的末次冰期,虽然整体处于一种干旱、寒冷的自然环境下,但地处内陆深处的优越地理条件,造就了这里在全球性的冰期大气候下,受反复交替气候旋回影响而轮回形成暖湿或温凉且降水丰富的局地小气候。新近发现的生活在距今6.5 万—5 万年前的乌兰木伦遗址的古人类,和生活在鄂尔多斯台地南缘的“水洞沟人”,便是相继追逐这些暖湿期形成的绿洲、活动在鄂尔多斯大地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类。
乌兰木伦遗址时代介于萨拉乌苏文化与水洞沟文化之间,文化面貌也与两者具有一定的相承关系(图1-4)。该遗址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物,还拥有埋藏学、年代学依据和以石器工业特征展现的文化系统,因此,在构筑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体系中的重图1-4 乌兰木伦遗址远景要作用令人瞩目。另外,乌兰木伦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密度之大,实属罕见,究其原因,或许和这里蕴含大量可供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原材料有直接的关联。假如确实如此,古老的鄂尔多斯不仅在21 世纪作为新型能源基地为世界所瞩目,数万年前,已经作为重要的能源基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水洞沟人生存的时代为距今4 万—1.5 万年,所处的自然环境远不及萨拉乌苏遗址和乌兰木伦遗址,因此,尽管他们仰仗弓箭技术等的娴熟应用使得生存能力大为提高,但在整体寒冷、干旱的恶劣气候面前,必须频繁地长途迁徙,去追逐适宜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赖以生存的各类动物。大范围的迁徙,使他们和欧亚草原地带的广大先民们产生了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水洞沟人以秉承着北方小石器文化传统,同时拥有大量成熟的欧亚草原地区特有的石叶形石片,而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即将开启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北方草原地带细石器文化(早期典型草原文化)的滥觞。水洞沟文化的这些特有属性,不但对我国华北地区同时期的远古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步入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生活繁衍在这里的古代先民,在这块水草丰美、气候宜人的神奇土地上,再次掀起了鄂尔多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中国北方文化圈中心区的鄂尔多斯先民,既与中原华夏族同源共祖,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所谱写的以“阳湾人”“海生不浪文化”“阿善文化”“老虎山(永兴店)文化”等为代表的壮美乐章,记录了他们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所做出的不朽功勋(图1-5)。
四千多年前,“朱开沟文化”的古代先民,面对生态环境向干冷方向的不断恶化,适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畜牧经济应运而生,也就此拉开了北方畜牧民族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活动的帷幕(图1-6)。两周时期,以狄—匈奴系统为代表的新兴马背民族,在广袤的鄂尔多斯大地上开创了中国北方早期游牧文明的新纪元。作为其物质文化载体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也以它原生态的草原文化气息、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1-5 新石器时代出土典型陶器
1. 贺家沙背遗址出土的红陶瓶 2. 永兴店遗址出土的陶鬲 3. 奎银生沟遗址出土的尖底瓶
公元前306 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把势力范围深入鄂尔多斯北部沿河地带。公元前304 年,秦昭襄王控地北至上郡,鄂尔多斯东南部纳入秦的疆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为巩固北方的统治,修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图1-7)。并从内地迁来大批移民,垦田耕植,广筑县城。伴随秦、汉封建王朝对鄂尔多斯地区的不断开发,这里不仅又一次掀起了民族汇集的浪潮,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给鄂尔多斯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等方民族的南迁,使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融合达到空前的境地,为古老的鄂尔多斯不断注入了新的生机。隋唐时期的鄂尔多斯,既是隋唐王朝的北疆重地,也是与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广阔的鄂尔多斯大地上,遗留下大量这一时期的珍贵文化遗存。
唐代后期,吐蕃的强大迫使党项人逐步迁徙到鄂尔多斯南部,并于北宋初期建立了西夏国。鄂尔多斯丰美的天然牧场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为西夏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使得西夏国实力大增,雄踞北方与辽、金、宋对峙,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朵奇葩(图1-8、图1-9)。
图1-6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蛇纹陶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