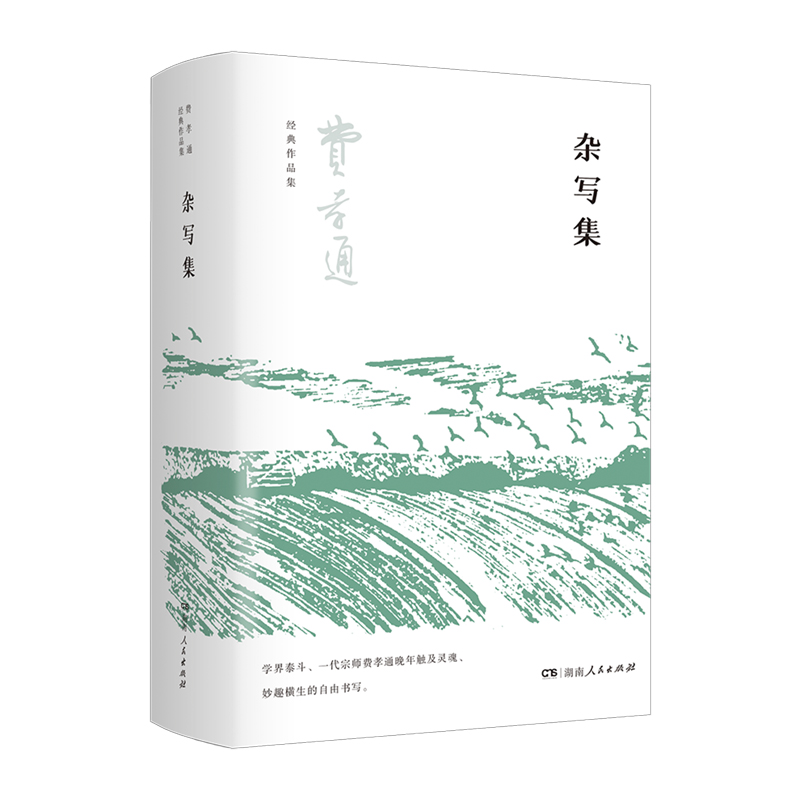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售价: 152.00
折扣价: 89.68
折扣购买: 杂写集
ISBN: 9787556130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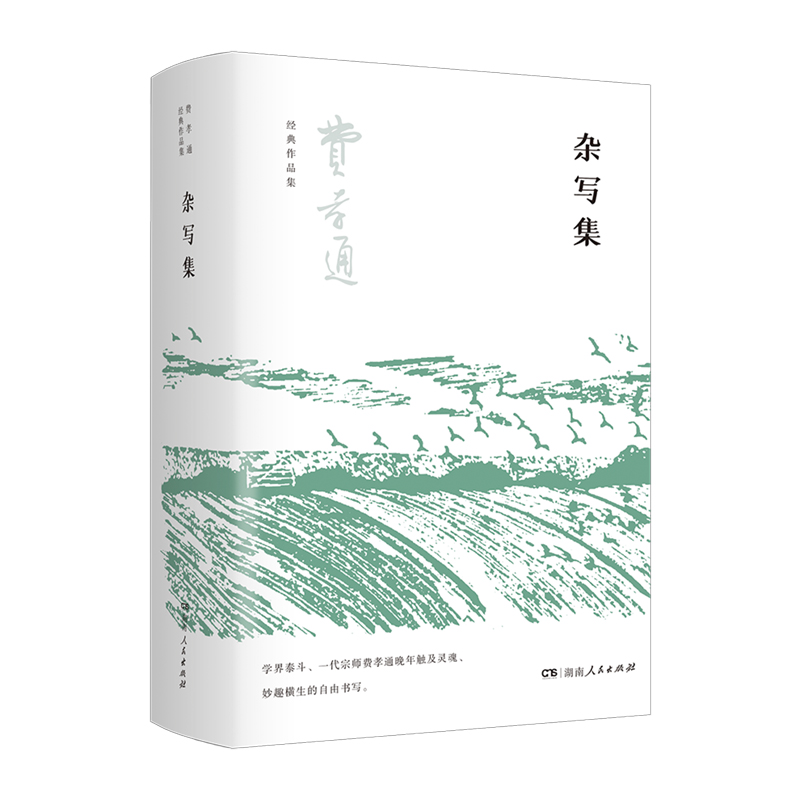
费孝通(1910—2005) 江苏吴江人。20世纪中国卓越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曾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
政治上的启蒙 每个人有他的政治生命。 我是依靠民盟这个组织走过来的。在发生着这样剧烈变动的中国, 近半个世纪以来, 我能始终跟着全国人民一起在前进的道路上坚持下来, 这不能不感激民盟给我的指引 : 实际上, 也就是党通过民盟这个组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导。 离开了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领导力量, 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和民盟是什么时候发生关系的呢? 这个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回答。 每次填写履历表时, 在这个问题上我总得踌躇一番。是有了点年纪记忆衰退了呢, 还是另有难于刻舟求剑的情景呢? 生理上的变化是免不了的, 许多事确是模糊了 ; 但是如果说像这样一件在个人政治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事, 脑中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是难于令人相信的。 实际的情形是, 那时参加一个政治组织和现在人们所熟习的那一套是不完全相同的。 填表申请那些手续当时被看成是一些形式。 说这些是形式就带有无足轻重、 可有可无的意思。 政治组织在我们那时候是一种道义之交, 握手成誓, 用不着形式。现在不妨批评说, 这是缺乏组织观念。 其实也可以说, 这些事情那时还没有制度化, 或还没有现代组织化。 总之, 像民盟那种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开始时多少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结社模式, 尽管向共产党学得了一些组织方面的现代办法, 这些办法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似乎并不看得那样重要。 这种缺乏组织观念的情况至少反映了当时像我那样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启蒙状态。 启蒙状态是从不自觉到自觉, 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 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 并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行动, 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前一辈的情况我不清楚, 以我这一辈来说, 这件事, 就是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启蒙运动,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在抗战时期, 40年代, 在解放区以外的西南大后方, 民主同盟在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 实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促进了他们政治上的启蒙,逐步组织起来, 进行当时所标榜的民主运动和救亡运动 ; 也可以说, 就是把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引入革命的队伍。 回想一下, 作为一个亲自经历过的人, 怎样被引入革命的队伍, 不仅是有历史的价值, 还有现实的意义。 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经过千艰万苦进入了这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山区。 他们身受亡国之痛, 为了光复祖国河山是甘心接受折磨和牺牲的。 但是怎样才能取得抗战胜利,自己能在争取抗战胜利上做些什么事——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答案, 就是各有各的看法。 这是说, 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 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 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 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 抗战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 国民党的腐化和抗战不力已经暴露得很清楚, 但是在为什么会这样, 和怎样改变这状态等问题上, 思想情况是很复杂的。 关键问题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战、 真反共” 对大后方的人民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革命的立场需要启蒙的过程, 1941年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 对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 是给对国民党所抱幻想的有力打击。 从那时起, 我见到潘光旦、 闻一多、 吴晗等同志时总是要打听延安的消息, 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共产党是有联系的。 通过这个渠道, 我在政治上逐步倒向革命的一面。 也许可以这样说 : 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 师生、 同学、 同乡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 政治的觉悟导致原有的朋友之间分出亲疏 ; 有些谈得拢,有些谈不拢了。 有些信得过, 有些信不过了。 这也是政治启蒙过程中的一种表现。 以我自己说, 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 在我进清华以前就熟识的。 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 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来往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 但也是由于他是个常到潘先生家去的朋友所以特别熟, 昵称老晗。 从许多老师和同学中逐渐突出这几个人, 那就是和民盟组织关系的开始。 要我划定一个年月日,那是不容易的。 那时我和这几位同志的来往不仅在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 而且在行动上也配合了起来。 潘先生和云南地方势力有联系, 这是他的政治任务。 他利用这个关系, 开展对云南地方机关人员的宣传工作, 由缪云台先生出面组织进步教授到各机关去演讲。 我是一个有约必允的讲员。 我那时生活困难, 必须靠卖文补给, 潘先生就介绍我为云南各报写社论, 宣传进步观点,在后方起到一定的效果。 吴晗同志是做青年工作的。 他组织种种活动, 像时事讨论会等, 总是拉我去参加、 发言, 使我和联大和云大的学生发生了亲密的感情, 受到他们的鼓励和督促 ;即使枪子在头上飞, 我也义无回顾的。 当我做这些工作时, 并没有打听过这些朋友有什么政治组织。 我只是认定他们是信得过的, 他们要我做的事, 我就应该做, 不会错。 比如吴晗同志有一次很郑重地把一个名字交给我,要我把他安置在云大社会学系。 我明白这位先生一定有来路,但是我问也不问, 就照办了。 这位先生就是华岗同志, 党中央派来西南指导工作的。 我这样做心里觉得这才算是“够朋友”。有时候我回想起当时这种朦胧劲儿, 有些确是幼稚可笑, 但也常觉得它的可爱和可贵。 同志之间能这样重然诺, 轻生死, 肝胆相照, 言从不疑, 政治组织才有真正的生命。 民盟作为一个正式的、 有形的政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我至今还不清楚, 也没有关心过。 也许这个问题和我什么时候参加民盟组织的问题一样, 能搞得清楚当然最好, 作为一个问题搁一下, 也未始不可。 不论我哪年哪月正式由组织通过成了盟的成员, 我在1944年秋天之后, 我记得和盟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那时潘、 闻、 吴三位同志住到昆明城里来了, 我不久也搬回城里, 住在云大。 我们之间的往来从此更多了。 楚图南、 尚钺和潘大逵等同志原是云大的同事, 我那时也知道是“自己人”了。《 民主周刊》 有了个办事处, 离我们的住处很近, 大家碰头见面的机会更密了。 冯素陶同志就是那时相识的。 我也被社会上认为是盟员, 自己也就以盟员自居了。 我仿佛记得多年后为了填什么表, 问过潘先生谁是我的入盟介绍人, 他说写上他和吴晗就是了。 昆明的民盟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在当时的民主运动中是做出贡献的。 以民盟内部来说, 尽管各人对各个问题可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总是能实事求是地取得一致, 坚持了团结。 这种相互支持, 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 给我很深刻的教育。 民盟对我起了政治上的启蒙作用。 今天回想那些日子, 人事俱逝,这些可贵的萌芽令人神往。 人生的道路尚未终结, 似乎还应当以善保其赤子之心来勉励自己。 1981年6月14日 1.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费孝通先生晚年触及灵魂、妙趣横生的自由书写。费孝通家人张荣华先生授权出版。 2. 尘封三十五年后的再次面世,了解费孝通及其学术脉络绕不开的书目。 3. 历时五年、随心而作的小品文,还原一个中国文人借由文字书写而完成自我升华的真正历程。 4. 著名社会学家、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晚年入室弟子赵旭东亲著一万余字导读。导读中,赵旭东教授直观概括了费孝通的观点,帮助读者更深刻地思考、理解费老作品思想。 5. 书中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谈,立体地展现了一代人对书写及知识传播价值的思考和实际运用。 6. 了解费孝通作为文人、学者将其生活、兴趣与事业融为一体的情趣与乐趣。费孝通先生在书中透露出的生活志趣与处事方法,对普通读者多有启发。 7. 费孝通文字简明易懂,言之有物,句句都有信息点,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文字, 今人读之仍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