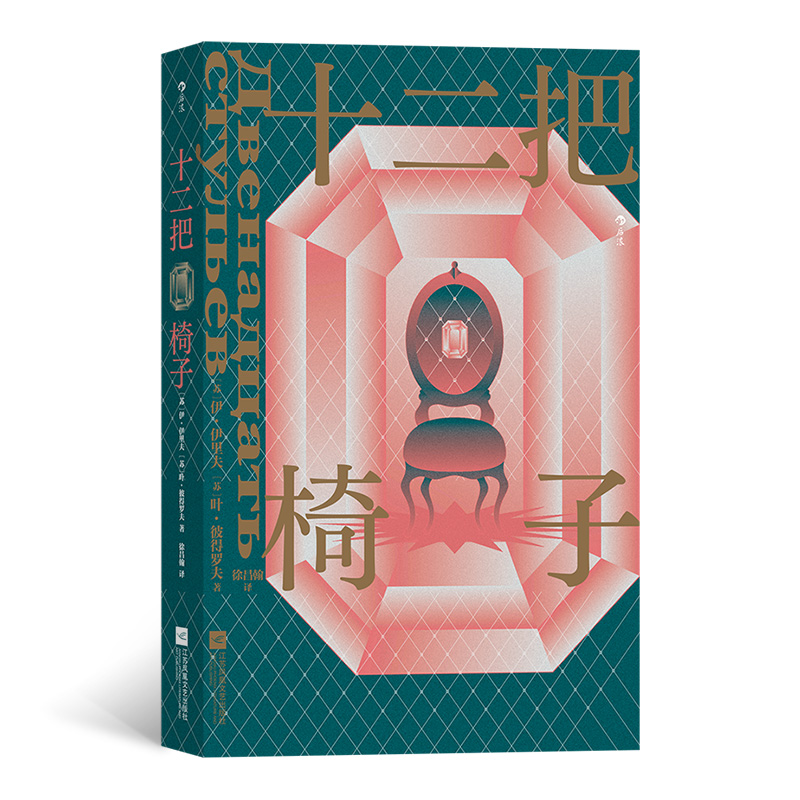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3.30
折扣购买: 十二把椅子
ISBN: 9787559461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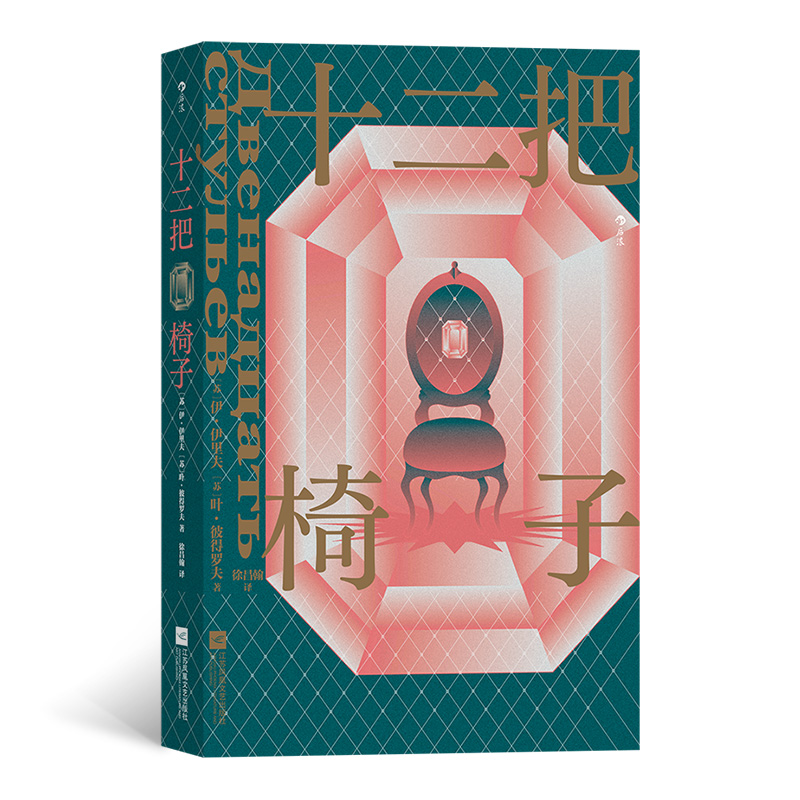
著者简介 伊·伊里夫 原名伊利亚?阿尔诺里多维奇?法因济尔贝格,一八九七年生于敖德萨一个银行职员家庭,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技术学校,曾任统计员和报刊编辑,一九二三年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铁路员工》《三十天》《苏维埃银幕》等刊物上发表了众多针砭时弊的特写、讽刺幽默小品、短篇故事和影评等。 叶·彼得罗夫 原名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卡达耶夫,一九〇三年生于敖德萨一个历史教师家庭,一九二〇年毕业于古典中学,先后担任乌克兰电讯社通讯员,刑事调査局检查员,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讽刺幽默杂志《红辣椒》编辑部工作,常以“外国人费道罗夫”的笔名在《共青团真理报》《笛声报》等刊物上发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杂文、特写、国际时事述评等。 一九二五年两位作家相识于莫斯科,次年开始合作。在他们共同创作的十年中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如: 《十二把椅子》(1928)及其续篇《金牛犊》(1931)、《光明磊落的人》(1928)、 《一层楼的美国》(1936),以及发表于《真理报》《文学报》《旗帜》杂志等重要刊物上的大量讽剌小品、短篇故事和剧作。令人惋惜的是,两位作家均为英年早逝:一九三七年伊里夫因肺病辞世,彼得罗夫则于一九四二年殉职于战地记者的工作岗位。
第一章 别津丘克和“山林女神” N 县城的理发馆和寿材铺是如此之多,好像当地人生来就是要刮刮脸,理理发,抹点生发油,然后好立刻去寿终正寝似的。其实,生儿育女、剃头刮脸、死人出殡之类的事在 N 县城还真是难得一见。这里的日子平平静静。春天的夜晚令人陶醉,月下的烂泥洼像无烟煤似的闪闪发光,城里的小伙子热恋着公用局工会的女秘书,缠得她连会费都没法收。 对于诸如恋爱、死亡之类的问题,伊坡利·沃罗边宁诺夫是无动于衷的,尽管按职权范围来说,每天早九点至晚五点,这些问题统统应归他处理,中间半小时午休吃饭除外。 早晨,他端起岳母佩图霍娃送来的凸花白奶杯,把自己那份滚烫的牛奶一饮而尽,然后就走出昏暗的小屋,踏上宽阔的古别伦斯基大 街。街头洒满了好久也不曾享受到的春天的阳光。在县城里,这样的大街算得上是顶顶顺眼的一条了,大街左侧,绿莹莹的玻璃窗凸凹不平,窗内陈列着山林女神寿材铺的一口口银白色的寿材。对街有几扇小窗,窗上的玻璃腻子已经掉光了,屋里堆了几口橡木棺材,都是棺材匠别津丘克的杰作,上面积满了灰尘,更显得阴沉而又乏味。往前去,是皮埃尔— 康斯坦丁理发馆,招牌上写着“修锉指甲,包您满意,上门烫发,服务周到”。接下去是一家旅馆,附设美容部,再往前,一片大空场上,孤零零矗立着一座大门,一头小黄牛正伸出舌头,含情脉脉地舔着那块靠在大门上的锈招牌: 敬请光临寿材店寿材铺虽说是鳞次栉比,上门的顾客却寥寥无几。早在伊坡利迁居 N 县城的前三年,敬请光临寿材店就已经破了产,棺材匠别津丘克愁得整天喝闷酒,有一天甚至想破罐子破摔,把他陈列的那口最好的寿材也押进当铺。 N 县城很少有死人的事,这一点伊坡利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供职的地方就是民事登记处,专管死亡和婚姻登记。伊坡利的办公桌活像一块旧棺材板,左角已经被耗子嗑得残缺不 全,桌上堆着一大摞胀鼓鼓、沉甸甸的黄褐色卷宗,压得四条细桌腿颤颤巍巍。卷宗里的登记表可以详细说明 N 县源远流长的住户们及其扎根于该县贫瘠土地上的列祖列宗的全部情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伊坡利照例于上午七时半睁开双眼,然后马上把一副老式金边夹鼻眼镜夹上鼻梁。这位先生从来没戴过普通眼镜。有一次,他觉得戴夹鼻眼镜有碍卫生,便到眼镜行配了一副镀金腿无框眼镜。乍一戴觉得挺好,可是老婆(那还是老婆死 前不久的事)却发现,一戴眼镜,他就成了个活脱的白匪头子米留科夫。这一来伊坡利只好把眼镜白白奉送给院子里的保洁。清扫夫并不近视,戴上眼镜却美滋滋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得劲。 伊坡利拖声懒调地用法语对自己说了声“日安”,把两腿从床边探下来。一声“日安”,说明伊坡利情绪颇佳。倘若醒过来用德语说一声“早上好”,那就往往意味着肝区不适。五十二岁啦,可不是闹着玩的!况且最近天气总这么潮乎乎的。 伊坡利伸出两条精瘦的细腿,朝单条出售的战前式裤子伸了进去,裤筒用腿带一扎,再把脚伸进柔软的小方头矮靿皮靴。五分钟后,他穿上漂亮的月白洒银坎肩,外面又罩上一件闪光料子上装,扑拉一下头发,挥去几颗洗脸时沾上的水珠,像只猫似的动动唇髭,犹犹豫豫地捋了捋刺哄哄的下巴,又拿起发刷刷了几下如银的短发,然后恭恭敬敬朝走进门来的岳母大人佩图霍娃微笑着迎了上去。 “伊坡 —利 —呀,”她的声音像打雷,“今天我做了个噩梦。” “梦”字说得带一股法国味儿。 伊坡利身高一米八五。有了这个高度,对岳母免不了就要有点儿轻慢。他居高临下,朝岳母瞥了一眼。 佩图霍娃接着说: “我梦见了死去的玛丽,披头散发,还系着一根金腰带。” 佩图霍娃的大嗓门响得像放大炮,震得铸铁吊灯的圆球和积满灰尘的玻璃璎珞都晃动起来。 “我担心,怕出什么事。” 最后这句话说得真有劲,震得伊坡利头上整整齐齐的头发竟轻轻一摇。他皱起眉头,一字一顿说: “妈,什么事也出不了。打水了吗?” 原来水还没打,套鞋也没擦。伊坡利可看不上这个岳母。佩图霍娃蠢得要命,年纪一大把,再想变聪明怕已来不及了。她吝啬得不像话,不过伊坡利穷得叮当响,所以她的这种绝妙的秉性倒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列位想必知道,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当年一声怒吼,曾吓 得战马四腿瘫软。这个女人嗓门又粗又大,就连狮心王理查听到,大概也要自叹弗如。除此而外,最可怕之处还在于佩图霍娃爱做梦。她总是梦个不停:梦见大姑娘扎着宽皮带,战马身上缝着龙骑兵的黄镶边;梦见扫院子的弹竖琴,宪兵老爷们穿着更夫的大皮袄,手里敲着 梆子巡夜;梦见毛衣针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发出一种听了叫人汗毛直竖的声音。 佩图霍娃是个无聊的老太婆,鼻子底下还长着两撇胡子,每一撇都像一把刮脸用的肥皂刷子。 伊坡利悻悻然出了家门。 ◎苏联幽默文学的至高杰作。 一经问世便广受好评,上至当时的苏维埃领袖,下到广大的基层群众,无不交口称赞。纳博科夫对本书青睐有加,称其为自己唯一喜爱的苏联文学作品。 ◎苏联笑话的完美展示。 全书内含大量苏联笑话,长短各异,题材丰富,既有市井八卦,也有政治调侃,堪称一本苏联笑话大全。苏联最专业的文学类报刊《文学报》将讽刺幽默专栏命名为“十二把椅子”。 ◎苏联文学影视改编之最。 本书共被10余个国家,直接改编超20余次。连纳粹德国都将这部苏联犹太人创作的小说拍成了电影,原作魅力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