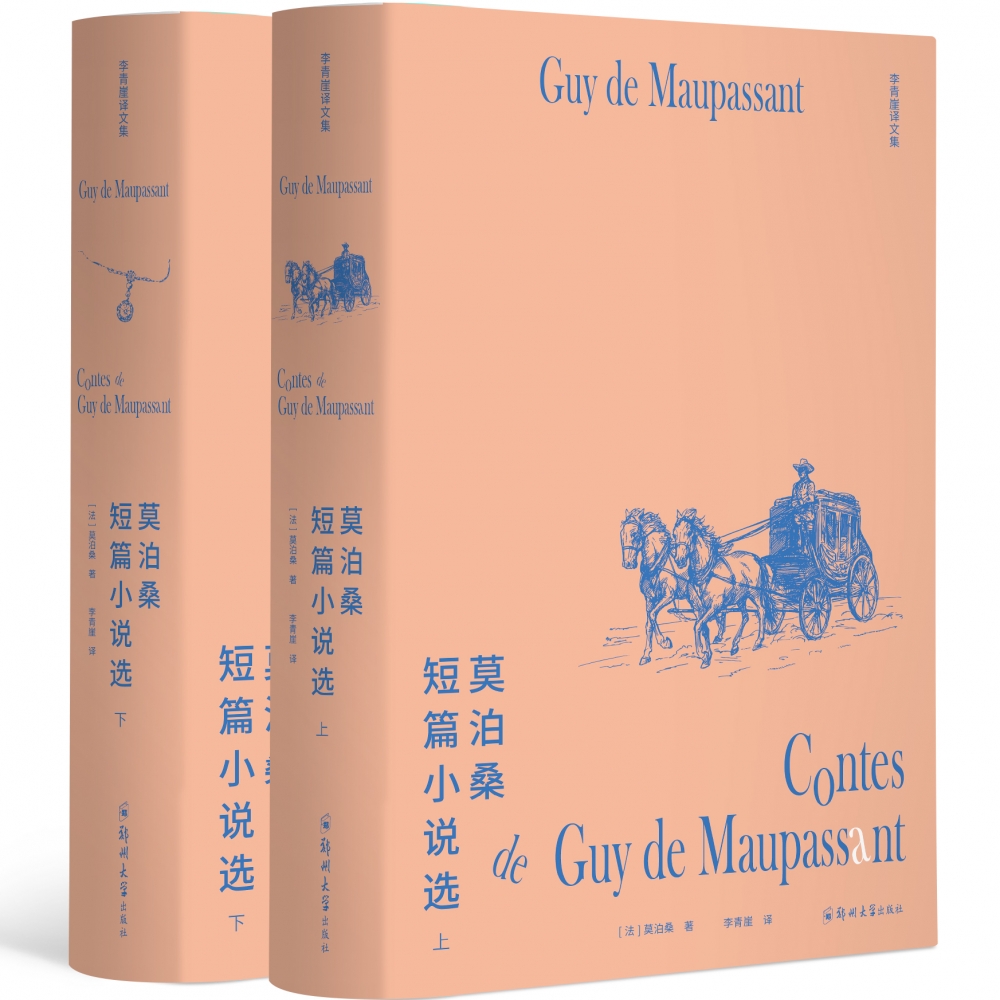
出版社: 郑州大学
原售价: 168.00
折扣价: 99.20
折扣购买: 李青崖译文集: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全两册插图版)
ISBN: 9787564581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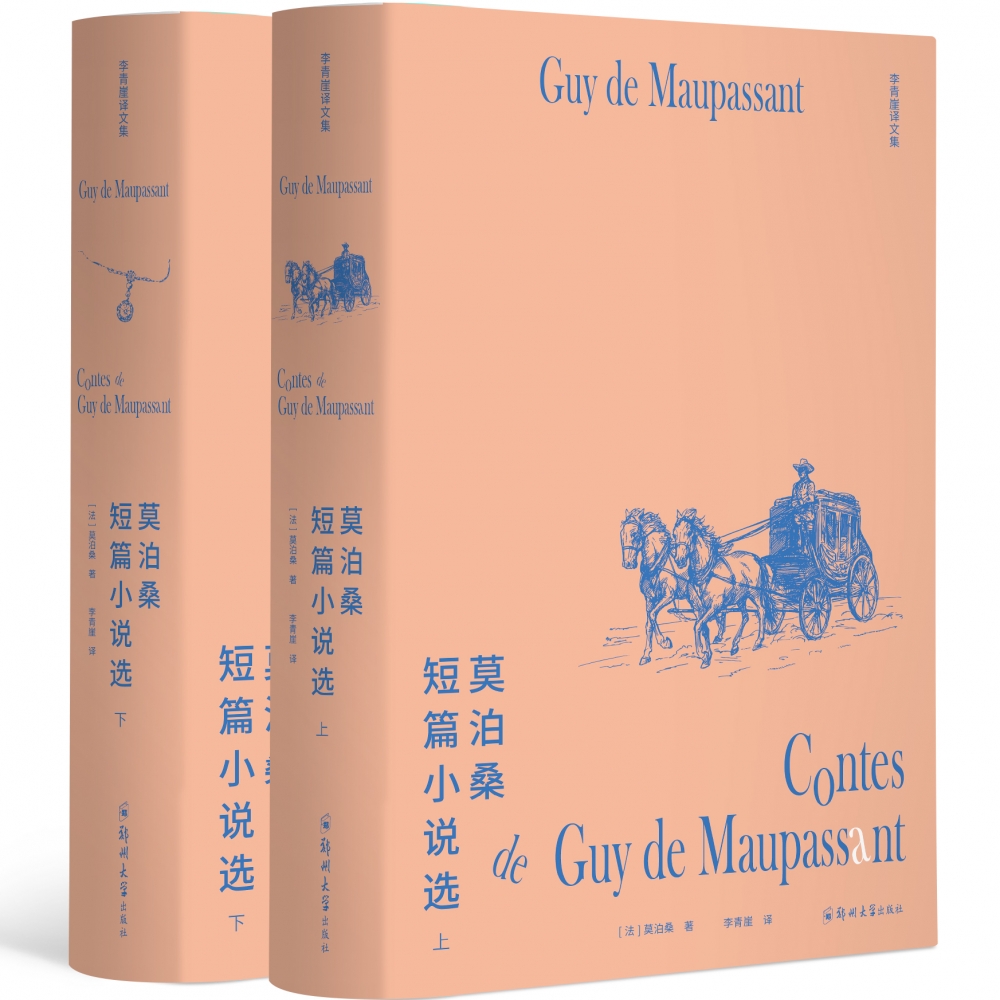
居伊?德?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师从福楼拜。 1880年,因中篇小说《羊脂球》一举成名。其一生创作了350多篇中短篇小说,以及《人生》《俊友》《温泉》等6部长篇小说和3部游记。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与契诃夫、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他善于从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挖掘出生命和生活的本质意义与美学价值的内涵,侧重描摹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其小说题材丰富,语言简洁而优美,清晰而犀利。 译者简介: 李青崖(1886-1969),名允,字戊如,号青崖,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其祖父李辅燿,官浙江候补道,被称为“清末修塘第一人”,他思想开明,将李青崖送入震旦学院攻读法语。 1907年,李青崖考取官费,赴比利时列日大学理学院攻读采矿专业。留学期间,他对法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同时选修文学课程。1912年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为支持进步学生留法,曾在自家开办预备班,教授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学习法语。 1921年,李青崖加入文学研究会,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在长沙组织湖光文学社。从此开始译介法国文学作品,并一生致力于这项事业。 李青崖堪称我国从法语原文翻译法国小说的第一人,对莫泊桑小说的翻译用功尤深,以二十余年心力,独自译出莫泊桑的所有作品。其他主要译著还有《包法利夫人》《饕餮的巴黎》《三个火枪手》《波纳尔之罪》等,为中国文坛与文学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写给洛倍尔?班史翁 鄱瓦代尔(安端)老爹在当地是个处理种种污秽工作具有专门技术的人。每逢我们应当扫除一条壕沟,一堆垃圾,一个积水坑,或者疏通一段下水道,一个泥坑之类,大家要去找的总是他。 他带着他那些做扫除疏通之用的工具和他那双满是污秽的木头鞋子过来,接着就动手工作,一面不住地抱怨自己的职业。到了有人因此问他为什么偏偏要做这种使人厌恶的工作,他就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气说: “还用多说,就是为了我那些不得不养活的孩子们。这工作比旁的赚得多一点。” 在事实上,他有十四个孩子。倘若旁人探询那些孩子们都做什么事,他就带着一种冷淡的神气说: “现在只剩下八个留在家里。有一个正在队伍里服务,五个都结了婚。” 到了有人要知道他们的婚姻是不是美满的时候,他就连忙回答道: “我从前并没有反对过他们。我从前简直没有反对过他们。他们全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结婚的。人总不应当反对旁人的口味,若是反对口味,结果总是弄不好的。我现在弄得这样肮脏,正因为我父母从前反对了我的口味。不然的话,我早可以变成一个像其余工人一样的工人。” 他父母从前反对他的口味的详细经过就在下面。 他当年是一个兵,在勒阿弗尔的营房里度着服务的年月,比起其他的兵并不来得愚笨些,也并不来得聪明些,不过头脑简单一点。在例假的钟点里,他的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码头上散步;沿码头一带本是鸟雀商人聚集的地方。他有时候独自一个人,有时候随着许多人,慢慢地沿着鸟笼子走过去,笼子里,有些是黄脑袋绿身子的巴西鹦鹉;有些是红脑袋灰色身子的西非洲鹦鹉;有些是身材巨大的南美洲鹦鹉,它们有五色的羽毛,撒开的长尾,矗立的冠毛,神气像是在暖房里培养的鸟;有些是大大小小的桐花凤,仿佛是由一个以“工笔画”出名的上帝用细腻的心情设色的,那些小的,很小很小跳来跳去的鹪鹩一般的鸟儿,红的,黄的,蓝的和杂色的,色色俱备;它们的叫唤和码头上的声响混在一起,在行人车辆和卸载船舶的喧闹中间,添入一种来自辽远而神秘的树林子里的激动,尖锐,嘈杂,震聋耳朵的噪音。 鄱瓦代尔站着不走了,睁着眼,张着嘴,喜笑颜开,露出牙齿,对着那些被人囚禁的鹦鹉,它们张开白的或者黄的冠毛,向他的军服裤子的鲜红颜色和他的腰带的光亮铜饰致敬。他到了遇见一只能够说话的鸟的时候,就向它提出好些问题;倘若那只鸟在那一天有能力回答他并且和他对谈,那么他直到夜间还是快活满意的。瞧着猴子,他也快快活活装出驼背的样子,并且他一点也没有想象到一个富人把这些动物像猫狗一样养着是最大的奢侈。这种口味,这种异国风光的口味,对他是深入血液的,正像旁人的口味着重于打猎,着重于做医生或者做教士一样。每逢营门一开,他总无法阻挡自己再到码头上去,俨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欲望的吸引。 谁知某一次,他站在一只来自南美洲的五色大鹦鹉跟前竟几乎是得意忘形的了,那只鹦鹉正张开了全身的毛,俯下了身子又竖起来,像是用鹦鹉国的宫廷礼貌致敬,他看见一家和那鸟店贴邻的小咖啡馆的门拉开了,接着就有一个头上缠着红包布的黑种青年女人出来了,她把馆里的酒瓶塞子和沙子向着街上扫。 鄱瓦代尔的精神立刻在鹦鹉和黑种女人之间分开了,他大概真的说不明白自己费了最为惊喜交集的态度去注视的,究竟是鹦鹉还是黑种女人。 把小咖啡馆里的垃圾扫出去以后,那黑种女人抬起头来望了,对着军人的服装她也目眩了好一会儿。她在他对面站着没有动,扫帚拿在手里正像是对着他举枪,同时那只鹦鹉也继续对着他鞠躬致敬。经过好一会儿之后,军人却被这样的注视弄得不好意思,于是他慢步走开了,表示自己并不是且战且退。 不过他又回来了。几乎每天一定在这家名叫“殖民地”的咖啡馆前面经过,并且时常透过窗口的玻璃,望见了那个黑种的矮小女堂倌给码头上来的海员们倒啤酒或者倒烧酒。她也常常在望见他的时候就走到了外边;不久,他们甚至于彼此从来没有说过话,就如同熟识的人似的互相向着微笑了;后来鄱瓦代尔看见那女人的颜色晦暗的嘴唇缝里有一排雪白的牙齿陡然发光,他觉得自己的心有点儿摇动。某一天,他终于进去了,发现她说的法国话和大家一样,因此很诧异起来。他叫了一瓶柠檬水,请她也喝一杯,她接受了,于是在军人的记忆当中那瓶水真是甜美得忘不了的;末后他养成了习惯,常到码头边的那家小酒馆里,去享受种种是他的腰包可以担负的甜美饮料了。 瞧着这个矮个儿女堂倌的黑手向他的杯子里斟上点儿东西,同时她满口的牙齿因为她笑着竟比眼睛还亮些,他心里觉得那是一个佳节,一种被他不住地思念的幸福。经过两个月的频繁来往,他和她完全成了知己了,而鄱瓦代尔在发现这个黑种姑娘的思想全和当地姑娘们的好思想一模一样以后,在发现她能够重视节约、劳动、宗教和品行以后,因此更其爱她了,他之对她的热衷竟到了想娶她的地步。 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她,这使她快乐得跳舞了一阵。并且她本有一笔数目不多的钱,那是一个买牡蛎的女商人留给她的,这女商人从前看见一个美国船长把她放在勒阿弗尔的码头上,她就收容了她。原来那船长在某次从纽约开船以后的几点钟,发现她蹲在他船上货舱的棉花包儿堆里,她当时的年龄约莫有六岁。到了勒阿弗尔,他就把这个不知怎样也不知被谁藏在他船上的皮肤乌黑小家伙,交给这个慈悲的女商人抚养了。女商人死了以后,于是青年的黑种姑娘就做了殖民地咖啡馆的女堂倌。 安端?鄱瓦代尔并且又说: “这是办得到的,倘若我父母不反对。我从来不违背他们,你听清楚,从来不!我最近一回到家乡,就把这事情先对他们说两句。” 第二周,得着了二十四小时的假期,他果然回到了家里,他父母在伊弗朵附近的都尔忒乡种着一个小田庄。 他静候着吃完饭以后的空儿,那时候,兑了烧酒的咖啡可以使人的胸襟格外开阔,他就告诉他的尊亲属,说自己找着了一个非常合他的口味的,合他一切口味的姑娘,世上应当再没有另外一个能够同样美满地和他合得上。 两老听到这种话立刻都成了顾虑周详的,对他盘问了好些情形。鄱瓦代尔什么话都没有隐瞒,除了她皮肤的颜色以外。 那是一个有好心眼儿的,没有多的财物,但是勇敢、节俭、清洁、有品行又有见识。这些事都比一点儿抓在一个坏女人手里的银钱的价值高些。并且她有好些铜子儿,好些大的铜子儿,都是从前抚养她的那个妇人遗下来的,差不多是一份小小的嫁奁费,一千五百金法郎的储蓄存款。两老被他的话说服了,尤其在他的判断之下表示信任,到了他快要提到微妙处所的时候,他们都慢慢地让步了。他用一阵略带拘束的笑容说: “只有一件事情将来不会合您们的意思。她的皮色简直不是白的。” 两老全没有懂,于是为了免得教他们失望,他不得不带着十分小心的态度来做了个长久的说明。他说她是属于颜色不鲜明的人种的,他们从前在埃皮纳勒那地方出产的画片上见过那个人种的样子。 这一来,两老都不放心了,迷糊了,害怕了,如同他对他们提议了一个要和魔鬼的结合。 那母亲说: “黑的?黑到什么样儿?全身可满是黑的?” 他回答说: “毫不折扣:全身,正和你全身满是白的一样。” 父亲接着说: “黑的?可是黑得像锅底一样?” 他们的儿子回答说: “也许没有那么黑!是黑的,固然,不过黑得一点也不教人倒胃口。教堂里堂长先生的袍子是很黑的,然而它并不比一件白的道袍难看。” 那父亲说: “在她的家乡,可有更黑的吗?” 儿子抱着信心高声嚷着: “自然一定有!” 但是老头儿摇着脑袋说: “那应当是教人不乐意的吧?” 儿子说: “那一点也不比旁的什么更教人不乐意,因为不要多久就看惯了。” 那母亲问: “不比旁的人要容易弄脏内衣吗,这种黑皮肤?” “不比你的更厉害,因为那是她的本来的颜色。” 又经过了好些问题,那件事终于谈出办法了,就是:两老在绝没有做任何决定以前,可以先和这姑娘见面,儿子在下个月兵役满期以后,可以引她到家里来,这样就教大家能够考查她,并且在谈天的时候,能够决定她加入鄱瓦代尔家庭中间是不是颜色太深一点。 于是安端声明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他服役满期的日子,可以带着他的女朋友到都尔忒乡来。 为了这次到她情人的父母家里的旅行,她穿上了最漂亮和最耀眼的衣服,其中的主要颜色是黄的红的和蓝的,使得她像是为了一个国庆佳节所以身上满挂着许多旗子。 由勒阿弗尔起身,车站里的人很注意她;因为自己的胳膊上面挽着一个这样被人留意的人,鄱瓦代尔感到了自负。随后在她和他并排坐着的三等车仓里,她对于同仓的乡下人散布了一种非常教人吃惊的事,使得左右隔壁两车仓里的旅客们为了能够从分仓的隔板顶上来端详她,都站在各人的长凳上了。一个孩子看见她的面貌竟吓得哭起来,另外一个把自己的脸儿藏在他母亲的围裙里。 然而一直走到目的地的车站,一切都是平安的。不过在列车快到伊弗朵而减低速度的时候,安端感到不自在了,正像是遇着官长视察而自己竟不知道他的操典一样。随后,伏在门窗边,他远远地看清楚了他的父亲正握着套在大车辕子里的那匹牲口的缰绳,他母亲站在那道阻挡闲人入站的栅栏子的边儿上。 他自己首先跳下车来,把手伸给了他这个心爱的女朋友,后来,挺直了脊梁,如同护卫一位将军一般向着他的父母走过去。 他母亲看见了那个衣裳五色皮肤乌黑的女宾同着儿子走过来,简直吓得好一会儿不能张嘴,他父亲正费尽气力带住那匹马,不知道究竟是火车头还是黑种女人,使得它不住地掀起两条后腿乱踢。但是安端由于看见两老而陡然发生单纯的快乐,连忙张开了胳膊跑过去,在母亲脸上啄也似的吻了一嘴,又在父亲脸上也啄了一嘴,并没有顾到那匹小马的惊惶;随后转过身来向着他那个女伴,他那个正被好些吃惊的过路者停止脚步来注视的女伴,然后说道: “她来了!从前我对你们说过:初看的时候,她是不大顺眼的,不过一到认识了以后,说句真而又真的话,世上再也没有更教人乐意的了。请你们和她道个早安吧,这样可以教她一点也不心慌哪。” 这一来,他那个慌张得发昏的母亲表示了一个像是打招呼的动作了,同时他父亲脱下了自己的便帽一面喃喃地说:“我恭喜您称心如意。”随后并不耽误时间,大家都攀到了车子上,两个女人坐的都是车尾上的椅子,每逢车子遇着路面上的凸凹,这种椅子就使她们向空中一蹦,两个男人坐的都是车子前段的长凳。 谁也没有说话。安端心里不安了,吹着一首在营房里流行的曲子。他父亲鞭着那匹小马,他母亲不时溜动黄鼠狼式的眼光,从旁瞅着那个黑种女人,发现她的额头和两颊在日光下面亮得像是擦得很好的黑皮鞋一样。 气氛像是冻结了似的,安端想要冲破这种气氛便转过头来了。 “喂,”他说,“大家不说话?” “这是要点时候的。”老妇人回答。 他接着又说: “快点儿,你把你那个母鸡的八个鸡子儿的故事说给小姑娘听吧。” 那是他们家里一个有名的滑稽故事。不过他母亲因为心绪激动弄得知觉麻痹,始终没有开口,于是他本人发言了,在笑哈哈的声音中间叙述那个值得记忆的奇遇了。他父亲本是背得出那个故事的,所以在开头几句话里就展开了自己的眉头;他母亲很快地跟上了他的榜样。后来那个黑种女人听到那段最滑稽的地方,陡然一下发动了一阵狂笑,那是非常喧闹的,旋转不止的,奔放的,以至于受了刺激的小马也飞跑了一小阵。 已经是相识的了,大家就谈起天来。 刚好走到家,在大家全下了车的时候,安端就引了他的好人到卧房里去宽下身上的裙袍,因为她预备照她的做法做一份使得两老称心果腹的好菜,这样就免得等会儿弄脏了衣裳。接着他又引了两老走到门外,在心房跳得厉害的情形之下问道: “喂,你们怎么说?” 父亲没有作声。母亲,比较胆大,高声说: “她太黑了!不成,真的,太黑了。我真因此打了好几次恶心。” “你们将来会惯的。”安端说。 “可能,不过现在还做不到。” 他们都进来了,那个老婆子看见黑种女人正在做菜,感到了过意不去。于是她来帮她了,卷起了裙子,不管自己的年迈也一样活动着。 那顿饭是有滋味的,吃得长久的,吃得快活的。以后到了大家到外面兜一个圈子的时候,安端就牵了他到一旁。 “喂,爸爸,你说她怎样?” 那父亲是从来不上当的。 “我没有一点意见。问你妈吧。” 于是安端赶到他母亲身边了,牵着她落后几步和她说话。 “喂,妈,你说她怎样?” “可怜的孩子,真的,她太黑了。只要稍许淡一点点,我也不会反对,但是太黑了。可以说是个撒旦!” 他知道老婆子素来是执拗的,所以他并不坚持,不过觉得自己的心里窜进了一阵狂风暴雨样的悲伤。他思索自己应当做的事,思索自己可以编造的话,此外,他觉得她从前能够诱惑他而现在却不能同样去诱惑两老倒是令人诧异的。末了他们四个人都提着慢步穿过麦田,渐渐又都变成了不说话的。等到大家沿着一圈做围墙的篱笆外面走着的时候,里面的农人都到了栅栏的门外,顽童们都爬到了土堤上,所有的人都赶到了路上,来看鄱瓦代尔的儿子带过来的黑种女人。他们看见了远处有好些人从田地里跑过来,活像是听见了报告奇闻的鼓声一样。乡村里的这种因为他们走过来而起的好奇心,使得鄱瓦代尔的父母感到了慌张,于是两老连忙提快了脚步,如同替儿子引路似的,彼此并排远远地在头里走,这时候,儿子的伴侣正向他问起两老对她个人的印象。 他迟疑地说是两老还没有决定。 但是在村子里的广场上直形成了一阵从所有受惊的房子里涌出来的人流,鄱瓦代尔两老在那阵增加不已的拥挤情形之下一齐逃回家去了。这时候,怒气冲天的安端正被他的女朋友挽着胳膊,在那些由于惊愕而愣起的眼光底下,带着尊严的姿态向前走。 他明白那是完结了,没有希望了,自己娶不成他的黑种女人了;她呢,也明白了这种结果;后来他俩在快要到家的路上都开始流泪了。一下回到了家里,她又脱下了裙袍帮着老婆子来做日常的事情;她四处跟着她,在牛奶房里,在牛圈里,在鸡埘边,都是她担任着最吃力的部分,不住地说着:“请让我来做,鄱瓦代尔太太。”以至于天要快黑的时候,这个被感动的严气正性的老婆子向她的儿子说: “这究竟是一个正直的女孩子。可惜她竟生得那么黑,到底真的,她太黑了。我将来和她弄不惯,她应当回去,她太黑了!” 后来小鄱瓦代尔向他的女朋友说: “她一点也不愿意,她觉得你太黑了,应当回去。我可以送你到铁路跟前。没有关系,你不用伤心。等你走了以后,我就和他们再谈这事儿。” 他终于送她到了车站,同时还许了她有好希望,后来吻过了她就教她上了车,又用一双饱含着眼泪的眼睛望着车子开走。 他徒然向两老恳求,他俩永远没有对他同意过。 等到述完这件被当地全知道的经过以后,安端?鄱瓦代尔一定又加上这么一段: “从此以后,我对于什么全不在心上了,全不在心上了。没有一件手艺合我的意思了,后来我变成了现在的我,一个阴沟匠。” 有人向他说过: “然而您是成了家的。” “对呀,而且我不能说我的妻子教我不快乐,因为我和她生了十四个孩子,不过并不是从前那一个,简直不是,不是!从前那一个,您看,我从前那个黑种女人,她只需瞧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如同失了主张一样……” 【青崖按】 《鄱瓦代尔》(Boitelle)的原文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巴黎回声日报》(L’?cho de Paris)发表。 推荐: ◎李青崖译文集精选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经典,囊括大仲马、左拉、福楼拜、莫泊桑、法朗士五位作家的八部小说作品。 ◎重温被遗忘的名家译本,译者李青崖当之无愧是我国从法语原文翻译法国小说的第一人,对中国文坛有着深远影响。 ◎中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语文学研究专家郭宏安导读;法语文学翻译家吴岳添、余中先、袁筱一作序。 ◎书内复原早期原版书精美插图。《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的插图取自法文报刊及法文版莫泊桑小说集,插图作者为法国画家福蒂内?梅奥勒(Fortuné Méaulle,1844-1916)、泰奥菲勒?亚历山大?斯坦伦(T. A. Steinlen,1859-1923)、勒内?勒隆(René Lelong,1871-1933)等。 ◎附赠作家画像藏书票一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