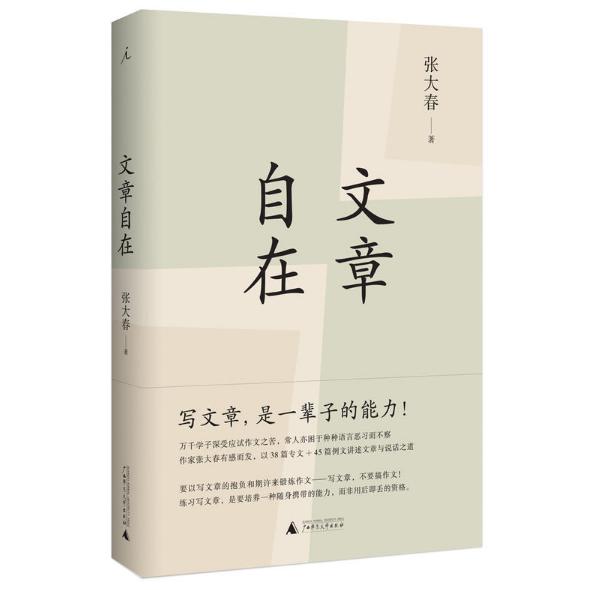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7.24
折扣购买: 文章自在
ISBN: 9787549587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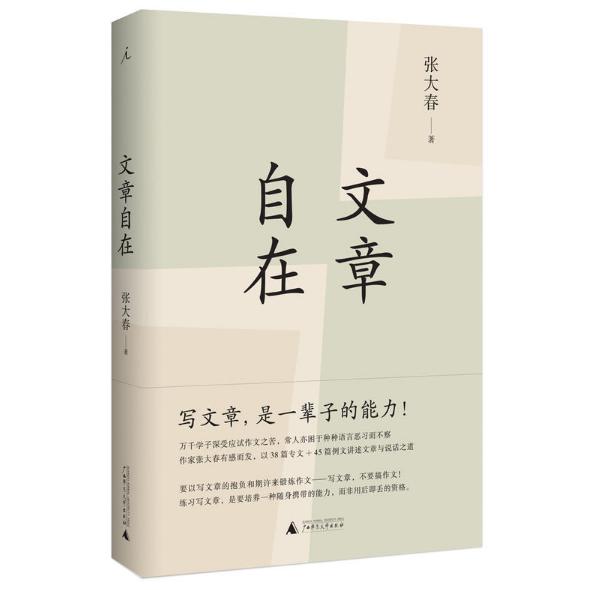
张大春 **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济南。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著作等身,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 张大春的作品着力跳脱*常语言的陷阱,小说充斥着虚构与现实交织的流动变化,具有魔幻写实主义的光泽。八零年代以来,评家、读者跟着张大春走过早期惊艳、融入时事、以文字颠覆政治的新闻写作时期,经历过风靡一时的“大头春生活周记”畅销现象,一路来到张大春为现代武侠小说开创新局的长篇代表作《城邦暴力团》,以及开拓历史小说写法的《大唐李白》系列,张大春坚持为自己写作、独树风骨的创作姿态,对**文坛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2008年、2009年,作品《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曾连续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手边不留底稿,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价值。二〇〇三年之后开始用电脑写作,一键轻敲,百篇庋藏, 都在硬碟文档之中,偶尔对屏卷看。不读则已,一读就想改;一改辄不能罢休,几乎除旧布新。也因之暗自庆幸:好在当时没有出书!在我的电脑里,*大部分的散文稿都集中在一个档名之下:“藏天下录”。 这就让我想起一则九百年前改文章的老故事。南宋宰辅晏敦复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晏几道的侄孙,可见传家文气,累世**。有一次晏敦复为某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作完了拿给另一位词家朱敦儒过目,朱敦儒阅后道:“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敦复苦苦相求,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有文集十卷”说:“此处欠。”晏敦复又问:“欠什么呢?”朱敦儒道:“欠‘不行于世’四字。”晏敦复明白了,他没有**依照老朋友的指示修改,仍遵其意,添了“藏于家”三个字。 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是“修辞立其诚”的用意。即使死者为大,也不应当予以过当的称许。文集十卷固然堪说是“立言”了,然而既未获刊行,便不可藉模糊之语谬赞。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遂宛转以“藏于家”来取代“不行于世”;既不失实,也保全了亡者颜面,如此修改,是小文章里的大判断。 然而,我毕竟还是把应该“藏于家”的一部分文字翻检出来,例以示法,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命题考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 由考试领导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的教学现场,老师们都有不得不逐潮而去、恐后争先、而徒呼负负的感慨。作文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说:本来文章无法,可是一考就考出了拘絷文词之法。你也可以说:本来文章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 于是学子所能悟者,反而是*恶劣的一种心思,以为写文章就是藉巧言、说假话, “修辞败其诚”。其上焉者多背诵一些能够广泛发挥的铭言事典,临考时兵来将挡,水来将也挡;中焉者多援引几句烂熟于胸的俗谚成语,临考时张冠李戴,李冠张也戴。下焉者只好闲话两句,“匆匆不及*书”,顺便问候批改老师:“您实 语言美好 我在小学五年级遇到了俞敏之老师。俞老师教国 文,也是班导,办公桌就在课室后面,她偶尔会坐在 那儿抽没有滤嘴的香烟,夹烟的手指黄黄的。坐在俞 老师对面的,是另一位教数学的班导刘美蓉。刘老师 在那一年还怀着孕——我对她的记忆不多,似乎总是 在俞老师的烟雾中改考卷,以及拿大板子抽打我们的 手掌心。 俞老师也打人,不过不用大板子,她的**是一 根较细的藤条;有的时候抽抽屁股,有的时候抽抽小 腿,点到为止。那一年“九年国教”的政策定案,初 中联考废止,对我们而言,风中传来的消息就是一句 话:比我们高一班的学长们都毋须联考就可以进入“ 国民中学”了。而俞老师却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们:“ 你们如果掉以轻心,就‘下去’了!” 五年级正式开课之前的暑假里,学校还是依往例 举办暑修,教习珠算、作文,还有大段时间的体育课 。俞老师使用的课本很特别,是一本有如小说的儿童 读物,国语*报出版,童书作家苏尚耀写的《好孩子 生活周记》。两年以后我考进另一所私立初中,才发 现苏尚耀也是一位老师,教的也是国文,长年穿着或 深蓝、或土绿的中山装,他也在办公室里抽没有滤嘴 的香烟,手指也是黄黄的。 我初见苏老师,是在中学的校长室里。那是我和 另一位女同学沈冬获派参加台北市初中生作文比赛。 行前,校长**高年级的国文老师来为我们“指导一 下”。苏老师点了一支烟,摘下老花眼镜端端正正插 在胸前的口袋里,问了两句话,也一口浙江腔:“你 们除了读课本,还读些什么书啊?除了写作文,还写 过什么东西啊?” 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师,想起了《好孩子生活 周记》,想起了小学课堂上烟雾缭绕的*子,但是我 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回答——苏老师没让我们说话— —他自己回答了:“我想是没有的!” 在校长室里,苏老师并没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 修辞秘笈,只是不断地提醒:要多多替校刊写稿子, “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至于我们所关 心的比赛,他也只是强调:“参加了就是参加了,得 名不得名只是运气,不必在意。” 我和沈冬运气不错,拿了个全市**。至于为什 么说“我和沈冬”呢?得名的虽然是我,可是我一直 认为,临场慌急匆忙,忘了检查座位,很可能我们调 换了号次,错坐彼此的位子。因为我深深相信:自己 写的那篇文章实在是烂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然而 市府和学校毕竟都颁发了奖励,我只能把奖品推让给 沈冬,至于注记了我的姓名的奖状,则收了压抽屉。 从此我对苏老师那运气之说深信不疑,若非如此,我 还实在无法面对窃取他人名誉这件事。 苏老师却从此成为我私心倾慕的偶像。每当我在 校园里、走廊上看他抱着课本踽踽独行,就会想起他 在辛苦了!”无论何者,面对考题,只能顺藤摸瓜,捕捉出题人的用意,趋赴而争鸣。国人多以中文系所、复献身教育的先生们会写文章,自然也知道如何教文章。事实却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但是所有的国文科教师都必须随时教作文、考作文、改作文。我们的教育主管当局只好辩称:作文是训练基本表达能力,不是培养专业作家。而我却要说: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八股”二字以讽作文考试。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的考八股——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还能引发、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纵文气,离合章句;条陈缕析,辨事知理。而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却由于不只一代的大人普遍不会写文章、教文章,而任令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运用文法学、修辞学上极其有限的概念,设局命题,制订评分标准,刻舟求剑,胶柱鼓瑟,*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抹煞。达官显贵一至于贩夫走卒,在这一点上倒是齐头立足皆平等:不会作文章而乃不知如何表达,遂成举国累世之共业。 有文藏于家,时或欠公德。毕竟我眼里还看着:年复一年、有如必要之恶、不得不为之的各种作文考试依旧行之如仪;而举目多有、也只能听任其各申己说,致使作文不断公式化、教条化的补习教育也依旧大兴其道。实难想象: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大概除了等待天才如果陀、却永无可期之外,安能启迪造就愿意独立思辨且乐于真诚书写的人们?就一个写了四十多年、自负各体文章无不能应心试手的我来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即使自私地从一职业作家的角度来说: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的人愈来愈多,能够体会我意的人愈来愈少,也着实大不利己。 于是搜筩发箧,检点篇什,编而辑之。在这本书里,除了序文之外,还包括概论三篇,引文三十四篇、例文四十篇,兼收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林今开、毛尖等古今诸家文各一篇,以及跋文、附录各一。 小子何莫学夫散文?即使一生尽写一部书,而不行于世,但能博得三数学子青眼, 以为比课本讲义教材评量等物有趣,便值得了。是为序。 的话:“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话里好 像有一种很宏大的鼓励。我的确开始给每月发行的报 纸型校刊投稿,每月一篇,一篇稿费十五块钱;有的 时候,一个月甚至可以领到三十块。每个月都和我一 起领稿费的,是另一位女同学,叫黄庆绮。后来她有 了很多笔名,有时候叫童大龙、有时候叫李格弟、有 时候叫夏宇——是的,就是那位风格**而广*各方 读者敬重的诗人。据我所知,她也没有代表过任何学 校参加作文比赛。 非但写稿写得勤,我还央求父亲多买些东方出版 社少年文库的书回来,父亲起初不同意,他认为那都 是小学生的读物,字边都还带着注音符号的。我都上 中学了,怎么回头看“小人儿书”呢?我说:我要看 的那些,都是我的老师写的。 其实不是。他大部分的出版品都是改写故纸之作 。从《孔子》到《诸葛亮》,从《班超》到《郑和》 ,以中国历史名人的传记为主,也有像《东周列国志 》、《聊斋志异》或《大明英烈传》之类的古典小说 。我曾经**熟悉的《好孩子生活周记》里那个充满 现实小康家庭生活细节与伦理教训的世界不见了,仿 佛他从来没有塑造过那样的一家人、那样的一个小学 时代。苏老师后来*多的作品,是把无论多长多短的 古典材料修剪或补充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中篇故事,总 是以主人翁人格上的特色为核心,洋溢着激励人情志 风骨的趣味。P7-9
接续《认得几个字》,作家张大春再谈文章妙趣!通过《认得几个字》一书,作家张大春曾带领我们领略“识字”的乐趣,以及文字背后深广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内涵。新作《文章自在》以七十余篇文章阐述文章之道和语言之美,示范各种写作技巧,矛头直指当前的语文教育和应试作文。作文本是练习写文章,但应试教育下的命题作文却与文章割裂开来:写文章,是我手写我口,是自主思想的训练;写作文,却要揣摩出题人之意、应和题旨,学生往往编织语言疲于应付,“修辞败其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