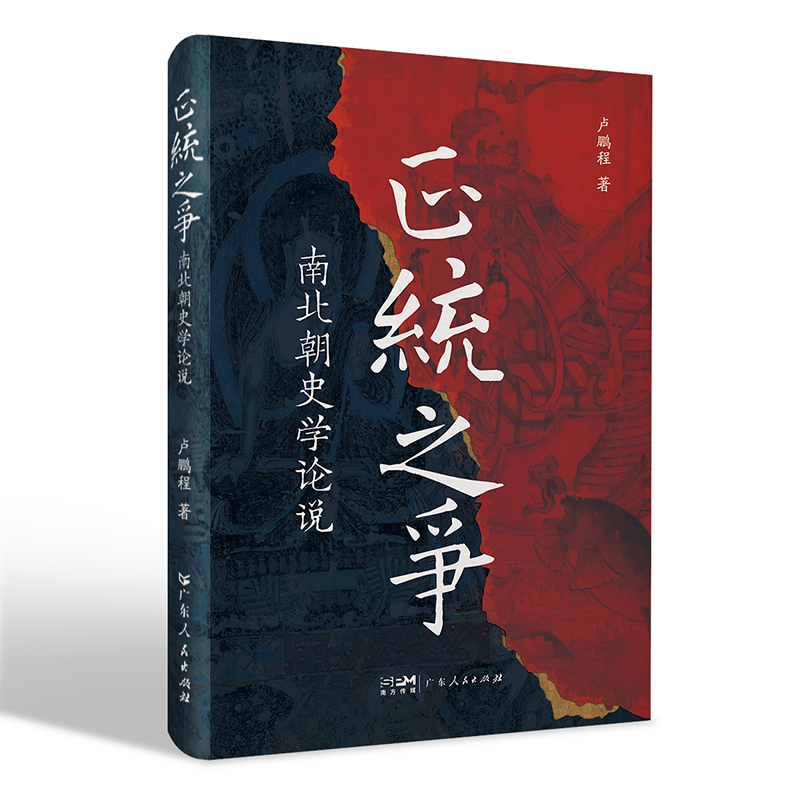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0.20
折扣购买: 正统之争
ISBN: 9787218173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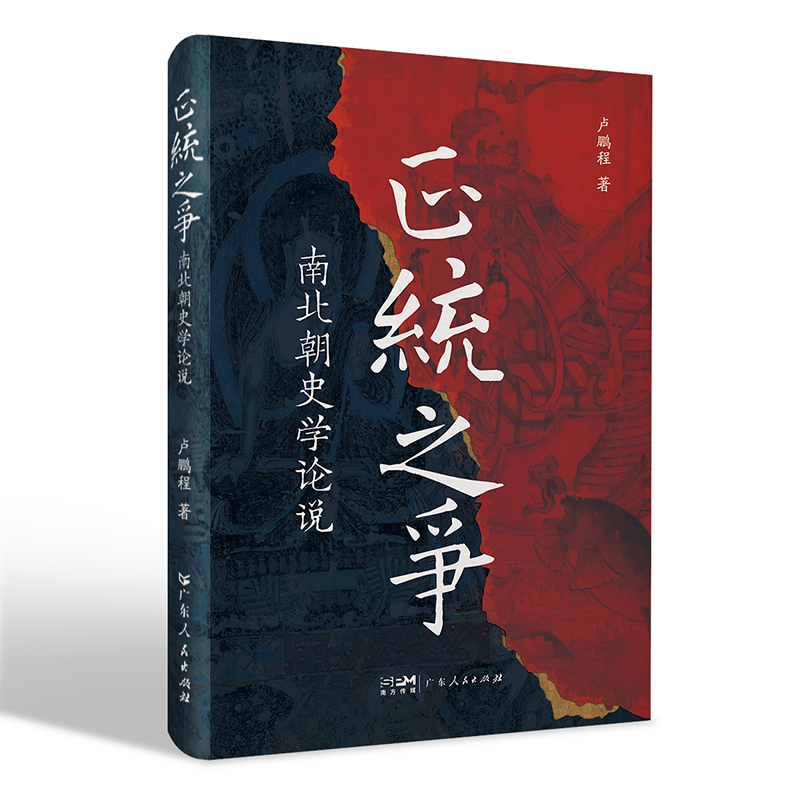
卢鹏程 著 卢鹏程,男,山东日照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基层治理等教学与研究工作。
绪 论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一般认为自420年刘裕篡晋建宋始,至589年杨坚灭陈止。这一时期南北政权虽各有更迭,北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有宋、齐、梁、陈,但主要以南北对峙为主。 南北分立,起源于北方游牧部族的内迁与反抗。游牧民族内迁自汉至魏晋时期,居于中原地区的少数部族民众人数逐渐增多,西晋江统《徙戎论》中所称“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的态势,在王朝内部爆发八王之乱时彻底无法阻挡。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政权纷纷自立,表面上看是一场场反抗压迫、追求独立的正义之战,又多少带有胡族在胡汉共存地区寻求自己部族权势地位的进取心态,这也成为北方混战不断的冲突点。或者说,最初南匈奴首领刘渊抗晋自立,主要是胡汉对立,内迁胡族在中原地区遭受歧视对待,自然追求属于本部族的自由独立。而当这种类似的反抗被不同部族效仿延续的时候,北方地区兴起的胡族政权已逐渐走向了诠释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道路,部族、民族冲突让位于统治权力的政治争斗。十六国政权大多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但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本质上并不会区分胡汉,胡族内部的阴谋血腥与权势谋夺可能与中原王朝的宗室内斗、异姓权力谋取并无本质区别。而以少数部族内更少数的贵族成员去统治居于多数的北方地区汉族民众,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自然为胡族统治者需要并逐渐重视,统治区域决定了作为后来者的胡族高层必须不断采取适应这一地区的统治政策,进而出现的只会是哪种因素更居主导地位,混入或融入的华夏传统文化的成分已无法驱除。当然,这种思想与文化转变更多是处于上层的胡族首领及其胡汉谋士所属的统治高层所呈现的,对普通下层民众而言,军事扩张与割据混战才是常态。 就南方政权而言,东晋皇室及南迁世家大族最初是主张北伐统一的,然而到南朝时,随着南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北方军事实力的强大,南方政权的统一之心渐消。或者说,迫于现实的军事压力与政治妥协,南方政权已经默认了北魏与南方并存的事实。南人北伐,虽有收复中原雄心壮志,但多数落脚于凭借军事胜利赚取个人威望,进而谋夺政治权力,成功者、效仿者众,后来统治者自然有所防范而压制下属北伐之心。而由帝王亲自主导的北伐往往用功大成效小,世家大族已然习惯安逸,自然尽力避免既有利益受损。南朝内耗不断,攻少守多,虽有鱼米之利,也仅限于自足自保。衣冠南渡,与其说是一场文化的散播与扩张,不如说是文化的转移与修复,并未在南方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迁移的历史力量是巨大的,“所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托耳。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农本思想下的安土重迁意识,在数代人的累积记忆中逐渐凝固,北土乃敌国,侨州是新乡,南人对北方的记忆已化为文学想象的符号。从军事到经济,乃至文化方面,南朝政权在南北一线上逐渐收缩保守。 甚至对生活在南北交界地带的民众而言,北方政权的统治者的少数部族属性与南方偏据政权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随着不同姓氏的王朝兴替、以司马氏代表的皇室南迁以及北方各部族自立称帝的历次变动,皇室的家国权威逐渐黯淡,而世家大族与地方豪族的宗族血缘乃至地缘的家族集团势力得以发展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体制中从上到下的权力通道实际上是断层的。这种集团势力甚至可视为南北朝时期政治变动的主要诱导群体,比如南朝政权的禅代,比如北魏末年的东西分离。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相较三国时期的特殊性在于,在中华大地角逐权力制高点的群体中,多了许多非汉族面孔,华夷之辨似乎成为这一时期复杂局面的关键要素。然而随着南北地区各自统治政权的相对稳定,华夷的区分并不再是理解南北对峙的切入点。刘宋何承天在《安边论》中称,“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当然,这主要是从中间地带民众的角度立论,夹缝中生存才是第一位的需求,并非抹杀北魏政权为拓跋鲜卑统治的事实。 脱胎于十六国政权的拓跋北魏,本质上与其他胡族政权并无不同。如果非要强调北魏鲜卑政权的特殊性,那么只能说是因为拓跋鲜卑进入中原最晚,而其变革又最彻底,故最终呈现为首个被纳入华夏正统王朝序列的胡族政权。拓跋鲜卑兴起于代北,覆灭于前秦,又因前秦灭亡得以复兴,北魏接收继承后燕等诸多势力入主中原,而这些之前的胡族政权已经部分地接纳融合了中原大地的华夏传统文化,因此北魏统治区域的扩大,伴随着将华夏传统文化逐渐内化的过程。前秦内部不稳、急于求成而败亡的教训仍历历在目,北魏在内部权力统一尤其是胡汉融合的道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但这种曲折前进是拓跋鲜卑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北魏也逐渐显示出迈向统一国家的意志。北魏中期的崛起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南方刘宋末年政治变动频繁,北魏乘机向山东、淮北方向扩展,也因此埋下了进一步向中原华夏文化靠拢的伏笔。作为胡族政权统治北方地区,拓跋鲜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居于少数的鲜卑部族统治广袤的汉地民众,延续十六国政权的做法,北方望族进入北魏统治阶层视野,北方望族与拓跋统治者在北魏发展道路上虽有曲折反复,但又相辅相成向前推进。最终在孝文帝时期,北魏的汉化改革走向顶峰。抛开这种激烈变革加速引发的边地与中央矛盾,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确实在客观上确定了北魏政权接续华夏文明的属性,哪怕只是短暂的,但却是早有端倪且影响深远。孝文、宣武二帝实行向南扩张的积极政策,已对南朝构成威胁,在南北对峙的竞争舞台上,主动权已逐渐归属北朝一方。 南北朝时期诸多政权前后相继,但除北魏外统治时间均较为短暂,维系王朝稳定主要依赖个别雄主,一旦雄主亡故,整个政权因缺乏强有力的中心而迅速分崩离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南朝梁武帝萧衍。从萧齐旧臣到开国之主,萧衍的政治智慧使其尽量避免刘宋、萧齐政局不稳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处理前朝宗室的问题上,他表现出相当的自信与宽容。这种自信当来源于他称帝时正值壮年,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亲自施展抱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霸府类似,萧梁立国之后可用的文武官员亦是其旧属班底,萧梁的稳定在于萧衍能继续掌握这些力量,而刘宋、萧齐等开国君主在位时间不长即亡,继位新君忌惮前朝佐命功臣,自然有上下猜疑导致大肆清洗的内部冲突。可以说,萧衍立身于南齐与北魏对峙之际,南朝内部的历史问题与北方鲜卑政权的强大共同促成了新王朝的新气象,但这种因个人能力形成的繁荣缺乏保障,浮华背后仍然存在着矛盾冲突。南北局势的奇特之处在于内忧外患往往相伴相生,稳定的内部与孱弱的对手同样重要,北魏有趁南方改朝换代之际兼并大片土地的兴盛,也有因内部动乱导致东西分裂的败亡,东西魏分别为高氏和宇文氏取代。梁武帝曾于北魏衰落时借元颢之名令陈庆之北伐,虽势如破竹但后续无为,近二百年的偏居一隅,南方政权早已失去北方地区的民心,尚须借助元魏宗室傀儡之举终难有所成就。直到侯景叛北齐入北周,入萧梁又反于萧梁,引发南北局势再次变动,南北对峙已变为后三国鼎立之局,又是另一番天地。 本书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第十二届(2023年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南北对峙的一百多年间,南北方政权各以正统自居,自称“中国”,指斥对方为“索虏”“岛夷”,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本书旨在分析中国古代的正统观,论述官修史书对这一观念的体现,试图解答中国历史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动力如何理解,为何中国古代分裂时期正统观念最为显著,处于分裂局面下的政权如何消除认同危机,以正统为核心的政权合法性与政治认同诉求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