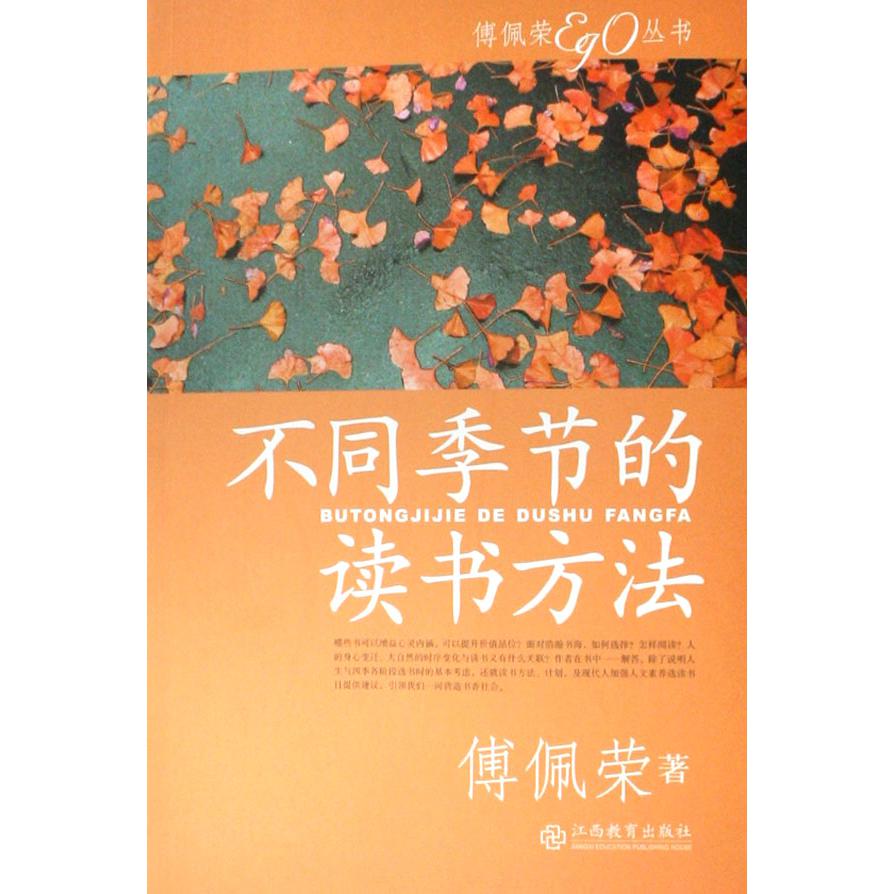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西教育
原售价: 20.00
折扣价: 14.00
折扣购买: 不同季节的读书方法
ISBN: 9787539247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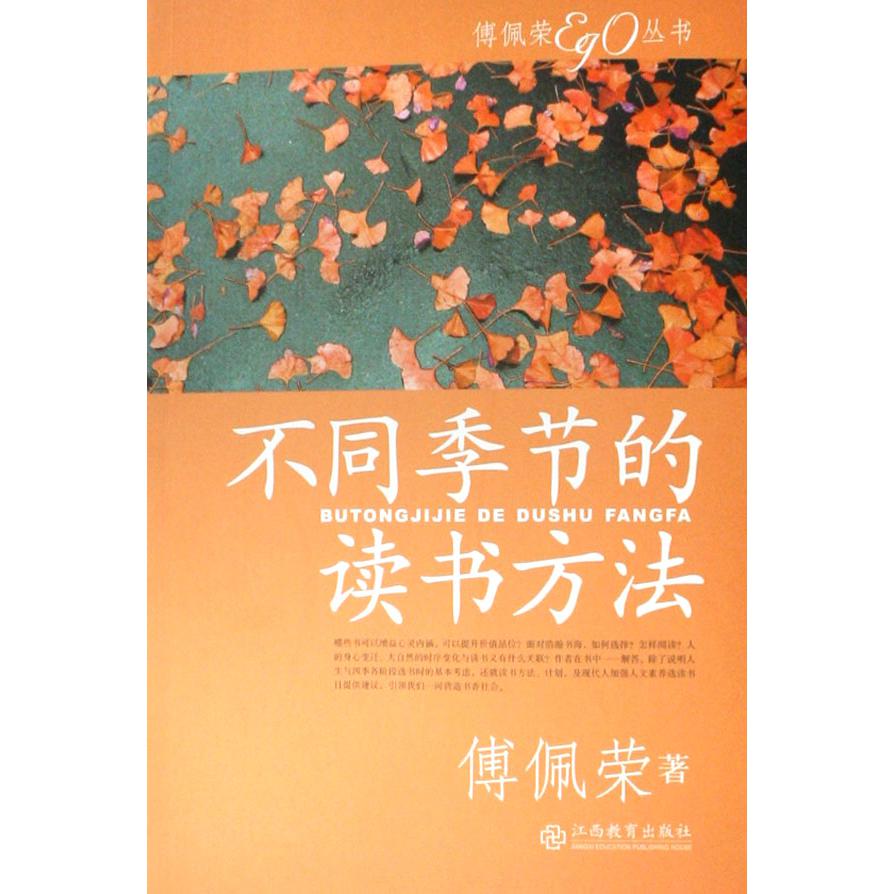
傅佩荣,祖籍上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范围涵盖哲学、宗教、神话、教育、文化、心理、励志等,著作达九十余部。于深化推广哲学研究、探讨当代重大议题、促进两岸思想交流,贡献甚多。近年来专心注解传统经典,已出版《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解读著作多种,对于经典的当代诠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读书的方法 我念的是哲学,哲学属于人文学科;凡是人文学科,都会互相呼应,犹 如大家常说的“文史哲不分家”。于是,在买书时,参考的领域就很广了。 任何一本人文方面的著作,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可以与我的兴趣拉上关 系。久而久之,书架上堆满了一些不知何年何月才会伸手取阅的书。 即使有些书曾经翻过,并且画下重点,写上眉批,但是隔几年之后再看 时,却觉得毫无印象,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翻过此书。原来人的记忆容量 十分有限,稍不注意,它就汰旧换新,以致忘记的总比记得的要多得多。根 据一项研究,我们背英文单字时,必须忘记六次之后,才能真正记下这个字 。因此,念外文不可气馁,如果让外国人来念中文,情况绝对更糟。 既然如此,念书必须讲求方法,否则无济于事。以较为机械的学习外文 为例。我念英文,原来也像一般中学生,背了所有的文法与片语,遇到句子 照样弄不清楚作者的意思。一直到大三暑假,我有机会翻译一本宗教哲学的 书,这才彻底提升了英文程度。当时我每日工作八小时,只能进行二千字左 右,辛苦之至。原来以为自己看懂的意思,改写为中文之后,就是念不通顺 ,其中道理更是模糊难辨。怎么办?我取出一大张白纸,把完整的句子抄在 上面,详细分析文法结构、主从子句、语气转折、基本观点,非到完全明白 不可。如此奋斗了两个月,译成了十万字,收获极大,从此不再惧怕英文, 甚至感受到由英文学习知识的乐趣。 如果翻译也能算是一种读书方法,那么它所代表的自然是“精读”了。 的确,泛泛地念一本书,不如不念,因为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养成坏习惯, 就是做事不够认真。我念外文书时,向来是采精读的方法,因此选书就十分 重要了。在这方面,其实问题不大,因为西方哲学不但经典之作早有定论, 连哲学史也都有标准范本。既然我们学西方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正确的理 解,那么选择标准材料去念,自然就事半功倍了。 但是,焦点转向中国哲学时,光靠精读几本代表作是不够的。这时需要 像胡适先生所说的:“为学应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所谓广大,其 实是指国学基本知识,包括历史、文学、思想等方面的材料;至于高,则是 专就个人的见解来说了。如何才算高?首先要融会贯通,就是把自己的思想 透过书本,整合起一切经验,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即所谓“六经皆我注脚” 。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只能像是两脚书橱,搬弄一些古典资料,炫耀一下 自己的博学而已。 其次还须推陈出新。孔子曾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从念古 书,明白日新又新的道理,其中需要个人的体会以及创见,能够即事说理, 为平凡的人生指出深刻的意义。一旦确定个人立场,接着就须参与讨论,切 磋琢磨,精益求精。不过,真正的见解未必都能找到合宜的批评者。 辛弃疾有词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 子!”他居然认为:古人看不到他的“狂”,反而是一大遗憾。人有学问及 心得,必然珍惜之至,然而知音难寻,徒呼负负。辛氏的狂,如果只是意气 嚣傲,目无古人,则后代不妨有人更狂过于他。他的狂,如果是由读书而彻 悟某项千古不易之理,然后相信“圣人复起,必从吾言”,那就值得注意了 。 谈读书方法,还须考虑:读什么书?目的何在?一般而言,技术性及工具 性的书,本身只是手段,学了可以应用。人文方面的书则需要主体“入乎其 内、出乎其外”,念完之后,起一种作用,像“变化气质”,在不知不觉中 ,提高了自己对生命的品味与期许。 四种读书的方法 有关读书方法,只要是念书人大都各有一套。最简易的是教小孩子念书 ,如“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久之就有心得。为了应付考试,方法依 学科而定,数学与英文,语文与地理,不能都靠死背硬记,不过在现行联考 的模式下,学生的选择机会不大。 如果摆脱学生的身份,想由一本书获益,那么方法不外乎以下四种:精 读、略读、重读、默读。精读是为了专业知识或个人兴趣,好像寻找涉水过 河时的立足点或垫脚石。若想站得稳、走得快,自然非有精读的细密工夫不 可。我研究哲学的初期,就以翻译《西洋哲学史》(柯普斯登著,黎明版)的 第一卷作为精读的人手,效果很好,以致后来在耶鲁攻读学位时,可以顺利 通过学科测验。翻译是学习外文的良方,看似笨拙其实却是捷径。至于中文 书籍的精读,主要是为了记住关键人物与术语,须到顺手拈来、出口成章的 地步。像《论语》、《孟子》,我是逐字逐句认真念了不知多少遍,才敢上 台讲课。 略读是为了增广见闻,并且许多书原本就是为了提供讯息的。讯息随时 代而改变,我们只需保持大概的认识即可。对于非本行的书,如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著作,我采用略读法,专挑几个章节,甚至几个观念就够了。幼 时念小说,只想知道故事情节,以便与人聊天,谈不上欣赏佳作。 重读是比较特别的。我在美国念书时,每周必读《纽约时报》星期专刊 里的“书评附册”。有一次年关将届,看到一辑专号,题目是“重读的书” ,内容则是访问十一位知名作家的谈话。从此我才明白:重读(就是重复去 读同一本书)的重要性。真正的念书是重读,如此才可配合自己的人生体验 ,起一种共鸣作用。初次阅读一本书,有如初识一位朋友,只是交换名片、 记得相貌而已;重读则像老友重逢,有渐成知己的可能。如果每隔一段时间 ,就重读几本书,其效果十分微妙,可以测知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成长历程 。譬如,我定期重读的书里面,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在每一次受感动的 地方作下记号,重读时会发现自己的现况是趋向“保持良知”、“丧失斗志 ”、“随俗浮沉”、“面目可憎”之中的哪一种?书本成为良友,其意亦近 于此。 至于默读,是就且读且思而言,并非只是安静念书。外表安静,内心却 不妨澎湃奔腾、起伏周旋,跟随作者走一趟心路历程。一句平凡的话,可以 想得精深,“思人风云变幻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起源于《圣经》上 的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念到“我信罪之赦”一语,忽然顿悟神爱世人之 真意。只要信,即可得救。我们读诗时,有时简单的一句“万物静观皆自得 ”,就能使人心平气和。我想,宗教圣典、诗词小品、哲理格言,皆以默读 为宜。 不论如何读法,念书的过程都是要靠我们的三力:理解力、想象力、创 造力。文字需要理解,字面的意义与“言外”之意,全文的用心与苦衷,作 者的洞识与定见等,都需要“再生”到某种程度。然后,想象力发挥作用, 由作者的眼去观看世界与人生,与作者亲切交谈,学习他的思考架构与线索 。我念《论语》时,经常想象一位活生生的孔子立在眼前,他对子路这么说 ,对子贡那么说,他会对我说什么呢?创造力则是配合读者个人体验,取其 合乎时空的新意。否则,书是书,我是我,再念又有何用?“学贵心悟,守 旧无功”、“温故而知新”,这些话都是真正念书人的体认。 总之,人生不可不读书,否则无以开拓心灵潜力,坐困狭隘的个人世界 。读书不可不讲求方法,否则徒然变成两脚书橱,人云亦云,何乐之有? P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