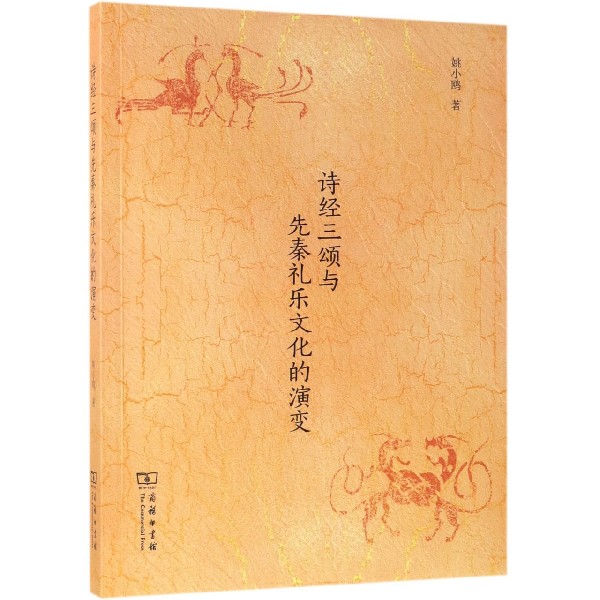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80.00
折扣价: 56.00
折扣购买: 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
ISBN: 9787100171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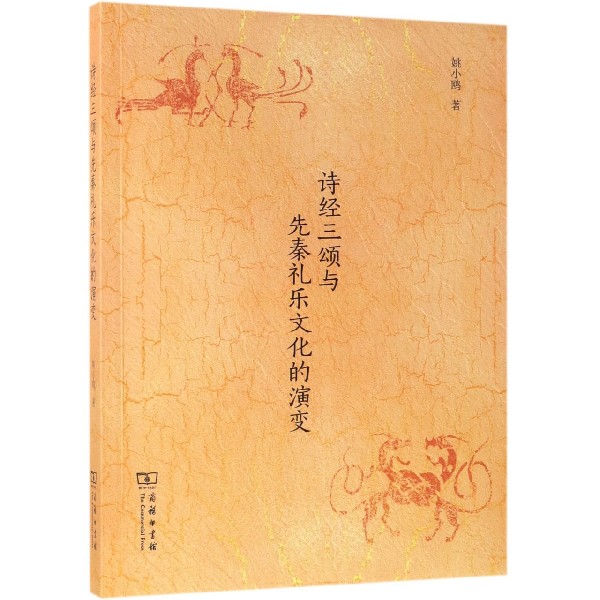
姚小鸥,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乐府学学会副会长。历年来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献》《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等重要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主要涉及《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与中国早期戏剧等领域。《诗经》是第一研究方向。出版《诗经译注》,论文自选集巜吹埙奏雅录》。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
导 论 《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崇高地位,就其对一民族文化的意义而言,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部诗歌总集。我们所进行的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在于具体阐明此种意义,并试图通过这一课题的讨论,说明中华民族基本文化特征形成过程的某些问题。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在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形成该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独特民族文化。这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根本标志。一个成熟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但具有鲜明的外部特征,而且具有强烈的内聚力,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都能在保持其基本特色的同时不断更新自身,从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由于其民族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任何断代史式的论述均不足以全面阐述其特征,但无疑却有可能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奠定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其基本形成时期的研究,更是必不可少和富有意义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其“原史时期”(protohistory)的历史,由于文献不足征,不便详述。较为简单的办法是,追溯到中华民族的直接前身—华夏族的形成。所谓华夏族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春秋时期,见于《左传》《国语》的记载。华夏亦称“华”“夏”“诸夏”等,是中原地区接受周礼的具有较高文化的诸族的总称。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其他诸族则被称为“蛮夷戎狄”。可见周礼在文化上对华夏民族的维系作用及象征意义。当然,“华夏”与“夷狄”又是相对而言的,二者通过不断地交流而走向融合,因为周礼本身就是先秦诸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下面我们稍稍追溯一下到春秋中期为止的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及周礼的历史渊源。 从传说时代,我们在历史学中称为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就活动着许多部族、部落,他们是华夏族的先民。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帝和炎帝两族。传说中的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先祖,据说都出自黄帝一族。同时,炎帝族也不断地通过婚姻、结盟和战争等方式,与黄帝族进行交往和融合。文献与考古发现都证实了三代文化是叠相承继的。孔子所说的殷周对于前代文化的继承绝非揣度之词。 武王克商,周人取代商的天下共主地位而成为政治上的正统,并以克商前后全面吸收、承继商文化而成为文化上的正统。关于殷周文化的异同,前人作过不少研究。现在看来,更应注目于周人对前代文化成果的集成与改造加工。由于这种集成带有瓜熟蒂落的性质,所以周文化的发展从程度上来说十分惊人。古代文献和考古研究告诉我们,周人在青铜礼器制造、建筑艺术、文字等各个重要的文化领域都得益于商人的文化积累并充分发展之。周人与前代相比最明显的文化成就是周礼的制定与实施。 按照孔子的说法,周礼是周人鉴于二代而有所损益的结果。即我们前述包括加工、改造与完善的文化之集成,这完全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证明。 礼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萌芽随着原始人群的出现而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礼也逐渐完备。直到成文法出现前(中国成文法的形成以春秋中叶刑书、刑鼎的出现为标志),它一直是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古代社会中,礼不但调整着人们直接的现实关系(法的关系、道德的关系),而且规范着人们非直接的现实关系(人神之间的关系等),并涉及除此之外的其他精神生产领域(如艺术、哲学等)、物质生产领域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由于古代社会中人们的活动无不与礼相关联,使得礼在当时的文化诸因素中处于核心地位。礼的代代相袭,使其基本精神逐渐积淀于本民族的心灵深处,从而成为民族基本特征的文化心理基础。《礼记?乐记》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这是说在中国古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往往与王朝的更迭相关联),礼都有其不同于前代的具体形态。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制典型的周礼,据说是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制定的,周公由是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圣人”之一。有关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对鲁文公问: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礼记?明堂位》在叙述周公制礼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时,又提到周公作乐: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上述记载虽系后儒根据传闻所作的追记,一些细节的真实性受到现代学者的怀疑,然而,考察礼、乐之间的关系,这一传说却完全符合历史的逻辑。 我们知道,礼是指包括具体的礼节仪式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周礼的主要内容,可以用“礼乐征伐”四字来概括。然而,人们一般称它为“礼乐制度”。礼乐联言,是由于二者之间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在狭义的礼,即祭祀、朝飨的顶礼膜拜和揖让周旋之间必有乐的规定;另一方面,乐在礼的实践中又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乐的自然属性和功能(节律、音响,发乎人性、感于人心)使其不仅能满足礼仪程序结构化的需要,而且能通过接受者个体的情感官能感受,使礼的精神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礼记?乐记》所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正是指出二者这种浑言则同,析言则异,互有区别,又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 作为礼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乐,包括器乐、舞蹈(广义的舞蹈)和声乐。而后者自然包括“诗”在内。所以,文献中又有“歌诗”的说法。 诗与乐的密切关系首先在于其自然属性与历史渊源。《毛诗序》对此曾有论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就其萌芽与最初的发展而言,《毛诗序》关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论述是正确的。所以古代的乐官,同时也是诗的记录者与保管者。《礼记?乐记》说:“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诗歌与音乐的各自发展,使两者在发达的形态上各有其独立性。所以诗与乐(狭义的乐)虽然具有共同的自然基础(感情、节律等),但诗的物质载体—语言与思维的一致性,使其在礼的构成与施行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根据现存文献及其他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礼作为华夏民族共同文化规范的过程中,诗的作用非常巨大。由于其本身的结构特点,其作用绝非狭义的周礼 所能概括,其影响也渐随时间的流逝而浸润于其他文化领域。 正如礼与乐的关系一样,诗与乐的关系也是浑言则同、析言则异的特殊关系。所以我们从诗与乐、诗与礼的关系史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诗经》的自然史(“诗”的结集)与周礼相始终。诗的创作和规范应用与周礼的关系如下:一部分诗是应礼的需要而制作,成为礼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也是在礼的规范下创作,在礼的规范下应用的,换言之,乃是礼的具体实践。可以说,《诗》的形成即礼的成熟。所以随着周礼由成熟而走向崩溃,《诗》的发展也就停止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这一理论可以用 来解释为什么《诗经》成书在春秋时期的礼乐崩坏之际。 《诗》与礼的特殊关系,使我们拥有了这种用来研究西周礼乐制度的可靠材料。具体的研究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诗经》的自然史—创作与成书过程来探讨周礼的渊源与历史。二是通过对《诗经》文本的阐释来解释周礼的性质、内容与演变。由于本书的体例及时间的促迫,许多问题, 如《诗经》成书过程具体细节的探讨,《诗经》所体现的华夏文化统一性的进一步阐述,周代礼乐制度及其精神向后世传递的具体途径,诗与乐(狭义的乐)在华夏民族融合过程中各自的具体表现与作用等,或未能涉及,或语焉未详。如果条件许可的 话,当在异日深入探讨之。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本书在引用出土文献时,尽量采用通行字体,特一并说明。 第一章 《 商颂》与殷周两代礼乐文化的传承与嬗变 第一节 关于《商颂》作年的论争及初步结论 研究华夏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全貌,《商颂》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内容。从宏观上来说,殷商文化研究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承担者。夏人的统治被殷人所取代,殷人的统治被周人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夏商文化也被后 代所叠相继承与吸收,最后演化为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 周人对夏商两代的文化继承是有区别的。首先,夏代的文化发展程度不及商代,能够提供给其继承者的遗产自然较殷代有所不及。其次,殷商时代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书面文献系统,它在商周两代的文化传递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尚书?多士》记载周公旦对“商王士”的训词中曾说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人的文献记载了夏商之际的历史变革,同时也记载了其他文化内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春秋末年的孔子,已经在言殷礼时慨叹文献不足征了。作为最可靠的先秦文献,《诗经》的文献价值为古今学者所共推服。收入周人所编辑的历史文献《诗经》中的《商颂》五篇,对于殷周文化研究的意义自可想见。就我们的研究论题而言,《商颂》还另有其特别的意义。从文化史的纵向来考查,在当时华夏文化集团内容的结构调整,即文化核心的更替过程中,《商颂》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对新的华夏文化模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商周时期华夏文化的区域构成这一角度来看,《商颂》所代表的商—宋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直到春秋时期,其影响还远及邻邦,尤其对鲁国的影响,又通过儒家学派的传承序列,影响到先秦以后的整个中国文化史。《商颂》所代表的商—宋文化使得华夏文明在统一的基本色调之下呈现出来的多彩画面具有更高品位的文化资质,从而使我们所叙述的华夏文 化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具有的历史深度得到一个明确的个案支持。 然而,对于《商颂》的上述意义,学术界却长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究其根源,在于对《商颂》文化性质的误解,而这一问题又首先归结于对《商颂》制作年代的疑问。 在先秦时期,没有人对《商颂》产生过怀疑。关于《商颂》制作年代的歧议,最早始于汉代。汉代《诗经》学主要分为四家。古文家的《毛诗》认为《商颂》传自商代。而齐、鲁、韩三家今文学派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商颂》是春秋时期宋国的作品,其作者是正考父,创作动机是为了赞美当时的宋国国君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但由于汉代经学家中有许多人并不专守一门(东汉以后更是如此),再加上经过郑玄整理的《毛诗》在东汉以后的读书人中影响很大,所以在清代以前,今文学家关于《商颂》作年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晚清以后疑古思潮的兴起,经学流派之一的今文学派翻起了《诗经》研究史上的这桩旧案,清季、民初有许多著名学者发表意见,表示支持今文家的观点。其中魏源、皮锡瑞、俞平伯和顾颉刚等人提出二十多条理由,论证《商颂》为春秋时期的作品。王国维不赞成《商颂》作于春秋时期,但他同时也不赞成《商颂》是商代的作品,而认为《商颂》当作于宗周中叶。在否定《商颂》作于商代这一方面,王说与《商颂》作于春秋说相通,所以从客观上增强了《商颂》作于春秋说的力量。自彼时以来,《商颂》作于春秋说开始在《诗经》研究界占据统治地位,并在文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今天我们讨论清代今文学派的观点时,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清代今文学派的学术观点与其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研究经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古讽今。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魏源在谈到他写作《诗古微》的目的时说: 《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故《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而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 至于其研究《诗经》时所持的原则和方法,魏源说: 虽然,《诗》教止于斯而已乎?……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故夫溯流頳则涵泳少矣,鼓弦急则适志微矣。《诗》之道可尽于是乎? 魏源说他要“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声称所论“非徒章句之《诗》”,实际上是一种不重训诂、宁求之深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基于清代今文学派学术主张的根本,即借经说以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张目。清代今文学派的政治主张虽然在历史上曾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它在学术上的可 信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李先 生还指出,清儒在学术上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其门户之见。严重的政治及学术偏见,不能不影响到疑古学派在学术态度上的客观公正,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其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商颂》的作年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1956年,杨公骥、张松如(公木)两先生合作,撰写了《论商颂》一文,刊载于《文学遗产》增刊二辑。之后,杨先生又作《商颂考》,附录于195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一书。1995年,张松如生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商颂研究》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商颂研究》一书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前举文相比,没有大的改变。所以杨、张两位先生关于《商颂》的学术观点可以前述文章为代表。杨、张两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商颂考》一文,材料详赡,考辨细密,全面反驳了今文学派关于《商颂》美宋襄公的错误说法,论驳极为有力。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杨、张两先生的上述文章在国内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实际达到的学术水平并不相称。几十年来,学术的发展,包括新材料的发现与相关理论认识的进步,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师辈工作的基础上对《商颂》的作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们进行《诗经》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必须进行的第一步工作。 品千年经典 扬文化之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