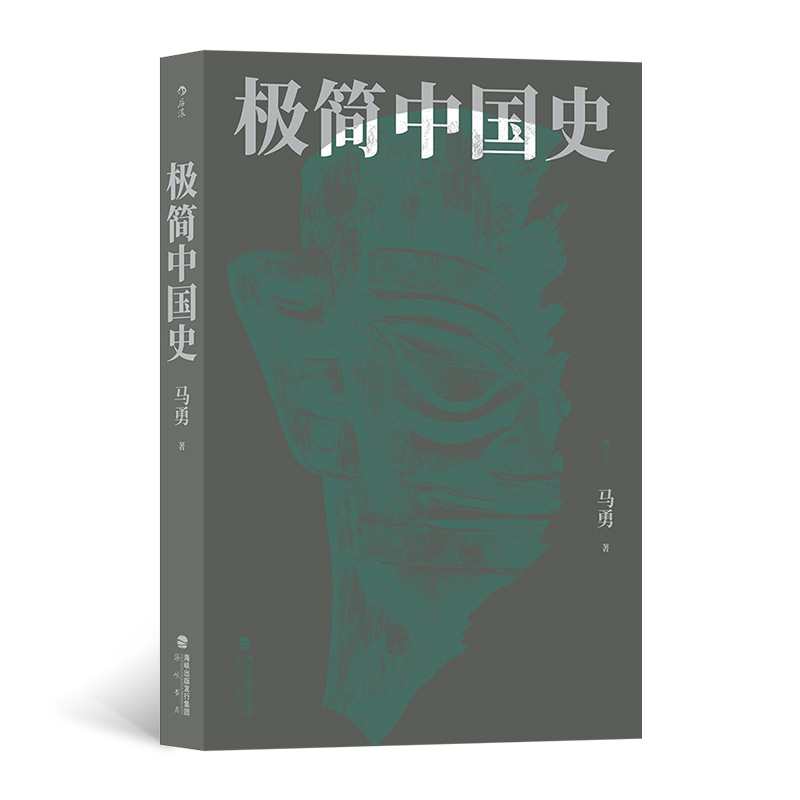
出版社: 海峡书局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70
折扣购买: 极简中国史
ISBN: 9787556710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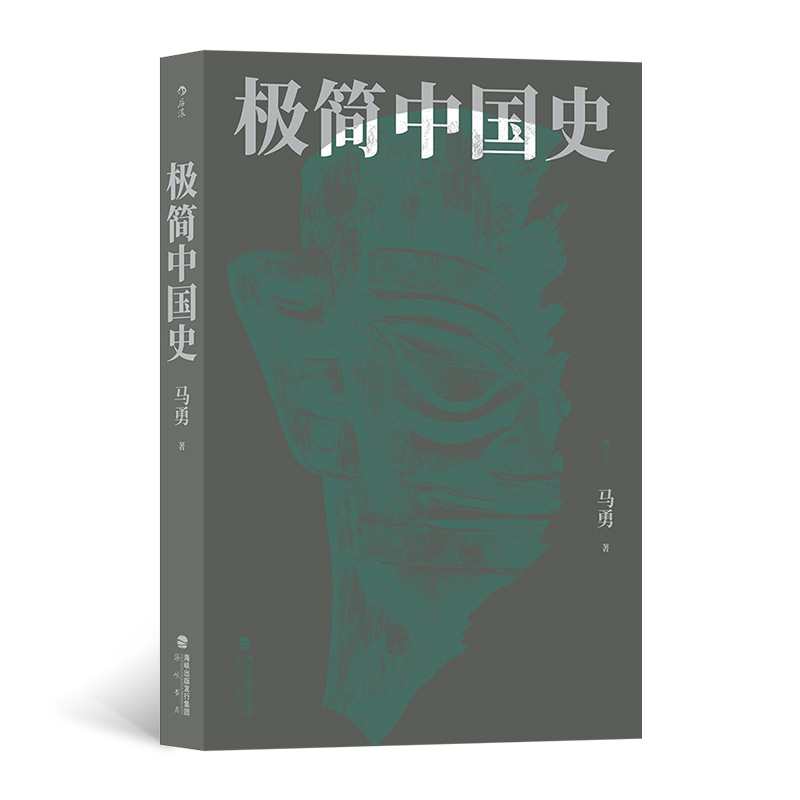
马勇,著名历史学者,现为研究员,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儒家经学、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汉代春秋学研究》《中国文明通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梦想与困惑: 1894—1915》等。
第 1 讲 导? 论 各位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家一起交流关于中国通史的一些看法。这个栏目的创意者将之定名为《极简中国史》。“极简”二字极好,如果能在一个极短的篇幅中给各位一个中国史的梗概,一个与先前不太一样的认知,我觉得就值得做。 在导论部分,我只想讲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当中来表达中国的过去,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印象。 到今天为止,中国历史有多久呢?在中国史学研究的框架中,在过去漫长的时间段,我们先讲的是 3000 年叙事,后来讲 5000 年叙事。当然我们讲到元谋猿人和北京猿人的时候,讲的(历史)会更漫长。但是从严格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而言,真正可以叙述的、有准确凭证的历史,还是应该遵循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思路,从三皇五帝开始往下讲,这是中国历史叙事起源的大致情况。 100 年来的现代中国考古学所做的主要工作,也大致不出这个范围。 从 孔 子 所 处 的 时 代 到 现 在, 是 2000 多 年 的 时 间。 其间历史不断发展,历史叙事也在不断调整。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再到班固的《汉书》,一直往下是《后汉书》,然后是唐朝几部史书的编写,又到宋朝司马光组织《资治通鉴》的写作。到了晚近,历史学者把中国历史上公私所修的历史书做了一个大概的分类处理,比较宏观地讨论记述了中国历史的一些作品,被概括为“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这些历史书都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传统框架,它们为我们认识过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即传统叙事当中的王朝政治史,这是最传统的、最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当然,虽然传统叙事格外注意政治史,但并不意味着政治之外的历史现象完全被视为无物。其实,“二十六史”中也有不小的篇幅记录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科学技术创造等方面的内容。 在清朝中期之前,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非常中国化的,没有夹杂外国因素。但是到了清朝中期之后,中国的历史叙事开始渗入一些西方因素,特别是受俄国因素的影响,那时人们开始加强对西北史地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框架模式也开始有了调整。到了 20 世纪初年,新史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叙事开始出现革命性改变,那时也叫作“史学革命”。这一次调整,仅从形式而言,一种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 章节体叙事方式— 出现了。而传统中受到广泛认同的纪传体、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甚至典章制度等历史书写方式渐渐退出或淡出。 20 世纪 20 年代由清朝遗老编纂完成的《清史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书写方式的绝响。之后即便有人试图恢复、改良旧的书写方式,基本上都不成功。在中国传统史学当中,没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叙事框架,但是新史学开始讲这些因素。这样,在距今 100—150 年这段时间,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开始有了很大调整。这个调整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很大帮助,通过新视角可以得到一种不一样的观察。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全球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这样,中国的历史叙事又发生了调整,民族主义史学开始崛起,历史叙事的观念性加强了。原来的历史学是就事论事地讲一个事情,民族主义史学则开始讲价值观。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上,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逐步构建起来,给历史研究注入了爱国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平等思想,这对我们认识过去有很大的帮助。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有它的局限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读者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一角。有个成语叫盲人摸象,你觉得你摸到这一块儿是历史的真相,其实可能不尽然。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在民族主义史学、爱国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我们这个栏目就是以这种综合的历史叙事方式加以展开。 民族主义史学认为近代中国问题的发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没有外国入侵,中国会缓慢地向前走。像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所说的那样,假如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像西方国家一样,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历史的发展确实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从 15 世纪(也就是明朝早中期)开始,大航海发生,全球史的叙事开始,中国的问题开始和全球有重大关联。 15世纪之后中国历史发生的许多问题,都能追到外部因素,比如明朝的闭关锁国、倭寇、白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可以从全球历史的变动中找到比较直接的原因。 从这个观点看 17 世纪明清易代,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内部问题,它实际上也有很多外部环境的背景。过去的气候史研究认为,小冰河时期气温骤降,促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全球环境变冷影响了政治的运转。从这里边可能看到很多全球因素,当然到了 18 世纪,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没有全球贸易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 18 世纪康雍乾时代清帝国的富强。康雍乾时代的中国还是农业社会,为什么在农业社会背景下能突然出现几千年来最繁华的盛世呢?就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当中,贸易顺差导致了 18 世纪中国的繁华。到了 19 世纪,这一点看得更明白,鸦片战争以及之后中国一系列的变革,就是因为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当中。 上面我们讲的是中国变化背后有全球因素的推动,反过来说,全球变化当中也有很强的中国因素。从全球史视角观察,在过去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国所有的发展都是因为和全球有一个互动的因果关系。现在全球史的研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不是 15 世纪大航海之后,中国才卷入全球化的背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和了解,现在可以追溯记录的时间,也往前推得很早。比如先秦时期齐国的邹衍,已经对“大九州”“小九州”有了很准确的描述,表明至少到那时,中国人已经对域外文明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秦汉帝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晰,更不要讲很早时期留存下来的文献《山海经》了。现在我们对《山海经》的研究也很充分,如果没有一定的勘查或者文字的记载启示,《山海经》不可能描述出那样一种世界图景,比如它里面提到了中亚地区和红海附近的情况。 以上说的是可以记录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而不可记录的,也就是考古学发现的中国和世界曾经发生的联系,那就更久远了。有些研究者根据基因组的考订,认为各色人种的祖先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从更遥远的年代开始,中国和世界就是一体的。 100 多年前曾经出现过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来自中亚。今天很多中国人不愿意认同这些观点,但是如果完全无视这些说法,有几个问题也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还有如何解读秦始皇陵寝里面的中亚因素。 我在这里不想强调很奇特的个案问题,而是想跟大家探讨交流大历史叙事当中,中国因素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到了中古以后、晚近时期,中国因素影响世界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汉唐时期,中国由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过渡,这个时间段极为漫长,差不多有 1000 年。其间,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秦汉时期,中国已经可以和罗马帝国有某种程度的沟通。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有很多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是外部因素进入中国,中国因素也开始渗透到外部地区。 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和历史学能够记录、表达,并进行研究的东西,是根本不成比例的。历史学家知道的再多,也没有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多。为什么?因为人们在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时时或有意识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隐私,历史的创造者甚至会有意识地毁掉我们历史学认为是史料的东西。现在如此,过去同样。 比如多年前在美洲发现了明朝宣德年间的文物,这能否表明明朝人曾经到过美洲呢?不能这么直接讲。六朝时期,南朝法显和尚可能到过美洲。但是他到美洲是不是有意识地要去发现新大陆呢?毫无关系。那只是很自然的原因,可能因为风向,因为非人力可控制的因素,飘洋过海就到那儿了。可能有很多人飘洋过海到过美洲,但是只有他活着回来了。历史上记录的事情极为有限,而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故事远远多于历史的记录。 历史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实证,需要史料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打开想象的空间,在历史各个节点中找寻历史关联中的合理逻辑。 我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做出以下解读:在过去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变之中,有哪些外部因素影响了中国,中国又是如何向世界进行反馈的。我希望能立足于一个大的视角,同各位一起讨论中国的过去。 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分析过去,它研究的问题都是不可再现的东西。历史学可能是所有学科中最不像科学的学问。对自然科学,人们可以去描述第二次发生的情况,经过实验,第二次一定和第一次一样,不一样就证明其中有问题。而历史学要讨论的是一个无尽的过去,是消失的过去,我们没办法起死人于九泉之下,更没有办法去重复、重现历史场景。 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去讨论李鸿章的功过是非,一切东西都是我们的主观诉求。我们可以把与李鸿章相关史料读得很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建构李鸿章和他同时代人心灵上的互动。我们再怎么建构史景,依然缺少心灵上的环节。 因此,历史学在描述过去的时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历史学的进步和改进,主要凭借的是历史学家不断对历史进行解构、重构、再解读、再重构,逐渐逼近历史真实,而不是强调自己的探究就是历史真实。在这本书当中,我希望通过自己粗浅的一家之言,跟诸君一起回顾先民曾经走过的路,曾经可能有的想法与意识。 ★以大视角回望“三代”至清末,破除“正统”崇拜,纠正历史“常识”的偏颇之处。 “华夏正统”是很长时间内中国历史研究的“政治正确”,似乎不排斥狄夷,不树立中原华夏正统,便是大逆不道。然而,从大历史角度来讲,不论是夏商/商周,还是宋、辽、金、西夏,乃至蒙古、明、后金,它们都是长期并存的共时政权,而它们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华文明的历史。同样的,与周边文明乃至世界其他文明的互动,都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只有以平等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文明互动过程,我们才能对我们自身的历史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也正是本书作者所尝试去阐述的内容。 ★探究中国历史长时演进的逻辑,庖丁解牛,点明中国历史发展之关键。 不拘泥于繁杂的历史细节,而是运用深厚的历史功力抓取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剖析中华文明的历史的传承与转折的关键,提纲挈领,让读者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历史形成整体性、框架性的认识与理解。 ★以解读“历史转折”为己任,尝试为处于第三次历史大转折中的我们勘定坐标、寻找未来。 以他者为镜,以历史为鉴,在当下变动的时代,回顾历史,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拨开迷雾,看清未来之路的方向。以静制动,借历史智慧,消解迷茫与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