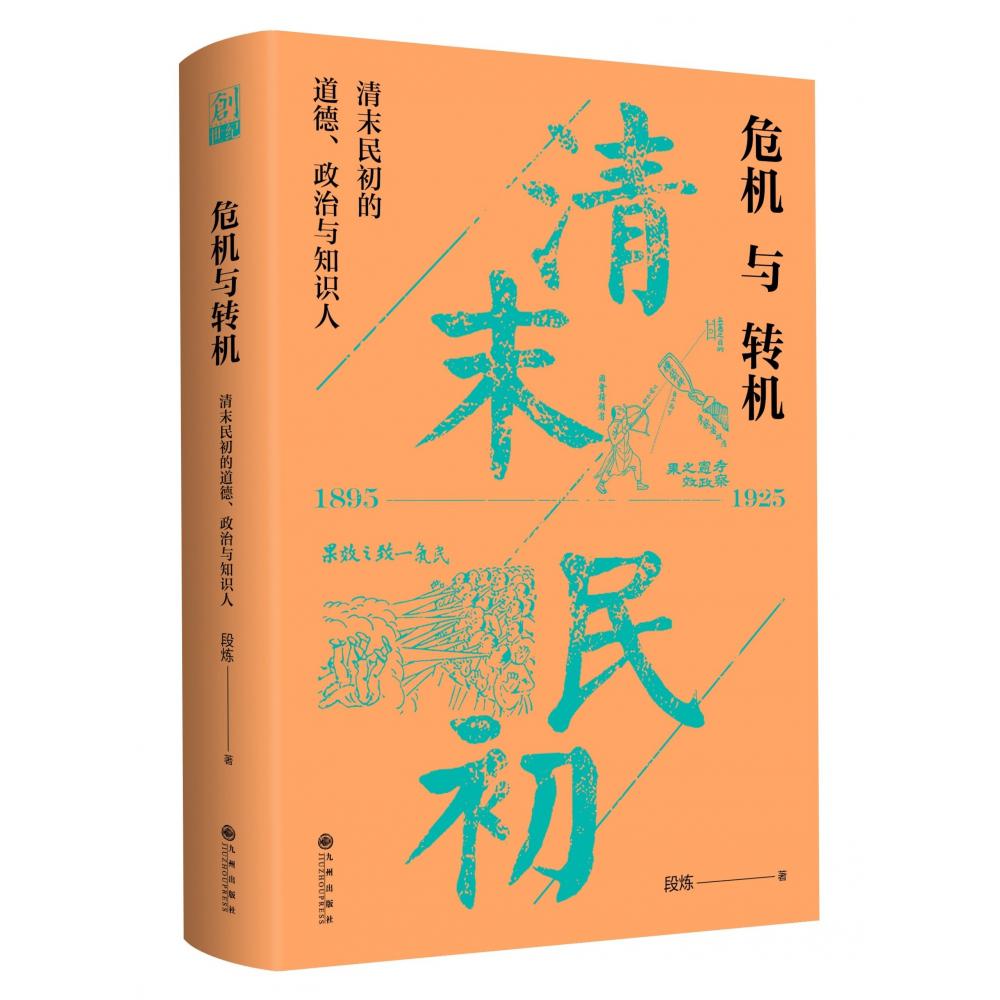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2.72
折扣购买: 危机与转机:清末民初的道德、政治与知识人
ISBN: 9787522508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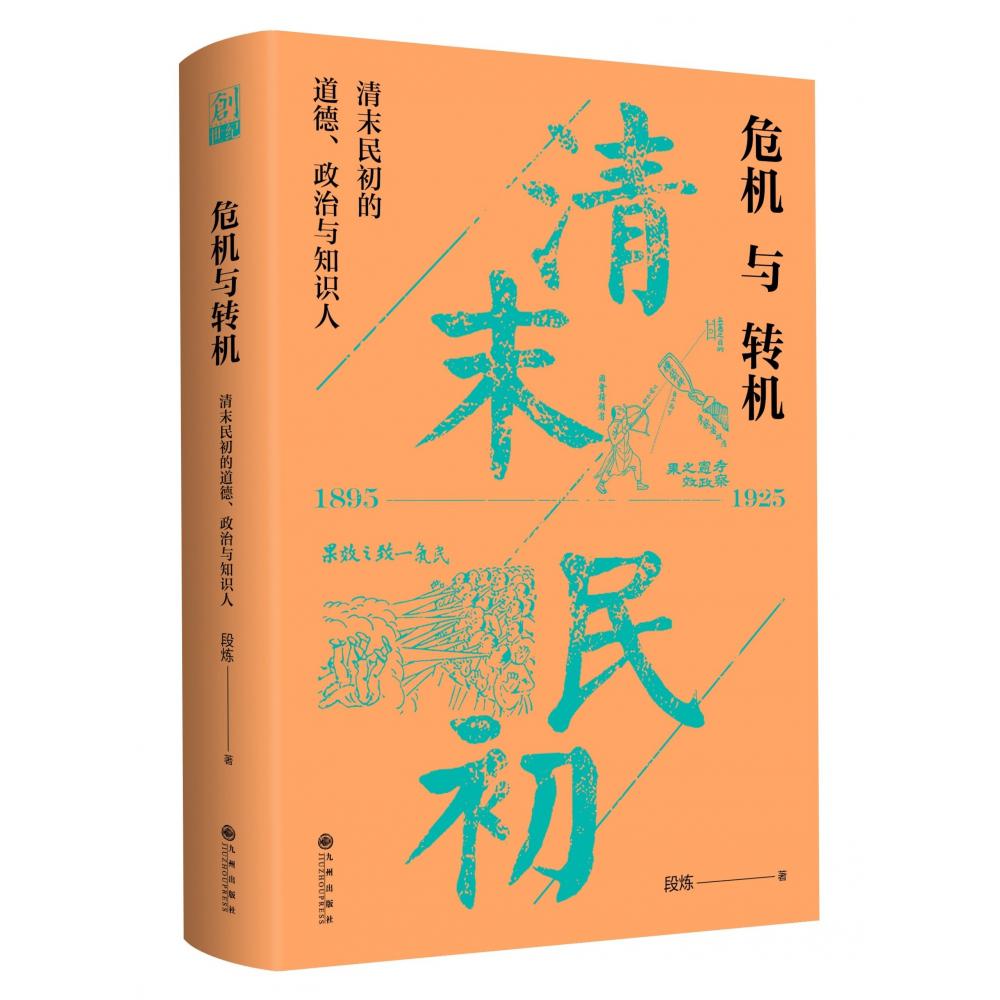
湖南省长沙市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联合培养博士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与知识分子,著有《“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读史早知今日事》等。
康有为:学术立场与政治态度 1887年,康有为在日记中写道:“列国并峙,是以有争。”他开始在经学内部,积极处理传统政教秩序、君权与制度改革的关系,并初步建立起以君权为中心的变革方案。《康子内外篇》的部分篇章正式发表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其时已在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之后。 故就文本的实际社会反响而言,不及康有为在1890年代编撰出版并随即引发聚讼纷纭的《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然而,作为体现康有为思想演变的核心文本之一,《康子内外篇》在学术立场与政治态度上的“守正出新”,却成为其未来主导的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声。 在《康子内外篇》中,基于对周礼所蕴含的“教学之道”的历史反思,康有为思考的重心,从高度重视儒家的“礼教伦理”转变为对政治制度及其变革方式的构想。他进而尝试在“君权独尊”的前提下,依托君权的绝对力量推进王朝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一方面,从康有为思想的延续性而言,他以“君权独尊”为中心,通过制度变革以因应危机的思考,依然延续着道咸以来经世思想中“理势互动”的内在脉络。但康有为的关注重心,开始从具有超越价值的儒家德性伦理,逐渐转向更趋客观性与世俗化的人类理性与知识追求,其目的在于通过形塑新的义理形态,化解因严峻时势所造成的儒家传统的“认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is),并由此论证国家制度变革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从康有为思想的变动性来看,在这一时期,经学逐渐从一种传统“天理”世界观支配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开始转变为一种关于国家制度的变革理论。《康子内外篇》中关于“势生理,理生道”的思考转型,不仅为康有为实现儒学的内在转化创造了新空间与新动力,也为他推动今文经学在晚清思想舞台上的崛起提供了理论前提。 与撰述《康子内外篇》几乎同步,康有为也在思考“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并且连续三年依托“几何”原理,著述《人类公理》 《公理书》,“手定大同之制”。对于此项工作,康有为自谓“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可见期许之高、期待之深。关于《人类公理》《公理书》《实理公法全书》以及《大同书》等著述之间的版本关联与思想脉络,学界素有争议。然而,《人类公理》与《公理书》书名聚焦的“公理”二字,以及在《康子内外篇》完成两年后,《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公法会通》等著述对于“公法”的阐释,则呈现出康有为的知识视野,开始从“周公之礼”扩充到至大无外的世界与人类。 饶有意味的是,康有为曾在日记中大胆设想:“斯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兵军永息,太平可睹矣。”为达到这一“新理想”,他甚至不惜未来“合其国”“废其君”,以泯除列国相争。其弟子后来亦注意到:“义理虽无定,先生又谓有公理焉。‘公理’二字在中国中,实自先生发之”。正是在一个“义理无定”的转型时代里,依托欧洲几何学所开启的实测、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形式,康有为开始尝试构建一种新的义理形式——“实理公法”,以此重新阐释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政教秩序,并将其纳入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世界观当中。 严复:寻求“超越富强”之道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严复以深具洞见的论述及其对一系列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步翻译,促成了“天演”论述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天演”论述的巨大影响之下,建立在天命、神道与圣人经典之上的“天理”世界观逐渐瓦解,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由“公理”“公例”“公法”等大经大法所主导的全球竞争时代——一方面,历史被描述为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线性过程,进步史观成为解释世界、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新框架;另一方面,“天演”理论将“群”作为“物竞天择”的基本单位,鼓吹通过“自强保种”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从此,如何提升民德、民智与民力适应文明竞争,成为朝野各界普遍认同的因应危机的根本途径。因此,严复关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诘问,通过更具普遍性与世俗性的“天演”之道获得了深沉的回响。 晚清时期的严复穿行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与中国同治、光绪年间的平行时空,却在两种迥然不同的知识谱系之间,创制出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文化视野。从本文对于严复关于道德与政治议题的描述、分析与评估可见,严复的思想摆荡于中西之间,接受多种“道”并存的历史现实,却同时执着追寻中西学理的“道通为一”。借用其在《天演论》自序中的话,即是“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在这一其乐融融的“考道”过程之中,严复对于中西思想各有批判与取舍,也各有调和与嫁接。他笔下文字与译述因之富含矛盾与张力。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他对于中国传统的抨击,往往激活了传统中的因子(如《易经》与《春秋》);而他对于西学的接纳,也包含着对于西学的修订与扬弃(如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的学说)——简单的线性叙事,无法精确描绘严复在这一时期对于“英国课业”的复杂反应。显然,严复的翻译与撰述活动所呈现的世界观转型与建构,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经典理论在相互交织、密切互动之中实现“典范转移”的过程。 严复认为,他正是在《老子道德经》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当中,发现了“天演开宗语”,认为其尽括“达尔文新理”。他赞同斯宾塞的看法,以“天演”统摄万物从而实现自然、个人、国家、社会的“止于至善”。但他自身固有的“儒学性格”,选择的却是推动民德、民智、民力的温和渐进的教化力量,而非推崇弱肉强食的无情淘汰与暴力革命。因此,“天演”作为宇宙运行的常理具有普遍伦理法则、历史哲学和价值源泉的多重含义,是万物殊异和变迁之中的终极不变性,亦即他在《政治讲义》中所谓的“道”。可见,晚清时期严复的思想探索,并非“寻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的世俗冲动和科学理性可以简单概括。在寻求“道通为一”的思想张力背后,严复依然有着对于“超越富强”(beyond wealth and power)的新普遍性的“道”的追寻。在清末民初“公理”世界观取代“天理”世界观的“由道变俗”的进程中,这种贯穿自然、道德与政治的超越价值信念与形而上的追求,仍然通过不同形式保留下来,并左右着未来人们对于中国命运的种种想象。 针对当日风靡一时的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严复则强调,“一国之政教学术”乃是有机整体。他讽刺说,若对中西文明作实用主义式的任意裁剪与平行移植,则类似“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既然“道器体用”必须一贯,如果不能寻觅统摄于超越中西政教学术的更高之“道”,则结果必然只能是全盘西化或全盘中化。而这二者皆非严复所能认可与接受,故只能勉力“道通为一”。然而,以“后见之明”观之,受制于对中西学术体系根本差异的准确理解,严复能否真正融通文明之间的“一体相关性”,其实仍有讨论空间。到了1912年,58岁的严复主持北大之时,已承认“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接踵而至的欧洲大战,更让他抨击西方世界“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并主张返归“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的孔孟之道。及至晚年,严复转而多从特殊性与历史性的角度阐述中西文明。这与他早年立意追寻二者“道通为一”的努力已经渐行渐远,以致在20世纪初日趋激进的革命时代里,饱受“保守”“复古”的讥评。其中的“经纬万端”,映照出严复一生心路的复杂彷徨与近代中国世界观转型的曲折往复。 杨度:国之内外的“文野之辨” 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让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如何在一个“列国竞争之世,而非一统闭关之时”,思考晚清中国对内对外的生存情境和因应之道,进而重新理解“何种世界,谁之中国”的时代命题,逐渐成为晚清读书人无法回避的挑战。而他们对于这一严峻挑战的积极思考与应对策略,也在不同程度上反向改造着他们自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进而交织成晚清民初知识界复杂多元的思想谱系。 杨度在20世纪初期世界观念的形塑过程,正是建立在“通乎内外”的视角之下,对于“公理”“强权”“公法”“文明”“野蛮”等政治议题的重新理解与认知。首先,无论是基于对《万国公法》的重新理解,审视晚清国家内外的新型政治关系,还是基于“文明”与“野蛮”新内涵对于“金铁主义”的深度阐发,20世纪初期杨度的思想中心,已经被以进化论为轴心的“公理”世界观占据:“自达尔文、黑〔赫〕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杨度笔下的两个“一切”明确昭示,从思想根源上看,晚清时期“天朝的崩溃”实质是世界观的崩溃。如果说,传统儒家“天理”世界观笼罩下的德性义理,其重心落实在道德人心的“善恶是非”之上,并由此产生解释中国与周边藩属与朝贡关系的知识论体系;那么,当“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为标准的“时势”成为朝野关切的重心,新世界观的价值坐标,就必然转移到国家“实力强弱”之上:“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 因此,在儒家“天下一家”的秩序瓦解之后,“公理”世界观作为重新支配世界和宇宙的普世法则,将杨度眼中的晚清中国转型之路,深深裹挟到一个由新兴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格局与外交关系当中:“今吾辈将谋中国之所以自立之道,亦世界中之一事。”这是杨度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而重构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中国文明完美形象与士大夫优越感的幻灭,另一方面,则是促使杨度在世界观念上,形成一套更为纠结的“文野之辨”的政治准则。在“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直白表达背后,是他自觉形成的区分“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尺度。从此,在传统“天理”世界观瓦解的背景下,杨度心目当中晚清中国所着力寻求的“自立之道”,就具有了思想和现实意义上的多重意涵: 第一,在彼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势优劣已经与道德善恶无关,甚至呈现彼此对立的趋势——前者由“力”支配,而后者由“理”决定:“夫所谓优劣者,非善恶之谓。瑞士之政善于吾国,若于吾国遇,彼犹当败;俄罗斯之政恶于吾国,若于吾国遇,彼犹当胜。若不欲世界之大势仅凭一己之所谓善恶者而造之,则吾之所谓善者,或即为其劣败之源,吾之所谓恶者,或即为其优胜之源。”可见,在这一新的“文野之辨”下所形成的世界观念,为杨度提供了观察国家政治和世界格局的独特历史视角,也彰显出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价值观念“世俗化”程度的大大加深。 第二,在这一世界观念的支配下,西方列强通过市场掠夺、贸易制裁、军事入侵等暴力手段,牢牢把持着分配和维持各自“世界权力”的地位——但是,这种瓜分世界的手段的合法性,却无法得到充分合理的解答。从更深层次看,19世纪、20世纪之交这一“野蛮世界”的秩序维系,正是因为无法诉诸一个高于民族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法则与国际组织,而是直接依赖国家之间军事与经济实力的抗衡。因此,从最为现实的角度,杨度势必鼓励晚清中国,仿效日本、德国等后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强化经济、贸易和军事战备能力为轴心(即“金铁主义”当中的军事立国、巩固国权与责任政府),进而走向全面促进国家政治结构和运作能力的变革(即“金铁主义”当中的工商立国、扩张民权与自由人民)。基于这一严峻的历史情境和对“野蛮世界”的重新理解,杨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国家政治的内部结构性变革,才能更有效地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必求与各国相遇而无不宜者,而后乃同居于世界而无不适”的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体系当中“免劣败而居优胜”的“文明国”。 第三,从现代民族国家“内与外”的关系而言,杨度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而立国,使全采用铁血主义,则以偏于野蛮之故,将于外于内均不适于生存”。在他看来,“国家的真正以言乎外,则人皆能为经济的战争,而我仅能为军事的战争,不劣败何待?以言乎内,则吾国政治方甚紊乱腐败,非取各文明国之所以治内者大改革而一新知,不足以发达国民之能力,使与世界各国之国民相见。”可见,杨度心目中的现代国家政治愿景与全球正义的最终实现,仍有赖于国民能力的文明展示,而非简单诉诸“去道德”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在心灵的深处,杨度似乎朝着当年嘉纳治五郎倡言的“公理主义”重新致意。因此,在传统思考与现代意识的关联之中,对于“何种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必然推演出知识人关于中国内部问题更为主动、全面的探寻,包括如何在政治权威动摇的基础上,重建国民、国权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平衡“立宪”与“革命”背后关于“中国”认知的民族主义思想分野。这是20世纪初期杨度在《金铁主义说》当中关于“谁之中国”的深沉之思,也将成为杨度和他的政治盟友(包括对手)在20世纪的破题之举。 1.参考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危机中寻求转机,对当下思考未来有重要启示。 2.在老话题上谈出了新意,关于近代思想史研究令人眼睛一亮的力作。 3.受到学界重视的研究成果,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黄克武教授联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