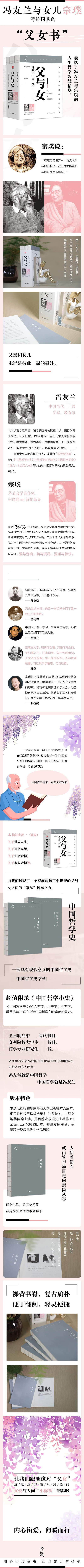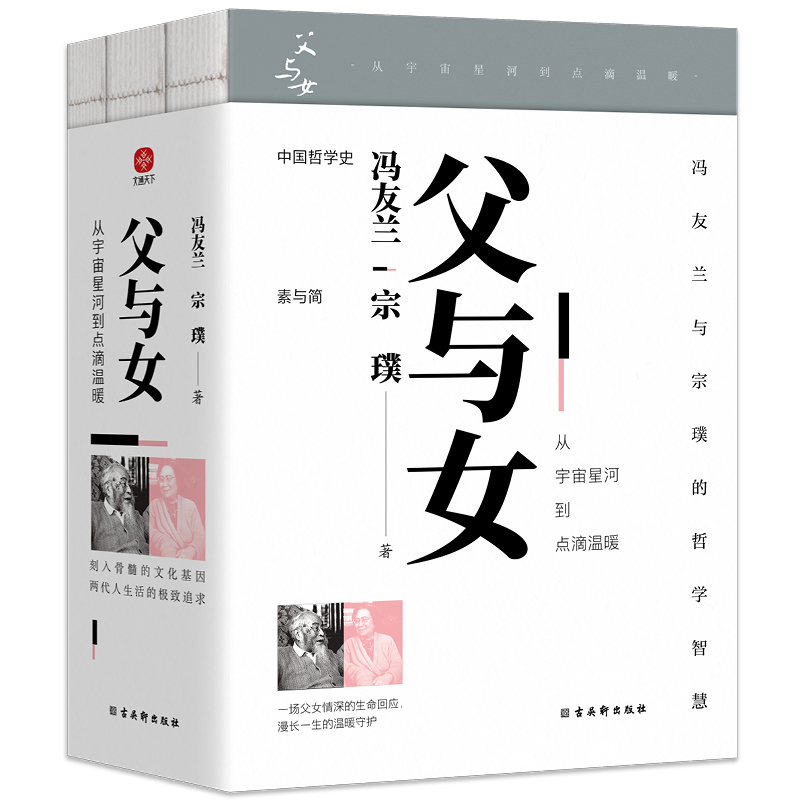
出版社: 古吴轩
原售价: 188.00
折扣价: 103.40
折扣购买: 父与女:从宇宙星河到点滴温暖
ISBN: 9787554617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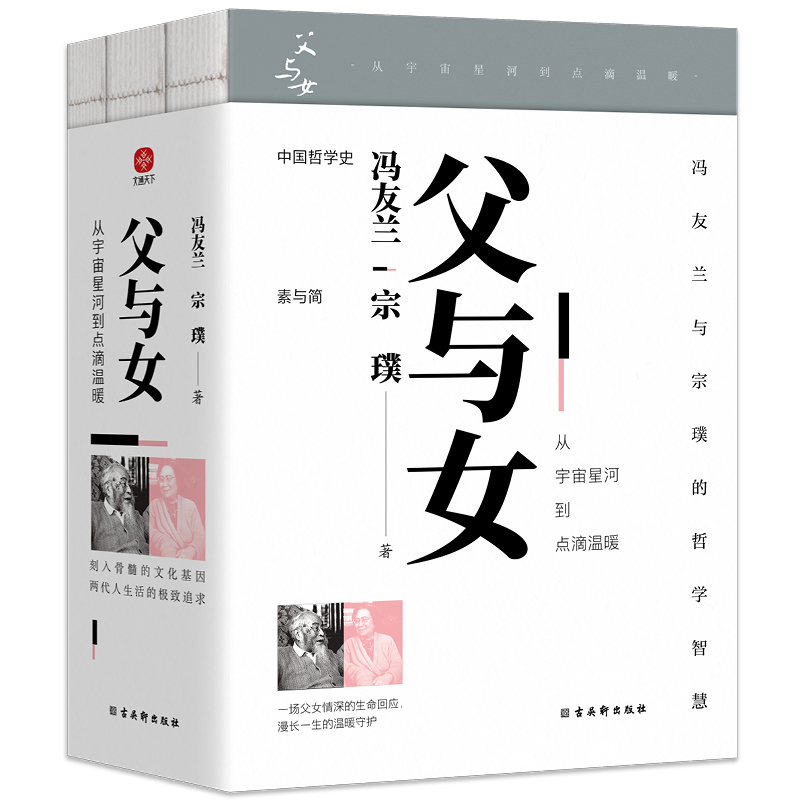
冯友兰 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师从杜威。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也是我国20世纪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哲人,被誉为“现代新儒家”。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英文)《贞元六书》等。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无人可代。 宗璞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于北京,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文坛上的常青树\\\\\\\\\\\\\\\\\\\\\\\\\\\\\\\\\\\\\\\\\\\\\\\\\\\\\\\\\\\\\\\\\\\\\\\\\\\\\\\\\\\\\\\\\\\\\\\\\\\\\\\\\\\\\\\\\\\\\\\\\\\\\\\"。宗璞家学深厚,又得外国文化润泽,却是一个非常简单淳朴而天真的人,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她的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清雅超脱,又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哲学史》 自序一 吾非历史家,此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其在“史”之方面,则似有一点可值提及。 中国近来,史学颇有进步。吾人今日研究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与前人不同。吾人今日对于中国古代之知识,与前人所知者亦大异。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吾人今日已多加以辨正。对于此种“古史辨”,王船山、崔东壁即已有贡献;不过近人更有意地向此方向努力耳。 吾于写此哲学史时,对于中国古代史,亦往往有自己之见解。积之既久,乃知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官僚查案报告中常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语。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近人皆知其多为“查无实据”者。然其同时亦多为“事出有因”,则吾人所须注意者也。 吾亦非黑格尔派之哲学家,但此哲学史对于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若与他观点联合观之,则颇可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之一例证。黑格尔谓历史进化常经“正”“反”“合”三阶段。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此“反”也;若谓前人说法虽多为“查无实据”,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顾颉刚先生云:“反”之方面之工作,尚多未做。吾深信之。吾亦非敢妄谓此哲学史中所说之中国古史,即真与事实相合。不过在现在之“古史辨”中,此哲学史,在“史”之方面,似有此一点值提及而已。 此书初稿成名,先在清华印为讲义,分送师友请正。其经改正者,及书中采用师友之说之处,皆随文注明。谨乘此机会,向诸师友致谢。 冯友兰 民国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清华园 第一篇 子学时代 第一章?绪论 (一)哲学之内容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做此工作之先,吾人须先明在西洋哲学一名词之意义。 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兹先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 希腊哲学家多分哲学为三大部: 物理学(Physics), 伦理学(Ethics), 论理学(Logic)。 此所谓物理学、伦理学与论理学,其范围较现在此三名所指为广。以现在之术语说之,哲学包含三大部: 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 Theory of World), 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 Theory of Life), 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 Theory of Knowledge)。 此三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之末,普遍流行;即至近世,亦多用之。哲学之内容,大略如此。 就以上三分中若复再分,则宇宙论可有两部: 一、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Ontology); 二、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Cosmology)(狭义的)。 人生论亦有两部: 一、研究人究竟是什么者,此即心理学所考究; 二、研究人究竟应该怎么者,此即伦理学(狭义的)、政治社会哲学等所考究。 知识论亦有两部: 一、研究知识之性质者,此即所谓知识论(Epistemology)(狭义的); 二、研究知识之规范者,此即所谓论理学(狭义的)。 就上三部中,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有密切之关系。一哲学之人生论,皆根据于其宇宙论。如《列子·杨朱篇》以宇宙为物质的,盲目的,机械的,故人生无他希望,只可追求目前快乐。西洋之挨比求伦学派(Epicureanism)以同一前提,得同一断案,其一例也。哲学家中有以知识论证成其宇宙论者;(如贝克莱Berkeley、康德Kant以及后来之知识论的唯心派Epistemological Idealism及佛教之相宗等)有因研究人之是什么而联带及知识问题者(如洛克Locke、休谟Hume等)哲学中各部分皆互有关系也。 [注]孟太葛先生(W.P.Montague)亦谓哲学有三部分,即方法论,形上学与价值论。方法论即上所谓知识论,复分为二部;形上学即上所谓宇宙论,亦复分为二部;皆与上所述同。价值论复分为二部:(一)伦理学,研究善之性质及若何可以应用之于行为;(二)美学,研究美之性质及若何可以应用之于艺术。(Montague: The Ways of Knowing,P1) (二)哲学之方法 近人有谓研究哲学所用之方法,与研究科学所用之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是逻辑的,理智的;哲学之方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其实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虽有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哲学方法之内。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凡著书立说之人,无不如此。故佛家之最高境界,虽“不可说,不可说”而有待于证悟,然其“不可说,不可说”者,非是哲学;其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说出之道理,方是所谓佛家哲学也。故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的经验(此经验果与“实在”符合否是另一问题)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换言之,直觉能使吾人得到一个经验,而不能使吾人成立一个道理。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合逻辑。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近人不明此故,于科学方法,大有争论;其实所谓科学方法,实即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之较认真、较精确者,非有若何奇妙也。惟其如此,故反对逻辑及科学方法者,其言论仍须依逻辑及科学方法。以此之故,吾人虽承认直觉等之价值,而不承认其为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与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亦仅有程度上的差异,无种类上的差异。 (三)哲学中论证之重要 自逻辑之观点言之,一哲学包有二部分,即其最终的断案,与其所以得此断案之根据,即此断案之前提。一哲学之断案固须是真的,然并非断案是真即可了事。对于宇宙人生,例如神之存在及灵魂有无之问题,普通人大都各有见解;其见解或与专门哲学家之见解无异。但普通人之见解乃自传说或直觉得来。普通人只知持其所持之见解,而不能以理论说明何以须持之。专门哲学家则不然,彼不但持一见解,而对于所以持此见解之理由,必有说明。彼不但有断案,且有前提。以比喻言之,普通人跳进其所持之见解;而专门哲学家,则走进其所持之见解。(参看William James: A Pluralistic Universe, P. 13—14) 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荀子所谓“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非十二子篇》,《荀子》卷三,《四部丛刊》本,页十二)是也。孟子曰:“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孟子》卷六,《四部丛刊》本,页十四)辩即以论证攻击他人之非,证明自己之是;因明家所谓显正摧邪是也。非惟孟子好辩,即欲超过辩之《齐物论》作者,亦须大辩以示不辩之是。盖欲立一哲学的道理以主张一事,与实行一事不同。实行不辩,则缄默即可;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者。其辩中或有逻辑的误谬,然此乃能用逻辑之程度之高下问题,非用不用逻辑之问题也。 (四)哲学与中国之“义理之学” 吾人观上所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若参用孟太葛先生之三分法(见本章第一节注),吾人可将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及方法论三部分。《论语》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公冶长》,《论语》卷三,《四部丛刊》本,页五),此一语即指出后来义理之学所研究之对象之二部分。其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其研究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论。惟西洋哲学方法论之部分,在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尚讨论及之;宋明而后,无研究之者。自另一方面言之,此后义理之学,亦有其方法论。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不过此方法论所讲,非求知识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所以求真,乃所以求善之方法。 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 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五)中国哲学之弱点及其所以 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所谓“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中国人向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中国哲学家,多讲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理想,即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成所谓圣王,即柏拉图所谓哲学王者。至于不能实举帝王之业,以推行其圣人之道,不得已然后退而立言。故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 [注]按中国古代用以写书之竹简,极为夯重。因竹简之夯重,故著书立言务求简短,往往仅将其结论写出。及此办法,成为风尚,后之作者,虽已不受此物质的限制,而亦因仍不改,此亦可备一说。 总之,中国哲学家多注重于人之是什么,而不注重于人之有什么。如人是圣人,即毫无知识亦是圣人;如人是恶人,即有无限之知识,亦是恶人。王阳明以精金喻圣人,以为只须成色精纯,即是圣人,至于知识才器,则虽有大小不同,如八千镒之金,与九千镒之金,分量虽不同,然其为精金一也。金之成色,属于“是什么”之方面;至其分量,则属于“有什么”之方面。中国人重“是什么”而不重“有什么”,故不重知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的科学,其理由一部分亦在于此。(参观拙著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etc,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32, No. 3)。 中国哲学亦未以第一节所述之知识问题(狭义的)为哲学中之重要问题。其所以,固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然亦以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 哲学家不辩论则已,辩论必用逻辑,上文已述。然以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故除一起即灭之所谓名家者外,亦少人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知识论之第二部,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 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 [注]近人有谓:“吾国哲学略于方法组织,近人多以此为病,不知吾国哲学之精神,即在于此。盖哲学之微言大义,非从悟入不可……文字所以载道,而道且在文字之外,遑论组织?遑论方法?”(陆懋德:《周秦哲学史》,页四)此言可代表现在一部分人之意见。吾人亦非不重视觉悟,特觉悟所得,乃是一种经验,不是一种学问,不是哲学。哲学必须是以语言文字表出之道理,“道”虽或在语言文字之外,而哲学必在语言文字之中。犹之科学所说之事物,亦在语言文字之外;然此等事物,只是事物,不是科学;语言文字所表之原理公式等,方是科学。依此原理公式所做成之事物,例如各种工业产品,亦是东西,不是科学。 (六)哲学之统一 由上述宇宙论与人生论之关系,亦可见一哲学家之思想皆为整个的。凡真正哲学系统,皆如枝叶扶疏之树,其中各部,皆首尾贯彻,打成一片。如一树虽有枝叶根干各部分,然其自身自是整个的也。威廉·詹姆士谓哲学家各有其“见”(Vision);又皆以其“见”为根本意思,以之适用于各方面;适用愈广,系统愈大。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论语》卷二,页十四)其实各大哲学系统,皆有其一以贯之。黄梨洲曰:“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明儒学案·发凡》) 中国哲学家中荀子善于批评哲学。荀子以为哲学家皆有所见;故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同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篇》,《荀子》卷十一,页二十四)荀子又以为哲学家皆有所蔽;故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篇》,《荀子》卷十五,页五)威廉·詹姆士谓:若宇宙之一方面,引起一哲学家之特别注意,彼即执此一端,以概其全。(见所著Pluralistic Universe)故哲学家之有所蔽,正因其有所见。惟其如此,所以大哲学家之思想,不但皆为整个的,而且各有其特别精神,特别面目。 中国哲学家之书,较少精心结撰,首尾贯串者,故论者多谓中国哲学无系统。上文所引近人所谓“吾国哲学略于方法组织”者,似亦指此。然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此两者并无连带的关系。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亦无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对话体。亚里士多德对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依上所说,则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素与简》 怎得长相依聚 ——蔡仲德三周年祭 蔡仲德(1937—2004),人本主义者。 这是我为仲德设计的墓碑刻字,我想这是他要的。他在病榻上的最后几个月,想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人本主义问题。如果他能多有些时日,会有正式的文章表达他的信念。但是天不佑人,他来不及了。只在为我写的一篇短文里提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等几个概念。虽然简单,却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理想。现在又想,理想只能说明他追求的高,不能说明他生活的广和深。因为他的一生虽然不够长,却足够丰富。他是一个好教师,也是一个好学者。生活最丰满处是因为他有了我,我有了他。世上有这样的拥有,永远不能成为过去。 人人都以为,我最后的岁月必定有仲德陪伴,他会为我安排一切。谁也没有料到,竟是他先走了,飘然飞向遥远的火星。我们原说过,在那里有一个家。有时我觉得,他正在院中的小路上走过来,穿着那件很旧的夹大衣;有时在这边说话,总觉得他的书房里有回应,细听时,却又没有。他已经消失了,消失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树木花草之间。也许真的能在火星上找到他,因为我们这里的事情,要经过漫长的光阴和遥远的距离,才能到达那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里可以重现。 首先,他是一个教师。他在入大学前曾教过两年小学,又任中学教员二十余年,以后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他四十六年的教学生涯里,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四十四年。他教中学时,课本比较简单,他自己添加教材,开了很长的古典诗词目录,要求学生背诵。有的学生当时很烦,说蔡老师的课难上。许多年后却对他说,现在才知道老师教课的苦心,我们总算有了一点文学知识,比别人丰富多了。确实,这不仅是知识,更是对性情的陶冶,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 七十年代初,在军营中经过政治磨难的音院师生回到北京,附中在京郊苏家坨上课,虽然上课很不正常,仲德却没有缺过一次课。一次刮大风,我劝他不要去,他硬是骑自行车顶着西北风赶二十几里路去上课,回来成了一个土人。上课对于一个教师是神圣的。他在音乐学系开设两门课:中国音乐美学史和士人格研究。人说他的课讲得漂亮。我听过几次,一次在河南大学讲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一次在香港浸会大学讲“说郑声”。一节课的时间被他安排得十分恰当,有头有尾,宛如一篇结构严密的文章。更让人称道的是下课铃响,他恰好讲出最后一个字,而且是节节课都如此,就连他出的考题也如一篇小文章。他在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准备,做严谨的教案。他说要在四十五分钟以内给学生最多的东西,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一次我们在外边用餐,不知为什么,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拿了一本唐诗,指出一首要我讲,我不记得是哪一首了,只记得其中有两个典故。我素来喜读书不求甚解,讲不出,仲德当时做了详细的讲解。他说做教师就要甚解,要经得起学生问。学生问了,对教师会有启发。 他淹缠病榻两年有半,一直惦记着他的课和他指导的学生。就在他生病的这一个秋天,录取了一名硕士生。他在化疗期间仍要这个学生来上课,在北京肿瘤医院室内花园,在北大医院的病室,甚至是一面打着吊针,一面在进行授课。他对学生非常严格,改文章一个标点都不放过。学生怕来回课,说若是回答草率,蔡老师有时激动起来,简直是怒发冲冠,头发胡子都根根竖起。不是他指导的学生也请他看文章,他一视同仁,十分认真地提意见挑毛病改文字。同学们敬他爱他又怕他。 他做手术的那一天,走廊里站了许多我不认识的音院师生,许多人要求值班。那天清晨,有位老学生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我家,陪伴我。一个现在台湾的老学生在电话中哭着恳求我们收下他们的捐助。我们并不需要捐助,可是学生们的关心从四面八方把我们沉重的心稍稍托起。 一个大学教师在教的同时,自己必须做学问,才能带领学生前进,才能不是一个教书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从研究《乐记》的成书年代开始,对中国音乐美学做了考察,写出了《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部巨著。这是我国的第一部音乐美学史。后来这本书要修订出版,那时他住在龙潭湖肿瘤医院。他坐一会儿躺一会儿,一字一字,一页一页,八百多页的书稿在不时插上又拔下针管的过程中修订完毕。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对各种文献非常熟悉,却从不炫耀,从不沾沾自喜,总是尽力地做好他承担的事,而且不断地思考,不知不觉间又写出了多篇论文。音乐方面的结集为《音乐之道的探求》,由上海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文化方面的结集为《艰难的涅槃》,正像书名一样,这本书命运多舛,现在尚未能出版。 他能够连续十几小时稳坐书案之前,真有把板凳坐穿的精神。他从事学术研究不限于音乐美学,冯学研究也是重要的部分。其著述材料之翔实,了解之深切,立论之精当,为学界所推重。还是不知不觉间,他写出了六十六万字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并整理、修订增补了七百余万字的《三松堂全集》第二版,又写出了《冯友兰先生评传》《教育家冯友兰》等。 对于我的父亲,他不只是一个研究者,而且也远远超过半子。幸亏有他,父亲才有这样安适的晚年。他推轮椅,抬担架,帮助喂饭、如厕。我的兄弟没有做到和来不及做的事,他做了;我自己承担不了的事,他承担了。从父母的墓地回来,荒寂的路上如果没有他,那会是怎样的日子!可是现在,他也去了。 在繁忙的教学、研究之余,他为我编辑了《宗璞文集》四卷本。他是我的第一读者,为我的草稿挑毛病。用引文懒得查时,便去问他,他会仔细地查好。我称他为风庐图书馆长,并因此很得意。现在我去问谁? 父亲去世以后,我把家中藏书赠给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设立了“冯友兰文库”,但留了《四部丛刊》和一些线装典籍,供仲德查阅。他阅读的范围,已经比父亲小多了。现在他走了,我把最后留下的书也送出。我已经告别阅读,连个范围也没有了。他自己几十年收集的关于音乐美学方面的书,我都送给了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学生们从这些书中得到帮助时,我想他会微笑。 他喜欢和人辩论,他的许多文章都在辩论。辩论就是各抒己见,当仁不让。他说思想经过碰撞会迸发出火花,互相启迪,得到升华,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如果只有“一言堂”,思想必然僵化,那是很可怕的。他看到的只是学问道理,从没有个人意气。 他关心社会,反对躲进象牙之塔。他认为每一个生命是独立的又是相连的。他在音乐学院任基层人民代表十年,总想多为别人做些事。他是太不量力了,简直有些多事,我这样说他。他说大家的事要大家管。音乐史专家毛宇宽说:“蔡仲德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他是当得起的。 我们居住的庭院中有三棵松树,因三松堂之名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常有人来,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就为了要看一看这三棵松树。三棵松中有两棵高大,一棵枝条平展,宛如舞者伸出的手臂。仲德在时,这一棵松树已经枯萎,剩下一段枯木,我想留着,不料很不好看,挖去了。又栽上一棵油松,树顶圆圆的,宛如垂髫少女。仲德和我曾在这棵树前合影,他坐我立,这是他最后的一张室外照片,也是我们最后的合影。又一棵松树在一次暴风雨中折断了,剩下很高的枯干,有些凶相。现在这棵树也挖去了,仍旧补上一棵油松,姿态和垂髫少女完全不同,像是个小娃娃,人们说它是仙童。 仲德没有看见这棵新松。万物变迁,一代又一代,仲德留下了他的著作和理想,留下了他的爱心。爱心和责任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家中从里到外许多事都是他管。他生病后的第一个冬天,在病房惦记着家里的暖气。他认为来暖气时应该打开暖气上的阀门,让水流出来,水才会通。他在病床上用电话指挥,每个房间依次打开不能搞乱。我们几个女流之辈,拿着水桶,被他指挥得团团转。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可是我领头依令而行,泪滴在水桶里…… 仲德和我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五年,因为有了他,我的生活才这样丰满。我们可以彼此倾诉一切,意见不同可以辩论,但永远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我觉得只要有他,实在别无所求。但是他去了。所幸的是他的力量是这样大,可以支持我,一直走上火星。 蔡仲德,我的夫君,在那里等着我。 女儿告诉我,她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仲德不知为什么起身要走。我们哭着要拉住他,可是怎么也拉不住。 人生的变化是拉不住的。 二〇〇七年一月五日 距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三日仲德逝世已将三年矣 【图书卖点】 1.一套书囊括冯友兰与女儿宗璞的人生哲学智慧精华 《中国哲学史》汇通古今,融贯中西,以现代眼光重构中国哲学。一本书讲透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带你探索宇宙星河的秘密。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素与简》宗璞大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书香名门,被称为最后的闺秀。中国当代最朴素、真挚、和普通女性生活最接近的作者,也最能获得大家认同,给读者带来最温煦的内心抚慰。平实的生活描述却蕴含深刻人生哲理,让人在美与感动中发现生活,从容优雅地去生活。 2.一套大家无论是“生活”还是“求学”都绕不开的经典 《中国哲学史》是“全日制高中新课标”阅读书目,各大高校大学生的必读书目、或相关专业教材。多所世界知名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通用教材,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图书,是一般大众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等不可错过的高品质读物。 《素与简》宗璞最新、最经典散文精选集,作品多次入选中小学课本、中高考试卷阅读材料。 收录《三松堂断忆》《怎得长相依聚》《哭小弟》《二十四番花信》《那青草覆盖的地方》《紫藤萝瀑布》《丁香结》等名篇。感动千万读者。 3.收录冯先生著作的权威的版本。附录陈寅恪、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三篇,体现学界权威审定情况。 当前市面《中国哲学史》多个版本,本次出版以通行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底本,相互参校《三松堂全集》本(《三松堂全集全》15册,是目前收录冯先生著作的权威版本,由其女婿蔡仲德倾心主编。)邀请专家审稿,尽量精准反应冯先生作品原貌。冯友兰之女宗璞推荐版本。 4.平凡而又独立的女性,写给大家的极简生活智慧。 宗璞,93岁的中国奶奶,一位平凡而又独立的女性,写给大家的极简生活智慧:人,走着走着,就由繁华满目走向素简从容。 5.陈寅恪、金岳霖、李慎之、冯亦代、张抗抗、王蒙、袁鹰、李子云等著名学者大力推崇的优秀作家; 6.小开本,32开本,内文用高档轻型纸印刷,精巧轻灵,厚重的学术尽量轻便,便于读者阅读、携带。 7.裸书脊装帧,复古典雅、质朴自然,便于翻越,轻灵便捷。 8.精美套装,用心设计,精细印制,可以传世的高品质“父女书”。 编辑推荐:本书价值 1.冯友兰与女儿宗璞写给国民的“父女书”,囊括了冯友兰与宗璞的人生哲学智慧精华。向读者一一诉说:关于世界人生,关于读书思想,关于生活爱情,关于家人亲情等等,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家族跨越三个世纪的父与女之间的“家风”传承之力。 2.一套大家无论是“生活”还是“求学”都绕不开的经典。《中国哲学史》是“全日制高中新课标”阅读书目,各大高校大学生的必读书目、或相关专业教材。《素与简》宗璞最新、最经典散文精选集,作品多次入选中小学课本、中高考试卷阅读材料。 3.收录冯先生著作最全面、最权威的版本。附录陈寅恪、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三篇,体现学界权威审定情况。 4.平凡而又独立的女性,写给大家的极简生活智慧。 5.陈寅恪、金岳霖、李慎之、冯亦代、张抗抗、王蒙、袁鹰、李子云等著名学者大力推崇的优秀作家; 6.小开本,32开本,内文用高档轻型纸印刷,精巧轻灵,厚重的学术尽量轻便,便于读者阅读、携带。 7.裸书脊装帧,复古典雅、质朴自然,便于翻越,轻灵便捷。 8.精美套装,用心设计,精细印制,可以传世的高品质“父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