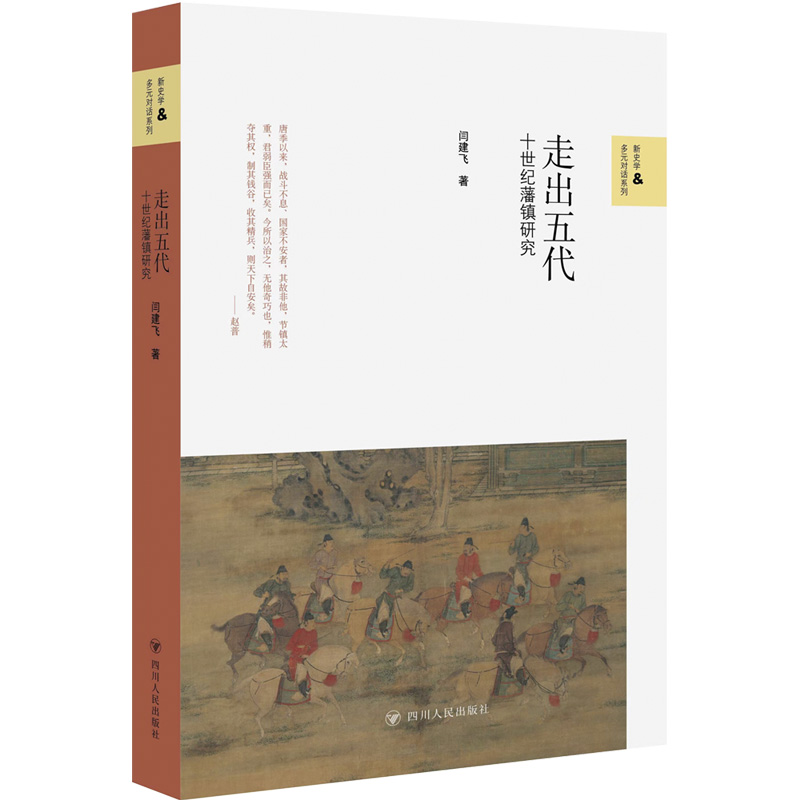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85.00
折扣价: 50.20
折扣购买: 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新史学与多元对话系列
ISBN: 9787220128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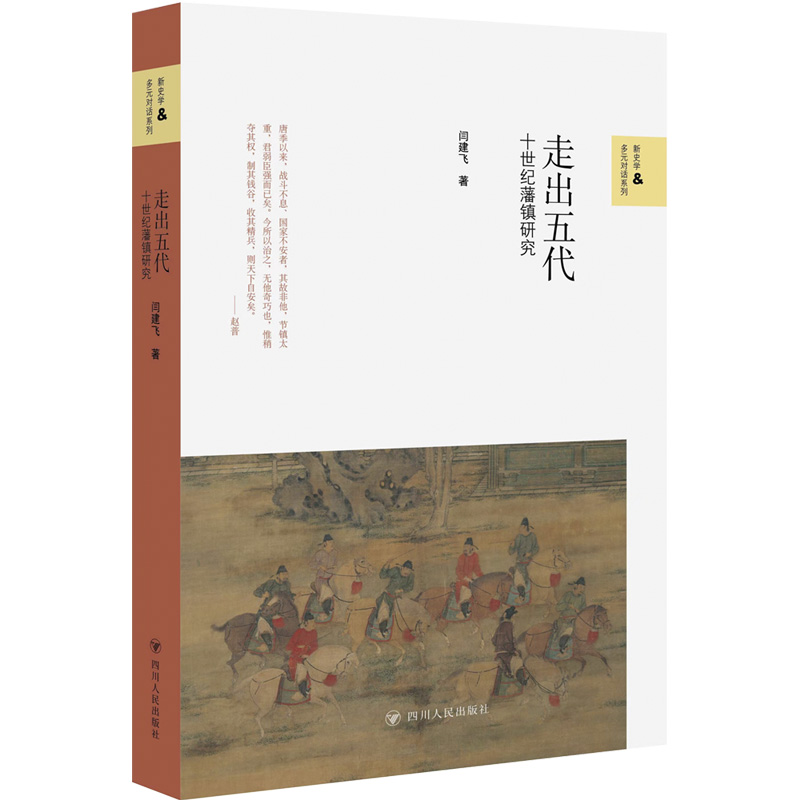
闫建飞,山东东明人,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出版古籍整理《愧郯录》《宋代官箴书五种》,在《世界宗教研究》《文史》《文史哲》《中华文史论丛》《中山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绪 论 一、问题缘起 建隆元年(960)正月,宋代周而立。在后世看来,这是一个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开创“太平盛世”的历史节点,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群心未尽归附,诸侯坐看兴亡”[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一〇《乞驾幸表》,《四部丛刊》景旧抄本,第11a页。],是更真实的历史图景。对当时的统治集团来说,“走出五代”、避免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是最迫切的历史任务,也是宋初政治体制调整的核心关切。 要想了解宋初如何“走出五代”,必须先“走进五代”,了解五代问题之所在。聂崇岐将五代政治大患归结为二:腹心之患的禁军和肢体之患的藩镇[ 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原刊《燕京学报》第34期,1948年,收入氏著《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6页。]。不过,相比于宋初禁军问题的快速缓和,持续两百余年的藩镇问题给宋廷带来的压力更为持久,牵动面也更广。于鹤年甚至将中唐至宋初称为“一整个的藩镇时代”。他认为这一时期: 可称道的固然不仅有藩镇一件事,然而他总不失为最重要者,因为政治的变革,宫庭的风潮,民族的兴衰,文化的递嬗,差不多都和他有关系。若以藩镇为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心,是最适当不过的。[ 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3月8日。] 因此,讨论宋初“走出五代”的历史过程,以藩镇为核心议题是十分合适的。 藩镇,或称“方镇”,在唐后期五代既可特指节度使,也可泛指包括州刺史在内的所有地方实权派,亦常指直属中央的节度使、观察使等连帅和直属州[ 罗凯:《何为方镇:方镇的特指、泛指与常指》,《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第159~169页。]。本书主要指当时以节度、观察使为长官的集军政、民政、财政权力于一体的高层政区[ 按照与县的统辖关系,中国古代地方政区可分为县级政区、统县政区和高层政区三层。参看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0~82页。]。其中节度使为军事使职,观察使为民政使职,藩镇统辖支郡的权力源于观察使,故节度使必兼观察使。唐后期的藩镇问题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很快攻占河北和洛阳、长安。为平定叛乱,玄宗幸蜀途中,于普安郡(剑州)发布诏书,将边地的节度使制度引入内地,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被平定后,藩镇又成为唐廷心腹之患,尤以代、德、宪三朝与大河南北的藩镇冲突最为剧烈。在应对藩镇挑战过程中,唐廷采取了许多措施,建中元年(780)的两税法、元和四年(809)的两税三分改革和元和十四年增加刺史军权的改革,经常被视为唐廷制衡藩镇的重要措施。经过肃、代、德、宪四朝的努力,唐廷逐步化解了安史之乱及其伴随的危机。凭借着对藩镇的整合与改造,以及江淮财赋的支持,安史之乱后唐朝维持了比之前更长的时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03~204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乾符元年(874),黄巢起义爆发,唐廷遭遇一场更严重的危机。与安史之乱主要波及北方不同,黄巢起义扰动区域遍及南北,不仅基本摧毁了唐王朝,也是藩镇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前藩镇主要被视为地方高层政区,之后情况则大不相同。一方面,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方镇为国”[ “方镇为国”的类似说法,最早见于欧阳修:“梁以宣武军建国。”《新五代史》卷二七《康义诚传赞》,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修订版,第338页。又见吕祖谦:“朱全忠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九《门人所记杂说一》,黄灵庚等编:《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册,第239页。]是他们共同的建国道路,由此藩镇体制深深嵌入诸政权乃至宋初的政治体制之中;幕府僚佐也往往凭藉潜邸关系,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构成诸政权的核心决策层,与相对稳定的文官群体共同维系着五代政治的日常运转。另一方面,五代十国政权建立后,凭藉建国过程中形成的中央军事优势,沿着唐后期削藩的道路继续前进,使藩镇从统辖区域、行政层级、官员设置、权力结构等方面逐渐趋同于州郡,是为“藩镇州郡化”。可见,黄巢起义后是藩镇体制向上影响中央朝廷、向下改造州郡体制,从更深更广层面影响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历史阶段。 十世纪藩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央层面的“方镇为国”,即五代十国诸政权是如何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在这一过程中,诸政权尤其是朱温、李存勖建国过程中如何控制辖下众多藩镇,建国之后藩镇体制对中央政治体制的影响、幕府僚佐化身朝廷重臣对朝廷人事体系的冲击等,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二是作为高层政区藩镇本身的变化。十世纪地方行政层级调整的趋势,是从唐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向宋初路、州、县三级制转变[ 宋代监司一般被认为处于监察区向行政区的过渡阶段。为便于与其他时段比较,本书暂且视之为行政区。],这一过程包括道级方镇的消失和路级监司的兴起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宋代监司兴起后,从表面上看地方行政回归三级制,但宋代高层政区本身、高层政区与统县政区的关系,与唐后期相比都发生了质变。三是统县政区州郡的权力结构变化。州郡权力结构调整是十世纪地方行政最关键的变化,也是藩镇州郡化的核心内容。藩镇州郡化并非是向唐前期州、县二级制下的州郡复归,而是向不断调整内部权力结构、确立起分权体制的宋代州郡迈进,最终在刬平藩镇、调整州郡权力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 不过,讨论十世纪藩镇,仅仅局限于制度的渊源流变是不够的,亦要关注与之相关的政治人群活动,他们是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其中,节帅作为藩镇长官,地方士人作为幕府文职僚佐,是研究藩镇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群。他们的政治参与既关系到本镇治理、朝藩关系,也对其政治命运有决定性影响。对节帅而言,积极参与还是抗拒藩镇州郡化进程;对地方士人而言,入仕还是归隐,盘桓幕府还是任职中央州县,入幕之后是自结府主还是主动向中央靠拢:既是个人选择,也受制于时势。通过观察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应对策略,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变迁和制度转换对政治人群的切身影响,也可以从纵深层面理解藩镇体制带给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深刻烙印,是藩镇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的研究时段为十世纪,起于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元年(874),这主要源于该事件对唐末五代历史和藩镇的巨大影响;终于宋太宗去世的至道三年(997)。需要指出的是,就藩镇问题而言,宋初的标志性事件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下诏废藩镇支郡,但废支郡后,州郡权力结构调整和藩镇州郡化进程尚未完成,直到宋太宗去世后,知州制取代刺史制,这一进程方告结束。 本书的研究区域为北方,这是由“走出五代”的主题决定的。北宋的政权基盘来自五代,宋初政策调整的重点也在“旧疆”而非“新土”,选择北方作为研究区域,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南方相比,十世纪北方的政治变动更剧烈,面临的情势更复杂,藩镇体制的影响更深,藩镇州郡化推进的难度更大,将研究区域放在北方,更有利于展现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政治势力的博弈过程。所谓北方,即五代封疆的大致范围,可分为河南、河北、河东、关中、淮南五个区域。河南地区指五代政权统治的黄河以南、潼关以东地区,相当于唐贞观河南道以及开元山南东道、淮南道部分地区。河东、河北地区即唐开元河东、河北道在五代封疆之内的部分,考虑到唐末特殊的政治军事格局,河东地区还包括属于关内道的振武、天德两镇,不包括黄河以南的虢州。关中地区即潼关以西的五代封疆。淮南地区即后周世宗所取淮南十四州。 从长时段来看,十世纪的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都在唐后期藩镇问题的延长线上,五代宋初政权同样要回应如何解决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问题。方镇为国重建了中央集权和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是五代王朝顺利推行藩镇州郡化措施的基础;藩镇州郡化则使藩镇实力不断被削弱,藩镇问题逐渐成为肢体之患:二者共同助推着藩镇问题的解决。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唐后期中央集权的衰落,朝廷无力消灭所有叛藩,其藩镇政策追求的目标并非瓦解藩镇,而是藩镇承认唐廷统治前提下朝藩关系的相对稳定。五代宋初则不然,随着朝廷的强势,其藩镇政策目标逐步转变为彻底废除藩镇体制,持续两百余年的藩镇问题也最终得到解决。藩镇问题解决后,藩镇州郡化的诸多措施和精神原则仍得以延续,持续影响着宋代乃至后世的地方行政体制。 二、研究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十世纪藩镇的研究已有比较深的积累。以下将分藩镇、政治人群两个方面,对与本书主旨相关者做一简要归纳。 藩镇问题一直是唐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学界已有不少总结[ 如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8、61~62、101~103、136页;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戦後の唐代藩鎮研究》,收入堀敏一撰:《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225~253页等。],对其研究模式也有反思[ 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55~65页;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7~349页。]。日本学者高濑奈津子将藩镇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二是藩镇辟召制和幕职官研究[ 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戦後の唐代藩鎮研究》,《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第225~253页。]。二者之中,藩镇的权力构造更能揭示藩镇问题的核心,辟召制和幕职官事实上也属于藩镇权力构造的一部分。高濑奈津子将藩镇的权力构造进一步划分为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朝藩关系)、藩镇的军事构造两部分。前者属于藩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后者属于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受此启发,本书按照内外之别,将藩镇研究分为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两部分,军事构造、辟召制、幕职官均可纳入后者范畴[ 这一调整参考了李碧妍的分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6页。]。 朝藩关系历来是藩镇研究的重点,成果丰硕,其中从朝廷削藩角度论述者最多。学者们或着眼于五代宋初朝廷的整体削藩措置[ 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宋史丛考》,第263~282页;李昌宪:《五代削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02~110页;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河北学刊》1993年第4期,第75~81页;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233页等。其中陈长征举证最为全面。],或聚焦于某一具体政策如监军制度等[ 友永植:《宋都監探原考(一)—唐代の行営都監—》,《别府大学纪要》第37辑,1996年,第28~39页;《宋都監探原考(二)—五代の行営都監—》,《別府大学アジア歴史文化研究所報》第14号,1997年,第1~16页;《宋都監探原考(三)—五代の州県都監—》,《史学论丛》第34号,2004年,第15~25页。张萌:《五代十国监军考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总的来看,五代宋初的削藩研究中,学者多采取列举式论证,且重复研究较多,对朝藩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不同区域的差异缺乏应有的关注。五代与宋初的研究壁垒也未完全打破。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多次强调唐末五代宋初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单元[ 邓广铭和李锦绣从宋代官僚制形成的角度,强调宋初与唐五代的连续性。邓广铭:《对申采湜教授论文的评议》,东洋史学会编:《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李锦绣:《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段的变革》,收入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邓小南认为:“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类似,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北宋的政治局面,正是从‘五代’走出来的。”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8页。],讨论宋初藩镇也应从唐末五代谈起,只是相关研究较少往前追溯,不少议题尚有推进的余地。 朝藩关系并非仅仅包含二者的对立面(削藩和叛乱),藩镇体制对中央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也是重要方面。藩镇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对藩镇体制的消化吸收。正如邓小南所言:“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逐步理顺,并不完全是由于五代的统治者成功地压制了强藩、彻底地摒弃了藩镇制度,而恰是因为他们消化吸纳了发展至此时的地方制度中的许多创获,从而生发出富于活力而应变有效的新机制。”[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205页。]这方面研究是五代宋初朝藩关系的重要内容。周藤吉之、王赓武、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政权与藩镇体制的继承关系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體制——特に宋代職役との關聯に於いて——》,《史学杂志》第61卷第4、6期,1952年,收入氏著《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第573~654页。Wang Gungwu(王赓武),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中译本见胡耀飞、尹承译:《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日野开三郎:《五代史の基調》,《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2卷,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第296~304页。],其中禁军与藩镇军制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 堀敏一:《五代宋初における禁軍の發展》,《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册,1953年,第83~151页。菊池英夫:《五代禁軍に於ける侍衛親軍司の成立》,《史渊》第70辑,1956年,第51~77页;《五代後周に於ける禁軍改革の背景——世宗軍制改革前史——》,《东方学》第16辑,1958年,第58~66页;《後周世宗の軍制改革と宋初三衙の成立》,《东洋史学》第22辑,1960年,第39~57页。富田孔明:《五代の禁軍構成に關する一考察——李克用軍団の變遷について——》,《东洋史苑》第26·27号,1986年,第83~115页;《五代侍衛親軍考——その始源を求めて——》,《东洋史苑》第29号,1987年,第1~32页;《後梁侍衛親軍考——その構成に関する諸説の矛盾を解いて》,《竜谷史壇》第92号,1988年,第32~49页。齐勇锋:《五代禁军初探》,《唐史论丛》第3辑,1987年,第157~230页。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赵雨乐:《唐末北衙禁军的权力基础——神策五十四都的活动试析》,收入《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1997年,第523~538页。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505页。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86页。]。 相对于唐后期藩镇内部军事结构、辟召制、幕职官研究的丰厚成果,十世纪藩镇的相关研究相对单薄。对藩镇牙军的研究,多集中在后梁、后唐和其他政权建国前的牙军部队,其实是禁军前史的一部分[ 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牙軍に關する一考察——部曲との關聯におい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册,1951年,第3~72页。来可泓:《五代十国牙兵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995年第11期,第64~70页。]。幕职官方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的形成过程[ 片山正毅:《宋代幕職官の成立について》,《东洋史学》第27辑,1964年,第58~74页。郑庆寰:《体制内外:宋代幕职官形成述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总的来说,十世纪藩镇研究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唐后期相提并论,二者关注的问题亦各有偏重。唐后期藩镇研究中学者们讨论的很多重要问题,在十世纪藩镇研究中则隐而不彰。如“胡化说”,自陈寅恪以来就是分析安史之乱、唐后期藩镇问题的重要视角[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9~235页。仇鹿鸣对“胡化说”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可以从是否维持部落形态、胡人对自身种族和文化的自我界定两个方面,将“胡化说”这一描述性概念化约为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第306~320页。],但在十世纪藩镇研究中,除了对入主中原的沙陀和西夏前身的党项关注较多外[ 相关研究甚多,无法枚举,仅举其要。沙陀研究如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森部丰:《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傅乐成:《沙陀之汉化》,原载《华冈学报》第2期,1965年,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319~338页;王义康:《沙陀汉化问题再评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132~137页;李丹婕:《沙陀部族特性与后唐的建立》,《文史》2005年第4期,第229~244页等。党项研究如冈崎精郎:《タング一卜古代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其他部族如突厥、粟特、回鹘等已较少进入藩镇研究者视野。这固然与学者关注重点的转移有关,但也反映出十世纪民族融合进入新阶段,“胡/汉”语境的消解[ 邓小南:《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收入氏著《朗润学史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4~94页。]。在十世纪藩镇研究中,既要关注这一时期藩镇发展的新特点,也要注意到相比唐后期藩镇“无”的层面,才能更好地把握藩镇问题的脉络和走向。 在中国传统官僚群体分类中,文武是最常见的分类方法。唐末五代宋初的文武群体有不少研究,关注的问题包括文武群体的构成和文武关系两个方面。就前者来说,学者们讨论了五代宋初来自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的文武官员数量、出身之不同及变化。同时学者们注意到,五代政权频繁更迭之下,文武官员历仕多朝的比例很高,文臣群体的相对稳定支撑起五代政权的延续[ Wolfram Eberhard(艾伯华),“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ading political group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Asiatische Studientudes Asiatiques,vol.1-2,1947,pp.19-28.西川正夫:《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官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7册,1962年,第211~261页。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原载《史语所集刊》第51本第2分,1980年,收入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18~474页。堀敏一:《朱全忠政権の性格》,《骏台史学》第11号,1961年,第38~61页。佐竹靖彦:《朱溫集團の特性と後梁王朝の形成》,收入《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第481~530页。]。时代乱离和“武夫当政”之下,士人在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抉择及出仕观念,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 赵效宣:《五代兵灾中士人之逃亡与隐居》,《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5期,1963年,第291~330页;罗宗涛:《唐末诗人对唐亡的反应试探》,收入《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381~405页;李定广:《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55页;铃木隆行:《五代の文官人事政策に関する一考察》,《北大史学》(札幌)第24卷,1984年,第25~38页;金宗燮:《五代政局变化与文人出仕观》,《唐研究》第9卷,2003年,第491~507页。]。就文武关系而言,最容易注意到的是五代宋初文武隔绝、对立,乃至敌视的现象。不过学者们的研究指出,五代激荡的时代环境,促使文武群体之间接触、沟通增多,双方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和改变[ 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1~110页;闫建飞:《评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中外论坛》2019年第1期,第159~172页;西川正夫:《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と武臣》,福岛正夫编:《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第1卷《前 近代アジアの法と社会》,东京:劲草书房,1967年,第289~314页;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原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朗润学史丛稿》,第36~73页。]。正如邓小南所提示和示范的,对文武群体和文武关系的讨论,一方面要注意到文武群体内部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的差异,另一方面要将文武关系嵌入当时的政权内部权力结构,才能更好地把握文武关系变动的实质[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朗润学史丛稿》,第36~73页。]。 三、本书结构 十世纪藩镇的变化包括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两个方面,前者为朝廷层面,后者包括高层政区和州郡层面,加上相关政治人群活动,本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方镇为国的角度讨论五代北宋王朝的建国道路。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后梁、后唐是方镇为国的典型案例。方镇为国过程中,朱温、李存勖如何在唐朝藩镇体制下,控制辖下藩镇,并从中发展出集权体制,建立新朝,是本章的核心关注。后晋、后汉的建立与契丹经略中原密不可分,后周、北宋的建立则是禁军崛起的结果。从表面来看,后晋以降诸政权的建国道路与后梁、后唐差异明显,并不属于方镇为国。但后晋、后汉均由河东藩镇发展而来,禁军崛起是藩镇军队禁军化的结果,诸政权的政治、军事、财政、人事等同样受到方镇为国的深刻影响,仍然在方镇为国的延长线上。 第二章以朝廷、藩镇、州三者的关系为核心,讨论地方行政层级的调整。唐后期地方行政是道、州、县三级制,藩镇州郡化表现在行政层级上,主要指削除藩镇一级。从这个角度来说,支郡专达、裂地分镇、直属州是藩镇州郡化的重措施。本章主要追踪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差异,展现藩镇层级消亡的历史过程,同时比较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与北宋路、州、县三级制下,高层政区及其与统县政区关系的差别。藩镇瓦解后,原来的节度使、刺史等阶衔继续存在,形成宋代的正任、遥郡序列。本章重点将讨论遥郡序列的形成过程。 第三章从分权的角度探讨州郡权力结构的调整,这是藩镇州郡化的核心内容。随着藩镇州郡化,州郡权力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五代宋初的朝廷通过削藩,使藩镇逐渐趋同于州郡,但州郡本身的权力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从唐后期由刺史掌握军政、民政权力的集权体制,逐渐过渡到宋初以知州掌民政,通判为其贰,兵马都监掌军事,监当官管榷税的分权体制。这一转变过程,本章将从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宋初“制其钱谷”的背景及措施、兵马都监演进与地方武力整合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四章希望以节帅和地方士人为核心,讨论藩镇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群活动,动态观察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对地方政治人群的影响。节帅选择张全义洛阳经营为个案。张全义活跃于唐末五代前期,是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治下的洛阳多次经历京城与藩镇治州的转变。从洛阳经营个案中,我们既能观察到京藩交错给都城建设的影响,也注意到京藩二重底色对张全义个人的仕宦与婚姻网络、社会关系等的影响。地方士人活动则以柳开家族为线索进行观察。柳开家族主要活跃于五代后期宋初,属于中下层士人,是藩镇州郡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柳氏家族成员在任职藩镇幕府还是朝廷州县之间的变化,仕宦区域的变动,对科举入仕的态度,都与藩镇州郡化进程密切相关。 十世纪藩镇的变化对宋代地方行政制度有何影响?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演进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是本书最后想回答的问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征引文献,仅在首次注明全部信息,再次征引则省略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地点等。征引文献均见于最后的引用书目,以备查考。在使用直接引文时,凡更正原文错误者,以“(误)〔正〕”的形式;补充解释者,加();引文中原有注释,以(原注:)的形式。 1.本书是探讨宋初政治关键问题的前沿著作; 2.本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新前沿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