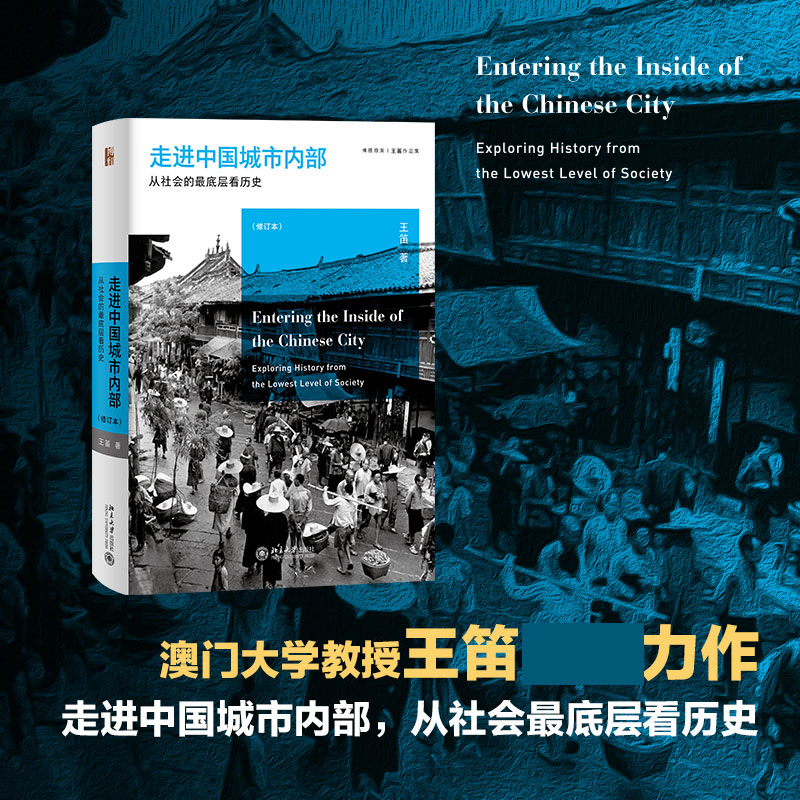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57.00
折扣价: 39.90
折扣购买: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
ISBN: 9787301315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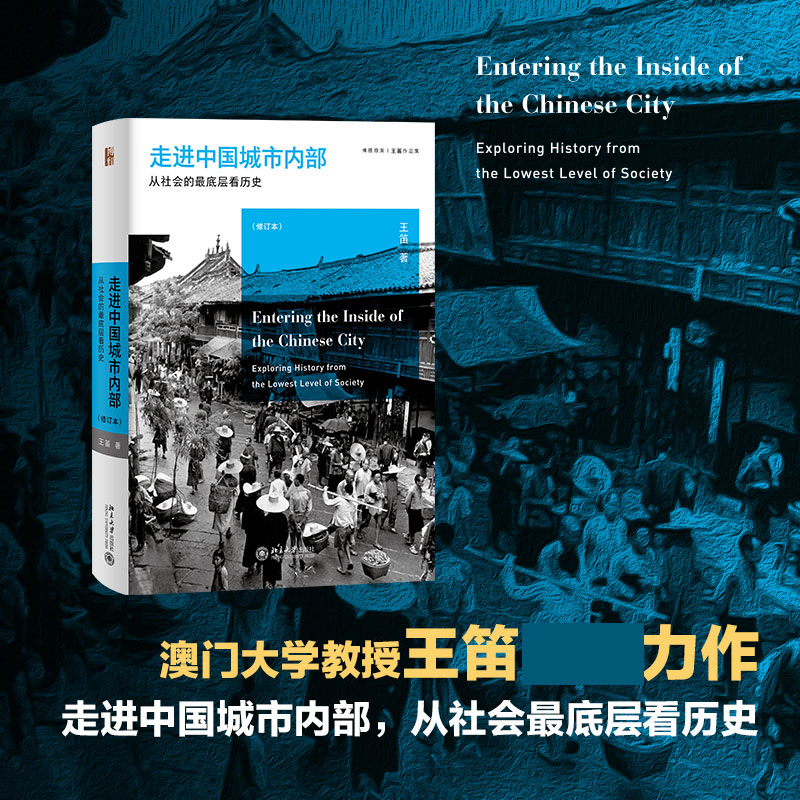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相关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
从文学看历史 这些年来,随着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日益发展,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对历史的研究有所影响,而且历史学家开始感到了一种危机感,担心历史这块蛋糕不断地被切去,可能最后就所剩无几了。人们开始怀疑,还有真正的历史学吗? 还是历史学已经被转化成了文学、 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其他什么学科的附属物? 但我对此并不担忧。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其他学科介入到历史学之后,不但没有阻碍历史学的发展,反而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实际上我们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当一个课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感到好像没办法继续深入下去。比如说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的主要焦点是放在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外交、战争、政治运动、思想、精英人物等,我们觉得好像这些课题已经走到尽头了。但当 其他的学科介入到历史学以后,我们感觉到好像无路可走的课题,就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一样,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甚至用不同的学术语言进行研究。过去我们都是用历史的语言,当新的学科介绍进来以后,不管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其他学科,我们感到认识同样一个主体、同 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人物,可以看到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他学科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对于其他学科及其方法,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这里我将着重谈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而且主要讨论如何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问题。 在过去二十年间,西方对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城市文化、下层人民等的研究日渐发展,这个倾向在西方便促成了新文化史。受西方的影响,大众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也开始影响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重视对文学资料的使用。如J·贝林(JudithBerling)的《宗教和大 众文化———<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中的道德资本控制》便使用小说作为分析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和文化的主要资料。《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是写于17世纪的社会小说,其中心是描写人性和礼仪、利益和欲望,显示了儒、佛、道的宣释者所规定的人际关系。这个小说反映了书中主角所经城镇的社会生活,包括客栈、茶馆和妓院等,还描述了各阶层的人,如盐商、小贩、铁匠、店老板、珠宝商、棺材匠、招牌匠和屠夫等三教九流。因此,通过对这个小说的分析,我们得到了在其他资料中所阙如的宗教与大众文化关系的信息。其实,从16、17世纪以来这种道德说教的书就相当普遍了,都反映了当时意识、宗教、文化和社会的状况,提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丰富资料。 在姜士彬关于地方戏的一组文章中,他使用戏曲资料把视角深入到戏曲本身的内容来观察地方戏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价值。例如他关于目连戏的研究,便涉及了对目连戏内容和表演形式的分析。他所使用的基本资料都是目连戏的剧本,如《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目连传》《目连 僧报恩经》,以及文学戏曲界学者关于目连救母故事演变的研究,如周作人的《谈目连戏》等。借助这些研究,其染指于过去文学史和戏曲史的领地,同时,延伸了历史学家的触角。目连救母是过去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更是戏剧中的一个经常的主题。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这出戏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注入了中国传统宗教和伦理说教的内容,因而对一般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因此,把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对象,触及了传统史学中所难以窥见的普通人与地方文化的纽带及其连接方式。 不过,用文学资料研究历史必须抱十分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到作者的写作并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大量“臆造”的东西。因此,当我们没有其他有力的资料作旁证时,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充分警觉自己使用的语言。如我们采用文学作品来分析晚清的大众文化时,必须分清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晚清的大众文化,还是作者笔下所“反映”的晚清的大众文化。 我在研究成都的时候,使用的文学资料首先是竹枝词。与其他诗词不同的是,竹枝词一般并不表现作者的想象、感情或人生哲学,而是客观地描述人或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精英对一般民众的态度。有关成都的竹枝词非常多,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但是,过去研究历史的人对利用诗词作为资料来写历史,是非常谨慎的。我们知道,一个诗人或一个作家,他写一首诗,填一首词,写一部小说,都是文学作品,历史研究者通常认为这不是可信的,因为文学作品只表现了作者的情感,是他头脑中的再创造,而非历史本身的真实记录。大概五六年前,我用英语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完全使用竹枝词来写19世纪的成都城市生活。在这里我列举几首在那篇论文中所引用过的竹枝词。 第一首:“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这首竹枝词描述了成都作为一个都市的热闹景象,还告诉我们在这个城市中,居住了有二十万家。其实在19世纪时,成都没有二十万户,大概成都全部居民有二三十万人。所以我们使用这个资料的时候应该非常仔细,不能说通过这首竹枝词就证明当时成都住了有二十万户。按照历史学家的一般算法,平均每户有四个到五个人,二十万户算起来的话成都就可能有一百万人。这里如果把“家”当作“人”理解,就和事实差不太远了。如果要知道成都的人口数字,还要和其他资料仔细地排比分析。但是第三句是正确的,19世纪成都大概有四百多条街道。最后一句“吹弹夜夜乱如麻”,则真正再现了成都丰富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地方戏和曲艺的演出。中国诗词基本上是一种情感或抽象的描述,但竹枝词的写作与其他诗词形式不一样,一般是作者对对象的真实描述,例如一个文人在街头上看到街头的面貌,他就如实地记录下来,大多是对现实的描述。所以我们可以用作历史资料。但在怎样使用竹枝词的问题上,还必须考证作者的背景,他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样的竹枝词。 第二首:“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幡。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这写的是站在成都中心的鼓楼上,往西望可以看到满城,往南望可以看到皇城,往东看起来人烟非常稠密,所谓“鼓楼北望好营盘”,因为北有北校场,是当时的清兵练兵的地方。 第三首:“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写的是文庙后街茶馆的环境和生意,描述了晚上是生意最好的时候,而且是灯光明亮,十分喧闹,这提供了另外一种场景。在这三首竹枝词中,第一首是讲了成都的总体情况,第二首是讲站到这 个鼓楼上看成都,第三首是讲一条街,具体到街头的茶馆。可以说是像电影镜头一样,由远逐步拉近。 第四首:“福德祠前影戏开,满街鞭pao响如雷。笑他会首醺醺醉,土偶何曾喝一杯?”这是描述在清明节前后成都的传统庆祝活动,当时成都每个街区或若干街区都成立有所谓的清明会(又叫土地会),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举行庆祝活动,每家每户凑钱雇戏班或曲艺班演出,并以街区为单位办宴会。这个以邻里为基础的活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居民间的密切关系。清明会有会首,并不由官方任命,而是邻里自己推选出来的。这首词中的会首在宴会上喝得醉醺醺的,而最后一句“土偶何曾喝一杯”,则是指的那些土地神像,其实人们拜土地神,也是为了他 们自己的娱乐。 清明会组织这个活动并非是简单的庆祝或聚会,而是有非常重要实际功效的。成都过去清明前后要清掏阴沟,把街边的盖阴沟的石板掀开,把污泥掏出来堆在路边,然后农民运出城作肥料。掏阴沟必须每年进行,因为成都地势低洼,到了雨季非常容易积水,必须通过阴沟及时排出去。但是过去这项事务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办理,而是由市民自己组织的清明会或土地会来负责的。每年清明聚餐结束后,各家各户就参与清掏阴沟。 这个例子实际上证明了我在《街头文化》一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传统中国,中国城市的管理并不是由地方政府来负责的,而是由市民自己来组织的。成都在20世纪初大概有三十几万到四十万人,由成都县和华阳县两个县合管,这两个县的全部人口加到一起大概有七八十万,可能甚至还要更多。但是成都县和华阳县的县府都非常小,县衙门的各种官员和衙役加到一起,也就差不多三四百人,因此成都和华阳两县总共加起来也就七八百人,但他们要管理七八十万人的事务。 政府非常之小,没有力量来控制地方,也不可能把他们的权力深入到社会底层。那么地方社区靠谁来组织? 就靠市民自己。 此外我在研究中甚至使用民间故事。虽然民间故事并非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但它们的确揭示了一种文化、思想观念或现象。正如M.德塞托(MicheldeCerteau)所指出的: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民间故事可视为一种口述史,生动地展现了过去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先后有上千当地学者参加一个巨大的采风活动,后精选为《成都民间文学集成》。这个集子不仅提供了有关成都历史和文化的故事,而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是怎样把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的。这可以说是我们了解民众文化、思想和生活的一部“宝典”。 王笛教授在微观史、新文化史领域卓有建树。所著《茶馆》《袍哥》《街头文化》等在学术界和大众中都产生了强烈反响。本书并非关于某一个问题的个案研究,而是以往研究的理论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