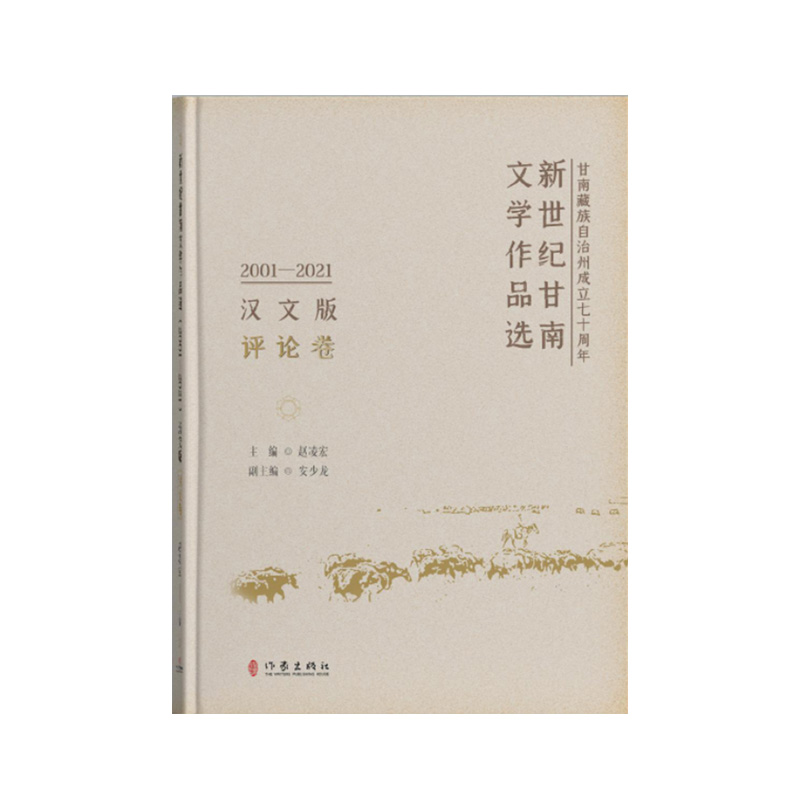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138.00
折扣价: 89.70
折扣购买: 新世纪甘南文学作品选(2001—2021)评论卷
ISBN: 9787521222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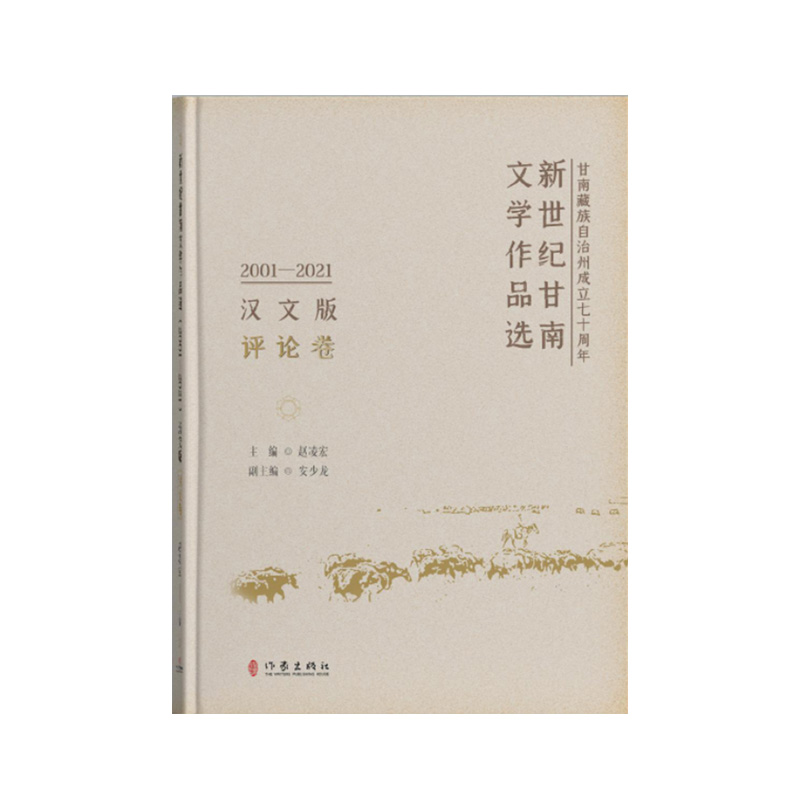
主编:赵凌宏,笔名牧风,藏族,中共党员,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已在《诗刊》《十月》《民族文学》《青年文学》《星星》《诗歌月刊》《诗潮》《中国诗歌》《中国诗人》《飞天》《延河》《西部》《山东文学》《北方文学》《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新诗近五十多万字。作品入选《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中国散文诗百年经典》《中国当代百家散文诗精选》《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散文诗精选》《中外散文诗60家》《岭南百年散文诗选》《中国新诗百年精选》《中国百年诗人新诗精选》《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名录》等多种新诗、散文诗权威年选。著有散文诗集《记忆深处的甘南》《六个人的青藏》《青藏旧时光》,诗集《竖起时光的耳朵》。曾获甘肃省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首届玉龙艺术奖、“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金奖。鲁迅文学院第22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创研培训班学员。被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评为2021年度中国十佳散文诗人。参编甘南州建州60周年历史文化丛书、甘南州九色历史文化丛书,主编《当代甘南散文精选》《当代甘南诗歌精选》《六个人的青藏——甘南诗人散文诗精选》等书籍。现供职于甘南州文联,任甘南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副主编:安少龙,男,汉族,中共党员,1967年10月出生,甘肃和政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散见于《诗刊》《民族文学》《文艺报》《中国艺术报》《飞天》《阿来研究》等报刊,著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域文本实践:新世纪甘南作家多元创作论》(民族出版社2020年版)、《甘南乡土文学导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曾获第二、第三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第五届格桑花文学奖。现任教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
甘南草原上的一束繁花 ——《六个人的青藏》序 耿林莽 甘肃是一个诗歌大省,而甘南藏区,居住着一个年青诗人的群落,这或许与这片美丽安静的草原环境有关。我早有一种感觉,放佛在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商品化的现代社会,愈是距离喧嚣的“经济社会”遥远的地方,诗歌的花朵愈加繁茂地盛开。这中间或有着某种发人深思的奥秘在吧,且不去深究,将目光移向这本诗集上来。 甘南青年诗人王小忠将一本题为《六个人的青藏》的散文诗合集的书稿寄来,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为序,这六位诗人是:牧风、扎西才让、王小忠、瘦水、花盛和陈拓,除陈拓略为年长外,全是年青人,且都是久居草原的藏族人,他们的诗风各有个性,而民族的、地域的共性更为鲜明,读过后有一种新鲜、质朴而清凉的草原露珠和晶莹澄净感,使人的心灵受到洗涤和浸润。尤为感到喜悦和兴奋的是,他们掌控、运用、驱驰汉语文学语言的能力和水平,达到异常成熟的高度,充分显示了汉藏文化水乳交融的和谐结合,令人感佩和惊羡。从这一意义来说,这本散文诗合集的出现,不仅是当代散文诗值得欣喜的收获,也是可以引起整个诗坛瞩目的一朵新花。 你:赤身裸体的甘南,贫穷的甘南。 我爱你这如饥似渴的甘南。 我爱你高悬的乳房:日和月, 神秘而温热的子宫里栖息的甘南。 我爱你金翅的太阳,蓝眼的月亮; 我爱你高处的血性河流,信仰你远方的白银雪山。 这是扎西才让《献词》中的片段,“赤身裸体”和“如饥似渴”是“贫穷”的形象,而“血性河流”与“白银雪山”则显示了一种刚毅与凛冽的气质,应该说,这是捕捉到了青藏地区自然风物之魂、之神的诗性表达。在《哑冬》中,他写道: 我们坐在牛车上,要经过桑多河。 赶车的老人,他浑浊之眼里暗藏着风雪。 将人与大自然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就尤感深沉。瘦水在《沱沱河源头》中写道: 在你的经卷上做一块石头。 在你的格桑上放一片经幡。 在你的寒冷中凝固成雪峰。 落下来啊,我的青藏,我就是那个双眼失明、被你的光芒击倒的人。 这样一种对于青藏高原土地和山川的感情,不是长久生于斯,在心灵中渗透了刻骨铭心的情感的人,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牧风的《高原窗外的小鸟》则展现了甘南草原轻盈明亮的色调: 分明是鸟儿在窗外唤醒睡眠。 我在清晨推开高原羚城的小窗,推开一个鸟的世界。 青藏腹地五月的天气,微寒中裸露着清新。 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就在窗外释放着浑身的解数,把玩着悦耳的晨曲。 它们是快活而自由的,小小翅羽煽动着草原夏日的诗情。 牧风对草原夏日描述是细腻的,准确的,抒情的,他以有限的文字,充分表达了对高原生活的热爱。他说:“鸟儿是幸福的,特别是草原上的小鸟。”实际上也写出了高原人阳光而幸福的情怀。 王小忠的《碎句》里也有着类似的情怀: 我喜欢露珠,喜欢它的干净。 喜欢它在阳光下进入大地深处时的笑语。 在《叶子》里,这种情感抒发得更感人: 甘南的叶子是记忆中翻飞的蝴蝶。 一只,三只,五只……其中一只在飘泊。 我潸然,我就是那飘泊的一只。 这一构思是独特的,“我就是那飘泊的一只”,人就是叶子,叶子就是人,物我一体了。 到花盛的诗里,这种情感化为了一朵花,而其背景则是草原多雪的冬天。花盛喜欢写雪,他写道: 但雪是真实的,就在眼前飘动,就落在你的身上和手心里。 那种瞬间的融化是迷乱的,迅速的,也是疼痛的,无助的。 雪,成为北方,成为青藏,成为甘南草原冬天的一种人格化的意象,在此背景下,花盛推出了他的“逆风飞翔的雄鹰”,这一意象是坚强的,也是忧伤的: 像一朵忧伤的花,绽放在草原之上,绽放在我的内心深处。 图腾着生命的另一种姿态。 我以为,这是一个卓越的草原精神的象征,它的涵盖空间,它的思想深度,是不寻常的。它写出了青藏高原生活着的人们的那种高远的诗性情怀。 陈拓有一章《游牧》,很短,异常精炼地勾勒了草原游牧生涯的画图,意境深远,只需读这一小节便为其迷住了: 今夜还有雨一样的马蹄飘落吗? 饮马在河源,游牧在河源,求索在河源,流淌在血管里的马蹄声沸腾,只留下片片灰烬。 作为向读者稍尽介绍之责的序,写至此似可“交卷”了。还想说一点,这种取“精选”方式编出的合集,有一个优越性,便是可以去粗取精,不像有些厚厚一本的个人选集那样,往往鱼龙相杂,而是几乎篇篇都值得细读,这是这本合集的一个值得推崇的特色,也是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验。 原载《六个人的青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雷达(1943年—2018年),原名雷达学,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奖项。出版《民族灵魂的重铸》《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下卷)《蜕变与新潮》《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当前文学症候分析》《重新发现文学》等论文集15部;出版《雷达散文》《缩略时代》《皋兰夜语》等散文集多部。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曾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 白雪与草地的歌者 ——谈雷建政的小说 雷 达 一九八二年,来自“黄河第一曲”—甘南平原的一个驯悍的小伙子,即本书作者雷建政,以其处女作《天葬》获全国“五四青年文学奖”,到北京人大会堂领奖来了。由于我正好担任评委,更由于我也来自甘肃,我们在会场见面的一刹那格外激动。虽然那是仅有的一次全国性青年文学评奖,得奖者却尽是当时驰骋文坛的最活跃的青年作家;我的偏远的,曾是那么闭塞、落后、荒凉的故乡能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脱颖而出,怎不叫人由衷的兴奋。 然而,兴奋中其实掺杂着担忧: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饱满的,潜能雄厚的生命的创造序曲,还是作者生命中极偶然、极幸运的一次闪光?当时和以后,都有过一些得奖者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犹如倏忽而逝的流星,那么,体着奖状的雷建政回到草原深处以后,会怎么样呢?在那个不通火车,用快马传递邮件的藏汉杂居的边地,他能把刚刚开始的事业继续下去吗?在文坛上思潮奔涌,长风疾进的年代,他能冲破狭窄的视野,跟上文学发展的脚步吗?可能我怀有甘肃人常有的自卑,可能我深知从故乡走向全国有多少困难,我对雷建政的创作前景当时并不乐观。要知道,坚持下去意味着毅力、修养、积累、信息、磨练,甘于寂寞、不怕失败,不怕出丑等等方面考验,少了一样也不行呵。 事实证明雷建政具有相当的耐力,他艰难而又成功地跋涉了不短的路程,他沉寂过却没有沉没。现在,他连续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少作品被转载和评介,他的作品与一些更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排在一起并不逊色。如果有谁在甘南草原住过半年以上,他一定会感到,雷建政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多么不容易。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处女作《天葬》其实包孕并显露了他日后创作特色的一些萌孽。小说写一个瘸腿的、卑微而又倔强的藏族青年,因其残疾而饱受冷眼,一也因其残疾而孤独深思。他没有任何背景可依,便被打发到烈士陵园当守墓人。木来,这样的安排不过是给他一个饭碗,他静悄悄地活着也就够了,不料他却认真得出奇,对陵园里的不正之风直言批评,、惹得上司恼怒。他曾因眼见亲人天葬的惨象而发誓自己死后决不天葬,想不到他为了援救儿童不幸落崖牺牲,他自己葬在哪里的问题便提前到来了。小说写到,不管他的父亲如何力争,他的亡灵就是不被允许进人陵园。“在约定俗成的社会潜流里,他不过是一拉细沙,何况人已经死了。”小说于冷静的叔述中蕴藏着悲愤,表现出对平凡而微小的生命刊理解和吁请,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公平的杭争。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从艺术表现上看,区区六、七千宇.能把许多复杂情事解析清楚,每个收落都有蕴含可嚼。比喻生动,对话有味,有种藏汉杂居地区特有的风致,显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剪裁、概括的本领。 我们无法揣测《天葬》之后雷建政经历了怎样的摸索,只知道有很长时间,他的作品的确看不到了。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在更边远的《西藏文艺》上,发现他有个短篇《花纹》发表出来。《花纹》以西藏之途,引起内地评论者的争鸣,并被一些刊物转载,收入争鸣作品选之类的书里,倒也出人意表。原来,事情正如一位评论者指出的,《花纹》是描写藏族地区改革生活的第一篇小说,它与内地的《条件尚未成熟》一作几乎同时出现,且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比起《条件尚未成熟》里的那个妒火中烧的岳拓夫来,《花纹》的主角副县长德合拉其人,似乎更为复杂和不可捉摸。在生活急邃变动的时刻,他是推动者,还是拦路石?他在假公济私,是“假私济公”——不自觉地附会了进步力量,!领难判断。面临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趋势,德合拉隐秘感到自己位置的岌岌可危,他甚至敏感到县委干部下班时重重的关门声和从他身旁经过时无所顾忌的事情,是对他的存在的藐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也嫉妒,也暗中使绊子,也装演门面掩人耳目,但同时他又不是阴冷得不可收拾,他的动机也许出于私欲,但他毕竟比那个古板正直的华尔贡更出色地处理了棘手的鼻疸马问题,赢得了牧民的人心。于是,对德合拉的评价问题成为评论者争执的热点。我想,这正是那种真正发现于生活,而且带着生活自身复杂性、两难性的作品所固有的特征。《花纹》的引起争鸣表明,只要沉潜于生活之巾,触摸到生活中最敏感的部位,即使远在甘南草原,即使写被人忽略的一角,一也会无意中碰响时代的琴弦,与最普遍、最现实的问题沟通。 一九八七年至今,是雷建政创作上的丰产期,却又正值文坛上的寂寞期,新人们不复象前些年那样大受青睐,在一个早晨突然成名了,而是难得受到社会公众和评论界的的注目和奖掖了。雷建政却写得耐心,写得纷繁,悄然地,初步地建构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如果说,早在《天葬》和《花纹》中即可见出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某种交织、碰撞情状(如对“天葬”的看法和选拔干部的标准化),只是因为它们的社会政治主题较为突出而使文化因素不甚明显,那么,现在他是自觉地游曳于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他的创作视角从社会政治转向文化。对于这种转化的得失,目前尚难下个判断,但他确乎存在明显的转化,则是事实。从文化形态上看,他的作品划然为二,或写草地藏民的生存、信仰和心理,或写草地汉民的历史和现状;从题材上看,他是现实,历史,魔幻,佛陀全写,但也有藏、汉之分;从格调上看,一而是严格的写实,沉重、严酷,一面是空灵漂渺,宗教文化的影子依稀可辨。总之,他既有《往年雪》《西北黑人》《劫道》一类藏地汉人的严峻之章,也有《白草地、黑草地》《沉寂的雪水湖》一类对草泽藏民的生态时空的描写;还有《画佛》《天火》《放生》《白塔》式的“悟道”之作。事实上,这些时见旁逸斜出的作品之间并无多少耗悟,它们都与作者近年来热衷于写“草地文化”的追求联系。雷建政立足于他所在的甘南草原,在他看来,尽管汉、藏风俗殊异,但作为共同生活于这片草地的人们,又受到大于各个民族自身文化历史的草地文化的制约,具有某种同一性。比起他开始写作时注重社会急遐变动的因素,他现在似乎更注重地域、气候、人文环境,宗教、自然观等一些稳定的、长时期的因素,社会因素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加人这个文化圈。我并不完全赞成这样的追求,我也深知这种追求是作者受到近年文化意识增强的潮流所致,但作为某个创作阶段的倚重点,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要真正向大而深湛的境界发展,必须加浓社会历史内容的蕴含。目前对雷建政提出过高的要求,似乎为时尚早,何况,他现在还只是在短篇小说的园地里播种。 《西北黑人》《往年雪》等都写出了生存的严酷和严酷中的人性颤栗。在作者眼中,西北的气候和自然是严冷的,而生活的路程也同样严峻。两篇小说所截取的都是我们社会生活出现重大失误的特殊年月,前者写文革浩劫中城镇人被盲目驱赶下乡,所谓“不在城里吃闲饭”时的情景,后者写大跃进后的饥荒岁月,小说的人物便被置于饥饿、生死的严重威胁下,而作者也就在这样的境况里直面人性、道义、伦理、性爱的净扎。《西北黑人》里的三个“黑人”(无户口者),首先是面对饥饿,与之纠裹的还有性、生命延续,所以各个人物经受的煎熬就特别剧烈。小说使用冷色调,如干冷的清晨,落雪的黄昏式的油画,而人物的生命欲望与冰雪激荡,就造成强烈的效果。无疑,麻哥和尕五都很质朴,都抱着传统的道义,都很重然诺,唯其如此,才使小说的悲剧意味非常浓郁。《往年雪》让我们惊骇的是,饥饿和贫穷可以扭曲传统的伦理道德,或者说,同样是维持生命(生育与温饱),却可以相悖到何等程度。自然,作者对短暂的非人道、非人性的厉史插曲的批判,是为了呼唤更美好、更文明的生活。 《劫道》和《白草地、黑草地》可以看作是作者刻意探索“草地文化”的作品。一篇写草地上的汉族小工匠,一篇写一草地上藏族生态和心灵。《劫道》有股草地烟瘴般的的神秘感,对生存于这块土地上的、旧时代的人们的命运的飘忽不定,有独特的表现。一位鞍子匠为了免遭土匪劫掠,经过苦苦哀求,被允许尾随商会意气轩昂的马队穿过草地,结果,骑着瘦弱老马的按子匠苟全了性命,万无一失的商会马队反倒陈尸荒野,仿佛命运的一场恶作剧。这个被作者叙述得神神道道的故事,本身并无多少深意,倒是诡异的氛围,神秘的瞎老头,豪强的骄横,鞍子匠的惊悸,把旧时代草地上阶级重压的现实,平民的理想之类生存相巧妙地展示出来了。《白草地、黑草地》读来就要晦涩滞重得多(不知作者自己写作此类作品时是否一也很费劲),它显然受到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启迪,其面貌与西藏近年来的一批魔幻之作非常相近。泛灵论的雾霭似乎笼罩着草地,对神灵世界的敬畏,对图腾的崇拜,使一切物件都泛着神秘之光。为什么脚户汉要到老牛临死时才出现,为什么孩子的舌纹与铜盒底上的纹路一模一样,灰鸽和大铜锅又预兆着什么?很难解析。不过,作品表现世居草地的人们的生存方式、情感方式、信仰方式的意图是看得清楚的。由于人不能驾驭自然,便信奉外在的超自然的力量,由于人与动物不可解的亲和力,便产生了相应的感悟。看完这样的小说,突出的感觉是,哦,草地上的人们就这样生存着,发展着。最后,社会的变革终究打破了草原上亘古的平衡,我们真需要走出草地,走出蒙昧,走向文明呵。 围绕着草地文化景观,雷建政还写了一大组关乎宗教情感与现世人生的小短篇,如《放生》《画佛》《天火》等等。因为作者所在地区佛教依然流行,他从这里切入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这组作品大都注意锤炼语言,营造意象,借现实的人事洁问宗教情感的真伪。例如《放生》,写一青年在佛寺近旁垂钓,遭到信徒的痛打。垂钓者因而犯了杀生戒,而打人者何尝不是同样犯了戒。这时髦青年似乎窥破了此中奥秘,继续垂钓,佛寺的长老们便也只好不断花钱买鱼放生,于是,青年发财,众人也相继模仿他而发财。这便无形中构成对神圣的奕续和佛教的尴尬。其它篇也大都如此。我们在欣赏这类作品构思的精巧的同时,会忍不住产生疑问:作者汲汲于此类意趣,是否是对自身创造潜力的一种自搏和限制呢? 事实上,若把雷建政的创作当作一个例证与近年来创作潮流的跌宕联系起来,是颇能发人深思的。就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发展脉络而言,说它经历了从政治反思到历史反思再到文化反思,说它由社会政治视角转为文化心理视角,是大体符合实际情况的(新写实小说的回归倾向另当别论)。雷建政的创作之所以走了这么一条线路,也正是受制约于总体趋向的。总的说来,文化视角作为一种认识生活的图式,具有更大的宏观性和包容性,是一种进步。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经常陷人二元对立的盲目性中,把社会性与文化对立起来,这就导致了一面从社会历史意识方而的大幅度“退却”,一面向狭义的文化意识方面的“推进”。在有些作者那里,写了现实的社会政治内容,似乎就不超脱,不永恒,不空灵了,于是竭力躲避,结果所谓文化就经常变成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语。为什么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地盘扩大,而小说的世界和读者都在缩小,原因虽然复杂,不能说与小说的现实性,社会性的稀薄无关。对小说而言,是否也有个从“纯粹的美”,“本体”,狭义的“文化”解放出来,多吃五谷杂粮,不排拒社会间题,不惧怕世俗化,烟火气的间题?雷建政近来的小说,愈来愈追求精致化,形式感和语言的雕镂,已经到了辞胜于质的地步。例如这样的句子:“四只马蹄子踩下的窝坑里汪满了垂暮”,“天,独自扯一片蓝,高高地去蓝了,丢下一个太阳傻傻地炽烈”,“门虚虚掩着,挤进来的阳光在门缝里夹成扁扁的一条,无脚地赖在地上”,“一马鞍甩下,惊裂了东方那纯黑得正浓的天,顿时有亮的意思渗出来”等等,就过于雕琢了。这是不是种有害的时髦,是不是才能的浪费,是不是“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的诗人”的癖好?毫无疑问,这些年雷建政的创作有明显的进展,艺术表现力提高了,但同时似乎失去了什么。对他来说,确实存在一个把主要精力凝聚到哪里的问题。作为创作历程的一个驿站,他目前的创作是应予肯定的,作为对长远创作方向的追求,他又是决不能停留在目前的格局上的。雷建政长得魁梧、厚实、强悍,他的创作也该象他和他的甘南平原一样,广阔而雄劲。 原载《小说评论》1991年第2期。 五彩甘南,大美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