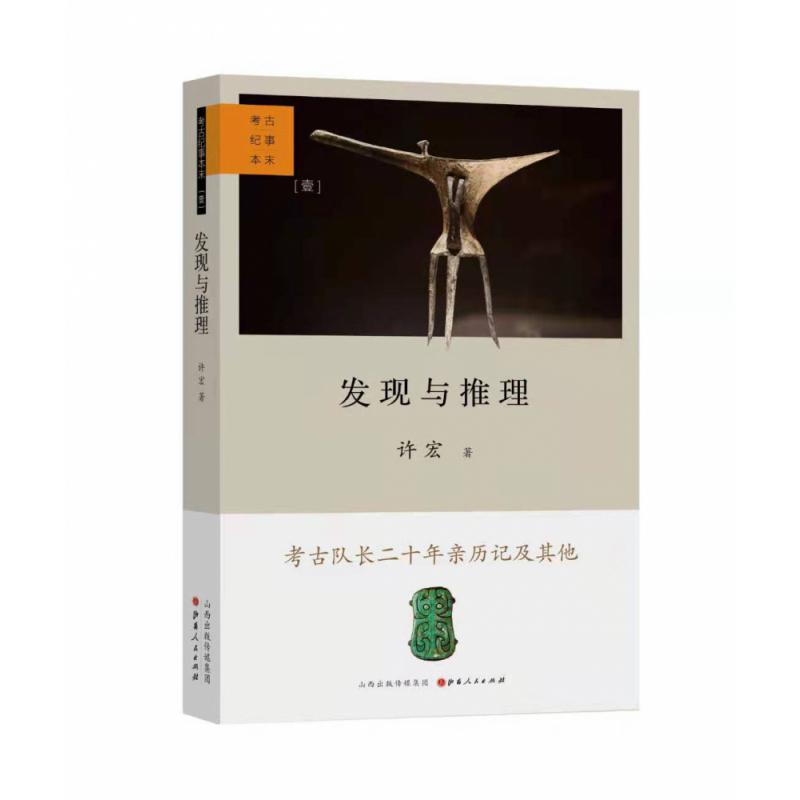
出版社: 山西人民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80
折扣购买: 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
ISBN: 9787203117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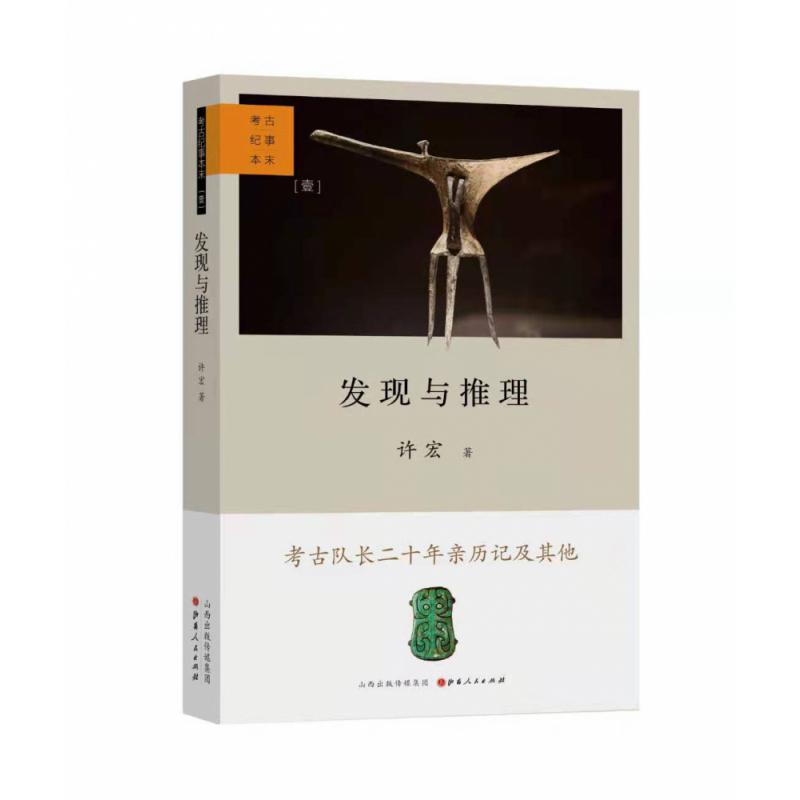
许宏,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等。
“超级国宝”绿松石龙现形记 中国是龙的国度,龙甚至被提升到中华民族图腾的高度。龙形象文物源远流长,最早出现于距今8000年前。但最初的龙形象异彩纷呈、五花八门。与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龙形象也经历了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它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与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大体同步。二里头都邑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问世,可以看作这一进程的一个大的节点。 宫殿区内的贵族墓 在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汇报会上,二里头遗址2002年发掘出土的贵族墓中的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引起了与会专家和公众的极大兴趣,这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的又一重大发现。这条碧龙“生存”在怎样的环境中,为什么迟至2004年才“浮出水面”呢? 话题还要先回到世纪之交。199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40周年之际,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从前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新官上任,有许多学术设想,于是在钻探确认了遗址的现存面积及成因、所处微环境、大的功能分区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以宫殿区为中心的遗址中心区的探究上来。 2001年秋开始,根据前辈工作的线索,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部揭露出相互叠压的二里头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建筑基址下,发现了一座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建筑基址,我们将其编为第3号基址。这是一座(或一组)多进院落的大型建筑,其主体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组成。时代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约当公元前1700—前1600年前后。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 发掘大型都邑遗址,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是只揭露到最上层的建筑基址的表面,清理打破基址的更晚遗迹如墓葬、灰坑等,利用这些遗迹的剖面来观察早期建筑和其他遗迹的情况。至于建筑的院落则只清理到踩踏面也即当时的地面,而不能像发掘一般小型村落那样,竭泽而渔地清理掉所有的文化堆积。这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吧。 2002年4月上中旬,发掘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一天上午,年轻队友李志鹏(本所同仁,当时来我队协助工作)走到我身旁,压低了声音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赶忙和他来到他负责的探方,这个探方中有一座很大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灰坑,灰坑打破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建筑基址之间的路土和垫土,并穿透了其下叠压着的3号建筑南院中的路土。灰坑已基本清毕,刚才李志鹏在刮灰坑的坑壁剖面时,发现有铜器露头,他赶忙又用土盖好,向我报告。我们仔细剥去表面的覆土,一件饰有凸弦纹(青铜器纹饰的一种,顾名思义,类似于凸起的琴弦)的铜铃的一角露了出来,阳光下青铜所特有的绿锈惹人心动。近旁还有人骨露头,这应是一座身份较高的贵族墓!被灰坑破坏的只是其一部分。我马上让他盖好,先扩大发掘面积,寻找墓葬范围,确认其开口层位(考古学术语,指现存遗迹口部的堆积情况)。考虑到在考古发掘工地上协助工作的民工已知此事,决定安排人在工余时间不间断看守,直至最后清理完毕。保护好文物的沉重责任感甚至盖过了发现的欣喜。 经仔细观察,墓葬开口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的路土层之间,说明墓葬系该建筑使用期间埋设的。因此,我们在墓葬正式清理前,已可确认其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自1959年首次发掘以来的40余年间,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早期墓葬仅发现过1座。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出有铜铃的墓一般同出嵌绿松石铜牌饰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玉器、漆器和陶礼器等。在这座墓发现前后,我们在该墓所在的3号建筑基址的南院和中院先后发现了建筑使用时期埋设的数座贵族墓,这些墓葬成排分布,间距相近,方向基本相同。尽管大多遭破坏,这些墓葬还是出土了不少随葬品。这是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以来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成组贵族墓。成组高规格贵族墓埋葬于宫殿院内的现象,对究明这一建筑的性质和二里头文化的葬俗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3号墓又是这些墓葬中最接近3号建筑基址中轴线的一座,它的规格很可能高于以往在宫殿区周围甚至它近旁发现的同类墓。 从这批墓葬的规格上看,当时是有一定身份的死者才可以入葬其中的。也许除了贵族外,他们还有其他特殊的身份,而这种特殊的身份又应与建筑的性质有一定的关系(李志鹏?2008)。已有学者对包括3号墓在内的这些墓葬所在建筑基址的性质加以讨论,大多认为应属宗庙建筑,到目前为止还难以作出确切的推断。无论如何,可以排除这些墓葬属祭祀活动形成的人牲坑的可能,它们所在之处也绝非当时的墓地,应属有较高社会地位者的正常埋葬(杜金鹏?2006)。 这些埋葬于宫殿区的贵族墓,让人想到1970年代发掘的著名的殷墟“妇好墓”(社科院考古所?1980)。那是位于安阳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一座高级贵族墓。妇好,一般认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她为什么不追随武丁陪葬于王陵区,至今仍是个谜。而发现于二里头都邑宫殿区的这些贵族墓,或许可为解开这些谜团提供有益的线索。贵族墓埋入宫殿区的原因与性质也许并不相同,但无论如何,那时人的生死观念应该与今天不同,他们不避讳死人,甚至亲近逝者,有“居葬合一”的习俗,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把这座墓编号为2002VM3(即2002年第V工作区第3号墓)。墓葬为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的方向接近正南北向。当时大部分的墓葬都是这个方向,说明葬俗是有讲究的。在揭开墓葬上面叠压的路土层后,我们得知这座墓的长度超过2.2米,宽度达1.1米以上,残存深度为半米余。可不要小看了这墓的规模,如果与后世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它实在是小得可怜,但在二里头时代,它属于迄今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之一(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王一级的墓葬,见本书《二里头“1号大墓”的是是非非》)。要知道,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以来,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总数达400余座,但墓圹面积超过2平方米(即大体为2米长、1米宽)的贵族墓却仅发现9座(李志鹏?2008)。所以,这座墓值得我们期待很多! 前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大灰坑打破了墓的西南部。墓主人侧身直肢,头朝北,面向东,部分肢骨被毁。后来经我所体质人类学家鉴定,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35岁之间。墓底散见有零星的朱砂(这种红色矿物质是二里头贵族墓中的常见之物,一般认为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是身份等级的标志物),没有发现明确的棺木的痕迹,或许已腐朽殆尽。 墓内出土随葬品相当丰富,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贝等,总数达上百件。墓主人头骨上方发现3件白陶器,呈品字形排列,2件顶面朝上,1件顶面朝下,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的组件。白陶器均呈斗笠状,顶部圆孔处皆有一穿孔绿松石珠,估计原来应该有丝带类的有机物把二者连缀起来。白陶器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贵族用器,但斗笠状器却属首次发现,也不见于以往在宫殿区周围发现的贵族墓。墓主人头部附近发现一件鸟首玉饰,其风格酷似长江中游一带的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就是典型的石家河遗物而非仿制品。头骨近旁发现2枚较大的穿孔绿松石珠。大量海贝置于墓主人的颈部,数量超过90枚,每个上面都有穿孔,上下摞压,局部呈花瓣状,应该是颈部的串饰,即“项链”。这种海贝叫作子安贝,仅产于南海、印度洋及以南地区。远隔上千里乃至数千里之外的玉器和海贝类珍罕品出现于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内的贵族墓中,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唯一一件铜器即李志鹏最早发现的铜铃,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铃内有玉石质的铃舌,铜铃表面黏附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的印痕,下葬时应以织物包裹。漆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多,见于墓内四周,而以墓主人左侧最为集中,可以辨认的器形有饮酒器觚、钵形器和带柄容器等。陶器有酒器爵、封顶盉、象鼻盉,以及作为炊器和盛食器的鼎、豆、尊、平底盆等共10余件,这些器物都被打碎,放置于墓主人身旁(社科院考古所?2014;许宏?2016)。 在另外几座贵族墓中,还出土了玉柄形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以及成组的蚌饰等珍贵遗物,其中也不乏首次发现者。 神秘的大型绿松石器 发现3号墓的当晚,我们即开始布置对墓葬进行“一级守护”。当时我手下有3名年轻队友(我队的陈国梁和外队来协助工作的李志鹏、唐锦琼)以及4名技师,又正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共9人来队实习,可谓兵强马壮。同学们听说要为了这一重要发现通宵值班,都非常兴奋,主动请战,女生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 我们安排“两班倒”,上半夜一拨,包括女生,下半夜则全为男性。我们又从邻近的圪当头村借来一只大狼狗,把我们的“大屁股”北京吉普2020开去,车头对着黑魆魆的墓穴,隔一会儿用车灯扫一下。上半夜还比较“浪漫”,大家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贪婪地嗅着晚春旷野上散发着麦香的空气,有男生还不时吼上一两句粗犷的民谣。下半夜则比较遭罪,4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在野地里要穿大衣。大家索性不睡,蜷曲在车里打牌,用一床大棉被合盖在几个人的腿上,被上放牌,大家戏称是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墓葬邻近圪当头村和四角楼村之间的土路,每有行人和车辆经过,大家都很警觉。 3号墓的清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靠上的器物露头,其中就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我们对绿松石片的出土并不惊奇,如前所述,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的长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一般都有铜质背托。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墓主人肩部一带的绿松石片位置较高,较为零星散乱,我们推测系棺木腐朽塌落时崩溅而致,因而对其保存状况并不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位于墓主人腰部以及胯部一带的绿松石片则相对保存较好,有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这颇令我们激动。以往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黏嵌于木、皮革或织物等有机物上,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时为墓葬填土压塌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的概念或清理经验不足而导致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回想起来,我们在阅读以往的发掘报告时,就经常在陶器、玉器等成形的耐用品介绍后,看到“此外,还有细小绿松石片若干”之类的描述,其实,它们大半应为某一镶嵌器物的“零部件”。因此,3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但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1毫米左右,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和周围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较大面积的移位,以后对原器的复原将成为不可能。 我意识到这样不行,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于是紧急向我所科技中心求援。我所科技中心对易损文物的清理复原保护工作在文物考古界素享盛誉。电话打给了科技中心文物修复保护组组长李存信技师,讲明情况后,李存信表示即便他们赶赴现场,因条件限制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好地揭取出来,最好是整体起取,运回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 就这么办!夜以继日地看守和清理,已使大家人困马乏,文物在田野中多放一天就意味着多冒一天的风险。何况,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这件珍贵文物妥善地保存下来。于是,我们改变战略,停止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同时抓紧时间清理其他遗迹遗物,照相、摄像、记录、绘图——考古操作程序一样都不能少。对于绿松石器,仅在平面图上标示出已知的大致轮廓。另一拨人则准备木板、绳子、钢丝、石膏等备品,准备整体起取绿松石器。 在按照田野操作规程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材料后,我们开始整体起取大型绿松石器。当然,最为理想的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依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起取体积越大,其松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何况偌大体积的土的重量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把墓主人颈部的海贝串饰也纳入了整体起取的范围,即从墓主人的下颌部(头骨在发掘前已被压塌)取至骨盆部。好在墓以下即为生土,将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这一长1米余、宽近1米的大箱子,由6个男劳力抬都十分吃力。它被抬上了吉普车,送到位于二里头村内的我们考古队的驻地。忙活完之后,已是发现铜铃的第四天晚上9点半了。 到了驻地,放在哪儿又成了问题。因为木箱内还有铜铃,恐怕会成为窃贼的目标。抬到二楼太困难,而一楼除了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和值班室外都无人住。于是有技师建议道:“队长,还是先放到你屋里吧!”也只好这样了。20余年的考古生涯,我已不介意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前的死者“亲密接触”。就这样,这位二里头贵族与盖在他身上的绿松石器与我“同居”了一个多月,直到被运到北京。 超级国宝惊艳面世 与李存信商量,他说在北京他的工作室清理可能比在我们队里做要好。也是,他清理绿松石器需要的各种工具和物品,要么得从北京专门带来,要么得我们开车去洛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在请示了考古所和研究室领导后,我开始安排把大木箱运回北京。那时已是2002年的7月,我当时在北京,押运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当时唯一的队友陈国梁身上。陈国梁与队里技师们一起,用我队的吉普车把大木箱及几个整体起取漆器的小木箱安全地运到了北京。一直在考古所等候的我,直到安排把木箱放进科技中心的大房间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科技中心的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完成所内的工作,又有许多兄弟单位的不时之请。李存信答应尽快处理我们的宝贝,但随后就是2003年春的“非典”,我们的大木箱也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这件国宝的重见天日。 2004年夏天,李存信开始揭开箱盖进行清理。从小心翼翼地剔凿去石膏,一直到总体轮廓出来,颇为不易。到了8月份的一天,李存信打电话给我,说有一定的轮廓了,保存得还不错。我急忙赶了过去,当看到我们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而保下来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你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分明也在瞪着你,仿佛催你读出它的身份。就这样,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逐渐“浮出水面”。 此后,我和队友赵海涛经常去清理现场,提供背景资料,与李存信商量如何一步步地处理及收集记录各种信息。后半段,我又从队里调来一名年轻技师,协助清理并负责绘图。 所里的领导来了,老专家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有人将其誉为“超级国宝”。经历了两年多的期盼,现在,我们可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了。 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由其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应黏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由铜铃在龙身之上这一现象看,可以排除龙形器置于棺板上的可能。又据以往的发现,铜铃一般位于墓主人腰际,有学者推测应置于手边甚或系于腕上,联系到墓主人侧身,而绿松石器与其骨架相比上部又略向外倾斜,这件龙形器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黏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龙头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为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在半圆形玉柱的底面发现有白色和浅黄色附着物,可能是黏接剂的痕迹。 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向两侧下斜。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体,由颈至尾至少12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因此更为逼真,尾尖内蜷,若游动状,跃然欲生。 距绿松石龙尾端3厘米余,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我们推测此物与龙身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条形饰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 龙牌、龙杖还是龙旗? 龙头部为何有一个略呈矩形的托座,说来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自从绿松石龙头部清理出来后,我们就对此百思不得其解。2004年秋季,二里头遗址持续发掘,工余时间我又开始端详起绿松石龙的照片。如前所述,绿松石龙形器在出土前即有多处石片松动或散乱,应是棺木塌落时受压变形,龙头部位就有因石片错位而导致图案不清之处,托座上的图案究竟表现了怎样的含意呢?这一问题一直萦绕于脑际。于是翻检相关材料,试图能找到某些启示。一日凭印象查找曾看过的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划兽面纹(顾万发?2000),再次看到这一兽面纹,不禁连连感叹其与绿松石龙头太像了!你看那面部的轮廓线、梭形眼、蒜头鼻子,甚至连鼻梁都是相同的三节,简直如出一辙!最具启发性的是从新砦兽面伸出的卷曲的须鬓,让我们茅塞顿开。托座上那一条条由龙头伸出的凹下的弧线,展现的不正是在绿松石上难以表现的龙须或龙鬓吗? 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之间的相似性,还有更深一层意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中原龙山文化向青铜时代初期的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作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当然这一认识主要是来源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比较。而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表现手法的高度一致,则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彰显了二者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说给绿松石龙找到了最直接的渊源与祖型。 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图案,则大部分应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因此,绿松石龙形器又成为解读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一国之瑰宝的一把钥匙。 总体上看,位于宫殿区内、最接近所在建筑的中轴线,且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3号墓的墓主人,其身份要远高于随葬铜牌饰的墓主人。绿松石龙形器或嵌绿松石铜牌饰都与铜铃共出,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是否与其他贵族有异?如是,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是乘龙驾云、可以沟通天地的巫师吗? 有学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黏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它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视觉冲击效果。“龙牌”上的龙图像,表现的是龙的俯视图。而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高级贵族,应系宗庙管理人员,“龙牌”则应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杜金鹏?2006)。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和日本学者把它直接称为“龙杖”或“龙形杖”——?一种特殊的权杖。的确,在此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用绿松石镶嵌龙图案的器具也是罕见的珍品,而绝非一般人可以享用的普通器物。 有学者则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履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旂(旗)”与“铃”并列对举,与该墓中龙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墓主人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冯时?2010)。 从众龙并起到饕餮归一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和绿松石镶嵌文物的又一重要发现。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杜金鹏?2006)。 绿松石龙形器,出现于二里头都邑初始兴盛期的宫殿区,此时的二里头聚落已经具备了东亚地区超大型都邑的内涵与气象,是中国古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表征。3号墓则属于迄今所知二里头都邑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墓主为具有特殊身份的较高等级的贵族。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上所表现的与沟通人与祖先或天地、神灵有关的神话性动物形象,此后成为商周青铜器纹饰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并且始终与当时社会中高等级贵族乃至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王朝时代礼器或威权物品最重要的纹样母题。这启示我们,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初期以龙等神化或半神化性动物图案为代表的动物母题与后来商周王朝礼器的特殊关系及其文化内涵,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早期文明文化底蕴的关键元素之一(许宏?2016)。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末期新砦文化刻于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应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已如前述;陶寺文化绘于陶盘上的彩绘蛇形蟠龙纹,早已享誉中外,也有学者指出其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龙纹相类。而二里头文化玉柄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所见兽面纹,应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的神祖面纹有关,其渊源甚至可上溯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邓淑苹?2014)。 显然,二里头文化所见以龙为主的神秘动物形象要较此前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复杂得多,龙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想象或虚拟的成分,呈现出多个系统的文化因素整合的态势。这类由其他区域引进的信仰与祭祀方式,有可能暗示了与上述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权崇拜理念被吸纳进来,成为二里头贵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作为大型移民城市,乃至跨地域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兴起过程(许宏?2009)。 不少学者把二里头出土的龙形象文物,与文献中种种关于夏人龙崇拜的记载联系在一起考察。但龙作为后来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其后的商王朝社会生活中的龙形象愈益兴盛。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密切的记载,但它的出土还是无法让我们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直接挂起钩来。 众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铸于国家重要祭器上的纹样是否就是以狞厉贪婪著称的怪兽饕餮,因而以较为平实的“兽面纹”一词取而代之。更有学者指出这些纹样主题的大部分,应即龙纹(王震中?1985;李学勤?199)。李零进一步指出“(商周时期)饕餮纹与龙纹同时存在,前者……就其主体而言,应是龙纹面部的特写,两者属于同一大类”(李零?2017)。随着早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广域王权国家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饕餮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可以显见,二里头正处在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奠基与转折的关键时期。前所述及的二里头龙形象的诸多要素,如整体面部特征、梭形目(或称臣形目)、额上的菱形装饰、龙身的连续鳞纹和菱形纹等形体和装饰特征,都为二里岗至殷墟期商王朝文化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而商周王朝青铜礼器中的龙形象,又奠定后世中国古代龙形象进一步递嬗演化的基础。 在发掘报告和学术文献中,我们把二里头3号墓出土的这件大型绿松石器称作龙形器,而不是直接称其为“龙”。容易理解的是,在缺乏自证性文字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对不会说话的文物性质之判定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众所周知,龙是人们想象和推衍的产物,只要具备“四不像”甚至“二不像”的特征,就进入了广义龙形象的范畴。这一大型绿松石器精工造就,至少由两种动物形象组合成的不见于自然界的灵物,当然会诱发人们关于“龙”的丰富联想。但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分析也是一种推论,有待进一步发现与研究的验证。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同时又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而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王震中:《“饕餮纹”一名质疑及其宗教意义新探》,《文博》1985年第3期。 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冯时:《二里头文化“常旜”及相关诸问题》,《考古学集刊》第1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许宏:《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李零:《说龙,兼及饕餮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 考古队长许宏生动回顾二十年田野亲历 缜密破解重大考古“悬案”的是是非非 ◎一枚小小的丁公陶片,何以掀起轩然大波? ◎二里头宫城的发现不是挖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 ◎二里头“1 号大墓”是真是假? ◎二里头“超级国宝”的现身如何一波三折? ◎“绿松石小兽”究竟是哪朝遗物? ◎传说中的“尸乡沟”如何进入正式的遗址名称? ◎武威铜奔马被断代为东汉是否准确? ◎西晋墓里出现金属铝,这可能吗? 我对这本小书的定位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学术史。 所谓“纪事本末”,就是希望把一些考古发现及其论争探索过程,述而不作地娓娓道来,热闹之外,得让诸位看出点儿门道来。 ——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