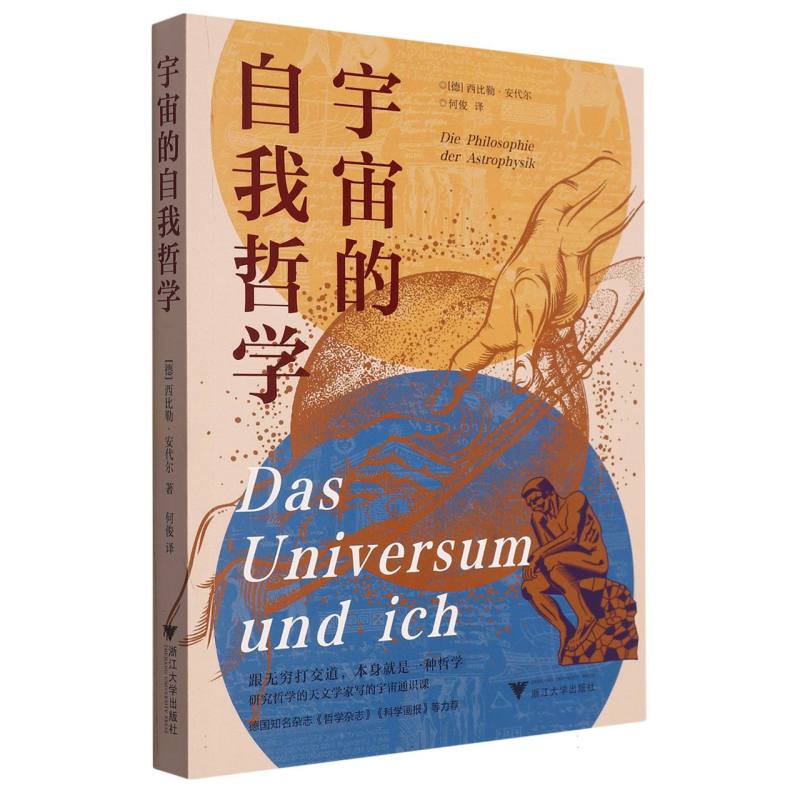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大学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6.60
折扣购买: 宇宙的自我哲学
ISBN: 9787308243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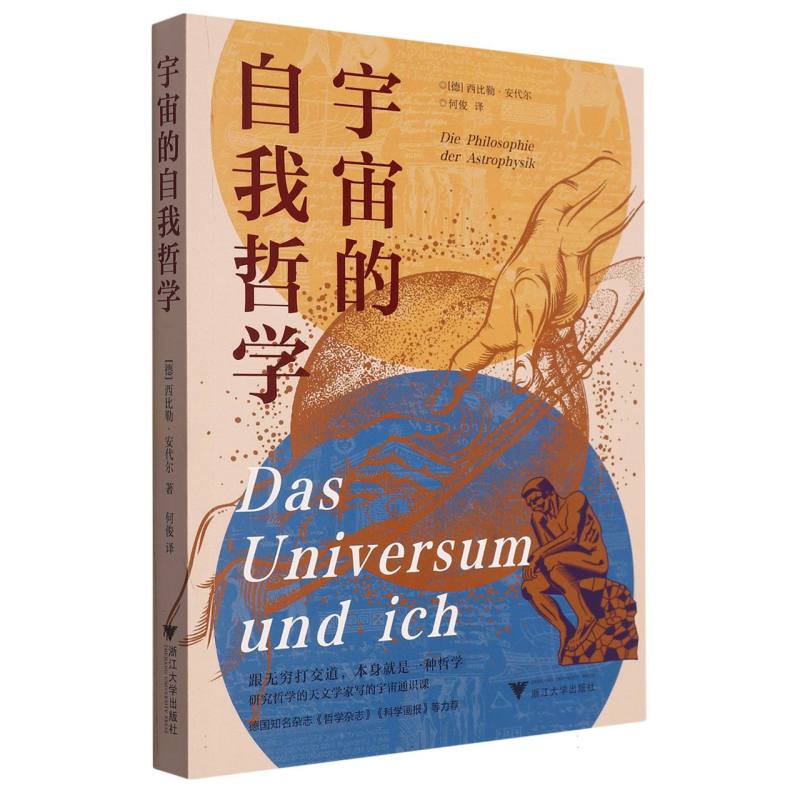
[德]西比勒·安代尔毕业于欧洲顶尖理工类大学之一的柏林工业大学,持有物理学和哲学的双学位,后又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天体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博士学位。自2013年以来,她在法国格勒诺布尔行星学和天体物理研究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恒星的形成和天体化学。已出版图书:《科学有多寻常?:一次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生命的物理学:宇宙尺度的反思》《暗物质:宇宙的大谜题》。
引言一 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是我父亲接的电话,这比较少见,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我母亲主动来做这件事。 “嘿,西比勒,现在我必须跟你直说。” “嗨,爸爸。” “我昨天看了科学类报纸,那上面说,发现了一个170 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170亿! 难以置信!” 他拉长了调子,一字一顿地说着“难以置信”四个字,特地强调自己对这堆难以置信的巨大物质心怀多大的敬畏。但仅仅几秒钟后,他的强调就被打断了,因为我母亲在旁边叫道: “胡说八道,我都无法想象有什么太阳质量。那也仅仅就是一些数字而已。” 我父亲一下子变得没好气起来,他说:“你也许无法想象! 但是,西比勒,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信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发现了那么大质量的东西时,这样的说法有多高的可信度? 因为我们没法飞过去,也没法称重。” 引言二 天体物理是一门特殊的学科 若是谈正事,去乌克马克可能是个好主意。乌克马克是柏林北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那里水域宽广,绿意盎然,静谧安宁,人烟稀少,没什么娱乐场所。但与此同时,如果在度假屋里待上几天,几乎就没什么机会避开人群了。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跟一批学者一起,在利兴[ 利兴和乌克马克都是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市镇。—.—译者注 ]附近留宿了几天。我们一行有十来个人,包括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哲学者和天体物理学者,有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和本硕学生。我们的共同点是希望理解天体物理学是如何运作的,并弄清楚科学家具体是怎样研究宇宙的。 当然,这乍看上去是一个有点奇怪的目标,人们可能会认为,作为一名天体物理学者,你肯定很无聊才会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去乌克马克。暂且撇开以上这点不论,实际上我们应该了解自身这个群体在做什么,而无须向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和哲学研究者取经。原则上也该如此。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尽管自我认知已经比较完善,但人们也会去看心理治疗师,或者做个医疗咨询,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或是改变自己的行为。正如治疗医生所建议的,要立足自己的病历和家族病史,更好地理解自身的行为、思想和感情中的某些部分;我们天体物理学者则希望,由此多了解一点自己的行动和自我认知,让学术史专家也来探究一下我们这个领域的历史。 在社会学者那里,我们天体物理学者希望得到一些洞见——关于学术政策、现存等级制度和社会动态是如何影响我们作为天体物理学者对宇宙的发现的——尽管我们自然希望完全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哲学者那儿,毕竟我们希望得到如何获得天体物理知识等相关问题的答案:比如是否存在认知的界限,认知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我觉得这些哲学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以天体物理学者兼哲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参加了那场聚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给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不想仅在两天内就把这些问题解释完毕,而是想借助更长的研究合作弄个水落石出。在乌克马克,我们只想定义一个共同的框架。而这一点总是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复杂一些。 例如,历史学者会说,只有就一定的历史背景而言,知识才是真实的。中世纪之人所相信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比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更不真切。这个论断在天体物理学者那儿可不讨好,在他们听来,好像是说“你们所做的都是错的”。这种打倒一片的说法不讨人喜欢,特别不受历史学者的待见。如果再加上社会学者关注谁穿哪件衣服,女士的讲话时间是不是跟男士的一样长,自然科学者的耐性很快就消耗光了。人文学者反过来又觉得自然科学者极度欠缺思考,而且妄自尊大。自己没有成为他人那样的人,这让每个人都暗自庆幸。如果各个学科的书呆子碰到一起,那场面也不总是容易对付的。 然而,乌克马克的和谐氛围首先不应被上述争吵打扰。在舒适的度假屋前方,屈斯特林湖的水在清冷的秋风中泛起涟漪,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我们坐在暖意融融的房间里,暂时思考一下实际上想要澄清哪些天体物理问题。为了真正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资金,因此我们这次聚会更重要的部分在于策划如何把项目计划“出售”给潜在的资助者,比如说德国研究联合会。当然,只有提交有力论证,才能获批资助。而当时的我则认为,若能展示项目的独特性——描述天体物理研究是如何进行的,总会大大提高卖点:这一点扣人心弦而且举足轻重,为什么呢? 因为天体物理有着诸多不一样的地方! 毕竟研究者无论如何都不能跟研究对象交互,而这样的学科寥寥无几。宇宙太过浩渺,而我们天体物理学者感兴趣的一切,几乎都跟我们相距遥远。宇宙中的各种情况又太极端,以至于我们没法在地面上的实验室里模拟这些情况;而宇宙里各种过程得以演进的时间尺度,相对于我们短暂的生命来说,实在太过漫长。这一切可真令人着迷。但在我们这个跨学科团队里面,我是唯一一个对天体物理的特性怀有高度热情的人。 历史学者说:“不,我不同意。夸大其词地说天体物理跟其他学科完全不一样是危险的。天体物理也是物理,应用于宇宙领域。” 我回答:“但比方说吧,天体物理也是一门观测科学,这一点确实引人入胜。” 历史学者又说:“还存在很多其他的观测科学。比如在生物学领域,也经常需要观测。” 我又答道:“生物学可以做实验,但天体物理不能。” 社会学者说:“考古学也不能做实验啊。” 我回答道:“但宇宙里的情况比我们了解的一切都要极端得多。” 哲学者又说:“然而这只是一个量上的区别,而不是质上的。” 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没人信服我的如下观点:原则上,比之其他一切学科,天体物理都来得不一样。虽然这一点对我来说一清二楚,但我没能说服任何人。我觉得不被别人理解,最后索性放弃。于是我跟其他学者暂时达成一致,认为虽然天体物理是一门有趣的学科,但原则上来说,我们的其他研究也同样如此,比如地质学,或者果蝇研究。在一个还有天体物理学者参与的团队里思考与天体物理相关的问题,这当然更有意义。但因为学术研究有时候是本着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多数派胜出——如果少数派恰好又无法自证,那么情况更是如此。于是我们最后一致同意,必须重新给项目找个由头,而不再执拗于天体物理的独特性。于是在乌克马克的那几天就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我永远记得,就在那几天,有几位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和哲学者,把我心目中天体物理的独特性给生生掠去了。 第一章宇宙有多么真实 1.一切都是空想出来的吗? 我在乌克马克经历的自恋伤害,此后还困扰了我一些时日。后来我认识了伊恩·哈金(Ian Hacking),一位加拿大哲学家,他生于1936年,曾写过一本相当知名的科学哲学入门书。这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是首批细致入微地探讨科学实验的著作之一。长期以来,哲学的做派让人觉得科学的首要问题是检验理论似的:凭空想出一个学术命题,然后验证它是否正确。具体是怎么做的,又该怎么做,对此进行细致研究曾是哲学的任务。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卡尔· 波普尔(Karl Popper)和他著名的证伪原则,以及他一再检验理论的要求,因为证明一个命题是伪命题,要比证明它是真的容易得多。比如我想证明所有的鱼都有鳃,即使我穷尽一生去抓有鳃的鱼,也无法获得最终证据。但只要我抓到哪怕是一条没有鳃的鱼,任务就完成了,因为我已经证实自己的假设是错误的。波普尔的要求符合假说演绎法:从一个与假设相矛盾的个案(无鳃的鱼)出发,推断出伪命题的错误性。在这一传统的哲学视域下,实验就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有助于开发、检验和完善科学理论。 伊恩·哈金是20 世纪80 年代首批强调实验独立性的哲学家之一。在哈金看来,实验有着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科学实践绝不是按照既定程序开展的,即让人可以先提出理论,然后再用实验来验证理论是否正确。实验经常也“只是因为”实验人员的好奇心,因为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不少情况下,理论也是从实验中得出的,也就是说,在观测到一些意料之外、尚还无法解释的现象之后,才会产生理论。有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理论家已经给出了一个解释,而实验者对它还一无所知。著名的宇宙背景辐射,即“宇宙婴儿照片”的发现,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两位射电天文学家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 实际上正在测试用于与卫星通信的一种新型的、特别敏感的射电望远镜。他们探测到从四面八方均匀发射过来的微弱射线,当时先是以为检测出现了错误,甚至把鸽子都赶走了,以排除它们作为潜在信号源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偶然发现了来自宇宙大爆炸的辐射,而几乎同时理论家也预测到了它。因为这一发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甚至还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他们检测时对自身用实验证实的理论一无所知。 伊恩·哈金是科学实验的忠实拥趸,坚决捍卫独立于理论、有着巨大价值的科学实验。他在书中甚至声称,只有通过实验才知道科学预测过的事物确实存在。他还认为,只有使用物品、与其相互作用的时候,才能确定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了解:比如说我的同事对我大谈他新买的沃尔沃,并给我看车的照片,但如果我恰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知道这个同事喜欢满嘴跑火车),那么只有在摸到这辆车,甚至最好是试驾一番的情况下,我才会相信真有这么一辆家用车的存在。对待科学,伊恩·哈金也是这么看的。 这当然也意味着伊恩·哈金不是天体物理学的铁粉,因为要在宇宙中“试驾”一番很难,超出太阳系就是我们的极限。也没有人可以从近处观测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我们永远无法用火箭来击中一颗“红巨星”,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永远无法站在一个“褐矮星” 上面,努力尝试看看可以跳多高。 长话短说。在乌克马克聚会后的几个月,有一天我读到了伊恩·哈金在那本入门读物出版6年后写的一篇论文,在文中,他表达了天体物理是一门完全特殊的学科的观点(耶!)。到此为止,皆大欢喜。但细节决定成败:哈金认为天体物理与其他学科全然不同,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径直断言天体物理学家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也许黑洞、椭圆星系、分子云、河外星系团、超新星完全不存在,可能这些都只是天体物理学家凭空臆想出来的,也许很快我们都会对此报以嘲笑。 这可太痛苦了。有人想与众不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跟他所见略同的人。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种与众不同就在于,自身并没有进行正确的科学研究。为了挽救我天体物理学者的名誉,除了更细致地探究哈金有关天体物理“反现实主义”的论述,别无他法。 2.桌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恰恰就是现实主义,让我大学期间的哲学生涯夭折了。在第一堂哲学课上,老师坐到我们前面,指着他前方的桌子问道:“这张桌子真的存在吗?”接着,他意味深长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学生。也就是因为这句话,那时我就已经意识到哲学并不适合我。毕竟,比起那些显然毫无意义的问题,确实存在更重要的东西可供思考。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我用桌子用得好好的(通常一天要用好几次),对其存在属性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有人显然跟桌子之间保持着更为复杂的关系,这自然很好,但我肯定不愿意成为这类人。因此,很快我就不去上哲学课了。 在后来的大学时光里,七弯八拐地,我又跟那些喜欢大谈家具及其存在的人扯上了联系,之后我无法避免更仔细地研究那些人的观点。显然,根本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都是通过感官体验获得的。我们观看、触摸、嗅闻和品尝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非百分之百正确。我们随时都可能犯错,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这还不算完,我们有时候甚至都不确定,所看、摸、嗅、尝的,是事物的特征,还是我们给这个世界打上了自己感知特征的烙。举个例子,就说对颜色的感知吧,人跟各类动物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我们看到了一个红色的球,那么这个球就真是红的? 在此,显然存在一个基本障碍:连接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总是我们的感觉,而这些感觉是专属于人类的。如果没有某个人的观察,没有我的观察,我就无法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我的感知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但我怎样才能确认这一点呢? 假如我早个两百年出世,也许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假如我是一只蝙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肯定是另外一码事。但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真实存在的呢? 带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很快就可以进入类似电影《黑客帝国》里的场景,影片中的世界是一个电脑生成的虚拟空间,由邪恶的人工智能在人的大脑里生成。可能我们人类大脑都被植入了芯片,因为神经脉冲的作用,深信人工智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并会有所表现。有谁知道呢? 老实说,无人知晓。但果真如此的话,我年事已高的哲学老师对桌子是否存在的提问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到此是一清二楚的。但同时又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承认这一点,也不能推动人获得更多新的认识。 前些时候我到一个朋友那儿去喝茶,她住在柏林市中心一套漂亮的旧式公寓里。我们坐在房间里的一张老式长毛绒沙发上,在前方那张巨大而老旧的木头桌子上,杯子里的茶冒着热气;一只长毛猫咪躺在我的大腿上,它发出呼噜声,我抚顺它的毛发,它的毛发渐渐地覆盖了我和沙发。在这样舒适的氛围中,朋友突然说道,只要她移开目光,我背后的书架就荡然无存,对此她深信不疑。我这朋友是艺术家,所以不必为这样的陈述感到担忧,反正她只是想玩点大脑游戏。但假设真如她所说的那样,她岂不是永远都要活在对满架图书的恐惧之中? 可能也不会如此,因为只要她一跟书架建立起视觉上的联系,一切就又都恢复原状。那么她那只猫呢? 那可怜的动物不是要被那个一再消失而又现形的书架折磨得死去活来吗? 或者说,当猫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书架也随之出现? 若是从隔壁房间那儿遥控拍照,那又会如何呢? 照片上会显示一堵空墙,还是一个书架? 其结果是,我们没有机会来证明以下情况:如果没有人朝那边望过去,我朋友的书架就不在那儿。那么接下来,我这样一个非艺术家身份的人就会说:“那又怎样呢?”在我个人看来,一个不需要不断重建自己的世界更有意义。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对以下事实——当我移开目光,然后又朝那边望过去的时候,一切都跟之前一样——的最好解释。关于桌子和书架就讲这么多了。我想说的是,它们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电子和夸克又当如何呢? 3.不可见之物的存在 伊恩·哈金,我那位可疑的支持者,他也认为天体物理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当他以哲学家身份研究现实主义这一问题的时候,关注的自然就不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家具了。他探讨的不如说是以下问题:本着解释世界的目的,人类对有些物体虽然已经做出了科学上的假设,但又无法直接感受,我们该怎样对待它们呢? 真的存在光子、中微子、希格斯玻色子、四维时空或者暗物质吗? 或者说,这些用于科学研究的天体无非只是我们发明出来的辅助工具,其目的无外乎是解释和预测那些可以直接感知的宏观现象? 之所以产生潜在怀疑,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科学曾经描述过的现象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现象确实被证明是不存在的。比如在17世纪末和18 世纪,化学家认为应该存在一种可以在燃烧时从可燃性材料中分离的物质,并称其为“燃素”。今天已经知悉的是,燃素是不 存在的。为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燃烧过程,需要理解氧气的作用。另一个知名的例子是以太。直到20世纪初,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其相对论中用四维时空取代以太之前,人类还相信它可以填充整个宇宙。还有些科学家认为,就连今天成为宇宙理论组成部分的暗能量和暗物 质,其实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必须承认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判定,要比就桌子的存在达成一致意见更加困难。 然而,对科学中发现的个别现象表示怀疑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反现实主义者。比如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今天所持的有关暗能量和暗物质的论断是错的,这两个概念早晚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是科学现实主义的拥趸,也会认为科学大体正在追寻这个世界的真实本质,即便偶尔出现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走上这样或那样的弯路。反现实主义者可不会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对其典型成员来说,科学理论对不可感知的物体和过程的论断,纯粹是虚构之言。但即便是反现实主义者,也会承认这些“杜撰”可能大有用处,可以用来解释我们能够感知的东西,只是必须谨防根据这种实际的成功推断出科学理论的真实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感知之物的界限也会发生变化,这一点也颇有意思。在100多年前,人类可能还有充足理由怀疑无法观测到的原子的存在(不少哲学家也坚持认为原子是不存在的)。到了今天,人类可以通过电子显微镜看见原子。通过这一方式,尽管还是没有“直接”感知原子(因为在可见图像和显微结构之间有一个复杂的、依赖理论的映射过程),但任何一个曾在电子显微镜里看到过光栅的人可能都会发现完全否认其存在是相当困难的。同样,要像100多年前那样怀疑其他星系的存在也几无可能,尤其是在使用类似哈勃太空望远镜这类强大观测工具的情况下,今天人类能够观测到的,是具有不同形态、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众多星系。科学现实主义者看似已经获得了一些可以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但即使在今天,对于不可感知事物的边界依然存在:我们只能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中质子和质子碰撞后的衰变产物来寻找希格斯粒子,但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相信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吗? 或者说粒子物理学家只是在自欺欺人? 暗物质之所以得名如此,就是因为它不会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我们看不见它。这些间接证据是否足够让我们相信,一定存在某种物质,它仅通过万有引力与宇宙中的其他天体保持关联? 在此,居于少数的怀疑派与目前占大多数的乐天派分道扬镳。前者主张科学理论跟真实性无关,科学家无外乎是在追逐幻影;后者认为人类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澄清理论结构的真实属性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哲学家伊恩·哈金是一位科学的现实主义者,至少在天体物理领域如此,据他自己所言,原因跟其个人经历有关。有位朋友曾向哈金讲述一个意在证明夸克存在的实验。为此,实验人员发射电子到铌球上。可以常规地发射电子,这一事实让哈金认为,怀疑电子的存在是荒唐 的。“如果我们可以发射一种物质的话,这种物质就是真实存在的,”他这样说道。若把某个物体当作工具使用,也就是说,如果非常熟悉某物产生的原因和效能,可以有目的地为己所用,那么它就一定是存在的。原因再清楚不过:既然我曾把某物用作工具,这预设了我可以放心大胆 地依赖我的相关认识。我清楚地知道它会有何反应,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之事。这似乎也完全证明该物体正是以我所设想的形式存在。如果我能听广播的话,一定有电磁波存在。如果我可以打开等离子体电视机,那么肯定是有等离子存在。 4.不要实验! 如果把“发射”一词看作实验操控的同义词,那么我们永远都无法“发射”矮恒星和黑洞。更糟糕的是,宇宙(都知道它的浩瀚)的绝大部分从来都会避免与我们产生任何可以想象的互动。我们可以发射宇宙探测器,等待它们最终离开太阳系,我们可以向宇宙发送信息,希望某人在某个时刻将它们解码。而相对论却让互动方式占领宇宙这一传播更广的希望显得几无可能。毕竟,光速限制了一个旅行速度的最大值。但即便是这个最大值,事实上也无法达到。因为根据相对论原理,天体飞得越快,它的质量也就越大。用于进一步加速的能量,随着速度越来越接近光速,会有越来越多的一部分转化为质量,而不是转变为更快的速度。这样,加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需要越来越多的能量。 但即便可以用光速开启宇宙之旅也不会有太多收获。真能那样的话,我们大约一秒钟就可抵达月球,八分钟就可到达太阳。但哪怕是到达最近的恒星,也要耗费四年多。而抵达银河系中心,差不多要三万年。这就是说,假如克罗马努人不把时间花在描绘洞穴壁画上面,而是建造了一艘以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那么他们的后代直到今天才能进入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要抵达下面的矮星系,即在南半球裸眼可见、像夜空中星云状斑点一样的大小麦哲伦星云,差不多要花20万年,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而要到达下一个螺旋星系——仙女座星座,则需要250 万年,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即使这样,也只是抵达了离我们最近的宇宙邻居,并没有走得更远。因此,我们必须勉强接受,我们被困在地球附近,并不能做太多事情主动探寻并操控宇宙。我们还得接受这一事实:我们能处理的信息,仅仅是宇宙从它那儿发送给我们的。谢天谢地,那些信息已经堆积如山。我们这些天体物理学者所用的主要信息源是电磁辐射。科学界过去利用的是可见光,而今天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整个光谱,从长波段的微波辐射到短波段的伽马射线,即便为此在被地球大气层阻碍的波长范围内必须使用卫星。此外,从宇宙发射过来的、速度极快的基本粒子和原子核,也就是所谓的宇宙射线,也会抵达地球。另外我们还会接收到中微子,但它们很难探测,因为它们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弱。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引力波这一新的信息渠道,未来几十年里,这一发现将开创一个以实验为基础的天体物理新分支。 这些大量的信息载体却无法改变如下事实:我们无法利用绝大多数的宇宙现象来做实验,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掌控和改变既有条件,观测发生了什么。对伊恩·哈金来说,这已是不相信天体物理学家的充足理由。 5.宇宙的阴谋 天体物理学家想要了解的天体简直太过遥远了,所以没法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实验,但这不是伊恩· 哈金不信服天体物理的唯一因素。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之所以不能说服他,是因为天体物理学家为了迎合他的口味,使用了一大堆模型和模拟,但这些稍后再详细说明。在他的文章中,他最为关注的一个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宇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副模样,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有点像阴谋论,它们的共同主题是:万物实际上跟众人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认为我们曾登上了月球,而事实上,因为当时的技术并不成熟,登月视频是在一个秘密的摄影棚拍摄的。众人都以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过世了,而实际上他几十年来都幽居在一座南海岛屿上面。阴谋论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对于某些明显的观察结果,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故事可以解释这些观察结果,而这两个故事在一开始听起来都基本可信,至少在人们的认知范围内是这样的。伊恩·哈金因此为宇宙设计了一个类似的阴谋论:假如存在我们看不见的天体,它们却能系统地扭曲所有从宇宙那里出发抵达地球的光线,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假定,光线无障碍地抵达地球,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宇宙里的现象。但因为我们对路途上光的变化——一无所知,我们整个的“了解”就出现了错误。于是天体物理的大部分发现都是不的,而我们全然不知。 对这一点的想象,可以借助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在影片中,一个原联邦德国家庭的儿子向病中的母亲隐瞒了东德解体的事实,希望她不要为此激动而加重病情。为了不让母亲了解到事实真相,他就必须相应地掌控母亲可以接触到的所有信息,让她觉得好像东德还继续存在一样。而这位母亲因为病情不能下床活动,所以儿子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保持了这个幻象。按照哈金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处于那位常年卧床的母亲的位置(房子是我们的太阳系),而那些让我们眼中的世界看起来与其本来面目迥然不同的骗术,将无助的我们牢牢攫住。 伊恩·哈金设计出这个颇有威胁性的场景,并非毫无根据。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自己的论文的时候,正值引力透镜研究产生之时。所谓引力透镜,就是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原理,让空间发生弯曲,这样一来,使得光线通过引力透镜得以偏移和增强。引力透镜效应与光学透镜效应非常相似。在观测光源的时候,如果在观测者跟光源之间存在一个大质量天体,光线就会受到该天体的影响。通常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非常大质量的引力透镜,如星系。这时光辐射的方向就会在透镜的作用下发生变化,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发光的天体;如果天体正好置于透镜后面的话,我们经常或有时就会看到一个圆环。以上情形并不适合构建阴谋论: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时候会出现引力透镜,并考虑其效应。 按照哈金的观点,那些对天文学认识产生潜在遏制作用的神秘天体,就是所谓的微透镜,亦即质量没有那么大的引力透镜,比如行星或者假定的“暗恒星”。微透镜效应非常弱,以至于无法看见光的偏转,但光的强度仍会受到透镜的影响。这里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个不同的场景,它们会给我们提供相同的观测效果:用具有加强功能的微透镜来观测光线微弱的天体,其效果跟不使用透镜去观测光线更强的天体完全一样。类比一下上文提到的电影场景:对病榻上的母亲而言,在她儿子的掌控行为下,生活在已经解体的东德里和生活在尚还存在的东德里是一模一样的,她没法将这两个场景区分开来。如果不能确定在我们与天体之间是否存在一面微透镜,也就没法区分是在观测强光的天体,还是在用不可见的透镜观测弱光的天体。所以说,我们再也不能相信天体光度的测量结果。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从光度中推断出了相当多的结论,比如说在光源中进行的物理和化学过程。那将会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宇宙发送给我们的大部分信息可能是受到操控的,至于这一操控发生在什么时候、又是怎么进行的,我们一无所知。可以说,我们成了宇宙范围内一场阴谋的受害者。而这场阴谋是我们无法发现的,因为我们被困在太阳系中,无法到现场核查,看看作为观测者的我们与天体之间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伊恩·哈金可能会得意扬扬地断言:如果你们天体物理学家能做实验,能直接核实在你们和光源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一切对你们来说都不曾发生。相对于能活动自如的人来说,卧病在床的人更容易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