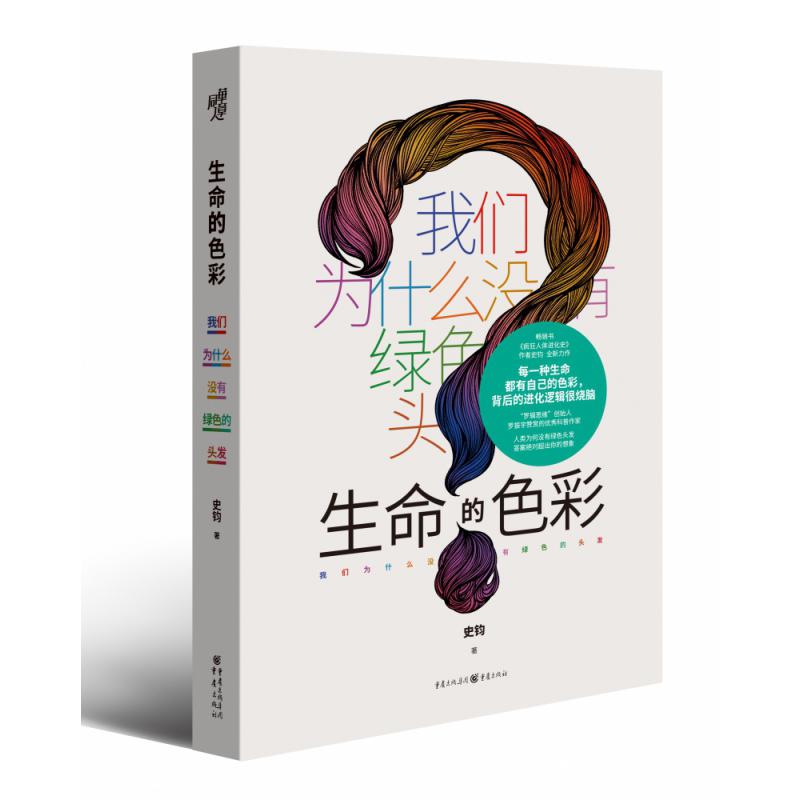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30.60
折扣购买: 生命的色彩 : 我们为什么没有绿色的头发
ISBN: 9787229152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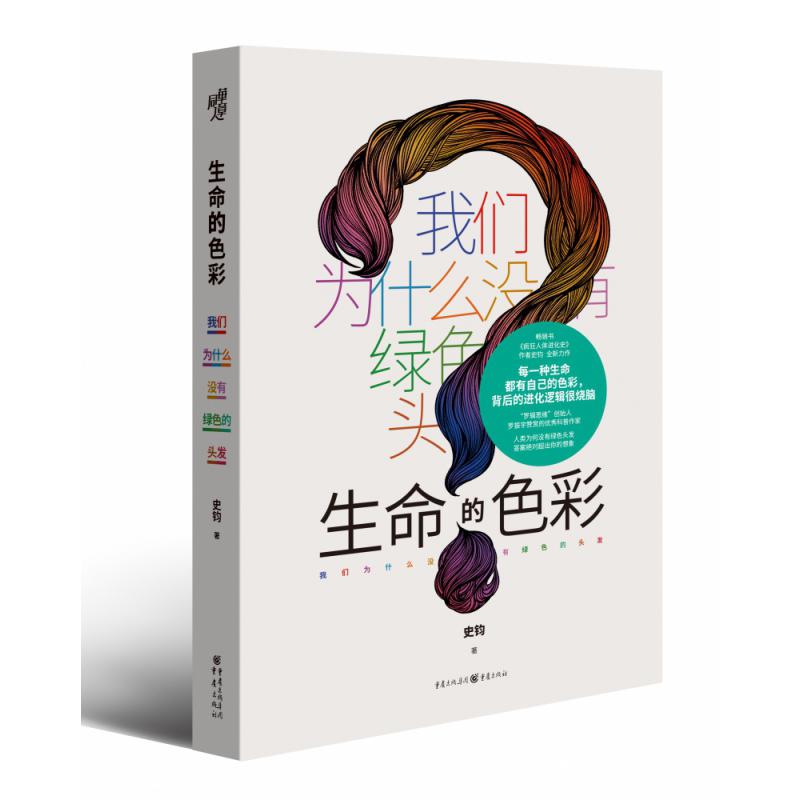
史钧:生物学博士,现任教于安徽科技学院。长期从事进化论领域的科普写作,擅长用轻松幽默的文笔介绍严谨的科学知识。曾出版科普作品《其实你不懂进化论》《疯狂人体进化史》《爱情简史》等,广受读者好评。
百无一用的绿色毛发 对于其他动物来说,无论昆虫还是鸟类,绿色都是一种常见体色,因为绿色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伪装作用,甚至是炫耀作用。对哺乳动物来说,情况却变得完全不同。哺乳动物之所以没有进化出绿色的毛发,是因为它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仅就身份识别功能而言,幼仔体色就不可能采用绿色。试想一下,如果羚羊幼仔长着一身绿色的毛发,蹲在绿草丛中就等于彻底隐形,那么母亲该如何识别自己的孩子呢?那只会给母亲带来极大的困扰,而不是极大的方便。 所以在身份识别方面,绿色并非哺乳动物的首选颜色。 再来看看哺乳动物在警戒色方面的表现。 对于昆虫、爬行动物或者两栖动物来说,警戒色极其常见,用绿色来警戒天敌更是常规手段。哺乳动物却不然,虽然哺乳动物的毛发颜色很多,但很少起到警戒作用。不但肉食动物不会使用警戒色,草食动物也不会使用警戒色,所以狮子和羚羊都没有警戒色。 逻辑是这样的。 作为捕食者,狮子披上警戒色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只会远远地把所有猎物全部吓跑,徒然增加捕猎的难度。身披豪华警戒色的捕食者很有可能会活活饿死。正因为如此,所有捕食者都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暗淡而低调,尽量不在杀死猎物之前惊动它们,所以狮子的毛发只会是暗淡的棕黄色,显得低调而朴素。 作为被捕食者,羚羊披上警戒色同样没有意义,因为羚羊本身并没有什么毒性,恰恰相反,它们吃起来味道还不错。既然味美无毒,华丽的警戒色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否则只会成为华丽的招揽食客的广告。 只有个别哺乳动物例外,它们可能会动用警戒色。比如平头哥蜜獾,它们的背部长有一条长长的白色毛发,明显可以起到警戒作用。作为杂食动物,蜜獾并不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还要面临许多天敌的威胁,比如狮子身材要比蜜獾高大许多,因此蜜獾的警戒色长在背部,可以让狮子一眼看见。它们之所以敢于向对手提出警告,是因为自身足够凶猛,或者带有臭腺,虽然毒不死对手,也能把对手熏得生不如死。还有一些住在洞穴里的肉食动物,出洞时往往脑袋先露出洞穴,它们的面部也会长出显眼的条纹——比如黄鼠狼的面部就带有明显的花纹,可以对敌人起到警戒作用。招惹刚刚露出洞穴的动物必然激起你死我活的搏杀。还有一种非洲冠鼠,本身无毒,却会将夹竹桃树皮中的毒液涂在自己的毛发上,等于自己给自己下毒。既然有毒,当然可以无所畏惧地警告敌人:你最好不要吃我,我真的有毒。为了起到很好的警告效果,这段有毒的特殊毛发就变成了显眼的白色,与灰色毛发形成鲜明对比,目的就是提醒捕食者千万不要看走眼。总地来说,哺乳动物对于警戒色的运用并不充分,因为它们没有强大的毒素作为后盾。羚羊就是因为无毒,狮子才可以放心捕杀。正因为如此,羚羊也不必发展警戒色。既然无毒,还能吓倒谁呢? 既然不能用毒,又不能对战,羚羊还有什么可以对抗狮子的策略呢? 自然选择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提高警惕,随时准备逃跑。现存的羚羊全部采取这个策略,凡是试图和狮子对战,或者决心把狮子毒死的羚羊,都没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后代。 正因为如此,哺乳动物很少发展出合成毒素的能力。既然无毒,当然也就没有必要用警戒色来标榜自己,那样无异于花样作死。放弃了警戒色,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进化出华丽体色的动力。 至于色彩的第三大功能——婚姻色,哺乳动物的表现同样不尽人意。 哺乳动物的毛发的根本任务是保暖,一般会随着季节变化而换毛,比如在秋天换上一层厚厚的绒毛,有助于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天。而到了春季,又该脱去厚毛,换上一身单装,免得在夏天中暑。如此大规模的换毛,是一个系统性的全身工程,成本极高,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供应。所以,哺乳动物不会轻易换毛,就算为了交配也不行。毕竟哺乳动物的寿命相对较长,多数都能经历好几个交配季节,为了一次交配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很难在有生之年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哺乳动物很少为了交配而换上一身全新的毛发。既然如此,它们的毛发颜色也就不会因为交配而发生变化,因为毛发染色必须与毛发生长同步,而不是像人类在理发店那样,在毛发生长完成之后再把它染成其他颜色。 有些雄性哺乳动物与雌性的毛色不同,但不是专门为了求偶,而是为了炫耀与展示,比如雄狮华丽的鬃毛,就算非求偶季节,也照样华丽。哺乳动物在求偶时主要依赖其他性信号,比如独特的气味,或者深情的吼叫。实在不行,还可以霸王硬上弓。所以,哺乳动物不会为了交配而披上鲜艳的婚姻色,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会进化出有助于交配的鲜艳绿色。 综上可知,哺乳动物既不会进化出绿色的警戒色,也不会进化出绿色的婚姻色,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即伪装色与保护色。 客观而言,哺乳动物确实需要毛发的保护,比如炎热沙漠中的胡狼,其毛发的颜色和沙子的不相上下。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即哺乳动物的毛发具有伪装和保护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高等植物为地球陆地定下了绿色的基调。在树叶和青草构成的绿色世界里,绿色的毛发应该是最好的保护色。请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绿色的羚羊静静地蹲在绿色的草丛中,难道不是最佳的自我保护策略吗?或者一头绿色的狮子,悄悄地穿过绿色的草丛,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猎物,难道不是最佳的攻击策略吗?也就是说,披上一身绿色的毛发,无论对于捕杀猎物,还是逃避追杀,都有很好的伪装效果。可放眼世界,我们找不到一头绿色的狮子,也找不到一只绿色的羚羊。不只是狮子和羚羊,而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全部都没有进化出绿色的毛发。它们居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具有最佳保护效果的绿色,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其实绿色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是有保护效果的,例如树懒,由于行动缓慢,毛发中间长满了细细的绿藻,给身体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当树懒慢吞吞地在树上移动时,就像缓缓摇动的树影,明显可以起到迷惑对手的作用。树懒行动如此缓慢,却依然能够存活到现在,满身绿藻应该功不可没。军人在执行秘密任务时,也会穿上绿色的迷彩服,可见绿色确实能制造有效的伪装效果。 那么哺乳动物为什么没有进化出绿色毛发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哺乳动物没有绿色毛发,不是因为绿色毛发的保护效果不好,而是因为哺乳动物缺乏合成绿色色素的能力,以至于树懒不得不借助绿藻来给自己染色。 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为色素理论。 那么哺乳动物为什么没有进化出合成绿色色素的能力呢? 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许多绿色动物。除了蝴蝶之类的昆虫,还有绿色的脊椎动物,比如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我们都见过绿色的热带鱼,比如孔雀鱼,还有绿色的蜥蜴和蛇。与哺乳动物的区别在于,它们都没有毛发,绿色直接从皮肤或者鳞片中产生,而皮肤色素则由色素细胞负责。其中有一种叫作彩虹色素的细胞,可以展示彩虹般迷幻的色彩。没有哪种单一色素可以制造出复杂的色彩效果,彩虹色素细胞当然也不例外。彩虹效果不是某种色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反射板作用的结果。 彩虹色素细胞中存在大量的微型反射板,可以将外界光线用复杂的方式反射回去,从而呈现从银白色到彩虹色等不同的迷幻效果,特别是与其他色素互补时,更是可以混搭出各种精致的色彩,这是青蛙和热带鱼的主要显色机制。也就是说,绿色青蛙的皮肤中并不含有绿色色素,而只是彩虹色素细胞在起作用。 与此类似,鸟类羽毛中也没有绿色色素,但鸟类照样可以展示华丽的绿色,因为羽毛主要依靠光的衍射作用展示色彩。相对于哺乳动物的毛发而言,鸟类的羽毛表面积比较大,可以构建细微的衍射光栅,再与色素结合,就可以呈现鲜艳的绿色。 由此可见,虽然许多动物都有绿色外衣,但都不是绿色色素作用的结果,而只能依赖其他途径。麻烦的是,这些显色途径在哺乳动物身上几乎被全部堵死了。 首先,哺乳动物身上披满了毛发。我们很少看到哺乳动物的皮肤,这导致皮肤中的色素细胞没有直接展示的机会。所以,哺乳动物放弃了彩虹色素细胞,同时也失去了制造迷幻色彩的能力。其次,哺乳动物的毛发过于纤细,无法像鸟类羽毛那样构建微妙的衍射光栅,因此也无法像鸟类那样展示复杂的色彩,当然也不能调配出绿色效果。这两大因素导致哺乳动物的毛发看起来相当单调,它们的色彩只能由毛发中的色素成分决定。 哺乳动物的毛发色素由皮肤色素细胞合成,主要有两大类色素:一类叫作真黑色素,主要呈黑色;另一类叫作褐黑色素,主要呈棕黄色。因为彩虹色素细胞的缺失,哺乳动物只能在这两种色素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不同的色彩。真黑色素含量较大时,毛发就会呈现黑色,否则就呈现棕黄色。如果两种色素都缺,就是白色。这三种色彩几乎决定了所有哺乳动物的毛发色彩模式,要么黑色,要么棕色,要么白色,要么混色。比如白色的北极熊、黄色的橘猫、棕红色的小熊猫,还有一些混杂结果,比如灰色、茶色等。当不同色彩随机出现时,就是花色毛发,比如狸猫的毛发。不同色彩按照某种规则出现时,就会呈现条纹样式,比如斑马。无论怎么混搭,都绝不可能呈现绿色,因为绿色是最难构建的色彩,所以哺乳动物没有绿色的毛发。 这就是色素理论给出的答案。 你不能说色素理论错了,相反,色素理论是最接近真相的科学解释,不过不是最好的科学解释。因为色素理论只是提供了生化层面的原因,也就是近因,而我们需要的是远因,或者说终极因。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哺乳动物缺乏合成绿色色素的能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哺乳动物缺乏绿色色素,是因为绿色并不会对哺乳动物起到保护效果,这个观点可以称为无效理论。 无效理论认为,哺乳动物不是蜥蜴,无法在树叶上生活,而只能生活在树干上、地面或地下,包括水中,在所有这些环境中,绿色都没有保护作用。既然如此,它们何必进化出绿色的毛发呢? 无效理论却无法解释草原上的兔子或地鼠,它们主要在草丛里活动,绿色肯定有益无害,所以,无效理论并不能让人信服。 与无效理论相反的是高效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绿色不是没有保护效果,而是保护效果太好,结果大家都在草丛中迷失了自我,甚至都找不到配偶在哪里。也就是说,绿色走向了婚姻色的反面,以至于影响了哺乳动物的求偶与交配工作,自然得不到进化的机会。 这种解释同样缺乏说服力。许多昆虫都生活在草丛中,并且全身都是绿色,它们从不存在交配困难的问题。毕竟看不见对方还可以听得见对方,听不见还可以闻得到。动物彼此交换性信号的方式很多,叫声和气味都可以发挥作用。总而言之,影响交配绝不是很好的理由,否则所有保护色都应该被淘汰。 既然绿色有资格作为有效的保护色,那么哺乳动物为什么不去合成绿色色素呢?毕竟我们抬眼所见,到处都是绿色的植物,说明合成绿色色素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生化鸿沟,哺乳动物为什么不去实现这个“小目标”呢? 有一种理论认为,哺乳动物之所以没有进化出绿色的毛发,不是不能够,而是不需要,因为哺乳动物基本都是双色视觉,通俗地说就是色盲。红色光谱和绿色光谱的峰值非常接近,哺乳动物把这两种光谱做了简并处理,当作一种色彩来看待,所以表现为双色视觉。在双色视觉动物的眼里,绿色的保护价值基本可以忽略。因为无论绿色还是红色,甚至是棕色,在它们看来都差不多。 那么哺乳动物为什么会是双色视觉呢? 要想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们不妨先从哺乳动物的起源说起。 在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个人的头发颜色各不相同,有黑色、灰色、黄色、棕红色、银白色等,但就是没有绿色。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早期人类来说,绿色的头发简直就是天然的迷彩服,可以起到完美的保护作用,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放弃如此优异的自我保护装置呢? “我们为什么没有绿色的头发”,史钧老师从这个饶有趣味、看似普通简单实则深奥复杂的小问题出发,串起诸多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的进化论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能看到一个彩色的世界?为什么树叶是绿色的,大多数果实是红色的?为什么北极熊是白色的,狮子是棕色的,而非洲的斑马却有着黑白条纹?为什么哺乳动物的血液只能是红色?等,将恢宏的生命色彩进化史诗娓娓道出,揭示了不同生命会呈现不同色彩的奥秘。 为了找寻生命色彩的终极原因,史钧老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像知识丛林中的私家侦探,游走在不同的专业领域,用心寻找不同研究成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并用某种逻辑链条将它们串联起来,将零散的知识整理成一张完整的知识网络。 阅读《生命的色彩:我们为什么没有绿色的头发》,体验无疑是丰富的——烧脑又有趣。书中的知识点密集:从眼睛的进化到绿色的树叶与动物体色之间的因果关系,从不同毛色的热调节功能到红色的水果是如何让人类丢掉了尾巴……多种假说渐次铺陈,跨学科互动横向联通,叙述逻辑环环相扣,追根究底层层递进。我们感受到知识带来的巨大乐趣之外,也会为生命进化历程的曲折与壮观而惊叹不已: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都是生命历经亿万年不断适应环境、不断调整自我的结果。在递进的进化阶梯上,每个环节都充满了奇妙的玄机;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藏着一个甚至多个生与死的抉择。 史钧老师的诙谐风趣,我们在他的爆笑科普畅销书《疯狂人体进化史》中早已充分体味,新作《生命的色彩:我们为什么没有绿色的头发》知识点虽然略为硬核和烧脑,通俗易懂的行文里依然埋着不少让我们会心一笑的“梗”。我们轻轻松松便可大涨知识。 作为科普书,《生命的色彩:我们为什么没有绿色的头发》并不限于科普相关知识,更注重让我们了解知识背后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这些精神和方法是比单纯的知识更重要的思维财富,不但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视野,而且可以让我们跳出生物本能的约束,在更高的层次上观察自然、认识生命,对世界永远保持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