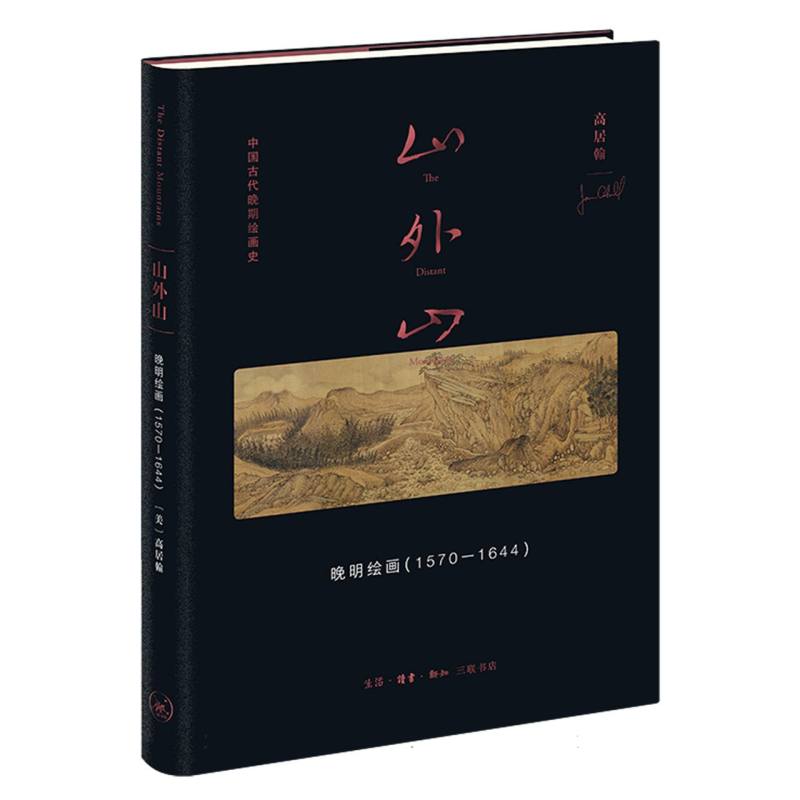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148.00
折扣价: 99.20
折扣购买: 山外山: 晚明绘画(1570—1644)
ISBN: 9787108076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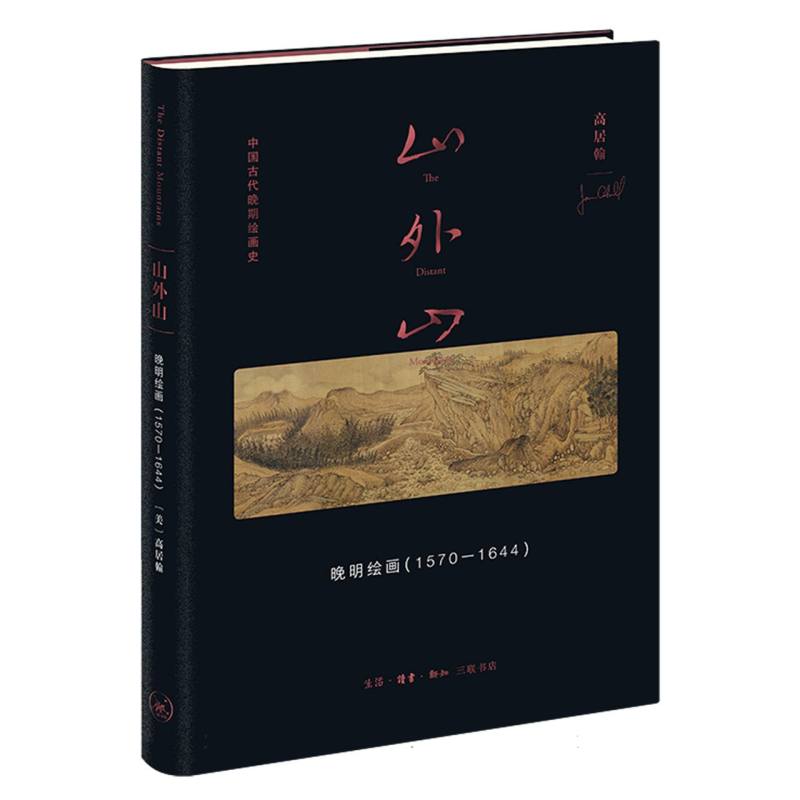
高居翰(1926—201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1997年获该校终身成就奖;亦曾长期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2010年,史密森尼尔学会授予其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在亚洲和近东艺术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高居翰教授的作品融会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重要作品有《图说中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画》等。
董其昌的南北两宗论 (选自第一章第六节)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董其昌,并曾数度论及他的画史理论,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从历史人物、画论家以及画家等多重角度,以更充分的篇幅探讨他。眼前,我们仅须指出,1570 年代至1580 年代期间,董其昌拜松江一地内外的鉴藏圈之赐,得以培养其艺术造诣,最后,他甚至成为此一文圈的中心人物——或更确实地说,是晚明时代整个艺术圈的中心人物。有关我们上面所引的论画著作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相关的著述,董其昌大多是极熟稔无疑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这一类的讨论活动,但上述著作仅录其片段。早年在松江时,他可能与何良俊有所接触,另外,他极可能也认识较他年长二十七岁的詹景凤,因为他们二人与王世贞、莫是龙都有交情。与詹景凤“两派”论的结构及名单相比,董其昌南北二宗的说法显得极为接近,似乎不可能对詹氏的说法毫无所闻。虽然董其昌的理论最初付梓的时间为1627 年,但是此一想法成形的时间,却颇有可能是在1598 年前后,仅仅比詹景凤1594 年的书跋晚了数年。当时的松江文圈在建构画史的规律性时,可能存有一种普遍的模式,而董其昌与詹景凤二人的理论可能就是根据此一模式变化而来。无论如何,董其昌理论最初的说 法,读起来像极了詹景凤书跋的缩版: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伯驹、伯兄弟,以至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雅澹,一变钩染之法,其传而为……荆、关……董、巨、米家父子(米芾及其子米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 选择两个彼此互不相属、但却平行发展的绘画传统,而后加以追根溯源,这样的思考模式,对于董其昌的历史观以及他对自己历史定位的看法,都是极为必要的。前面已经指出,这样的观点容许已经停滞或过气的风格传统再兴,使得已经遁入地下的绘画潮流得以复活。以此观之,元代大家可以说复兴了董、巨以及其他被遗忘了数百年之久的早期传统;同样地,董其昌也会宣称自己复兴了元代大家的风格,并且也超越了自己近时代的风格。 但是,如我们先前所见,这种对待画史的模式并非前无古人。董其昌思想中的新意,主要在于引进禅宗二派的分法,以其作为追溯画史系脉的典范。即使如此,此一看法并不是空前的创见;宋代的文论家严羽早已引此作为区别诗中两大传统的基础。而严羽所属意的,乃是极于盛唐的一脉传统,正好与禅宗的南宗或“顿悟”宗相对应。此派的诗传统力主严羽所称的“第一义”,亦即以一种发乎自然的方式去感知现实的世界。严氏极谨慎地辩称,他只是“以禅喻诗”,但在同时,他又刻意将自己心仪的诗家归纳为禅宗的南派,讲究以比较直接、直观(intuitive)的方式寻求解悟。 董其昌也大同小异地指出,将绘画分为南北两宗,乃是一种关系的类比,不过,他的用意更深一些:按照他的分法,当所谓北宗的画家以类似禅宗“渐悟”的方式,逐渐累积到成熟的技巧时,南宗画家则无须经历如此艰辛的学习过程;拜个人教养与美感所赐,他们本身就具有一种直觉理解的能力,而相应体现在画作上的,则是种种非刻意经营、发乎自然的风格。由于这些特质与宋代以降画论对业余文人画家所称颂的特色大体相同,因此,任何读者在阅读董其昌的分类方式时,约莫不难看出,董其昌笔下的南宗即是暗示,且几乎等同于业余文人画运动。不过,董其昌利用禅宗作为类比,则规避了以业余与职业二分法为基础所会带来的一些困境。此时,业余、职业二家所形成的大脉系,早已建立,少有质辩的余地,同时,一些问题重重的细节,例如应当如何为荆浩与关仝正名,将其纳入业余画家之流等等,如今也都被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在此,荆浩、关仝与“顿悟”一派绘画的从属关系,则已毋庸置疑。今日,南北宗理论时而为作家所鄙弃,因其不符历史的发展;实则,却也因为此一立论超越了纯粹历史的层面,反而正是其最大的成就。 在其文集《容台集》之中,董其昌有一段较长的文字,其中,他进一步将南宗的地位与业余主义(amateurism)作直接的印证,不过,他还是与詹景凤不同,并未以“利家”、“行家”区分画家。他所追溯的乃是“文人”的宗脉,并且以之对抗另一个未被命名的脉系: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李公麟)、王晋卿(王诜)、米南宫(米芾)及虎儿(米友仁)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黄公望)、王叔明(王蒙)、倪元镇(倪瓒)、吴仲圭(吴镇)皆其正传。吾朝文(徵明)、沈(周)则又远接衣钵。若马(远)、夏( )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李思训)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嫡子”、“衣钵”、“正传”等用语。关于“正传”一脉,前面已经引过杜琼及何良俊的著作,不过,真正一劳永逸建立正统观念的,则是董其昌;为此,他在画史中追根溯源,同时,他还以身作则,自奉为同时代画家的典范,并且为后世的追随者铺下正道。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的是,这些追随者迄今仍被称为正宗派。在上面的引文当中,董其昌谦逊地避开了自己的定位,并未将自己定为正传脉系在晚明阶段的继承人,反倒是他的朋友郑元勋(1598—1645),为他下了注脚:“国朝画以沈石田(沈周)、董思白(董其昌)为正派,可以上接宋、元。”上引董其昌1627 年之南北宗论,即首见于郑氏所编纂的文选。 不仅如此,董其昌也避免将他理论中的北宗或“非文人”(uncultivated)脉系,用来归纳明代的画家,正如詹景凤也仅仅是在“作家”的名单之末,约略提及戴进和周臣二人;其他有几位谨守董其昌的分类方式,比董其昌略晚,但格局却更大的画论家,也是如此。不过,董其昌也在别处明确地表明,他对戴进虽有敬意,但是,在他个人看来,戴进殁后,浙派整体即急速趋于没落。他在一篇画跋中题到,浙江一地在元代期间,确曾产生过几位画坛的佼佼者,不过,他也继续说道:“至于今乃有浙画之目,钝滞山川不少,迩来又复矫而事吴装,亦文(徵明)、沈(周)之剩馥耳。”此一评析颇为深刻,正符合董其昌一向的企图心;十六世纪浙派晚期的一些画家,似乎也确曾借用过吴派风格,意图一扫评家所责难的“日就澌灭”(decadent)等因素。这一做法终究由于画家决意不坚,无疾而终;到了董其昌的时代,浙派早已不值一评。对董其昌及其文圈而言,真正意义重大的对手反而转向了苏州一地(与其他各地相比)。在他们认为,吴派自从沈周与文徵明的时代之后,也已趋于衰败;这是自从十四世纪以来,绘画“正传”首度由苏州转向了董其昌文圈所在的松江府及其治下的华亭县。 就此观之,董其昌在南北宗论及其他著作中所持的论点和艺术史观,乃是从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情境中衍生出来的:在其二分法背后,预伏着稍早评家的论点,也就是拥浙或拥吴两派,不过,到了董其昌所在的时代,浙派早已过气,而吴派画家也已丧失其“嫡派真传”的正统性。浙、吴两派最后都是盛极而衰。这样的划分方式,一方面包含了一种颇为合理的认知——也就是画派的形成,大都以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宗匠作为开端,最后则结束于能力较弱的创作者——另一方面,则是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模式,也就是以朝代的兴亡作为画派兴衰的范例。按照中国人记史的方式,前朝的兴亡始末乃是由后朝的史家所载录,而且,每一朝代大抵都是由圣祖、明君所创,最后则亡于积弱无道的昏君。同样地,表现在艺术方面,评者往往以近代及当代的画家为对象,极尽攻讦之能事,认为他们继承了固有辉煌的传统,但却促使其走向败亡的命运。以元代画家及批评家为例,他们虽未反对前朝(宋代)所有的风格,但是对于南宋末期在诗、书、画方面所表现的“衰蹇之气”,却有所不满。 而当画坛的处境到了已经被认为是病入膏肓的时候,其解决的良方总是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一洗画家所承袭的“近世谬习”,另外,也希望重新以较有系统的方式,专研早期画家较为纯粹的创作。董其昌和他的文人圈子便是以此作为标的。他们首先要求的,便是对已经笼罩画坛主流达百年之久的吴门画派进行口诛笔伐。 晚明的中国,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改朝换代巨变,朝廷体制的松动,文人思潮活泼、多元而富批判性,艺术家与政治的关系诡谲而复杂,各种景况造成了画坛空前的大震荡,为晚明绘画赋予了特殊的属性与活力:较诸以往而言,此一时期的绘画更为知性化、自觉、内省,不但深具感染力,且极引人注目;而晚明画家在创作时,也往往带有极强的、针对艺术史和画论的自觉意识。此一阶段的作品,虽不像明代稍早或宋代作品那么具有“娱乐价值”,而且在画作表现方面也显得较为复杂,但他们也却以极为错综的方式,与传统画史建立起关联,同时,也与当时的文艺理论结合,形成独特的互动关系,使绘画成为此一时期特受钟爱的一种文化游戏。 高居翰在本书中深入晚明罕见的多重艺术史情境,条分缕析当时不同类型/流派的画家及其令人震撼惊异的绘画图像,如相互对立的苏州和松江两派,在晚明“用艺术活动替代政治活动”的董其昌,以及当时各种流派中的业余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中九友、吴彬、蓝瑛、陈洪绶等。尤其对核心人物董其昌进行了极为全面的研究,包括其人、其作、其画论以及其对画史的影响,高居翰表示:“中国画论对于自己画史的归纳,最终总结于董其昌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在对晚明绘画广泛而详尽的叙述中,揭示出这一时期的中国绘画,在形式、内涵、意义以及实践上,所达到的空前未有的复杂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