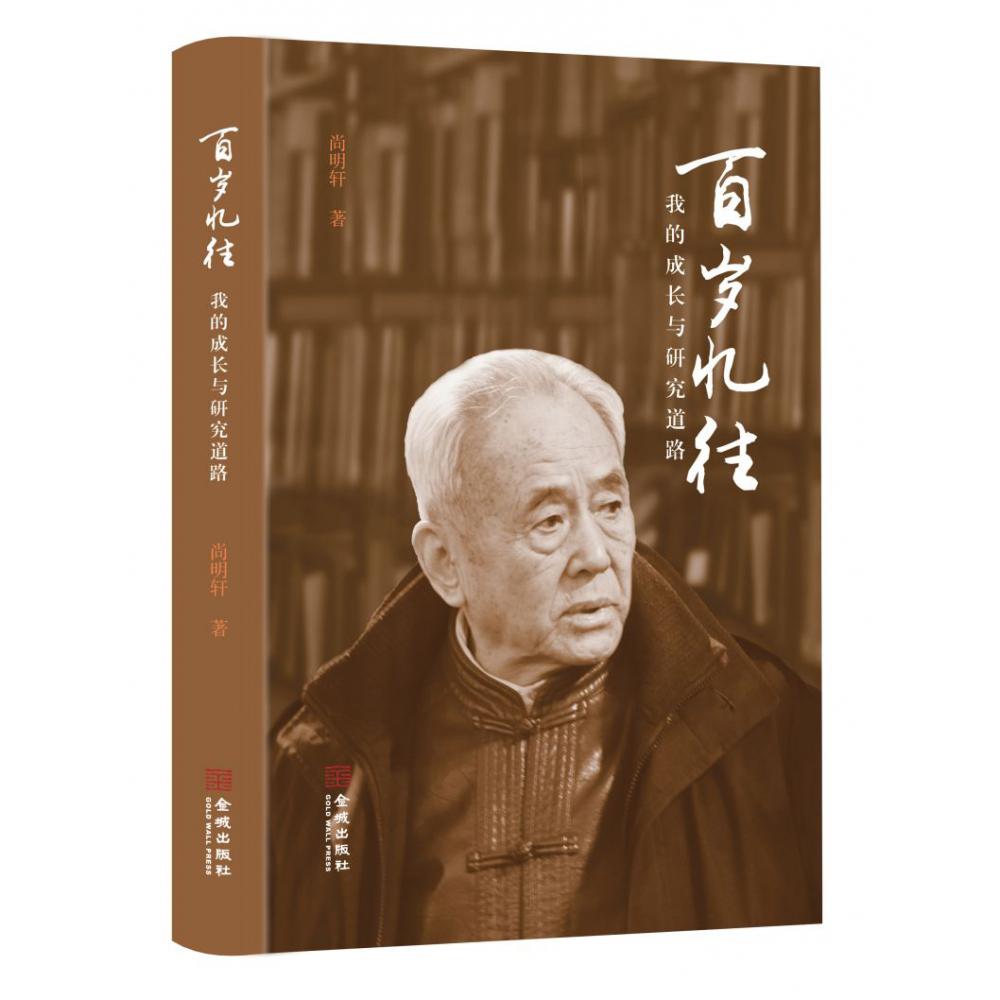
出版社: 金城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9.20
折扣购买: 百岁忆往:我的成长与学术道路
ISBN: 9787515521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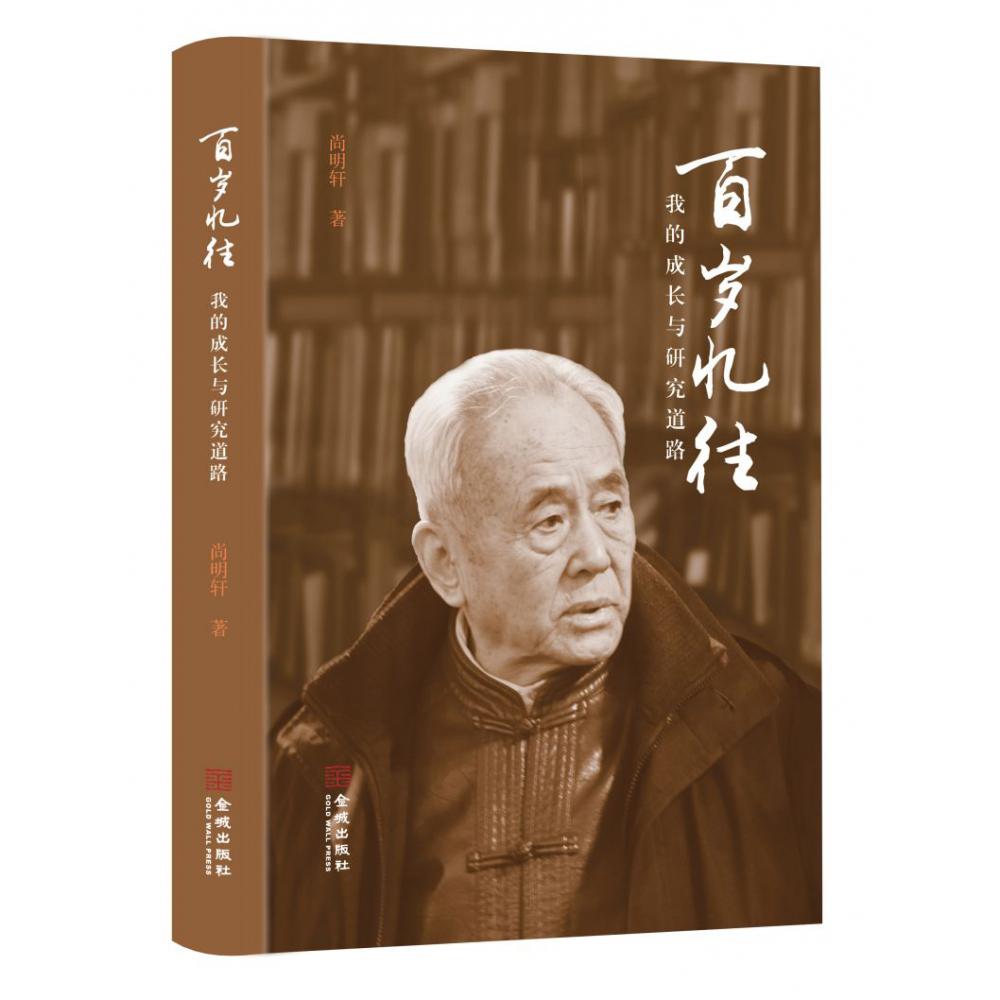
尚明轩,1921年10月生于河南许昌,1948年6月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3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名誉理事及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委员会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名誉教授。1987年10月离休。代表作有《孙中山传》、《孙中山图文全传》、《孙中山年谱》(合编)、《孙中山全集》(主编)、《宋庆龄传》(合著)、《宋庆龄图文全传》、《宋庆龄年谱长编》(主编)、《廖仲恺传》、《何香凝传》。
1956年10月,我走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在一座有高大门楼的深宅大院内的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报到,成为该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从此,我又开始转向史学研究工作。 在尚未到近代史所报到之前,曾与我在中央税务学校工作过的领导、刚担任中央劳动大学校长的罗青同志,为了请我去该校主持政治教研室工作,曾亲自到西郊我的住处相邀;在我刚到近代史所后,他又跑到近代史所他的老友刘大年(近代史所副所长,实际主持全所日常工作)处,请他协助要我去他处工作,极为热情。为此,刘大年同志专门征求了我的意见。但此事有关个人兴趣与终身职业,我婉言谢绝了。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在明朝是宦官专权的特务机构所在地,有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曾在这里被囚禁;清朝末年是军机大臣荣禄的府邸;到民国时期,又先后成为黎元洪的官邸、胡适的寓所。院内有多个完整的四合院,非常气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那里就成了一个潜心治学的府地。我在离休前的三十多年里,一直在此工作。其中,前期八年还曾在此安家居住,对这个院落相当有感情。2019年1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12月初,近代史所搬到了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2号楼(同中国历史研究院和所属的六个研究所在同一个大院)。 近代史所正式成立于1950年5月,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又是国际知名的学术研究部门。它承接延安史学的脉络,主要以华北大学研究室人员为班底,具有多位对历史学造诣很深的教授和学者。他们立足于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曾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推出了一部部精品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学界瞩目的重镇。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任首任所长,直到1969年去世。所里的主要研究人员有刘大年、荣孟源、王禹夫、刘桂五、钱宏、贾岩、唐彪、王可风、牟安石等。之后,又有罗尔纲、黎澍、李新等多人进所。范文澜是这个研究所的组建者和精神领袖。它刚成立时,研究人员不过十余人。截至1955年10月,全所共有研究人员、编辑58人。到1956年底,我进所时的所有人员,还是这58人。 我是饱含热情并自愿到近代史所工作的。所长范文澜以其倡导的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为近代史所树立了优良的严谨学风。所里专家们积极奋进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感染和熏陶了我,鼓舞和激励了我。正是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熏陶和启迪下,我坚定了将研究中国近代史作为自己工作目标的信心,追求能够做个学问家,从而促使我能够安心地成长起来。我满怀激情地想把这种学风发扬光大,并砥砺前行。我的学术研究生涯从此开始。 屈指算来,我在近代史所迄今有长达65年(包括在职31年、离休34年)的时间,在职、离休都一样读书和做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近代史所学习、工作和生活。我成长在近代史所,经历了近代史所的发展变迁、沧桑辉煌。所里的房舍环境、良师益友、史坛学风等,无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难以忘怀。我是怀着既爱又痛的心情,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的职业生涯,度过了甜酸苦辣的长期生活。可以说,没有近代史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近代史所怀有深厚的情怀。我爱历史学,我爱近代史所的学风,我爱近代史所。 中国自古就有编写史书、修撰志书的优良传统。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最好的老师,可以鉴古知今,资政育人。它对于保存和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启迪和教育后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我来就,对历史是怎样发生兴趣的呢?追其缘由,说来话长。如在第一章所述,主要是出于幼年经常听父亲讲述历史故事,以及敬佩可歌可泣的岳飞、文天祥和孙中山等历史人物。之后,在我读小学和中学的少年时代,通过学习教科书,接受师长的教诲,在仅仅对英雄人物们有些懵懂认识时,就对他们非常推崇和敬仰。 我在上学以后,对历史书就更有兴趣了。那时还是民国时期,每周一都要念诵《总理遗嘱》;读中学时,尽管时局动荡,但是通过上“三民主义”课,开始理解了孙中山为国家谋幸福的远大理想;后来读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系。可以说,我是逐步走上了充满乐趣地爱读历史书籍的道路,对历史有了深厚的感情,从而打下了治史问学之路。 在大学阶段,我的兴趣本来是研读明史,如前所述,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晚明的农民起义》,从揭露明末阉党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崩溃,论述到明末农民起义发展的过程,歌颂了农民领袖李自成及其所执行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天津两所女子中学高中部讲授历史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继而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高校讲授中国革命史课程。通过这些经历,我对中国近代史及孙中山等这些人物,有关他们的生平事迹、思想理论和精神人格等,逐步有了较多的了解,也就逐步产生了要从事研究这些近代人物的想法和浓厚兴趣。 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理解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察古知今”“鉴往知来”,为着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进。可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喜爱历史,研究历史的根源,就是由此而产生,并从此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我到近代史所后,被分配在现代史组(后改为现代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组长是董其昉,干事是王来棣,全组共有13名研究人员。 1972年,现代史研究室改为民国史研究室。1973年,山东大学孙思白教授调入近代史所,并任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那时,全所各个研究组都是采用集体撰著模式,大家围绕着一个专题分工合作,集体完成一部专著。现代史组计划撰写《五四运动史》一书,预定三年时间完成。先后参与此书者有十多人,或提供资料长编,或撰写章节初稿。这是我到近代史所后参与编撰的第一本书,所承担的是《巴黎和会的骗局》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两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从“巴黎和会”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当时,出版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都是集体的智慧,不署个人的名字,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史》,也是以编写组的集体名义出版的。 在收集和整理资料过程中,我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很感兴趣。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幼年对英雄人物的尊崇,促使我对他们尤其是对孙中山这一历史人物,特为重视,想方设法收集到涉及的有关资料,研读有关方面的专书。日子一久,便促使我逐步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孙中山的生平和事业方面。 当时,研究所里强调的是集体工作,反对个人单干,认为那是开“地下工厂”,会遭到反对和受到严格批评。因此,这项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悄悄地进行,难能得到顺利开展。 随着时间推移,在实践中发现集体撰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改革开放后,个体价值得到了尊重。个人择题进行研究和著作,可以与集体撰著模式并存。 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涉猎有关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物的有关史籍,着手收集和整理史料,立志探究历史人物。 研究历史人物,是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从踏上这一研究道路开始,我便与研究历史人物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孙中山、宋庆龄研究资深专家尚明轩先生,回忆个人百年求学和治学历程,见证近现代中国的苦难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