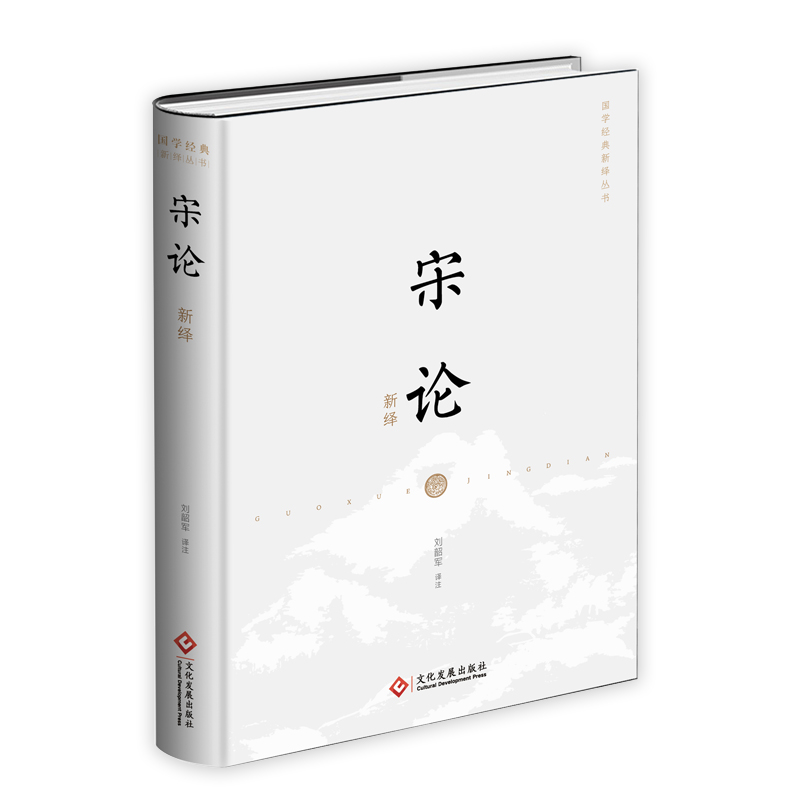
出版社: 文化发展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宋论新绎(精)/国学经典新绎丛书
ISBN: 9787514235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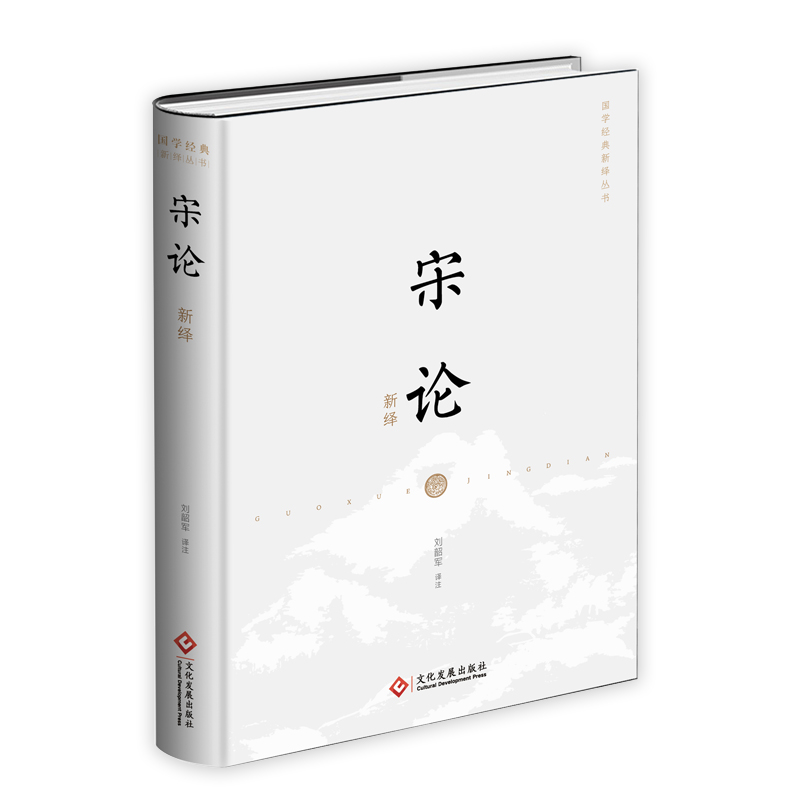
刘韶军,男,1954年3月生,山东掖县人,师从文献学大师张舜徽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研究等,出版著作《杨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太玄集注》(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太玄校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宋元韬略》(崇文书局2018年)、《月印千江——智慧度人<金刚经>》(海燕出版社2014年)、《国学基础教程》(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神秘的星象》(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日本现代老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重订庄子集注》(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纲鉴易知录》(全译主编,中华书局2012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又完成了《中国老学通史?近现代卷》、《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研究》两部著作,点校了《清经解》中的五经总义部分(共55种),都即将出版。
论仁宗 【题解】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1023 年至1063 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第六子,立为皇太子后,赐名赵祯,1023 年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期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推行“庆历新政”, 也未能成功。 宋代党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宋之朋党始于仁宗在位时的各位大臣:“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 不亡而不息。”宋代的朋党不是仅在仁宗时期,而是长期存在,到徽宗时演变成剧烈的灾祸。一般人都批评说朋党是小人加在君子头上的罪名,王夫之此论与众不同。他认为国家既要有“刚方挺直之正气”,又要有“敦庞笃厚之醇风”,这就可以使君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这就是说朋党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君主身上。君主要保持平静的态度,小心听取各种意见,做事不急迫,对人们的各种说法不要轻率听信,这样就不会让小人与君子之间形成紧张对立的关系,也就不会进一步引起朋党之争。也就是说,现实之中,总有小人与君子,不能保持纯粹无杂的状态, 问题是不使小人与君子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而这需要由君主掌控大局。 但在仁宗之世,君主对局面失控,原因在于“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有人来仁宗面前说这说那,他都容受了,“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 于是君子和小人都“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群起以言论相争,于是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亦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言满天下,蔚然可观。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这个分析说明了仁宗使此前的敦庞笃厚之风丧失,于是人们以言论相攻击,逐渐使君子、小人各自结党成群而攻讦不止,这就奠定了后来朋党之争的基础。 由君子、小人形成朋党,而又导致宋的乱政,所以王夫之又说后来神宗时的乱政,实质上是从仁宗之世开启的。神宗兴怨于天下,不是因为他有奢淫暴虐之行,只是因为他“求治也亟”,而引起“下之言治者已烦”。而“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这是对神宗变法原因的一种分析,值得研究宋史者重视。 王夫之认为,再好的制度法度,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也会产生弊端,这是“自然之数”。就拿西周初期的“成周治教之隆”来说,到了穆王、昭王的时候,也是“蛹蠹亦生于简策”。如何对待产生弊端的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起而改之就能成功的。王夫之说:“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苟循其故常,吏虽贪冒,无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士虽浮靡,无意指之可窥,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民虽强可凌弱,无以启之,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俾富者贫而贫者死。兵虽名存实亡,无以乱之,则无游惰之民以嚣张而起,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他认为制度上的弊端产生之后,不改也有危害,但改制造成的危害更大。急于变法,并不能保证变法的措施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变法必然成功。而且变法不能保证所变都是正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变法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这一点,往往是论史的人们未曾注意的。认为只要是变法就是进步的,反对变法就是保守的。这样的简单化,是不能真正把历史研究清楚,也不能正确从中总结出鉴戒的。 王夫之认为,仁宗时还有一大弊政,“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这就是实行交子。研究历史的人都称赞宋代开始使用交子是进步,但王夫之不这样看,他说:“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则官以之愚商, 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又说:“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敝纸而已矣。”他认为交子、会子都不过是纸币,凡是有纸有墨,就可以印,而且其价值也是由人们随意决定的,结果是引导人们相互欺骗,而交子、会子并不能真实对应实际的财富,所以实行交子或会子,就对真实的财富造成巨大伤害。所以这种制度到明代宣德以后, 就不复能行于天下了。 因此他总结说:“君天下者,一举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无穷,不可不审也。”这说明变法(包括使用交子和会子)的种种措施都必须慎重,不可轻率听信人们的言论,否则就有两种可能:“从善如流,而从恶亦如流。”不管是善是恶,都会造成长远影响,这是当初实行变法的君臣无法控制的,甚至还会骑虎难下。他告诫帝王们:“舜之大智也,从善若决江河,而戒禹曰: ‘无稽之言勿听。’”这才是真正的治国“大智”,有了这种大智才能“成其至仁”,而“治道尽此矣”。 仁宗时,范仲淹曾对科举中的问题,提出科举考试要先试策论而后试诗赋,王夫之认为科举要考经义、策问、诗赋,经义最重要,因为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其次是策问,因为它“有所利用于天下”;而诗赋“无所利用于天下”,是最没有价值的。范仲淹要求把策问放在诗赋之前,还是有眼光的。 王夫之是学者,所以最重视经义,实际上古代国家实行科举考试,也以经义为最重要。但大多数读书人,只是对经书内容加以“记诵”,而不能“引而伸之,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这就不能达到考经义的根本目的,“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反而使经义走上了邪路:“习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支离者旁出于邪, 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王夫之非常痛恨这种变得虚浮的经义之学。 范仲淹要重视策问,也有弊端,王夫之说:“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于是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希文之过,不可辞矣。”这一点又是范仲淹始料未及的,即提倡策问,会引起人们不按儒家正统学说来论述问题,而用儒家以外的兵家、法家等学说来回答策问的问题,王夫之认为不坚持儒家的正道,乱用异端邪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今天看来,王夫之对仁宗及其大臣的批评,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仁宗的盛治 【题解】 王夫之对仁宗的盛治,表面上是称赞,实际上还是批评,因为神宗时的政治之乱,是由仁宗启其端的。对这一点,研究宋代历史的人,认识到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实有必要认真地读一读王夫之的评论。 【正文】 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乃其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 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①,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 【注释】 ① 莫:通“漠”,寂静。民不能莫,指民心不能安宁。 【译文】 仁宗之时被称为治国的盛世,至今还让了解这个时期的人们羡慕。仁宗躬行慈爱节俭的品德,而宰相台谏侍从的大臣,都是所谓的君子之人,当时成为治国的盛世,也是理所当然的。考察宋代政治的混乱,是从神宗时开始的。神宗让天下人怨恨、留下讥评给后人的,不是他有奢侈、荒淫、暴虐的行为,只是在于他在上追求大治过于急迫,而在下的人论议国家大治已很烦琐。但是召来在下的大臣提出烦琐的治国之论,从而开启了在上的皇帝的过大的志向,则是从仁宗开其端的。而朝廷不能安宁,民众不能心静,在仁宗的时候就已是这样了。 【正文】 国家当创业之始,繇乱而治,则必有所兴革,以为一代之规。其所兴革不足以为规一代者,则必速亡。非然,则略而不详、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竞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时会之所凑,适可至于是;既至于是,而亦足以持国于不衰,乃传之数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则归咎于法也,不患无辞。其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实,民骄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有志者愤之,而求治之情,迫动于上,言治之术,竞起于下;听其言,推其心,皆当时所可厌苦之情事,而厘正之于旦夕,有余快焉。虽然,抑岂必归咎于法而别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肃之大臣以饬仕阶而得矣。士靡而亡实,崇醇雅之师儒以兴正学而得矣。民骄而不均,豪民日竞,罢民日瘠,人事盈虚之必有也;宽其征徭,疲者苏而竞者无所容其指画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无,伍有而战无,战争久息之必然也;无荐贿之将,无私杀之兵,委任专而弛者且劝以强劲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无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挂漏,创法者固留有余以养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妇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奸民为鼠为雀之啄龁,恶足坏纲纪而伤教化?有天下者,无容心焉可矣。 【译文】 国家在创业初期,由乱世而向治世转变,就必定会有所兴建和变革,以完成一代的制度。那些经过兴建和变革而不足以作为一代制度的,则必定很快灭亡。如果不是这样,制度中那些省略而不详备、因陋就简而不完善、仍处于衰弱而不强大的部分,就一定都是含有某种深意的。君主的德行、民众的心愿、时势的变化几个方面凑在一起,正好到了这一步,既然已到了这一步,也足以保持国家的不衰败,但传了几代以后就会产生出弊端了。弊端的产生,都是依据制度而出现的,那么归咎于制度,是不怕没有说法的。其作为弊端,官吏玩弄制度而不加理会,士人侈靡而没有实际的才能,民众骄纵而贫富不均,军队松弛而不振奋强大,不是破坏制度来推行私心,就是利用制度而巧妙地藏匿他们的奸邪。有志之士对此感到愤慨,于是追求国家大治的心情,急迫地打动在上的皇帝,讨论治国的方法,也竞相地在下面的大臣中出现,倾听他们的言论,推察他们的心情,都是当时令人厌恶和痛苦的情与事,而在旦夕之间加以纠正,那是令人快乐的。虽然如此,难道一定要把原因归到制度上面而另外来寻求治国之道吗?官吏对制度玩忽而不理睬,对此只要任用廉洁严厉的大臣通过整顿官吏的等级就能加以解决。士人侈靡而没有实际的才能,对此只要尊崇醇正高雅的儒家学者来兴办符合正道的学术就可以纠正了。民众骄纵而贫富不均,豪强之民日益富裕,疲惫的弱民日益贫困,这是人们的事业中盈虚变化所必有的现象,对此只要放宽征税和徭役, 让疲惫的民户得以苏缓,豪强之民就不能利用贫民有求于他们而谋利了。军队松弛而不振奋强大,有兵籍而军中没有兵员,在军中有兵员而没有战争, 这是战争长久停息之后的必然现象。没有进献贿赂的将领,没有私自杀人的士兵,委任专人为将领而松弛的人就将勤勉而变得强劲了。像这样,委任的将领是合适的人选,而制度就无不可执行了。至于制度中还存在着各种缺漏, 创建制度的人本来就是留有余地来养育天下而使天下之人的心情能够平静的。匹夫匹妇在严寒、暑热、暴雨时的怨尤,猾吏奸民像鼠雀一样啄食一点公家的财物,哪里足以破坏国家纲纪而伤害教化呢?统治天下的人,对这种情况不用计较就可以了。 【评析】 对所谓盛治,不能简单地只加以赞颂,而应冷静地从中找出问题,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历史评论。而要找出问题,就需要冷静细致的思考。如儒家说到国家之治,就要称先王,认为先王之治是最好的榜样。但所谓的先王之治究竟有哪些内容?先王治国的成功经验究竟是什么?都必须细致地加以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先王及先王之治。但也不能一概地否定尊先王的说法,认为尊先王就是保守和倒退,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国家的治理,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这都要到先王那里去观察和总结,所以, 所谓的先王之治,不是说全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也有不正确的。因此, 只能以前人的治国历史为借鉴,认真细致地加以总结,找出治国的正道, 在当今之世加以践行。 1.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论名著,文献学专家刘韶军倾力打造 《宋论》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论著作。王夫之仔细观察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把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文献学专家刘韶军从《宋论》原本中拣选出精彩内容进行全新注译评析,以使现代广大读者都能读懂《宋论》,并由此更深地理解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2.全新译注,标题新创,解读新颖,评析新锐,帮助读者轻松阅读宋代历史 本书是《宋论》的精选本,作者从原书十五卷的内容中精选七十篇并加上标题,通过题解、注释、译文、评析,详尽、细致、准确地呈现了《宋论》的主要内容,对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与读者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帮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宋代历史。 3.更正现行经典版本中的一些知识性差错 本书出版过程中,参考了一些现行经典版本。编辑加工书稿时,发现现行版本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比如:年号“端平”错写为“瑞平”,“元祐党人集”错写为“元祜党人集”,以及古今地名不一致的情形,这些错误在《宋论新绎》中都进行了更正。 4.大开本,双封面,硬精装,值得收藏 本书采用双封面、圆脊精装锁线。外封采用特纸质印刷,书名烫金;内封采用2.5毫米厚纸板,外覆特种纸,书名烫银,整体呈现厚重典雅的效果,具有收藏价值,亦可作为馈赠亲朋的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