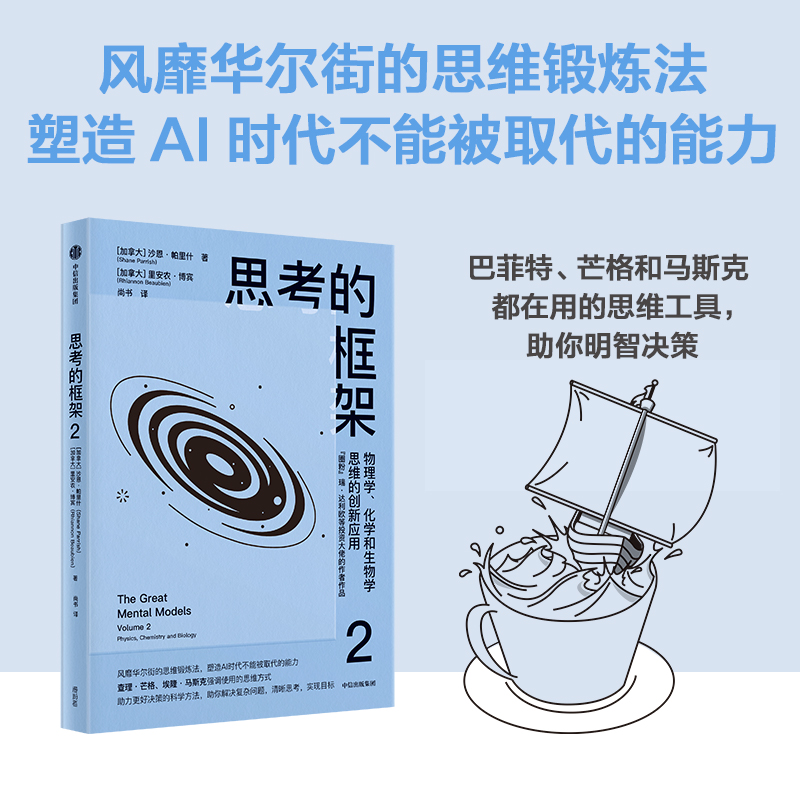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8.30
折扣购买: 思考的框架2
ISBN: 9787521766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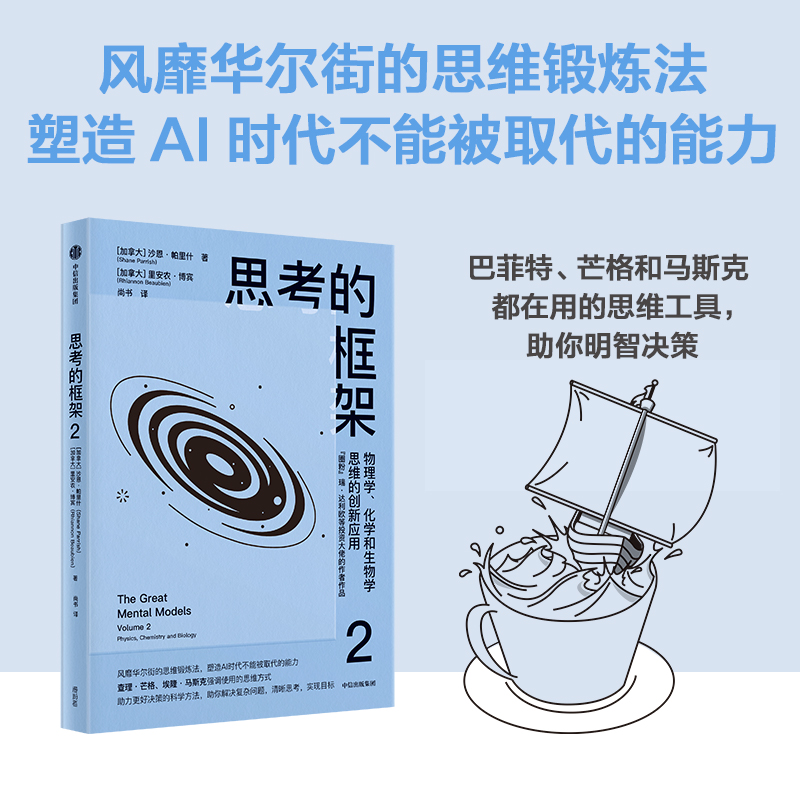
企业家、投资人、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创始人、华尔街颇有影响力的博主。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对冲基金第三点创始人丹尼尔·勒布、私募基金传奇人物查克·罗伊斯等投资大佬都是他的博客粉丝。法纳姆街开通了全网学习社区,业务遍及全球,已帮助数百万人系统地学习,他开发的“决策设计”课程已帮助数千名高管和领导者学习提升决策。
自下而上式创新 类似摩擦力和黏度模型中的对立力量视角还有什么用处呢?一个运用场景是组织效能。在一个组织当中,影响创新的力量对管理团队和一线员工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是鼓励一线加大创新力度,那你就需要关注在一线而非管理层的环境中鼓励和限制创新的因素有哪些。 福特T型车给世人留下了两笔财富:汽车时代开始的标志性形象,以及大规模生产系统。对福特和后来的通用汽车而言,大规模生产系统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到工厂工人层面的创新潜力。实际上,“车间的工人不过是生产系统中完全可以被替换的螺丝”47。大量的库存产品被堆放在地上,问题直到流水线的尽头才能得到解决。工人不是来解决问题或改进生产系统的,他们只是在那里从事机械重复的劳动,任何需要返工的工作或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留给专家即可。 20世纪40年代,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战后濒临破产,艰难求生。日本政府的期望是通过财政支持帮助企业发展,从而大幅提高出口,让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在研究了北美汽车制造商的大规模生产系统之后,丰田知道这样的生产体系并不适合他们。他们缺乏足够的启动资源和能力,无法让这么大规模的机器运转起来。不过,他们注意到了一点:大规模生产造成了大量浪费,效率低下,因为它把解决问题的时间推迟到了生产线末端,而此时再来纠错的成本是最高的。此外,在新车型上线时,往往要花很长时间调整流水线。丰田的发展专家大野耐一48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他的一个观点是要多多关注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 大野耐一发现,减少一线层面的摩擦力可以显著影响产出。“如果工人没有及时预见问题并主动提出解决方案,整个工厂的生产工作就很容易陷入停滞。”因此,要有效增加车间工人的产出,关键不在于加快工作速度或者设定更高的工作量指标,而在于创造一个更顺畅的环境,帮助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如果想让基层员工开拓创新、及时主动出击,就必须要有组织文化和架构的支撑,助力员工大胆创新。那么怎样才能为员工创造一个低摩擦力的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采取行动,创造积极的改变呢? 大野耐一注意到,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除了装配工人,没有一位技术专家真正在为汽车增加价值。更重要的是,大野耐一认为,专家的大部分工作装配工人可能都会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们能直接接触到生产线”。因此,第一步是改变生产线的作业方式,把小修小补和质量检查等纳入工人的职责。每个工人都被赋予了“一旦出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叫停生产线的能力”。 正如詹姆斯·P.沃麦克、丹尼尔·T.琼斯和丹尼尔·鲁斯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所述:“在大规模生产工厂里,只有高级生产线经理才有责任在必要时叫停流水线,大野耐一却独树一帜,在每个工作站上都挂了一根绳子,指示工人在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立即拉动绳子,停下整条装配线,接着整个团队都会围拢过来帮忙解决问题。”拉动这条“安东绳”就相当于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好比泳池里的水一瞬间从水变成了水泥,但也因此使流水线上的问题能立即得到解决。此外,在日常工作安排中,丰田也会专门留出时间让工人相互分享改进流程的想法。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长远地减少工作环境中的摩擦力。 装配线改造的结果是产出的返工率大大降低。因此,即使“每个工人都可以停下生产线……生产线也几乎没停过,因为问题都已经提前解决了,同样的差错不会再发生第二次”。这些对工人工作环境的切实改变最终提升了汽车质量和生产效率,也鼓舞了工人的士气。 士气对于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员工只有得到支持才敢于冒险。丰田在工厂车间营造了一种重视沟通和合作的环境。工人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可以根据情况快速调整工作重心。大野耐一开发的系统鼓励他们了解整个流程,对寻找解决方案、提高生产效率保持求知欲。这样的生产流程被称为“精益生产”,即“尽可能将任务和责任转移给真正为生产线上的汽车增值的工人,并建立了一个用于发现缺陷的系统,一旦发现问题,就能迅速定位到根本原因”。关注员工的工作环境是企业保持脚踏实地的一种方式。通过改变工作环境,他们可以赋权于最接近问题的人,减少组织中的摩擦力。 变革必须得到领导层的支持,每个人都需要认识到,高层提出的公司战略或者愿景等宏伟蓝图与基层工作并不那么密切相关。阐明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固然很好,但同时也需要减少工作环境中的摩擦力,以免大家觉得实现目标的路途举步维艰。 丰田设计了一种环境,“为工人提供控制工作环境所需的技能,并赋予他们持续挑战以优化流程的权力。大规模生产工厂通常意味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为工人疲于手工组装‘不可制造’49的产品,也无法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精益生产则提供了一种‘创造性张力’,工人有很多方法来应对挑战”。 在精益生产中,环境的设计和不断改善都是为了鼓励工人积极主动创新。从摩擦力的角度分析,影响工人工作环境的因素与塑造高管所处环境的因素是迥然不同的。要想改变现状,必须认识到在这种特定环境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 结论 为了达到目的,减少阻力往往比加大推力更容易。尽管往往不被察觉,但不管我们尝试做任何事情,摩擦力和黏性都会从中作梗。为了克服阻力,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更加使劲,而非采用更简单的方法—减少摩擦力或黏度。二者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好。也可以把摩擦力和黏度当作武器使用,与其加倍努力追赶竞争对手,不如通过增加阻力来拖慢他们的速度。 人们常将速度和速率混为一谈,但这两个概念其实天差地别。有运动就有速率,即使是在原地踏步也有速率。而速度还涉及方向,必须有位移才有速度。这个模型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前进的方向,而非走得多快。没人愿意沦为滚轮上的仓鼠,拼命奔跑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速率确保运动,但速度产生结果。 使用速度作为模型的前提概念是位移。向前迈一步就有了速度,原地踏步就只有速率。因此,在某一领域取得了多少进步,不是看我们现在走得有多快,而是看我们相对起点走了多远。为了达到某个目标,我们不能只求快,更应该想明白自己要去的方向。 速度等于位移的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变化量。如果某物以恒定的速率沿着直线运动而不改变运动方向,那它就具有恒定的速度。通常,在正确的方向上保持恒定速度是抵达目的地最有效的策略。不停改变方向,最终只会在原地打转。 更快达到目标 拿破仑·波拿巴50因在军事行动中重视速度而闻名。“‘军队的力量,’他表示,‘就好比力学中的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51他希望在计划的方向上更快采取行动,这一策略助他赢得了许多场战斗,改变了敌军的应对方式。他改写了传统的作战战术以实现对速度的追求,最终影响了军事战略。这里说的速度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他麾下军队的行动速度之快堪称史无前例。但这一速度是朝着特定目标前进的。加快部队调动是他整体战略的其中一环。 要理解拿破仑快速调动军队的能力是如何成就他的赫赫战功的,不妨先了解一下意大利战役。这是他职业生涯初期的一次战役,也是他毕生以速度为本策略的一次鲜活例证。正如亚当·扎莫伊斯基在《拿破仑:一生》一书中所述,拿破仑在年仅26岁时在意大利指挥了一场对抗奥地利人的战役。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军队总司令,也是第一次在战场上独立指挥作战。战前他不过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无名小卒,经此一役摇身一变,成了法国著名的领袖、保家卫国的英雄。个中奥妙便是他采用了新颖而出人意表的战术,其中不少都是受到了速度这一原理的启发。 拿破仑把速度作为他的核心作战原则之一。在意大利,他的军队既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训练有素的,因此他提出了快速行军的战斗策略。“波拿巴需要保持势头,这样两个对手才会来不及反击。”52因为打得敌人猝不及防,提升速度的策略有效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向目标快速推进也排除了潜在的障碍,因为奥地利人还来不及设防。 拿破仑的军队的行军速度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哪怕有些士兵光着脚或者衣衫褴褛。有记录显示,一个师在36小时内行进了80千米。还有一次,他的军队在4天内打了3场仗,走了90千米。在《拿破仑大帝》一书中,安德鲁·罗伯茨写道:“作战的节奏确保了他始终掌握主动权。狭窄的山谷原本易守难攻,但他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一路飞驰,势如破竹。” 拿破仑之所以在战斗中得以迅速行动,首先是因为“他在踏上意大利国土之前就对其历史和地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愿意尝试他人好的想法”。这样的熟悉程度给了他极大的灵活性,可以为保持恒定速度选择适合的行军路线。 为了快速行军,拿破仑还需要让其他人以同样的速度移动。他非常关心将士的生活和福利,一部分也是为了激励他们跟上他的节奏。他采用了各种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首先,“他从一开始就精心揣摩了如何对待麾下军队,不仅要使他们成为更富战斗力的战士,更要把他们变成他忠诚的手下”。通过“分享胜利的荣耀和展开平等的对话”,拿破仑使他们感到自己取得了其他人和其他军队难以企及的成就,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崇敬爱戴拿破仑,完全相信他擘画的愿景。速度成了集体的目标。他们都希望行动迅速,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其次,拿破仑发出的指令都清晰明确。他不仅能提出巧妙的作战策略,而且似乎天生就明白,策略奏效的前提是必须易于理解和执行。将士花在理解复杂指令上的时间越多,他们朝着既定目标行进的速度就越慢。由于随着行动的展开和战斗的日趋复杂,作战策略往往被弃之不顾,他明白清晰明确的沟通对于提升速度的重要性。 在尝试提升速度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认识并考虑到可能限制速度的因素。对拿破仑而言,有些限制因素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比如随军流动的平民太多,于是他大大削减了这部分人的数量。但还有一些并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比如天气状况。不过他行军速度的提升,一部分也要归功于此前一个世纪道路条件的改善。 拿破仑的节奏还取决于补给能否跟上。他还会尽可能甩掉包袱或多余的重量。他的军队“晚上不睡帐篷,因为军队行进得太快,无法携带搭帐篷所需的所有物件”。拿破仑的“军队时常因行进得太远而出现补给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在战斗中保持极大灵活性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资源做其他事情”。 但要完整理解“速度”这一概念,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反面的例子。对拿破仑来说,在他经历的诸多战役中,加快行军速度以提高胜率的策略屡屡奏效,但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也有其局限性。在某些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目标其实反倒削弱了他的军事能力。在意大利战役的科塞里亚一战中,拿破仑的急于求成“使法军损失了至少600人,甚至可能多达1 000人”。1812年进军俄国更能充分说明过分强调速度所产生的局限性。 巴黎与莫斯科相距约2 490千米,是从巴黎到罗马或巴黎到维也纳距离的两倍多。在此之前,拿破仑从未发动过这么远距离的军事行动,而且此次的军队规模也堪称史无前例。为了攻下莫斯科城,他采用了惯常的策略,这也很好理解,原因有二:第一,这个策略屡试不爽;第二,在如此遥远的地方调遣如此庞大的军队,成本很高,难度不小。这场战役需要速战速决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军队没有足够的物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撑过俄国漫长的冬季。 然而,速度的复杂性之一就在于,因为方向是重中之重,规模有时会限制速度。如果必须调整方向,规模越大,调整就越艰难。 在前莫斯科的路上,拿破仑对速率的追求最终减损了他的速度。他为了快速前进而牺牲了太多,当前方道路对于军队越发凶险,目标也变得岌岌可危时,他没有充分的资源及时进行调整。克劳塞维茨在描述这场战役时指出,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前损失了1/3的军队,在莫斯科战役前又损失了1/3。疾病和饥渴使士兵和马匹都失去了战斗力。这还只是到达战场前的情况。 拿破仑抵达莫斯科时,起程时的40万人只剩下了区区9万人。克劳塞维茨表示:“倘若制定了更多预防措施和更好的保障规定,更谨慎地思索行军路线,他可能就不会将大批队伍都集中在同一条路上,也就可以避免一开始就如影随形的饥荒,更好地保存军队的实力。” 拿破仑的目标不仅是抵达莫斯科,他要占领并征服俄国,巩固法国的地位。这就是拿破仑失败的地方。他既没有足够的人力跟随俄国人深入其领土,也没有制订好撤退计划,于是在折返途中的惨烈交战中又失去了数千名部下。 由此看来,拿破仑的计划很不充分,徒有速率,攻占的领土却没有增加分毫。他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和俄国不断变化的战略及时进行调整和适应。回到原地从来不是什么好事,更糟糕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还失去了很多。尽管行军数千千米,拿破仑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伤亡惨重,声誉受损。不过这也在另一个方向上加快了他前进的速度,让法国不再尊重、不再需要他领导的那一天提前到来。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想要实现目标,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速率并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因为时间并非成功的唯一条件。当有人说想在40岁前还清债务时,他们可以通过做出某些财务选择来加快这个方向上的速率。然而,“还清债务”还有其潜台词,可能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在还清债务的同时维系好重要的关系,遵纪守法,保持身体健康,好在还清债务后还能充分享受生活。要弄清楚如何提高速度,必须充分思考彼岸的模样。缓慢走向正确的方向,好过飞快抵达错误的目标。 为什么要使用思维模型? 无论是在商业世界中还是在生活中,盲点更少的人往往能够胜出。 “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你看什么都像钉子。”世界纷繁复杂,事物之间彼此关联,只有通过理解多种模型才能加以解释。要消除盲点就意味着要运用不同的视角和模型来思考问题,更深刻地理解世界运转的法则。 爱因斯坦、巴菲特、马斯克、黄仁勋等一众大佬强调使用的思维工具到底是什么,怎么用? “在所有模型中,80 ~ 90 个重要的模型占了90% 的权重,掌握它们就能让你拥有普世智慧。而在这80 ~ 90 个模型中,只有个别几个含金量最高。” ——查理·芒格 “思考的框架系列”精选含金量高的思维模型,助你建立个人思维模型网络 “第一性原理是看待世界最本质的方法,它意味着你需要将事物拆解到最基础的本元上,找到可以确信的东西,或者最接近本质的东西,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往上推导。我们运用第一性原理,而不是类比思维去思考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埃隆·马斯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