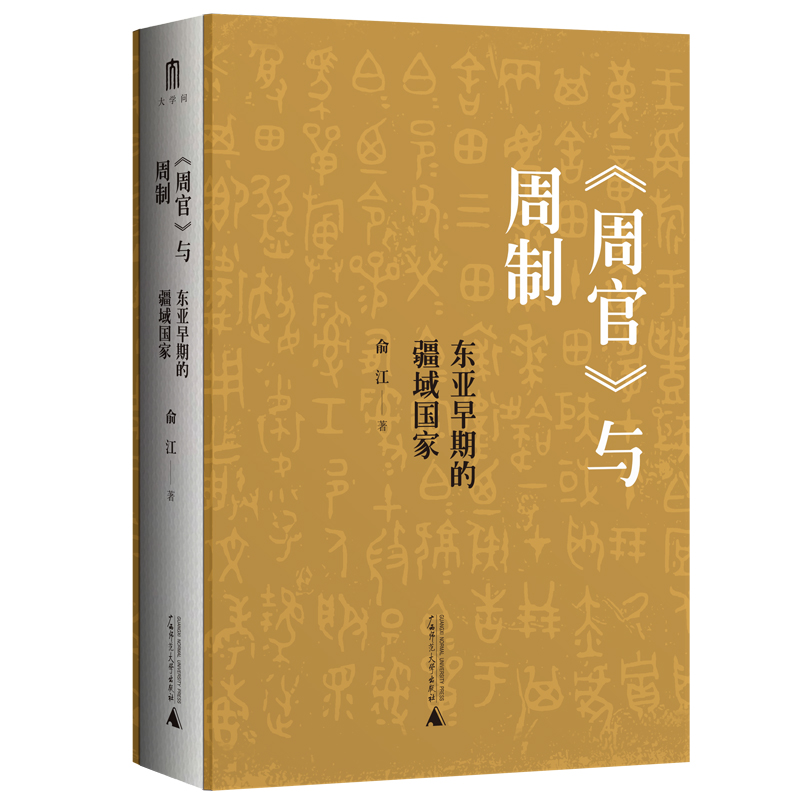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118.00
折扣价: 67.30
折扣购买: 《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
ISBN: 9787559872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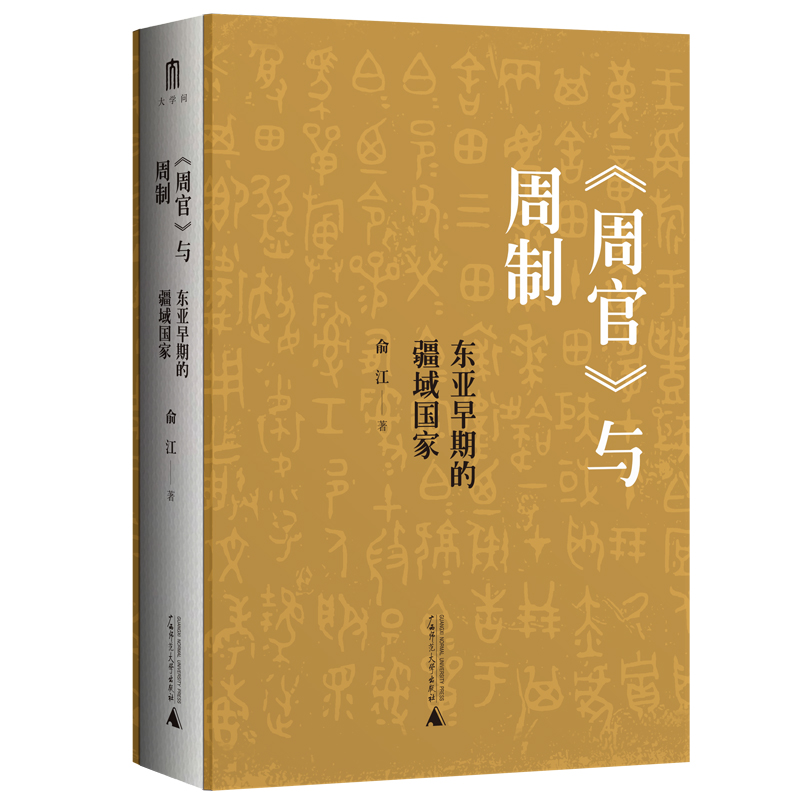
俞江,出版专著《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清代的合同》《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影印本、点校本。
本文深入探讨了《周官》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并对《周官》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首先反驳了《周官》出自“山岩屋壁”的传说,认为《周官》不可能是民间高人所作,而是基于周大宰官署保存的官制档案编纂而成。文章强调《周官》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其体系性影响了中国官制两千多年,并认为《周官》是系统认识三代制度的唯一途径。作者提出,由于现代学科体系中缺乏对《周官》研究的定位,导致了《周官》学研究的不足。文章还讨论了研究《周官》所需的特殊方法,包括传统的解经方法和制度史的分析方法,并强调了制度本身的真实性和系统性。最后,作者呼吁更多学者关注《周官》的研究,以充分挖掘其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价值。 ——编者按 《周官》学探幽:古代制度史的钥匙 《隋书·经籍一》说,李氏献《周官》 一书给河间献王。这个李氏,连名字都不全。于是有了《周官》出自“山岩屋壁”的传说。此说断不足信! 《周官》真不是哪个“民间高人”能作。从未在朝堂上站过一天的人要写此书,纯属天方夜谭! 张爱玲在她的《红楼梦魇》 中说:“《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这话是否过了些,我不敢判断。但没有豪门世家的生活经验,连续写小说尚不能蒙混过关,何以有人会相信专论官制的经典,居然出自江湖高人。今文经学家说《周官》是刘歆或孔安国等人伪造。在《周官》中篡改个别文字,或许难免。说哪个人全本伪造此书,实在是过分抬高此人的才华。要我说,即便是周公旦,手边若无官方档案可资查阅,也断不能办。无论刘歆或孔安国如何大才,也无力撰出此书,除非他们得到了周大宰官署的职文簿籍。若如此,此书也就不伪! 《周官》既然称得上“六经”之一,它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就是一等一的。《红楼梦》虽然是一等一的伟大作品,但它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岂能跟上古经典相比。然而,世间有“红学”,却无“《周官》学”,岂不怪哉? 一、何以没有“《周官》学”? 《周官》遭冷落的主要原因,还是它的重要性未得充分说明。有人断定它全是伪书,说它不必读。有人断定它真伪参半,说它无法读。今本《周官》约五万字,就算大半是注文如果它的珍贵程度与《周易》《尚书》比肩,或者只要与《老子》《论语》一样重要,人们断不 敢不读。须知,在古文《尚书》的性质不明之前,没人因为《尚书》中有可疑文字,就敢说《尚书》不可读。现在断为今文《尚书》的篇章,如《金縢》《吕刑》等,仍有明显的后人添加文字,也没人因真伪参半,敢说无法读。所以,无法读只是不必读的借口,若文献足够重要,虽不可读,也非读不可。《周官》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周官》的底子,是周大宰官署保存的官制档案。未毁之前,由深谙周官制之人依据档案编纂而成。自两汉经师至近代的周史专家,皆深知《周官》的珍贵性,但还不够。 金景芳先生早年的认识,很能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那时他认为,《周官》中“保存不少 极为珍贵的古史料”。但他在晚年改变了看法,说:“《周礼》 一书很可能是西周乱亡时,某氏得见大量官方档案所作。”甚是! 重申这一判断尤其重要。《周官》一书具有极强的体系性。 某种意义上,它的体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官制,明清以吏、户、礼、兵、刑、工设置六部,仍是摆脱不了《周官》的体系约束。而《周官》的体系是由三百多个官吏职文搭建起来的。无法想象,没有原始档册的支撑,谁能凭空臆造。且不说职文,光是臆造这三百多个官名都难。考虑到《周官》的体系性,不得不承认,该书编纂者是以较完整的官档为基础。 至于它究竟编纂于何时,何人主持,这两个问题是次要的。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影响《周官》的根本性质。以为此书的编纂时间在战国,就将这一等一的经籍视为末流,是不通之论。 可以假设,若周的官制档案完整地保存到西汉,由汉儒编纂此书,此书照样是经,地位至少在各种传、记之上。反过来说,若没有周的官制档案,就算孔子欲纂此书,也不可得。事实上,战国时期的大儒,如孟、荀等人,对周的官爵制度也只知皮毛,原因就在于周官制在战国时期已不是平常人可知。 孟、荀若生前得见此书,也只有拜服的份。 今天,人们对于新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视若珍宝,因为它们是原始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殊不知,从文化价值上说,《周官》依据的档案,其等级和珍贵程度远在新发现的简牍之上。这批档案毁于秦火,再无重见之日。 第二,《周官》是系统认识三代制度的唯一门径。《周官》与其他五经一样,是史上第一等的著作。《周官》所载是王官制度,是王制的一部分。在王制全盛时,诸侯与大夫士礼俱不足道。欲说三代礼乐,王制可代表,王制以下皆不足以代表。不知王制,不可谓知礼 乐,亦不可谓知三代文明。若无《周官》,认识王制只能凭《礼记》和《荀子》中的两篇号为《王制》的记文,二者又多扞格,莫衷一是。认识到《周官》本是一等一的著作还不够,就上古制度史而言,《周官》具有皇冠一样的地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这还有注文的干扰,真身未显。若擦拭干净,光彩尤为夺目。如果没有《周官》,后世只能通过《左传》等史籍,以及甲金文和考古去了解周制的零碎知识。万幸它保留了下来,让王制的系统研究成为可能。它是打开上古国家及制度文明最关键的一把钥匙,也是无法逾越的关隘。不过此关, 不足以谈三代文明。 由于文献阙略,因此许多国家或民族要认识自己的上古史,只能靠考古发现的器物和文字。多亏六经传承有序,中国的上古史研究才享有文献有征的优势。怎样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起来,一直是上古史的重中之重。但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存在着以文献记载为主,还是以考古资料为主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原则是不言自明的,当研究对象是古代制度时,只能以文献为主,辅之以考古资料。而文献又以系统阐述者为上,零星记载辅之。 当然,文献的真伪,另当别论。 什么这样说? 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体系性,体系性必须通过语言加以体现,而且要求系统的、阐述的语言。要满足制度研究的体系性,不但考古发掘出来的城池、聚落、器物、墓葬等不堪胜任,连甲金文也不能。甲金文达不到呈现制度所需的体系性。从甲金文中得到的制度信息,必是详者甚详,阙者照阙,只能发挥填补和校正的作用。而在六经中,唯有《周官》系统地阐述了一种王制,鉴于其他的王制皆已失传,这就足以奠定它在上古制度史的至上地位。可以说,有《周官》在,研究上古制度时,五经和其他史籍只能屈居次席。史学家一边嫌弃《周官》真伪不明,一边又不得不到它里面去找史料,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的体系性。或许有人认为《周官》阐述的仅是官制,不足以涵盖上古制度的方方面面。当然,上古制度不可能尽在一本书里。还好官制部分较完整地流传下来,才使我们体会到上古制度的复杂、多面和多层次。试想,若无《周官》,研究王制将失去层次、远近和深浅,则上古史将是何等浅薄。 以上两点重要性,都不是我的创见。《周官》在王室官档基础上编纂而来,是我缵绪先贤旧说。它在三代制度中享有无上地位,自西汉以来就公认。莽新之后,它在政治上有污名,但它在经籍中的排名,仍在第四、第五。贬低和埋没《周官》,不过是近百年之事。以上还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它在秦以后历朝政治、立法中的重大影响,牵涉太多,非本书重点,不再申论。 要强调的是,《周官》乏人研究,还因为它在现代学科体系没有归属。经学,原先居于古典学的顶端。只要有经学,就总有人研究《周官》。现在经学衰亡,以前的经典只能依附于现代学科体系。而在“六经”中,只有四部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是《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在文学史的地位至高无上。二是《尚书》,是政治史、伦理史的必读。三是《周易》,定位为中国哲学的起源之一。四是《春秋》,既是史著,也是史学史的祖宗,有上古史研究群体支撑。唯礼类的二经,即《周官》和《仪礼》,学科归属不明。现代学科中没有制度学,只有法律学。法律学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学科,法学家认为古代的礼仪或制度与己无干,制度史不归于任何专业史,而法学以外的学者不擅规范分析方法,于是大好一部经典,居然没有关于它的研究方法,没有专属的理论框架,更不用说传承有序。 二、特殊性与研究方法 (一)解经的方法 要说清楚上古的经籍,首先需要传统的解经方法。《周官》原是经学的一部分,基本的解经方法是适用的。然而,鉴于今本《周官》是经注囫囵本,不能盲目套用“以经解经”的规则。以经解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此经解此经”。比如,要解释某一字词,而这一字词在同书中多次出现,可以分析它在同书中的不同用法,来获得它的准确含义。二是“以他经解此经”。比如,某字在书中只出现一次,却在他书多次出现,可资援引。相较而言,肯定是“以此经解此经”较可信。然而,今本《周官》中窜入了大量的注文,这些注文又写 作于不同时代或不同区域,在没有把这些注文一一分辨出来之前,“以此经解此经”的规则并不当然有效。现在看来,今本《周官》号为难读,根本原因就在于经师们严格遵循“以此经解此经”的办法,却不自觉地陷入“以他经解此经”的境地,结果似是而非。当然,“以经解经”的规矩是不能坏的,否则解经就没有可信度。我的看法是,将经注分离之后,方能有效运用“以此经解此经”。若仍有疑,再参考“五经”,尤其有用的是《诗经》和《左传》。 分离出来的注文可视为《周官传》。若有疑或不足,再稽金文。 (二)制度史的方法 解经的方法存在极大不足,主要是不能为所有的制度断代,这就必须用到制度史的方法。 制度史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历史学家不熟悉,经学家也不熟悉。经学家看不出今本《周官》是经注囫囵本,就是因为看不出职文自成体系,根本原因在于不熟悉制度分析的方法。 史学家同样不擅长制度分析,纠缠于《周官》的成书年代这类问题,正是不能走入制度体系的表现。需要明确的是,制度本身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无形的,不在文字中,而在文字之下的相互联系。这种真实性的保障,就在于制度的系统性。当我们辨认出一条制度是真实的,意思不是它在历史上发生过,而是说它属于它所在的时代。把战国的制度说成春秋的,这就是伪史。把秦国的制度 经过四年的精心撰写,本书围绕《周官》复原、疆域国家、周制三大方面,系统、翔实地阐释了周制与周史,它的价值值得认真咀嚼,分享几个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周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制系统制度化的展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在本书中便明确说道:“我们研究周史与周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抱着自审与自新的决心。”《周官》蒙尘已久,向来有真伪和地位两大争议,真伪尤为要害,叱《周官》为伪书者,竟将其打出经籍的地位,以至于如今《周官》的地位、价值具不明朗。《周官》不明,周史该如何谈起,中华文明的源头又该如何谈起? 本书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即复原了《周官》职文,有力地为《周官》洗雪了被认为是汉儒伪纂的冤屈,并从经学的本质、传经与传道的辨析、解经的方法等多个角度严密而周圆地为《周官》正名。 第二个,书中有许多精彩绝伦的细节考辨。限于篇幅,兹取一例。过往编校书稿,常见藉田与籍田两种写法。一般以为藉籍二字通,便囫囵吞枣统一采用一字。看了本书,才知道不仅二字并不相通,藉田与籍田还代表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制度。此例还体现了制度史研究方法(法学规范分析方法)视野之宏大,使用之美妙。这样精妙的考辨构成了本书的主体。 上述两点或许会让人产生一种高山仰止,因而望而却步的感觉。而这里要说的第三点则恰恰能够打消这样的疑虑和畏惧,那就是不仅本书对《周官》经文的复原,让《周官》变得清晰易懂;还因系统、恢宏的视野而免于支离、琐碎、枯燥的论证,使这本释读之作同样生动有趣,易于理解。作者的笔墨并不止步于考订名物、辨别制度真伪,而是横向落点于国家疆域,纵向立足于有效时代。作者认为,能读《史记》的高中生,阅读复原后的《周官经》就没问题,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本书。 “山川名物,无非制度。”用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治经学是发人深省的。《周官》系统地阐述了王制,是中国社会制度规范设计的一次集中体现。《〈周官〉与周制》的任务就是以《周官》为主线,勾勒和整理书中的上古制度,进而呈现上古史和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智慧与精髓。但愿这本揭示周制架构及其原则精神的图书,能够让您重新审视《周官》这座文献宝藏,打开探索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