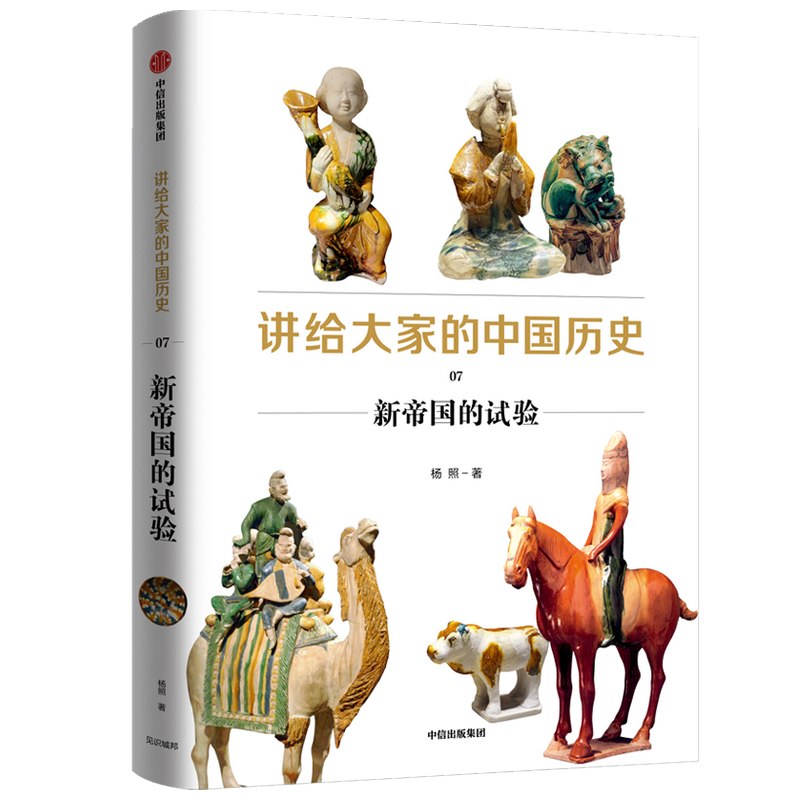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80
折扣购买: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7新帝国的试验)
ISBN: 9787521716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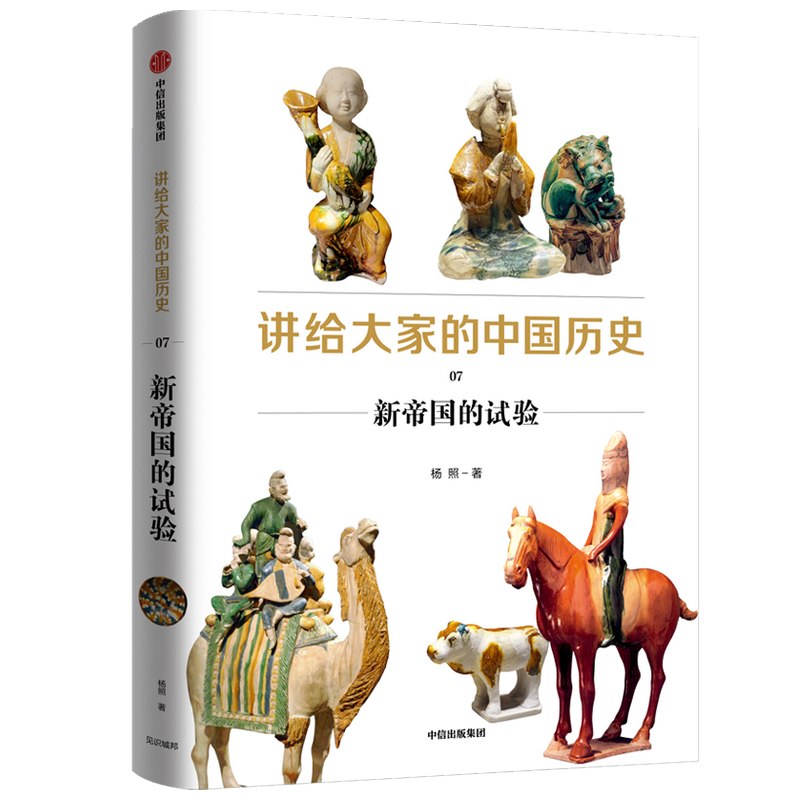
杨照,历史学家,1963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兼修考古学和人类学,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张光直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类学。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多所大学讲师,后以历史学术普及和历史写作为重心。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常年开设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经典的课程,他的历史创作延续吕思勉、钱穆的治学和教学路径,将艰深而丰富的学术成果以生动通俗的方式传达给大众读者。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杨照)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上下两千年的时代,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如何收集两千年来留下来的种种数据,而在如何从庞大的数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间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数据;留下记录数据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导致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藉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正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索出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样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还是从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进历史中才能回答的关键大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这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自不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的一部份,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认识”。意思是我自觉针对已经有过中国历史一定认识的读者,透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甚至大众传媒有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刻板印象。我试图要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选择我的中国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活在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都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是根本随时在互联网上都能查得到,二来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不然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吗?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连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 and Wh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存在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毕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而认识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逻辑。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藉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今日当下这个文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二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一块,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变貌,总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让我们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当作是斩金截铁的事实,而能够在阅读中部份地主动参与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最主要是有台湾的“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能够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开讲算起,花了超过十年。十年备课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消化各式各样的论文、专书,也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含夹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失误降到最低,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是“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 第七册《新帝国的试验》 第一讲 隋唐统一的基础 01 隋唐:具有强烈分裂性格的统合时期 中古时期的中国,有着强烈的分裂倾向,尽管在这段时期出现了隋唐帝国,然而如果和大汉帝国前后四百年的统一相比,隋唐真正维持统一的时间要短得多。隋代在589 年灭了南朝陈,正式统一,但没有多久又陷入了隋末战乱,才再由李家建立唐朝,重新统一。然后到755 年发生了“安史之乱”,这个乱局后来只能靠着实质分裂的藩镇割据来收拾,维持帝国表面的稳定秩序,中唐、晚唐已经不是大汉帝国式的统一了,更不用说后来“五代十国”的那种大分裂、大混乱。 中古社会一个强烈的特色是在帝国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强大的中间阶层。最常见的中间阶层力量来自世家大族。唐朝建立后,中央朝廷的控制增强了,加上“均田制”“府兵制”的建立,世家大族的影响确实削弱了,但这时候仍然有寺院以宗教和经济双重的实力,隐隐然和朝廷争夺对于人民的控制权。促使唐武宗进行“灭佛”的动机,从寺院那里夺回对人民的控制力,和宗教信仰的冲突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到了中、晚唐,军事藩镇兴起,除了在政治上、地理上制造了新的分裂,对社会也产生了新的分裂,再度阻绝朝廷有效地直接统治人民。因而整个中古时期,从三国开始,一直到五代结束,中国历史的主要状况,其实是分裂而不是统一。 从更长远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古夹在中间,是个异数。上古、古代,以及取代中古的近世,中国都是具备统一精神、呈现统一状态的。而从比较窄一点的眼光,只看中古史的话,那么在长期分裂中,隋唐帝国的统一又是这段历史的异数、例外。这是具有强烈分裂性格的统合时期。 02 必须由北朝追溯隋唐由来 过去传统历史观中,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正统朝代”。“正统朝代”观念建立了一套单一传承的系谱,这套系谱上列的是“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对于分裂的南北朝,是将南朝视为“正统”的。隋唐紧接在宋齐梁陈之后。如此走下来,在解释历史时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困扰,那就是忽略甚至扭曲了隋唐的来历。杨家建立的隋代、李家建立的唐代,其根据地都是北方而不是南方,他们的武力与权力不是继承南朝的,而是来自北朝,在北方崛起之后才兴兵南下,灭亡了南朝。如果照原来的系谱看,我们是无法从南朝历史中追索理解隋唐的。 建立隋唐这两个朝代的势力,都来自北周,要从北朝的历史中才能弄清楚这两个朝代是怎么来的,以及他们用什么方式取得政权、建立了什么样的朝廷。例如隋朝这个“隋”字,我们小时候读书考试常常被提醒不要写错,是“隋”而不是“随”,但为什么有这个朝代、这个字呢?那就得回到北周的历史来查考。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是杨忠,在北周时被封为“随国公”,是那个常见的“随”,而不是“隋”。杨坚篡夺了北周,要建立新朝代,很自然就选择了原有的封号“随”,可是这个字里有一个辵部(俗称“走之旁”)在中间,辵部的原意,就是走,杨坚觉得不太吉利,要走、要离开,去哪里?建立的新朝代最好是长长远远,不要变动,不要被取代,所以就决定将“随”改成了“隋”。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考史”的阶段,这个“隋”字还曾经一度成为焦点,学者们找到了一些文献或碑文的资料,用的不是“隋”而是“随”,从而提出了假设,认为“隋”字是唐朝人传抄时写错了,后来以讹传讹的。不过到了民国时期,经过岑仲勉等人更仔细的检验,确认了应该是朝代建立时就决定创造了这个少见的“隋”字为名。 明明朝代叫作“隋”,为什么唐朝还有许多写成“随”的记录?岑仲勉的解释是唐人知道杨坚创“隋”字的用意,既然“隋”没有维持几年就灭亡了,表示这个朝代还真是坐不稳政权位子,早早就上路离开了,所以就带着嘲弄的意味帮他们把辵部给补了回去。 另外一种可能更符合事实的解释,则必须先弄清楚隋朝杨家和唐朝李家在北周的关系。在这两家建立前后相续的朝代之前,他们是一起在北周带兵当官的。很像是少年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其中一个虽然后来改了名,但老朋友总是习惯仍以旧名相称。唐代留下的“随”旧字来自记得杨家是北周的“随国公”,也就提示了这两家在北周曾经并肩发展的过去。 追索隋唐的来历,就要从北周上溯到宇文泰的西魏。经过了“六镇之乱”,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元氏家的,但东魏实权掌握在高欢手中,西魏的实质统治者则是宇文泰。宇文泰掌控的西魏,在当时的南北政权中,是最小、最弱,而且形势最不利的一个。在西边有突厥威胁,东边紧邻东魏,东魏的人口与资源远远多过西魏。在它的南边还有南朝,即梁朝和后来的陈朝,尤其是梁朝在梁武帝时代,不断发动北伐。 然而正是为了应付这样的不利局势,西魏发展出一套方法,后来的隋唐就是靠这套方法才得以统一中国的。 03 西魏和东魏实力悬殊 东魏和西魏都源自“六镇”。原本留在北方的鲜卑人因为地位不断下降,待遇愈来愈差,加上柔然的侵扰攻击,终于无法继续留在边境,往南迁徙后,一部分人由高欢统领,另一部分人则跟随宇文泰。 北魏分裂之后,东魏和西魏的实力并不对等,光是从地理条件看,西魏就不如东魏。由宇文泰率领的这批鲜卑人,远离了鲜卑起源的根据地,进入关陇地区,在这里鲜卑不只是少数,而且很不容易得到鲜卑人的补充支援。关陇的面积、资源不如东魏所占据的山东区域,差别更大的是鲜卑起源的根据地在东魏领土中,相对地,西魏就被和其他鲜卑人隔离开了。战争中,尤其是和东魏的战争,兵力补充条件就有很大的落差。 单纯看现实条件,特别是直接和军事武力相关的条件,很显然,东魏要击败西魏甚至吞并西魏的胜算要高得多。不过,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有许多不是由单纯现实条件来决定的其他因素,改变了原先的估计。 东魏这边,高欢是胡化的汉人,汉人血统对于他在山东地区崛起有一定的帮助,带领六镇民兵时,他特别用心调和胡汉关系,将对于定居汉人地区的伤害尽量降到最低,同时也就缓和了胡汉之间的敌意与不信任。不过这种情况,到了他建立东魏政权后,却维持不下去了,他无法再有效地约束鲜卑贵族。 《北齐书·杜弼传》中有一段记录值得注意。杜弼向高欢建议“先除内贼,却讨外寇”,就是先处理好朝廷内部矛盾,才能集中力量对付外面的西魏或南朝。高欢就问杜弼:“你所谓的内贼是谁呢?”杜弼的回答是:“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内贼”就是高欢身边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这些人持续在剥削、掠夺平民百姓。 听到杜弼这样明白地将“诸勋贵”视为内贼,史书中记载高欢的反应是: 高祖然后喻之曰:“…… 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他劝告杜弼要弄清楚:杜弼讨厌的这些“勋贵”是和他一起打仗,在战斗中冒过生命危险的。他们能活下来不容易,有过这种经历才得到这种地位,就算贪一点、坏一点,这里跟人家敲诈一点,那里偷人家一点,和他们对政权的贡献比,所求都不算多。不能拿一般欺压百姓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应该多一点宽容。 这就是高欢的基本态度。他和这些从“六镇”流亡出来的军人有一起出生入死的特殊情感,建立东魏后就对他们特别宽容。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鲜卑人,而且是在汉化后受到歧视的鲜卑人,因此才会愤而举兵南下。高欢要照顾他们的感受,在新政权中给予他们尊严,重视他们,无疑是合理的。 中国这个独特的生命体是如何诞生、成长、进取、挑战、变革的,汇集近百年历史学、考古学的丰硕成果,运用搁置在学术象牙塔的新知识、新方法,提供中国通史的全新读法,讲透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 特色之一:把中国看作一个生命体 中国是一个生命体,有它的起源和定型,也有它的生长和成熟,还要经历巅峰和逆转。假设我们忘掉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切,假设我们是一个在火星上观察中国的局外人,我们好奇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中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这就是这套书打算讲解的核心内容。 ----------------- 特色之二:挖掘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这套中国历史,关注历史演进的深层脉络,关心历史运作的背后逻辑,而不是讲述某个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烦琐地考证一个新的历史知识,更不是突出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宫廷内斗的血雨腥风。中国到底是怎么从满天星斗一般的诸多新石器部落,演化成大一统的帝国,而游牧与农耕的帝国在历史上又是如何彼此冲击,塑造出今天的中国,这是这套书关注的重点。 ----------------- 特色之三:文学读蒋勋,历史看杨照 这套中国历史,杨照先生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时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到处都是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这套讲解,不那么学术,却到处都是精深的学术成果;这套讲解,不追求戏说,却充满了畅快而愉悦的轻松氛围。 ----------------- 特色之四:中国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这套中国历史,关注王朝更替、杀伐决断、远交近攻这些“大历史”,也关心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关心古人的生活作息和衣食住行,关心不同阶层之人的所思所想,关心不同时代人们表达自我的方式,这些“小历史”让我们看见,中国的深刻底蕴,中国历史的深层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 特色之五:新材料、新观点、新写法,全新的中国通史 这套书是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给今天中国人的中国历史。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历史,太多都是50年前的老书,而100年以来全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却被人们束之高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这套书提供的就是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讲透中国历史的运作逻辑。 1、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2、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3、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