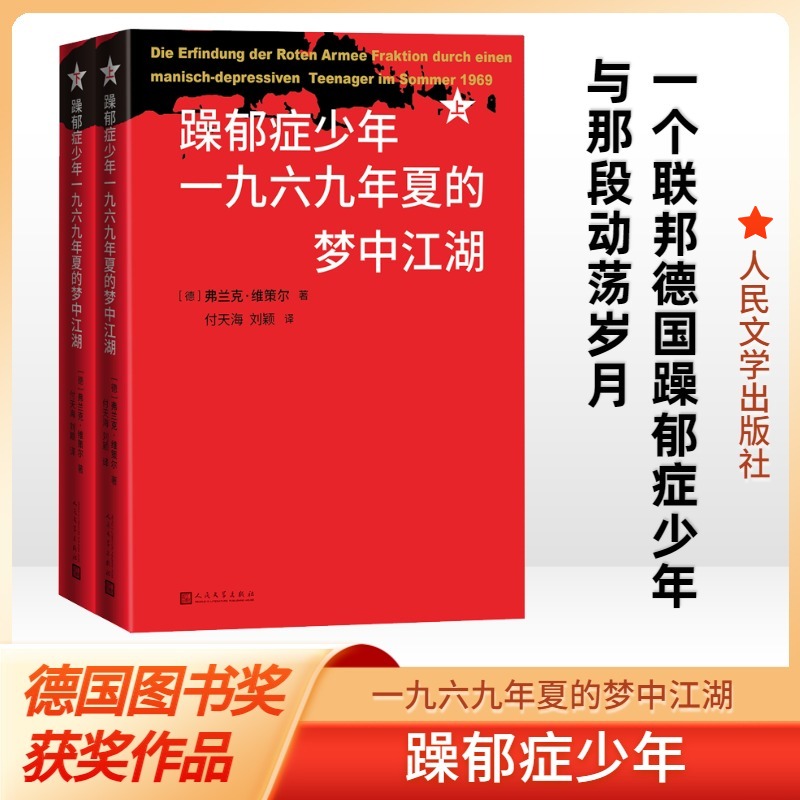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138.00
折扣价: 91.10
折扣购买: 躁郁症少年一九六九年夏的梦中江湖(上下)
ISBN: 9787020182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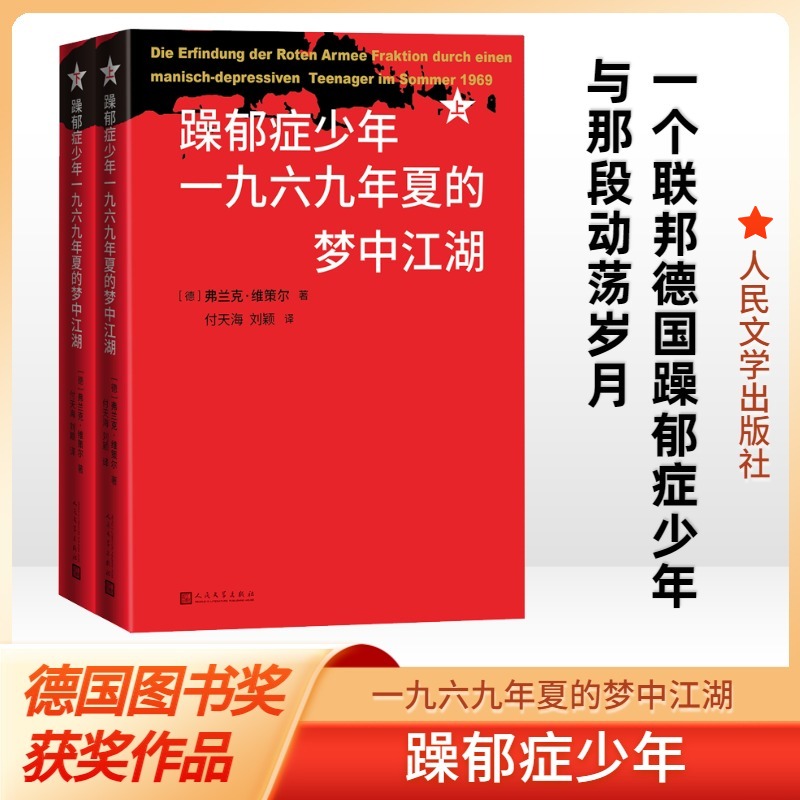
弗兰克·维策尔,1955年生于威斯巴登,德国作家、画家和音乐人。著有诗集《无尽的日子》(1980)、小说《内心沉船》(2020)等。凭长篇小说《躁郁症少年一九六九年的梦中江湖》获2015年德国图书奖。2021年获埃里希·傅立特奖。
1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不让自己被抓获 那是一月份大雪纷飞的一天。我站在一处被大雪覆盖的狭长山丘上,望着山下熟睡的、同样埋在雪中的一个村庄,尝试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山下村里一间几乎没有家具和供暖的住房里度过了两个半月时光,所住的房子更像是一个仓库,它紧邻一条溪流,一半河面在许多年前类似于今冬的严寒天气里都冻住了。我站在山丘上,目送自己一呼出便凝结的气息,目光一直延伸到那只松鸦身上,它刚刚还蹲在一根堆满积雪的树枝上,转眼间便飞向灰色的苍穹,消失在下一个山顶后面。 那条乡间公路就像一幅儿童画所描绘的那样,从灰白色的地平线一直蜿蜒到我脚下的原野。这时公路上已经有一辆汽车驶近。它不是法拉利250高性能跑车(12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2953立方厘米,功率240马力,最大速度230千米/小时),甚至连保时捷501也算不上(6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1995立方厘米,功率120马力,最大速度200千米/小时),而仅仅是一辆NSU 王子(2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578立方厘米,30马力),它正以每小时120千米的速度驶出被大雪覆盖的村庄,在这个路段顺风上坡行驶。而此时我连轻型摩托车驾照也没有,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在车上大喊大叫,让我继续保持靠右行驶,以便躲过转弯处警察们的视线。但是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NSU王子的两个后轮轮胎几乎都瘪了,以至于我几乎无法使车体保持平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领先了一大截。塞满警察的大众T2型公务用车在我们身后追赶,车里的警察开始噼噼啪啪地开枪射击。子弹射入雪堆,从沥青路面上弹起,敲击着汽车挡泥板柠檬色的油漆。克劳迪娅在杂物箱里翻寻到一把手枪。它没有装子弹,我说道。什么,没有装弹?里面没有水。水?这是我的水枪。天哪,你发疯了?贝尔恩德喊道。豌豆枪到底在哪儿?不记得了,但是这把水枪的性能真不错,它前面有一个环圈,这样你就可以向拐角处射击了。你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地地道道的胡思乱想者,我心里想,你们本想向阿希姆借气枪。他不在家,只有他祖母在场,而她不愿把气枪交出来。小心!我的身体向左侧倾斜,差一点儿我们就翻车了,但是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机智果断地把自己甩向车厢另一侧,这样我只是暂时脱离了行车道。积雪高高扬起,飞溅到挡风玻璃上。雨刷疯狂地刷个不停。或许我们应该干脆掉头,克劳迪娅喊道,他们做梦也不会料到我们会这样做。对,贝尔恩德也喊道,然后我们就从他们旁边飞速驶过,在他们意识到情况有变之前我们早已逃之夭夭了。不,别胡闹了,这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必须赶到下一个地方,它离这儿不太远了,此外前方就已经开始下坡了。是的,没错,我已经看到几栋房子了。我们必须甩掉他们。我驾驶汽车毫不减速、发狂般地驶进居民点,顺着白坪大街往下开,然后向右拐入池塘巷,从出售裹有巧克力糖衣的香蕉切块的福尔面包店旁边驶过,沿途又经过施帕尔丁卫生用品店、布赖登巴赫食品店、毛厄尔杂志和烟草店、勒尔食品店和歌咏协会,在快到道姆面包店门口的地方我停了下来。快点儿,我喊道,警察们还没赶到。我们下了车,跑到对面的院落门口,穿过院门来到后院。我们必须翻过院墙,那边就是校园,从那里我们可以继续跑向凯尔伯绿地。我们跳到垃圾桶上。你们在那儿干嘛呢?一个声音从后排房屋的一扇窗户里喊道。马上站住!我认识你们!马上站住别动!否则的话我去找你们父母!我很快转过身去。一名扎着长围裙的妇女从三楼的走廊窗户里探出身来,手里晃着鸡毛掸子在威胁我们。此时警车刚刚从敞开的院门口疾驰而过。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我说道,他们肯定开往高处的格雷泽尔贝格了。要是这样我们最好往反方向逃跑,贝尔恩德说道。赶紧。我们又从垃圾桶上跳了下来,飞奔穿过门廊。站住!那名妇女又大声吼道。我们小心翼翼地窥探外面的大街。街上看不到警察的一丝踪影。开溜,动作快点儿!我们向左沿着池塘巷一路飞奔下去,向右转入费尔德大街,跑到铁路路基处又向右朝韦德曼废品站方向继续飞奔。我们必须分开,克劳迪娅说道。对,我附和说,如果我7点钟还没有到家,无论如何都会惹麻烦的。我8点钟到家就行,贝尔恩德说。最好我们好几天都不见面。我们点头称是。如果警察到谁家登门的话,他要立即电话通知其他人。但是我们应当说些什么呢?干脆就说事由是周一的数学家庭作业。周一的数学家庭作业,就这么定了。然后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出意外周六4点在洛赫碾磨厂会合。周六我必须去教堂忏悔,此外在爵士音乐俱乐部碰面不行吗?那就说好5点半,可以了吧? 晚上8点20当我穿着睡衣、在放电视的房门口道晚安的时候,我尝试很快捕捉一下荧光屏上的画面,看到了在湿滑的马路上飞奔的男子们的模糊录像,心里感觉又紧张起来。不,那不是我们。但是他们好像并未放弃搜寻。一张罪犯的模拟像被公示出来,它是用铅笔画成的,但幸运的是画像上嫌犯的头发要长得多,因为我上周才刚刚去剪完头,现在头发连耳朵都没有盖住。但是前突的下颚,这一点可能会像我。然后又是下一张画像,这一次是女的。不,她也不是克劳迪娅。克劳迪娅长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画像上的女人一点儿也不像她,她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眼睛,嘴唇也没有那么薄。 然后电视上又讲了一些跟一封招供信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供认。从未有过,此前也没有。曾经有一次我们共同写了一些东西,但并未把信寄出,而且马上就把它烧掉了。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把信带在身上,在穿过亨克尔公园回家时路上正好没人,我就点着了信,把它扔到砾石路上,在信彻底烧毁之后我又把剩余的纸灰踩碎。但是奇怪的是,那些人说出了我们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们组织的名字“红军派”,尽管这个名字还根本未被确定,原本我们想再表决一次,因为克劳迪娅觉得这样命名不太好,只是她也想不出其他建议,只好说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命名,毕竟我们不是要成立一家俱乐部的孩子,她这话也有道理,尽管最好还是给组织起个名字,特别是如果以后还有其他人加入的话。尽管如此我在心里自问,播报新闻的那些人是从哪儿知道这事的,因为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此事,我没说过,就连阿希姆也不会。 克劳迪娅肯定会守口如瓶的,因为她也属于基层组织,这样成员们商谈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向外泄露的。贝尔恩德反正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故弄玄虚有时已经够让人心情烦躁的了。但是米夏埃尔·雷泽就不好说了,他总是可疑地待在我们附近,因为他想“偶然”听到我们都在谈论些什么,了解到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以便他可以仿效。但是恰恰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因为他的模仿让人神经紧张,所以我们特别提防他,在学校里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闭口不谈,这是我们事先商定好的,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谈论。如果有事要商量,我们干脆就说今天中午在洛赫碾磨厂或者随便其他地方,如果情况紧急,就在回家路上的操场上,但是即使是在那儿我们也总是格外小心,因为有时会有老师在操场。但是雷泽真让人猜不透,贝尔恩德也认为,这家伙或许在我们背后刺探了很多情况,当我们课间在地下自行车车棚里匆匆地吸一支烟的时候,他会溜回教室乱翻我们的书包,因此我们从不在班级里放任何可疑的东西,而是始终把一切都装在外套里。雷泽也看《士兵》连载小说,是班上唯一借助润发油把头发向后梳的人。这种发型使他看上去非常市侩,当他在体育课上被汗水湿透的时候,头发就会向前散落,长长的盖住他的整张脸。然后在一次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只是相互比画着各种拳击动作,在快要击打到对方脸部时就立即收手,而他却直接打到了贝尔恩德的鼻子上,声称他是不小心失手才这样的。但是或许当时他就是故意的,或许他真的跟在我们后面想报复,因为我们总开他的玩笑,原因是每当一支笔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笔之后,总会很快变得满脸通红,看样子仿佛是简单的弯腰都会使血液涌入他的头部。当然这样做很卑鄙,因此我偶尔也会同情雷泽,有一次甚至中午跟他约定见面,尽管贝尔恩德认为雷泽这个人不值得人们同情,所以我没有告诉贝尔恩德任何我和雷泽约会的事情,在那之后也没有。不管怎样这件事挺难为情的,我必须专程坐6路车出城去往卡斯特尔,因为我不希望他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就坐在雷泽的房间里,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单曲唱片,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他只有《士兵》连载小说和铅质小兵,他用这些小兵在一个自制的沙盘上模拟各种战役,沙盘上有山包、一条河流以及我们也有的法勒铁路模型的撒草粉。小兵模型分量都很沉,大约有火柴盒那么大。雷泽把其他人物称作平民,他们必须全部丧命,或者在逃亡途中淹死在河里,这些人物模型却要小得多,因为它们也来自法勒模型公司,这些人其实都属于火车站乘客,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提着箱包,某些甚至挥动着手帕,我觉得这样挺傻的,因为这与沙盘场景一点儿都不匹配。然而雷泽却认为,那些提箱子的是在逃难途中,挥手帕的是想要投降,因为人们在投降时会挥动一条白手帕。在游戏中我总是扮演那些法勒平民,提着箱子试图跨越河流登上山丘,但是雷泽的士兵已经站在那儿恭候了,于是我就把手里挥动手帕的派到前面,但是雷泽索性把他们也一块儿射杀,这样一来我也不再打心眼里同情他了,特别是当他全神贯注的时候,总是把舌头怪怪地向外翻转。他在暴怒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当我让一个法勒公司造的小人模型干脆从一名士兵双腿间溜掉时,他随即生气地说道:这不公平,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对这种蠢傻的游戏不再感兴趣了,想最好马上就走,见我这样雷泽让步了,给我看了一个大约有橡胶小球那么大的银色圆球,问我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当我回答不知道时他说:这是真正的火车机车所用的轴承里的一颗滚珠。我说:搞错了,因为我尝试想象火车机车的滚珠轴承得有多大,因为我只熟悉挂有小珠子的细链。然后我们又闲坐了一会儿,雷泽问我觉得阿妮塔这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挺好的。然后我说我现在必须要走了,这也算是一半的理由吧。于是雷泽说道:好吧,兄弟。这让我觉得有点儿怪,因为我们班级没有人这么说过,我在思考还有谁说过“兄弟”这样的字眼,因为我曾经听到过有人这么说,但就是想不起是谁了。 现在他们在电视上展示那辆黄色的NSU王子,以及我们画在厚纸板上的车辆牌照。我觉得NSU这个名字很好,因为它是英国“奶油乐队”(Cream)唱的一支歌。“开着我的汽车,抽着我的雪茄,唯一让我快乐的时光,就是弹起我的吉他,啊哈哈哈哈,啊哈。”此外那辆NSU停在那里,车门未锁,车上还插着钥匙。现在他们开始展示我的水枪,当时我们把它忘在车上的杂物箱里了,我心里在想:真让人恼火,因为这把水枪很独特,也因为它肯定不再有售了。这时母亲问道:哎,你不是也有一把这样的水枪吗?我答道:不,我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把枪不也能转向射击吗?是的,但是外观不一样。你的在哪儿?我把它借给阿希姆了。 我还在想:如果他们在水枪上找到指纹,然后去学校采集我们所有人的指纹,那该如何是好?我曾经读到过,有人专门为此把指尖磨平,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指尖总是马上就重新长出,而且带有相同的纹路。即便水枪上有我的指纹,也不足以说明那辆NSU就是我偷的。毕竟我可能真的把枪借给别人了。我也确实把水枪借给过别人,尽管不是这把,因为它是我最珍贵的,那一把是用透明塑料制成的浅绿色的,人们总能看出枪把里还剩多少水。我可能会说我把枪借给了雷泽,然后他们将会驱车去雷泽家搜查他的房间,会在那儿找到所有的《士兵》连载小说和铅质小兵,还有那颗铁珠,他们或许会认为它是一颗用来装填武器的子弹,任由雷泽怎么解释它来自火车机车上的滚珠轴承,他们也不会信他的。他是怎么得到火车机车上的滚珠轴承的呢? 我还特别想知道,电视上那些用模拟像搜寻嫌犯的人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母亲打发我下楼回自己房间了。那里一直还摆放着我的骑士城堡,尽管我早已过了玩这种玩具的年龄了。去年我用我的“威望”模型的边角余料对它进行了改装,但是人们一直还能看出,它在改装前是一座骑士城堡。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是我最珍贵的骑士,因为他身着一套乌黑锃亮的甲胄,现在他正忙于锯开吊桥,古德龙·恩斯林b正把白人骑士中的一员推进城堡壕沟。古德龙·恩斯林是一个用棕色塑料做成的印第安女人模型,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她,因为她一点儿详细背景也没有,但是她是众多人物模型中唯一的女性。我是有一次通过抽奖在一个魔术袋里赢到了她,当时她正躺在一堆爆米花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禁不住一下子想起了去年复活节我得到的那个肥皂兔。当时人们必须把它从包装里取出放到洗手盆边缘。第二天它就长出了一层特别柔软的绒毛。当然人们不准用它来洗手,然后绒毛不见了,也没有再次长出。我从未用它洗过手,但是我的小弟弟肯定用他沾水的手指抓过它,因为一天早晨它身上的绒毛褪得干干净净。接下来我又等了几天,看那绒毛是否再生,在确定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之后,我也开始用它来洗手了。我今年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肥皂兔,但是并未如愿得到。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大了,不适合获赠这样的东西,而我弟弟还年纪太小。我之所以想起那只兔子,或许是因为我在考虑我们怎样才能伪装自己,考虑可能在哪儿搞到一副假发。虽然我从克尔伯那儿得到了一副披头士乐队假发,但是它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塑料头盔,而且对我来说也太大了。戴这样的假发会立即引起别人注意,此外我根本不喜欢当时的发型,就像老师们所说的“蘑菇头”,而是喜欢甲壳虫乐队自演唱Help(“救命”)以来所风靡的那种头型。长长的头发反倒更引人注意。盖尔就总是遭到别人的辱骂,被问及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把藏在柜子后面的那个标准A4笔记本拽出,本子上写着所有与红军派有关的事项。比如里面写着,谁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什么时候碰面,谁带来了哪些单曲唱片,还有我们的标志,尽管它还没有被完全设计好。起初我尝试把它设计成类似于体操协会的标志那样。比伯里希体操协会的缩写是TVB,这正好也是三个字母。在一个七角形的红色的骑士盾牌里,首先自上而下写着一个长长的字母T,在T的纵向笔画上写着小一些的V,V下面又是字母B。然后标志上还写着该协会成立的年份数字:1846。在字母T的纵向笔画的左侧是18,右侧写着46。于是我用透明纸描印了这家协会的徽章,自上而下分别把T、V、B改画成R、A和F,其中A跟原先的V一样要小一些,然后把左、右两侧的年份数字分别换成19和69。我觉得这种设计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克劳迪娅不喜欢。她认为这样的标志太庸俗了,毕竟我们不是体操协会。她的话有道理。我也很久没有去过体操协会了。每次都必须穿黑色的体操裤和滑稽的汗衫,首先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无聊。而且我们谁都不允许穿毛巾布袜。 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数字(1969)还是挺好的,我也建议不要在标志上写上我们俱乐部成立的真实年份,而是干脆写上一个更为久远的年份,就像我也在组织名单上罗列了一些根本不属于我们的成员一样,因为每一家协会都有自己的名誉会员,他们并不真正参与体操训练或者在体操馆出现,但尽管如此也是协会的一员。在我们组织约翰·列侬、斯蒂夫·马里奥特、金格尔·贝克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是名誉会员。因此我们需另想一个成立日期。不一定非要是1846年,但是可以久远一些。所以我收集了关于野孩帮、新护卫队,也包括圣星唱派的所有可能性历史。在收集到的资料中我碰到了小马克斯·雷格尔这个人。他于1913年3月19日出生在威斯巴登。我觉得1913是一个不错的日期,因为我十三岁,准确地说是十三岁半,也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十三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这个小马克斯·雷格尔虽然没有直接成立过团体、帮派或者俱乐部,但是我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俱乐部,而更像是一群单独的斗士,正如克劳迪娅所说的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员。这些乌拉圭游击队员的标志是一颗恒星,跟比伯里希体操协会的标志一样,恒星上自上而下也印有三个字母:M、L和N。令我不解的是图案上根本没有出现字母T,要是这样TVB也可以叫作比伯里希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或许我们干脆就应当这样命名。贝尔恩德也许会赞同,但是克劳迪娅不会,因为她觉得“比伯里希”太俗气,在这一点上她也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红军派”这个名字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