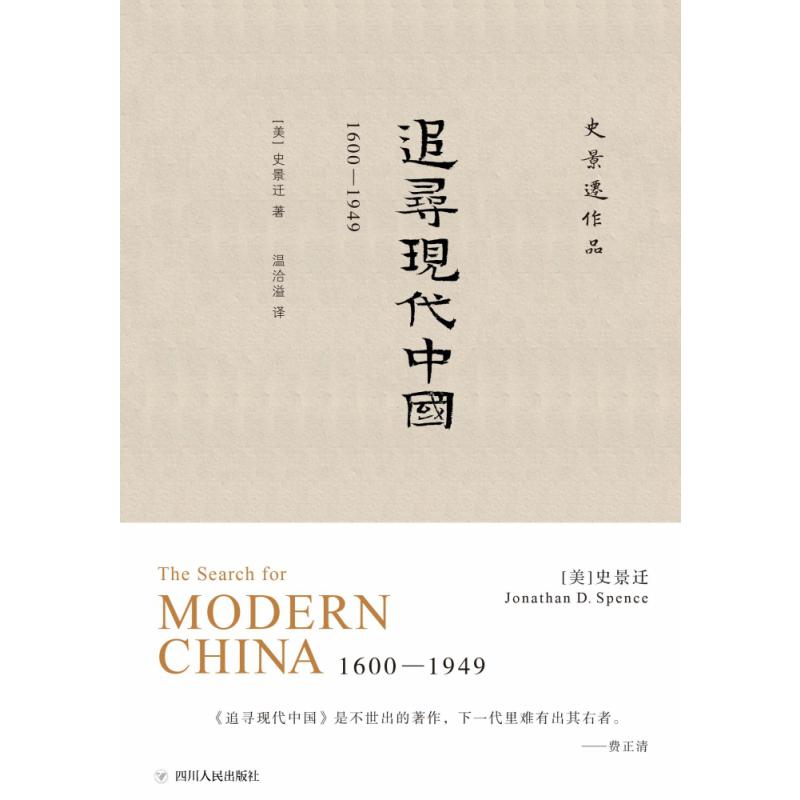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79.40
折扣购买: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精)/史景迁作品
ISBN: 97872201097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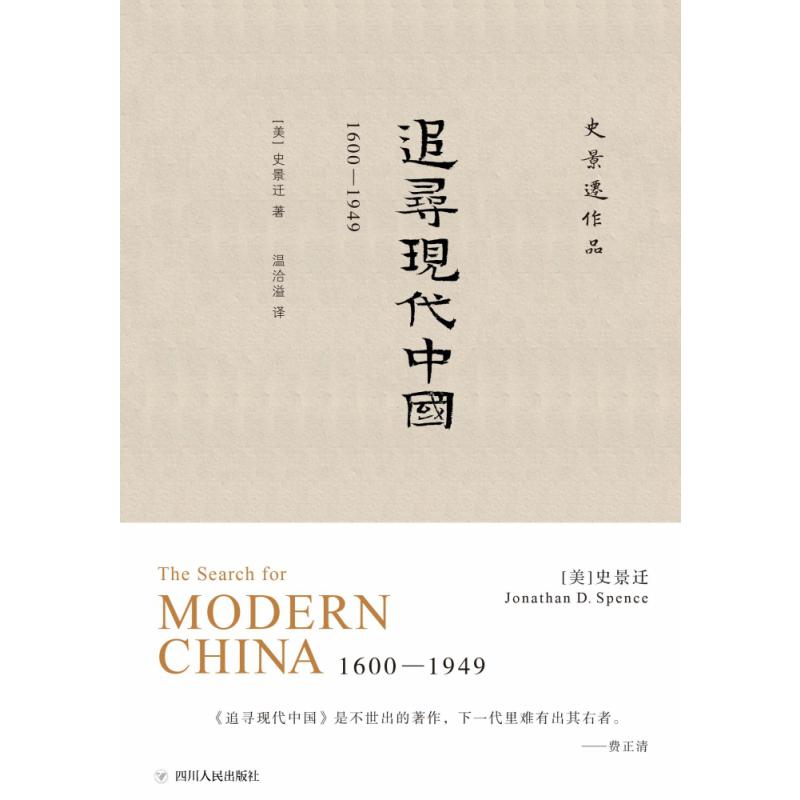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1965—200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著作极丰,主要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改变中国》、《曹寅与康熙》、《康熙》、《天安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
第一部 征服与巩固 16世纪末,明朝似乎正是国力鼎盛之时,其文化与艺术成就璀璨夺目,城市与商业生活繁荣富庶,中国人在印刷技艺与丝绸、瓷器的制造能力,令当时欧洲人望尘莫及。不过,即便人们习惯性地把这一时期视为“现代欧洲”崛起的年代,却不太能说现代中国也发轫于此。正当西方世界竞相纵横大海、拓展世界的知识视野之际,明朝统治者不仅严令禁止海外探险,阻绝了可能因此获得的知识,还采取一连串自毁长城的行政措施,结果不到五十年,明朝即在战火中覆亡了。 晚明国家与经济结构组织的涣散,业已开始在各个层面浮现。财政收入锐减,朝廷无法如期发出军饷;士兵的逃逸使虎视眈眈的北方部族得以乘机进犯;欧洲白银的流入对中国造成超乎预料的经济压力;官仓监管不善,天灾四起,导致农村人口普遍营养不良,疫疠丛生;叛民蜂起,聚而为寇,只为了苟活于乱世。到了1644年,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纷纷汇聚成流,明思宗在四面楚歌中自缢身亡。 在动荡之中重建社会秩序者,既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已经对明朝离心离德的士绅官吏,而是突破北方边防,自称“满洲人”的女真部落。满人的胜利得力于其组织结构,早在伺机入主中原之前,他们就已成功地打造出一套军事与行政建制,官僚机器的核心也告形成。随着这些制度的建立,以及大批归降、被俘的明朝人权充满人的谋士、士兵、匠人及农人,满人遂于1644年乘机进犯中原。 成千上万军队的转战运动,一如满人当时所感受到的,让我们见识到中国江山的百般风貌。四处叛乱的农民,以及明朝的残余势力,各自据地以抵抗满人的扫掠。满人自北南下、由东向西的征服模式,主要是依循中国山川的地理形貌,同时将各区域的政治与经济地缘中心融入新的国家结构之中。 意欲征服像中国这般幅员广阔的国家,满人势必要把成千上万的汉人支持者纳入其官僚体系,倚赖汉族的管理人才,使其听从满人的号令来统理国家。少数明室的后裔犹作困兽顽斗之时,大部分的汉人已能够接纳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大致承诺维护中国传统观念与社会结构。清军的入关就算掀起社会的沸腾动荡,也是为期甚短,满人所建立的清王朝屹立不摇,统治中国迄至1912年。 不仅清朝,对历代各朝或后继者而言,统一中国需要各种相应的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手段的配套。清朝皇图霸业奠于康熙皇帝之手。康熙一朝从1661至1722年,在位期间依次完成了中国南、东、北、西北疆域的防御工事,同时进一步强化入关前满人所施行的统治机制。康熙特别着力维护科考制度,凭仗着可靠又秘密的驿递讯息,疏通了朝廷的耳目渠道,同时又以朝廷之力,笼络那些可能心怀二志的知识分子。康熙皇帝还设法化解了潜隐在官僚体系甚至广大社会之中的满汉族群的紧张关系。不过,康熙在经济方面的建树就略显逊色。康熙一朝虽然商业兴盛、农业富饶,但未有效课税,终大清王朝,此一弊端始终相随。 康熙之子敏于修补康熙遗留的积弊,特别致力于改革税制、组织文化生活、消弭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强化中央官僚体系。然而中国总人口数在18世纪后半叶急遽膨胀,土地分配压力随之而来,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庙堂风尚开始隳坏堕落。官吏颟顸昏聩,贪污腐化成风,削弱了朝廷的反应能力,致使清廷对国内问题避之不及,遑论解决。在对外政策方面亦然,气势汹汹的西方商人远渡重洋抵达中国沿海口岸,不断挑战清廷加诸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清廷的涉外机构面临新挑战,清廷在这方面也是迟钝无方。在灵活适应方面的无能,为日后19世纪的一连串浩劫埋下了祸因。18世纪曾经一度迷恋中国文明的西方作家、政治哲学家,现在开始细察中国的积弱,认为中国人若无法适应世界丛林的生活,则有朝一日,中国必定覆亡。 第二部 分裂与改革 19世纪初,中国士人已察觉到社会承受的道德与经济压力。他们秉承儒家智识传统,主张行政与教育改革,呼吁重视人口急速增长问题,同时提倡财富的合理分配。有人也指出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吁请重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地位。 鸦片成瘾日渐普遍,造成尤其棘手的社会问题。士人、阁臣甚至皇帝本人,对于到底要合法化还是要禁革鸦片各持己见,举棋不定。同时,英国大举投资于鸦片制造与流通,贩卖鸦片所得在整个英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甚大,使得鸦片交易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清朝视鸦片为内政问题,决定禁烟。英国则以武力击败清朝后,于1842年强迫清朝签订一纸条约,自此改变了其与外国强权的关系架构,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统治者对来华外国人的有效控制。 外国力量新面貌的出现,恰巧赶上新一轮的国内动荡,前者无疑也对后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清动乱在18世纪后期愈加频繁。19世纪社会失序加剧,带来更大的动荡,到中叶时,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起义,至少其中的两起——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差一点就推翻了清王朝。太平天国奉基督教基本教义与平均主义为圭臬,直击儒家思想与中华帝国的价值命脉。捻军则以新的游击作战模式,撼动了清朝正规军事机制的威信。另外两次起义分别由西南与西北边疆的回民掀起,对朝廷在边远地区非汉民族的统治造成了威胁。一群忠于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士人,锐意维系既有的社会、教育、家庭体系,正是他们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使清朝的国祚得以延续。 讽刺的是,这群士大夫在屡建战功之后,也忍不住开始仿效或采用一些外国军事科技与国际法,最终瓦解了他们原来力图维护的价值体系。不过,一开始谁也无法料想到这样的结果,清廷以“自强”为名,不仅建立新式兵工厂、造船厂,还成立了现代化的学堂,教授外国语言,聘雇外国人合理征收关税,试图招募一支由西方船只、海员组成的小型船队,设立了中国首个等同于外交部的机构——总理衙门。 然而,中外关系依然紧张。中国境内爆发教案后,美国国内随即发生排华暴行,美国也发布一连串的禁令,使得华人移民人数锐减。从这些案例可知,纵使个人的努力证明不同种族间可以和平相处,相互包容,然而在民族的文化与价值目标上,彼此之间仍充满误解。 到了19世纪末,尽管外有压力,内有动乱,但清朝似乎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综合体。然而以夷之技所取得的种种军事与工业成就,在对法与对日这两次短暂却惨烈的战败中被粉碎,让中国沾沾自喜的“现代化”海军葬身海底。1898年的一股改革热情因保守势力反扑而胎死腹中,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做好了铺垫。这场动乱挑起了中国人内心的仇外情绪,导致攻击外国传教士与信徒的行为大范围出现。拳民虽然遭到外国武装力量的镇压,但紧随而来的“反清复明”民族主义,开始在报纸文章、宣传册子中出现,经济抵制运动以及一系列意欲从内部削弱清王朝势力的起义也反映了这种苗头。 清朝亟思救亡图存,推动或可收效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通盘改革计划,其中包括试行西方模式的立宪政府,以西方建制重整军队,建设中央掌控的铁路网络以加强控制中国的经济。然而,这套改革计划不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激化了冲突,滋生了新的误解。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成为批判清朝政权、地方利益涌现的大本营。而一支由满人娴熟指挥的现代化强悍军队若建成,对梦想推翻清朝、谋求独立的汉族民族主义者来说,只能是一种威胁。同时,朝廷试图集中管理铁路并向外国贷款以收回路权的举措,激怒了各省的投资者与爱国人士。这股怒火被激进派领袖与其焦躁的追随者巧妙煽动起来,这时清朝才惊觉国本已被严重损毁。 面对1911年底爆发的武装起义,一筹莫展的满人别无选择,只得在1912年初拱手让出政权,至此清朝宣告覆亡。不过国家的权力中枢依然悬荡,又无旷世雄杰能填补这个真空,徒有几个意识形态对立、主张相异的集团相互竞逐。清朝崩解后,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崭新且充满自信的共和国,而是一段内战连绵不绝、思想彷徨无依的时期,对百姓而言,其残酷程度比自二百六十八年前明朝灭亡后的动荡更甚。然而在杌陧不安的时局中,治世经国的思想家、自强运动者、立宪改革者和革命者胸中所萦绕的那份富强中国的美好梦想,却从未全然销蚀。当然,清朝最后一百年的统治,也留下了其积极一面,那就是:泱泱中华的信念,决不能消亡。 第三部 国家与社会的展望 造成清朝政局紊乱的潜在根源之一便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中国的革新派倾力想要建构一套可行的共和体制来取代威信尽失的帝国体系,缔造新的政府组织,将中国改造成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由各省代表在北京组成的议会,把中央与地方连接起来,而近四千万的选民人数,可确保不同区域和利益都能得到广泛代表。恢复生机的地方政府体制,将会缓和地方利益,为中央带来新的税收,以便迫切的改革能够进行,外国势力可以受到压制。 然而,在1912年中国第一次全国普选之后不到数月,这样的梦想就破灭了。临时总统袁世凯派人行刺多数党领袖,同时取缔了其所属组织。尽管袁世凯胸怀复兴中国的远大抱负,但他欠缺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圆熟的组织技巧,无法整合中央。于是政治权力不是流向了城乡各省的实权人物,就是落到了数百名军阀手中,军阀逐渐成为各地主要的权力掮客。中国政治的弱点随着国际局势发展也益形凸显:日本的索求益加蛮横粗暴,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虽然大胆派遣了一百万劳工援助西欧的协约国,但仍然无法赢得强权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尊重。 结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政治形势杌陧不安,但思想上却进入空前的反省与探索时期。许多有学问的中国人深信国家灭亡在即,开始钻研各种政治和制度理论,分析他们所处社会结构的本质,论辩教育和语言新形式的价值,探索进步的各种可能性,那是西方科学的核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时期。在此期间,虽然追寻的议题同样可见于明清嬗替之际与清末有关国家前途的争论中,但是这种集中涌现的活跃智慧和怀疑精神,却是中国两千年来所未见的。 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探讨了种种选择方案,其中一些佼佼者,在苏联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巧妙牵引下,开始醉心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到了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已经各就其位,并在1921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享有优势,追随者亦众,但是共产党强有力地表达出了反抗军阀、打倒地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决心,以及解决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困境的抱负。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的激进派,组织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罢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有时这类行动是以罢工工人的生命为代价。 国共结盟,一半是因为双方都迫不得已,另一半则掺杂了双方共同的希望。迫不得已是因为军阀割据和外国势力特权造成了中国的分崩离析,而双方都希望依靠中国人的精神、技术和智识力量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尽管两党在长期发展目标上相互抵触,党员志趣也不尽相投,但至少在以下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必须结合军事力量和社会改革来重新统一国家。在南方城市广州,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训练了一批新的军事精兵,成立了农民协会,让农民加入了工人组织的行列。1926年,新成立不久的国民革命军举兵北伐,推进至长江流域,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军阀迅速被推翻后,国共双方在社会政策上的分歧之深却越发凸显。对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灾难的一年,虽然他们努力要比自己的国民党盟友技高一筹,以扭转新国家的走向,但在此过程中,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革命运动几乎毁于一旦。 就在共产党从城市撤离,准备在偏僻的农村重新整编队伍之时,国民党试图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到1928年年底,从东北到广东,都已处于同一旗帜之下。蒋介石拼命利用好微薄的财政资源,将精力集中在了重新改造国家行政机关之上,并发展配套的交通运输、城市公共设施及教育设备。同一时期,中国的都市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地区——特别是上海——从西方吸取了许多元素,一股现代氛围开始弥漫。当时不少外国强权对中国政策有重要影响。除传教士之外,美国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德国则贡献了军事专家,并拟定了大宗交易计划,包括德国军事设备及中国稀有矿产;只有日本依然不让步,成立了傀儡政权,扩大对东北的控制,并将势力扩张至长城以内,直到中国同意宣布东北成为非军事区。随着兴国梦想的再度破灭,知识分子开始不满国民党姑息日本侵略的行径。与此同时,共产党把自创的土地改革和游击战彻底组合起来,开始建构起庞大且强韧的农村政府组织。 1930年中期,日本曾一度刺激了中国的民族复兴,也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在蒋介石军队持续不断的“围剿”下,共产党被迫离开了他们最大也最坚固的中央根据地——江西苏区,开始长征,转移到了贫瘠的北方。共产党一到那里,便成功动员起了早已对中国人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产生厌倦情绪的老百姓。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对外的机会再次出现。在多年的国家分裂与改革过程中,无数生灵涂炭,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却从未泯灭。 第四部 战争与革命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失去了建立一个强大集权国家的一切机会。日军在一年内席卷整个华东,占领了昔日国民党治下的工业重镇与丰饶土地,几乎切断了中国所有的对外联系。蒋介石的新根据地,也就是位于长江上游的战时陪都重庆,虽然成为抗日的象征,但并不适宜发动任何反攻。而共产党的势力同样亦孤立在陕西延安根据地,那里堪称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连重庆那样的农业资源都付之阙如,更欠缺发展工业的能力。我们甚至很难说共产党人可以在延安存活下去,遑论它会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圣域。 在战争的头几年,靠着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原则下形成有名无实的同盟关系,国家统一的梦想依然存在。当日军借由扶持汉奸的傀儡政权来统治华东时,重庆与延安双方有意寻求更有意义的共同基础。共产党人暂缓了他们的土地改革,淡化了昔日尖锐的政治口号;国民党则瞄准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了经济、行政改革。然而到了1941年年初,国共两党再度兵戎相向,看起来,内战似乎较抗日的燃眉之急更有可能发生。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改变了原来的均衡态势。中国至少在书面上被视为同盟国的“四强”之一,开始取得军事协助和巨额贷款,而军事物资及燃料等后勤补给则经由印度空运进来——这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最后一条补给线。这些援助大都流入当时被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的重庆国民政府手中。延安的共产党仅能依靠自制的粗劣武器或是袭击日军获得的用品来逆境求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共产党利用在江西苏区发展出的群众运动技巧,精练游击战术,在日军封锁线的后方成立无数的根据地。嗣后,为进一步赢得农村地区的广大民心,共产党人还恢复了较为激进的土地征收与再分配政策。 1945年抗战结束后,历经长期战乱的国民党显得士气低落,而人事倾轧,通货膨胀严重,亦使国民政府积弱不振。虽然国民党试图迅速在曾经的日占区树立统治权威,但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和足够的资金,既无法填补日军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也无力重建战后的残局。同样资源紧缺的共产党,也迅捷地接管了那些自己能抢到的日军占领区,并在华北建立稳固的据点。共产党尤其想得到东北,希望以其作为秣马厉兵的根据地,给蒋介石以最后一击。事后证明,他们的战略选择相当正确。到了1948年,蒋介石在东北的部队已溃不成军,而他的权力基础又因新一波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严重受损,大多数知识分子、学生、专业人士、城市工人也逐渐对他的统治心生不满。1949年,蒋介石的余部很轻易便瓦解了。是年晚些时候,当他率领残部撤退至台湾时,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凭天赋和本能写作的历史学家,无人可以模仿 ★继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之后,西方新一代中国历史巨著 ★香港城市大学鄢秀教授、郑培凯教授联袂主编,专业团队精心校译 ★丰满的细节,真实的人事,一百余幅图片,呈现中国近四百年的全相 ★作者自言:这是一部发自内心深处而非只是在故纸堆里写成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