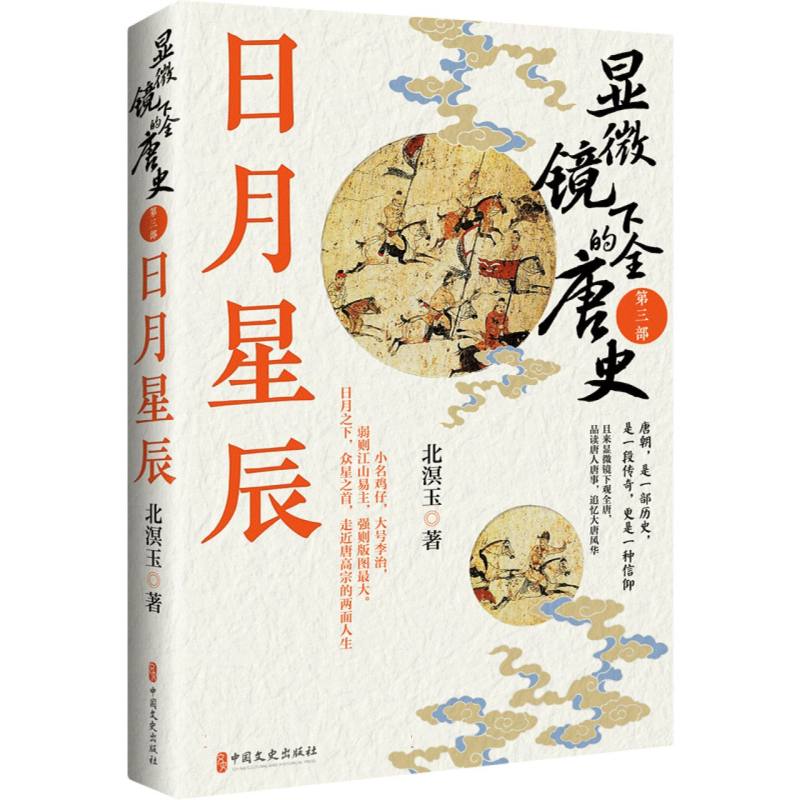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文史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33.10
折扣购买: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三部日月星辰
ISBN: 9787520546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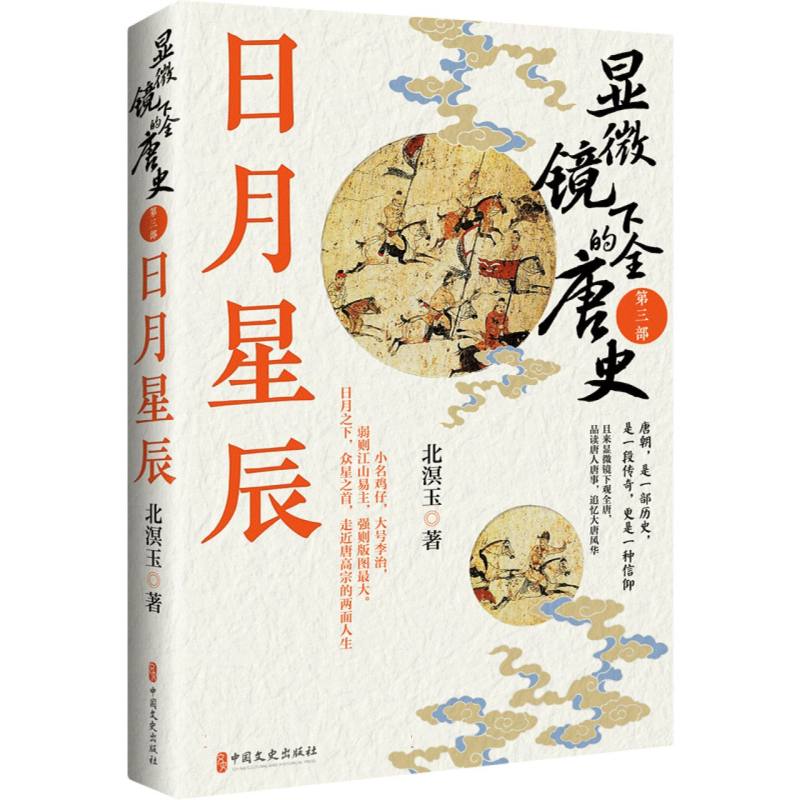
北溟玉,内蒙古武川人,唐太祖李虎的老乡,通俗历史作者,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已出版《玄武门的血》《隋唐那些人》《天可汗李世民》等作品。自认是一个有趣的人类男性个体,一个固执的码字民工,一个芸芸人海里的路人甲,一个新时代里的孔乙己。《自嘲诗》:“本是后山人,偶做京华客。卌载浮沉忙淘漉,滋味百般尝。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如此这般也如意,不怨老天错。”
帝后矛盾 刘仁轨在百济的几年间,朝廷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曾经为他美言的宰相上官仪被灭族,武后由幕后走上台前,与高宗一道坐朝问政,并称“二圣”了。 这种变化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长孙无忌谋反案后,高宗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舅舅的控制,可以伸张自我了。但懦弱如他,其实并不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注定只能被强者控制。当他是太子时,这个“强者”是父亲李世民;当他即位时,这个“强者”是舅舅长孙无忌;舅舅倒台后,这个“强者”就变成妻子武后了。 武后能控制高宗,一是得益于高宗的性格弱,二是得益于他的身子弱。 高宗刚即位的时候很勤勉,他爹三日一朝,他改为每日一朝,即便高宗八年时因为身体不适做了调整,依旧达到了两日一朝的频率。但他从小体弱,身体素质不行,娶了倾城倾国妻,却成了多愁多病身。高宗十一年后,他又得了风眩病,经常头晕目眩,严重时目不能视,渐渐地就影响到了政务处理。 皇帝不同于宰相。宰相是职业经理人,累了可以休息,病了可以请假,实在干不动了还可以申请致仕,想当宰相的人多得是。但皇帝是老板,老板只有一个,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起初高宗咬着牙硬撑,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了,终于在某个瞬间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让媚娘为朕分忧?一念起,天地变色,江山易主。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很正:一来媚娘的才智足可胜任。媚娘爱读书,尤喜历史和文学,而且爱思考、招法多。他有时向媚娘念叨朝政,媚娘的见解经常切中要害,而且给出的措施办法也非常管用。二来让媚娘分担朝政,他很放心。俩人睡一个被窝,是亲亲的两口子,他对谁放心不下,也不会对老婆放心不下。 于是,高宗开始让武后参与批阅奏章。最开始的时候是武后念给他听,然后他指示怎么批,渐渐地就变成武后阅完提出建议,他来拍板。在这一过程中,武后越发让高宗感到惊喜连连,因为聪明能干的她“处事皆称旨”。打从这一刻起,高宗就视武后为良佐贤内助了,开始逐渐放权,越放权越倚重,越倚重越放权,发展到后来,很多一般性的决策,武后就直接拍板了。此时的武后于高宗而言,既是妻子,又是姐姐,还是参谋。 如果是一般的女人,对这些枯燥乏味的政事多半是不感兴趣的,但武后不是脂粉小女人,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女人,是一个事业心、进取心都很重的女强人。这么多年来,她都不知道自己最爱什么。男人?不可能的!金钱?她不缺!但从协理政事的那天起,她忽然明白了,她最爱的是权力,她太喜欢这种手握乾坤、口衔日月、一言九鼎、言莫予违的感觉了,一点儿都不觉得枯燥乏味,她从这里面找到了无比强烈的兴趣点和兴奋点,并乐此不疲。 但夫妻间这种和谐的状态仅仅维持了一年多,就变得不和谐甚至很尖锐了。 为什么呢?因为权力是排他的,武后的权力欲上来了,控制欲跟着也上来了。举凡御姐,控制欲都很强,更何况武后还是御姐中的御姐。故事最开头,凡事都是她依着高宗,渐渐地她开始劝诱高宗遵从她的意愿,乃至发展到非要高宗按她的意思来。 高宗性格再软,毕竟是个皇帝,再不济他也是个男人,时间久了就受不了,“不胜其忿”,这大唐到底是谁说了算?他认定皇后试图控制自己,刚摆脱了舅舅的控制,老婆又想控制他,真是前门驱狼后门入虎。当然,他肯定想不到,这头母老虎可比大公狼厉害多了。 一个要压迫,一个要抗争,两口子嫌隙日生,从高宗十三年起就开始闹别扭较劲。当然,毕竟都是有身份的人,不可能像寻常夫妻那样大吵大闹。第一夫妻PK,战场是全国,而且都是大领域。先是在宗教领域,以“致拜君亲”事件过招。 经玄奘推动,佛教又开始兴盛起来。十年九月,高宗下令迎奉佛骨。 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城(今印度北方邦戈勒克布尔镇卡西亚村)郊外的娑罗树下圆寂,遗体火化后共得八万四千颗真身舍利,其中19份传入中土。东汉桓帝在全国建立19座舍利宝塔,用以存放佛祖舍利。距离长安最近的一处舍利存放地是位处今陕西宝鸡扶风县的法门寺。该寺始建于东汉桓灵年间,北朝以前叫“阿育王寺”,隋文帝时改称“成实道场”,唐高祖时叫过一阵子“法门寺”,高宗时叫“无忧王寺”。 什么是迎奉佛骨呢?就是将无忧王寺里珍藏的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迎入长安、迎入皇宫,供天子与百姓瞻仰。因为太过珍贵,所以舍利不轻易示人,藏于法门寺的地宫之中。不知从啥时候起,社会上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是大吉之兆。 高宗为了讨彩头,举办了大唐首次迎奉佛骨盛典。他将舍利迎入宫内道场后,亲自供养。武后还别出心裁地造了九重金棺银椁瘗藏佛指舍利。按理说,盛典结束后就该把舍利还给法门寺封入地宫了,但高宗和武后愣是将舍利留在宫中长达两年之久,直到高宗十三年才送回法门寺。 首次迎奉佛骨仪式让佛教的影响力越发蓬勃,这下道教和儒教不干了,高宗也后悔了,就在送回舍利当年昭告天下:“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皇太子及其父母所致拜。”啥意思呢?就是说打从命令下达之日起,所有的佛道二教教徒,在面对皇帝、皇后、太子、父母时都要行拜礼。这其实就是用儒家伦理体系去约束佛道二教。 此令一出,道教还算消停,但佛教徒的反应可是太激烈了。因为出家人是谁都不拜的,他们眼中既无父母也无君长。长安各寺僧尼二百余人联名上表,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朝廷选择了沉默。随后,各寺庙各宗派高僧齐集西明寺开会,打算串联全国佛教徒再次上表,要求废除该诏敕。 这当中,西明寺有一个法号道宣的僧人想了一条野路子,先是向武后次子、雍州牧李贤上书,未果。然后,他又向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杨牡丹上书。为什么找杨老太太呢?因为她是一个资深佛教徒。道宣希望通过老太太策动皇后,说服皇帝收回成命。 这条野路子还真就成了。因为武后也是一个铁杆佛教徒。她对佛教的兴趣始于少女时代母亲的熏陶,奠定于感业寺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那是她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她无数次地向佛祖祈求,终于佛祖“听到”了,为她打开了生门。所以,她对佛教那是相当尊崇,不仅与玄奘频繁酬答,为法门寺佛骨舍利营造金棺银椁,还请玄奘为三子李显剃了度。 武后一出面,成天耳边念叨,高宗就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回应了。五月,他大集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各地州县代表,计有千人之众,商讨应对之策。 开了这么大一个会,愣是没达成一致。因为这一千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拥护佛道二教的,并不认同致拜君亲。高宗一看这分歧太大、社会影响太大,继续搞下去恐有动乱,只得发布《停沙门拜君诏》:“若夫华裔列圣,异轸而齐驱;中外裁风,百虑而同致。自周霄陨照,汉梦延辉,妙化西移,慧流东被。至于玄牝邃旨,碧落希声,具开六顺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于爱敬之地,忘乎跪拜之仪,其来永久,罔革兹弊。朕席图登政,崇真导俗,凝襟解脱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亲之道,礼经之格,言孝友之义,诗人之明,岂可以绝尘峻范,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贞规,乃遗温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将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粉纶相半。朕商榷群议,沈研幽赜,然箕颍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什么意思呢?其实核心就一句话:出家人可以不拜君长,但父母还是要拜的。佛教徒也做了让步,应该拜父母时还是要拜的。所以,这件事情回头看,其实就是武后打了高宗的阻击,高宗的目标是100%,武后给他削减到了50%。 高宗当然不甘心啊,在宗教领域输掉了,就想在政治领域找补回来。于是,双方的PK 就延伸到了朝廷的人事,尤其是对相权的掌控上。 李猫倒台 先出手的还是高宗。就在发布《停沙门拜君诏》的当月,他册拜散骑常侍许圉师(许绍之子)为左相。虽然父亲是高祖李渊的同学许绍,但许圉师是靠真才实学发迹的,进士出身,博学多才,于高宗八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许圉师的一个孙女嫁给了一位诗人,那个诗人的名字叫作李白。 高宗推出一许,武后紧跟着也推出一许。八月,许敬宗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实际上成了右相。 高宗很不爽,两个月后又让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上官仪的出身非常好,他的父亲名叫上官弘,曾是隋炀帝的近臣。江都政变时,上官弘为宇文化及一党所杀。上官仪因藏匿得以幸免,为求避祸,自行剃度为僧。他研习佛典,精通“三论”,而且涉猎经史,善做文章。贞观年间,上官仪考中了进士,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至秘书郎,成为太宗的秘书。高宗七年,上官仪又当上了太子李弘的中舍人。他不仅是当朝显贵,也是初唐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歌“绮错婉媚”,具有重视形式技巧、追求声辞之美的特点,被誉为“上官体”。在“初唐四杰”冒头之前,上官仪是唐诗界当仁不让的扛把子。 武后的反击既迅速又猛烈,上官仪刚刚当上宰相,许圉师就被武后一系绊倒了。 许圉师有个儿子叫许自然,前不久外出畋猎,践踏了民田。田主估计也是有些背景的,对宰相之子很不客气,说话很难听。许自然年轻气盛,居然“以鸣镝射之”,确实很过分。田主就跑到司宪府把他告了。司宪大夫杨德裔一看被告是宰相的儿子,做了冷处理,“不为治”。田主事后也没有再纠缠。许圉师狠狠地教训了儿子,足足打了一百杖。 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不承想西台舍人袁公瑜指使人写了封匿名信,把这事给抖搂了出来。宰相之子竟跋扈至此,高宗大发雷霆,当堂训斥许圉师:“你可是宰相呀!你儿子欺凌百姓,你居然压着不报,你们父子是不是也太作威作福了?!”这话虽然是气话,但确实说得有点重了,犯事的是许自然,又不是许圉师,他顶多是教子无方。 皇帝不开心,训斥臣子几句,换作一般人,忍忍就得了,让皇帝把飙发完、把气撒完就好了。偏偏许圉师也是个直性子,非要解释:“臣一贯以直道侍奉陛下,难免会得罪人,这是别人故意在整我。陛下说我作威作福,作威作福的不是手握强兵的将帅,就是身居重镇的地方大员,臣只不过是一个文吏,哪儿敢作威作福呀?!”这话软中带硬,的确有点给皇帝甩脸的意思。 高宗被气得够呛,怎么的,你还想要兵权,怒曰:“汝恨无兵邪!”眼见皇帝的火儿被拱起来了,许敬宗悠悠地添了一句话:“人臣如此,罪不容诛。”这火儿拱得恰到火候,高宗当场罢免许圉师的相职,将其投入大牢。 许圉师倒台,便宜了李义府。高宗十四年正月,李义府出任右相,而且掌“典选”,把持了人事权。 三月,许圉师被贬官江西赣州,其子许文思、许自然均被免官。司宪大夫杨德裔取巧不成,被流放庭州。 此时的李义府已经站到了荣宠的巅峰。高宗九年,他祖父改葬到永康陵(唐太祖李虎的陵寝)侧,不仅由高宗御批,而且由附近七县县令征调民夫,“载土筑坟,昼夜不息”。高陵县令张敬业甚至因为“不堪其劳”,累死在了施工现场。好家伙,比给亲爹迁坟还上心!满朝文武自王公以下争相馈赠奠仪,“穷极奢侈”。送葬队伍绵延七十里而“相继不绝”。史载,“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此外,李义府的父亲被追赠为魏州刺史,他所有的儿子,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当了大唐的官。 李义府的官品大家是知道的,嚣张跋扈,贪财暴敛。让他管人事,无异于向这只馋猫打开了鱼塘的大门。他刚刚履职,就动员母亲、妻子、儿子、女婿、亲信齐上阵,大肆卖官鬻爵。史书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形容词,“门如沸汤”,登临李府求官的人多得就跟烧开了的水似的。 如此胡搞乱搞不出事儿才怪!短短数月间,朝野“怨讟盈路”,连高宗都知道了。 人是自己用的,高宗颜面无光,又不好发作,只能提醒李义府:“你的儿子和女婿最近有些膨胀,干了很多不法之事。朕已经替你遮过去了,希望你要引以为戒,好好约束家人!”讲真,领导能说出这话,够给面子了!可李义府听了,竟“勃然变色,颈颊俱张”,反问道:“谁告陛下?”他的嚣张跋扈令高宗十分吃惊,这还是那个低眉顺眼、肯干能干的李义府吗?他强忍不悦道:“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你听朕的话就是了,何必问朕从哪儿听到的?!岂料,李义府“殊不引咎”,竟“缓步而去”。 当臣子的如此无礼,眼里还有天子吗?私下一调查,高宗气上加气,原来李义府早就傍上了皇后。 李义府聪明吗?能爬到宰相的位置上,应该是个聪明人。李义府愚蠢吗?从给皇帝甩脸子的事来看,他是真的蠢。皇帝毕竟是皇帝,皇后终究只是皇后,皇帝真想收拾他,皇后是拦不住的。而且,皇帝收拾他根本不用亲自出面,有的是人替他张罗。 果不其然,四月,李义府就完蛋了。 他与术士杜元纪过从甚密。一日,二人结伴到长安郊外游玩,登上一座古墓,眺望长安的气色。当日就有人就向高宗打了小报告,说李义府请术士望气,图谋不轨。紧接着,又有人揭发李义府通过其子右司议郎李精,收受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钱七百缗,帮助长孙延获得了司津监的职位。 高宗可逮着机会了,不顾武后阻拦,将李义府下入大牢,命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主审。经调查,“事皆有实”。李义府随即被除名,流放四川西昌,李精流放三亚,其余诸子及婿并除名,全部流放庭州陪杨德裔去了。李家人天南海北,一朝破灭。“朝野莫不称庆”。有人甚至写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贴在街上,以示普天同庆。 扳倒李义府,高宗就雄起了,八月又以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代理左相。算上上官仪,已经有三个宰相是自己人了,他就想“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口气把武后废掉算了。 北溟玉坚持微观写史的思路,深耕10年,述晚隋全唐300年间人事。全书四梁八柱、脉络清晰,文风平白不失趣味,见人见事见思想,写生写真写人性,读之可以佐酒,思之犹可回甘,实为近年少有之通俗历史佳作。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一部:李唐开国》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二部:贞观之治》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三部:日月星辰》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四部:女皇则天》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五部:开元天宝》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六部:藩镇铁幕》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七部:四祸叠加》 《显微镜下的全唐史第八部:长河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