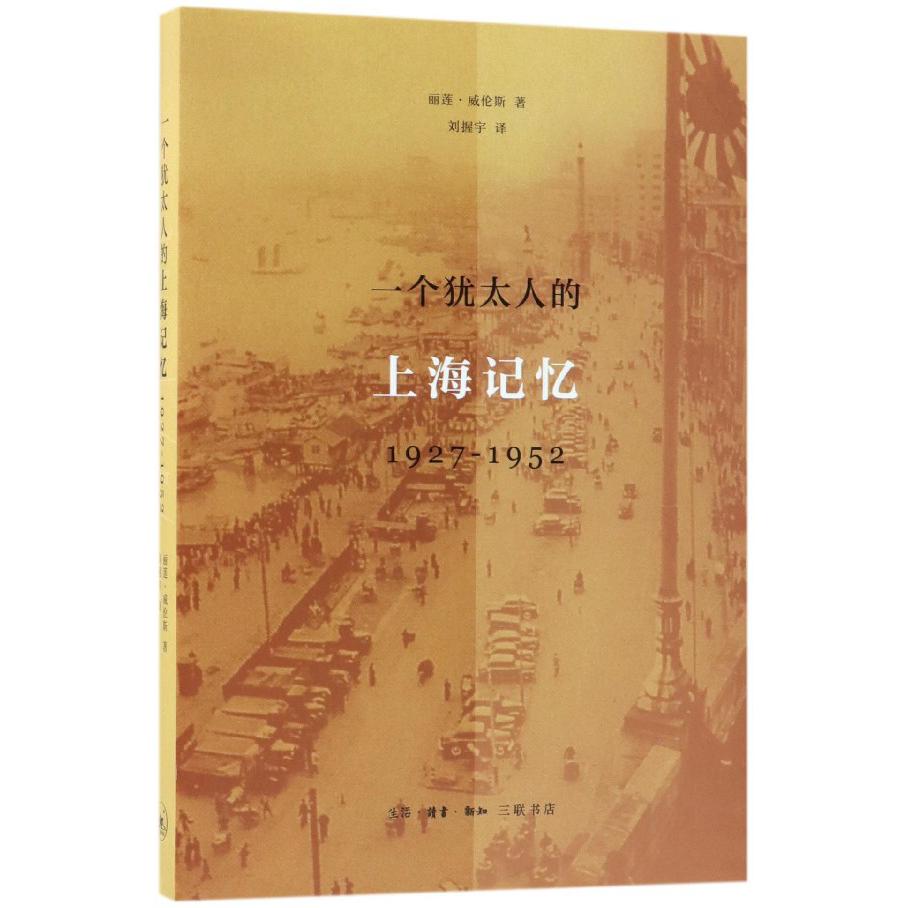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2.20
折扣购买: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
ISBN: 9787108060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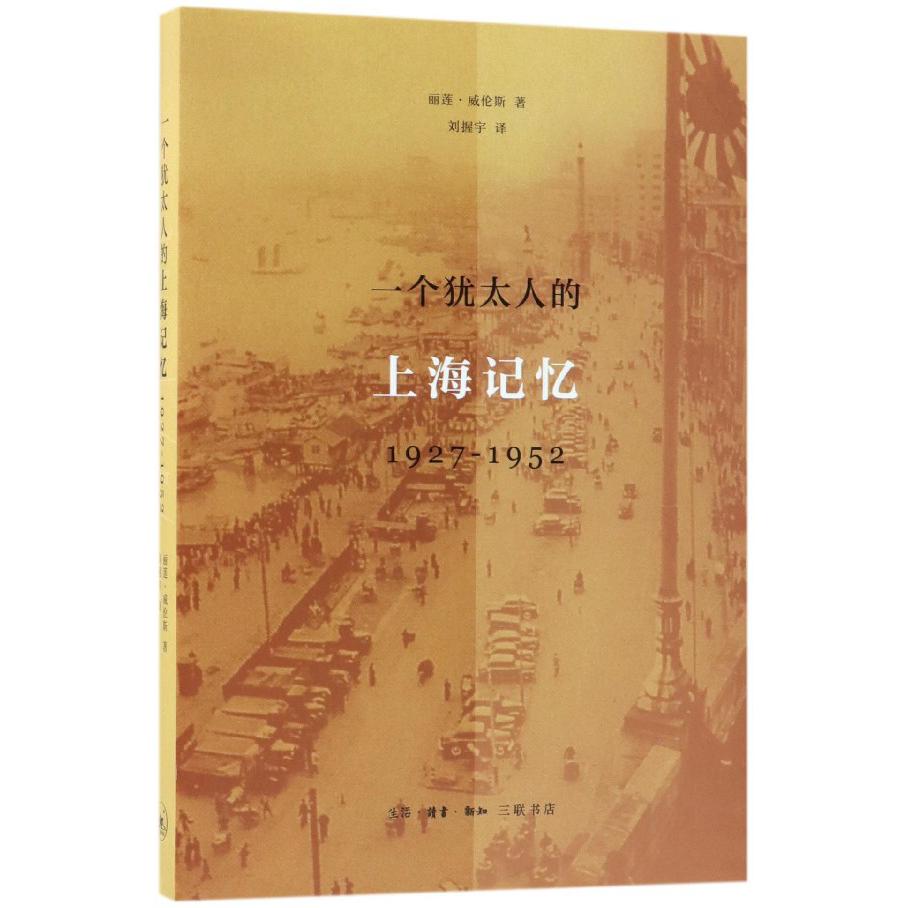
我是个好动的小孩,而我的好奇心也很强。我经 常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校长查尔斯·格罗布瓦——他经 常来听我们一年级的课——总戴着一只棕色的皮手套 。对此我一直心存疑惑。我的结论是,他肯定弄丢了 另一只手套,而且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在学校里听课, 所以没时间去买一副新的。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 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右手。 虽然手有残疾,但在与朋友们一起演出的室内音乐会 上,格罗布瓦却担任小提琴手。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被反复教导,不正确地使用法 语是一项不赦之罪!很多年后,在巴黎的一次法国公 学校友聚会上,我以前的同学珍宁·雷诺回忆说,她 在小学时曾经问过我是不是法国人,我回答说“不, 罗马尼亚人 (Roumanienne)”,而她则傲慢地向我指 出,罗马尼亚人应该说成“Roumaine”。 法国公学的五百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是法国籍, 其中一小部分来自比利时和瑞士的法语地区,还有一 些是来自印度支那和非洲的会讲法语的小孩(他们的 父亲在法国殖民军队中服役,就驻扎在上海)。非法 籍的学生则主要包括无国籍的俄国人、欧亚混血儿( 父母一方是法国人)和少数上流阶层的中国人。这所 学校并不采取任何基于种族或国籍的歧视性政策。瑞 娃的同学玛格丽特·何的父亲就是中国政府的一名高 官,她和妹妹经常来我们家一起学习、吃饭和玩耍。 我们也去过她们家,但我们双方的家长却从未见过面 。我父母从来没有结识过说英语的中产阶级或上流社 会的中国家庭。这两个社会地位相似的群体之所以如 此隔膜,与其说是因为各自都有优越感,倒不如说是 因为他们彼此都缺乏兴趣去了解对方的文化。我有个 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名叫克劳德·达罗索,他有个妹妹 叫克里斯蒂亚娜,虽然他们的父母是来自安地列斯群 岛的非洲人,但他们俩却被大家认为是真正的法国人 ,并被白人学生们视作自己人。他们的父亲曾在一战 期间服役于法国军队,在上海时是军队里的一名军需 官,因此他的家庭也跟法国人同属一个社会等级。可 是,中国人的看法却与此不同。每当克劳德跟我们一 起骑车离开学校时,总会有中国的行人停下脚步盯着 他看,并冲着他指指点点,因为非洲人在上海很少见 ,通常所谓的外国人要么是白种人要么是日本人。所 以说,虽然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自视很高,但跟美国 人和英国人(尤其是后者)比起来,他们对其他民族 倒并不是特别地蔑视。 公共学校必须实施非宗教的世俗教育,这一点早 于1881成为法国的法律,但一位上海的天主教神甫博 塞神父每周都要来我们学校一次,向准备领圣餐的小 学生们讲授教义问答。生活在中国的法国官僚们并不 认为,在世俗学校进行每周一次的宗教教育违反了法 国本土政教分离的严格法律。另一位神甫——来自耶 稣会的雅坎诺(中文名为饶家驹)——也经常来我们 学校,大概是来见我们的校长吧。有好几次,他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