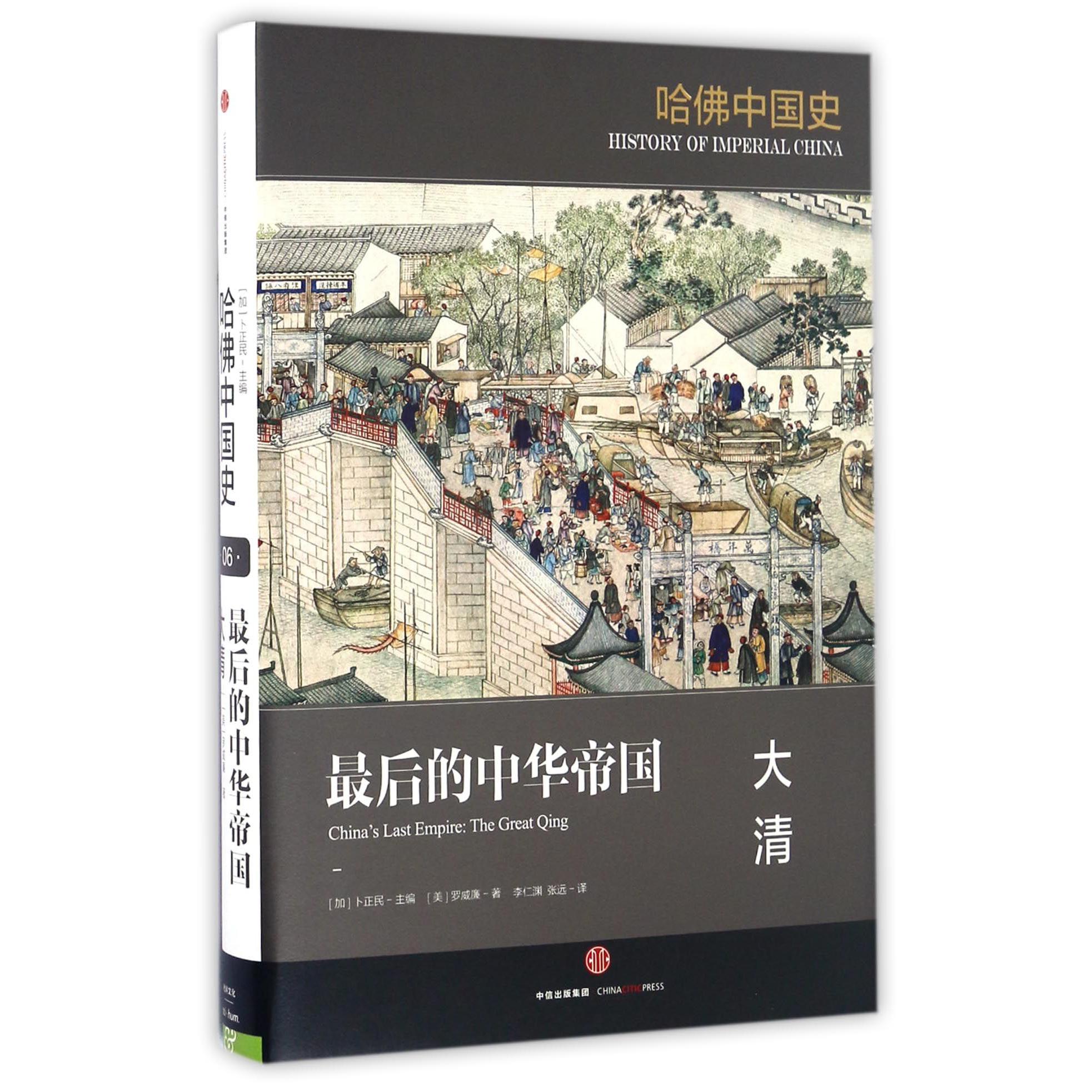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精)/哈佛中国史
ISBN: 97875086656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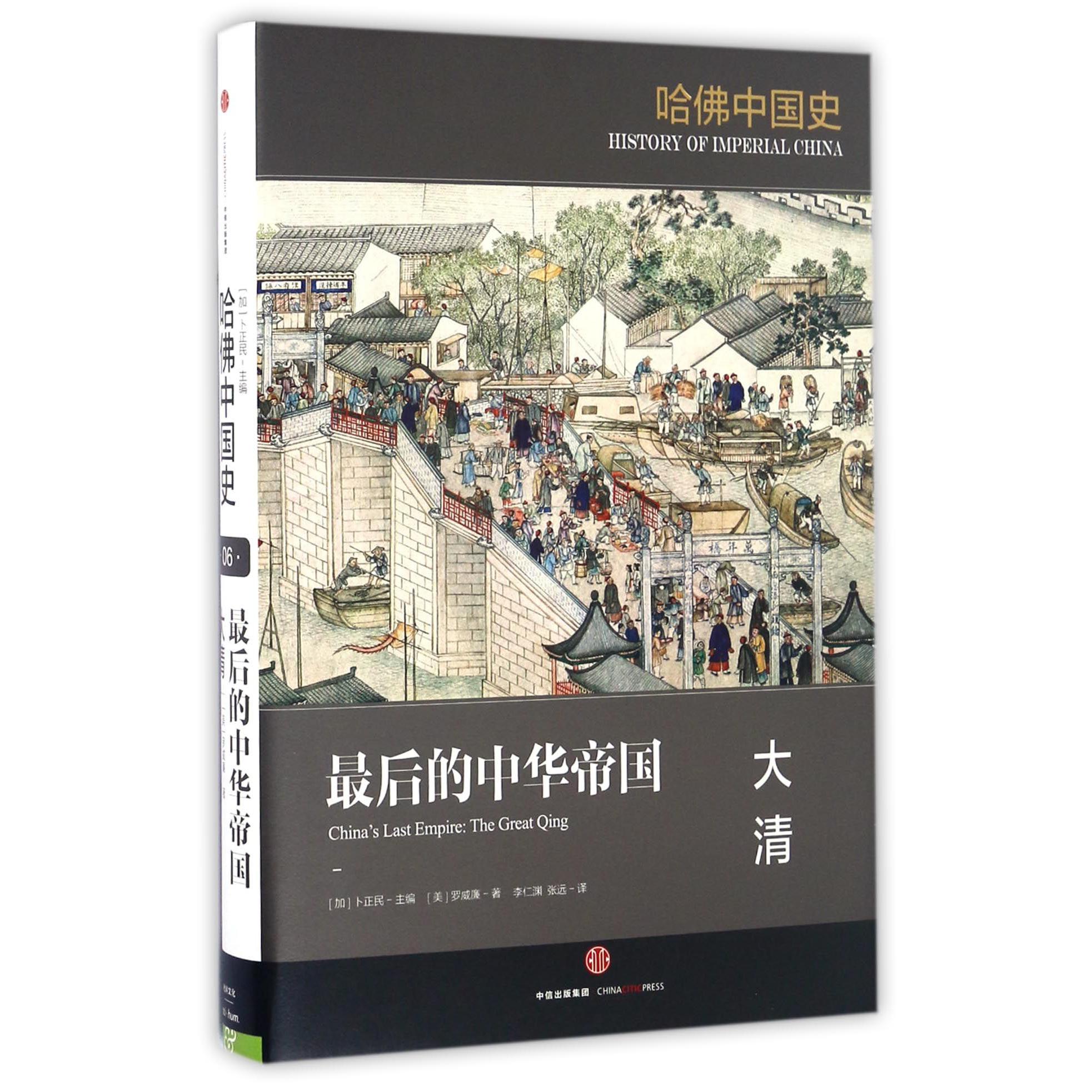
张远,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现为德明财经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朝至近代的性别与通俗文化,着有《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清中期北京梨园花谱中的性别特质想象》等。 李仁渊,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博士。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史。著有《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等。 卜正民 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亲自撰写其中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已译为中文的作品多达十几种,在海峡两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他主要作品有:《秩序的沦陷》《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杀千刀》等。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第一章 征 服 1688年,正蓝旗官员佟国纲上书康熙皇帝,希望 将他正式登记的族属从“汉军”转为“满洲”。他的 伯祖父佟卜年于1580年左右在辽东出生,而后迁徙到 位于华中的武昌。他以武昌为籍通过1616年的会试, 先是担任明朝底下的县官,之后受召前往东北防守满 洲。在一场惨烈的败仗之后,佟卜年被控叛国,且于 1625年死在狱中,但他始终坚称自己忠于明朝。他的 儿子佟国器在武昌长大,并在武昌编了一本族谱,证 明自家至少从十代以来都是明代忠勇的军士,以此为 父亲的忠诚辩护。不过佟国器于1645年在清军征服长 江地区时被俘,他与他的家族都被编入正蓝旗汉军。 然而原来那些被佟国器诚实地收入族谱、佟家在 辽东的后裔,在清军的征服事业中也表现一如保卫明 朝的佟卜年那样英勇。实际上,辽东佟家的其中一位 ,后来成为康熙皇帝的外祖父,而使得佟国纲自己亦 可算是康熙的叔伯辈。因此,康熙皇帝同意佟国纲的 请求,将他重新纳入满洲,然而皇帝也指出,如果将 他的远亲也一起改籍可能造成管理上的不便。从此之 后,佟国纲和他的部分亲属成为满人,而其他佟姓族 人则仍保持汉人身分。在这样的时空下,族群认同远 非由基因所决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可以经由协 商改变的。 像这样的故事对重新从历史理解这个在1644年入 主中国的统治者来说非常重要。不久以前,一般对满 族的认识一方面来自“种族终究是种族”的本质性预 设,认为每个种族(如同满族)都是由生物或基因因 素所决定,一旦决定便永远如此。另一方面,这样的 本质性观点也同时建立在一种目的论式的汉族民族主 义史学之上,认为在20世纪出现的汉族民族国家是中 国两千年王朝历史的必然结果。在这个逻辑之下,包 括异族统治在内的所有国祚较久的朝代都大体相似。 如满洲或蒙古等外族或可征服汉人的地盘,但如果要 让政权保持下去,就得要以中国的方式统治,而最终 将他们自己变为中国人。 在这种对清朝统治的设想之下,满洲作为一个种 族或族群在征服明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他们在 各方面都是“野蛮人”,在文化上较汉族低等。但在 他们入主中原之后,经过一些内部辩论,满人选择以 儒家的天子概念来统治中国。这样的决定不可避免的 导向文化“同化”(assimilation)甚而在生物层面 上也令满族消失。一些如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 位)的满族统治者警觉到,他们族人与其他人群的区 别性逐渐消失,主张维持“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以为后盾,然而这些尝试注定要失败。所以当中 华民国在1911年推翻满清时,真正的满人已所剩无几 ,大部分已融入中国人口当中。这样的叙述同时也有 一种暗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于东 北建立一个满洲民族国家的企图基本上是一种阴谋, 因为以中国的观点,所谓满洲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存 在了。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清史学家开始以几乎完全 相反的观点改写这段叙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学 者不再相信像“种族”这类生物性范畴的本质化概念 ,而视种族分类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协商 过程下的产物。因此,根据这样的新观点,在17世纪 时实际上没有“满洲”这个种族,只有接邻在明帝国 东北边疆的众多人群,各自具有相当不同的祖先谱系 与文化传统,其中不少人全部或部分的祖先是汉族。 这个承继明代皇位的群体不是种族上的满族,而是一 个以胜战为目的、有意创造出来的人群组织。这个“ 征服组织”的领导者认为,分派不同族群认同给他的 成员,如蒙古、汉军乃至于满洲等是有用的,而这样 的族裔分派与其说是依循既定的生物事实,还不如说 是图政治之便。如同上述佟家案例,如果情况需要的 话,这些初始的分派可轻易地撤销或改变。 较早的观点认为,刚开始可被区分出来的满人随 着时间逐渐被同化或消失,而新的清史叙述则认为满 人在整个清朝都实际存在。乾隆皇帝与其他人的努力 与其说在守护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还不如是说 在创造一个具有起源神话、民族语言与文学、明确文 化特征的民族文化,而这个计划出乎意外地成功。讽 刺的是,若满洲在1644年之前实际并不存在,他们在 1911年确实存在了。以这样的观点,满洲国的故事的 确如同贝托鲁奇(Bertolucci)的伟大电影《末代皇 帝》(The Last Emperor)中所呈现的那样。电影中 逊位之后的溥仪从上海的颓废生活中被唤醒,回应这 些他诚心认为的满洲人民的召唤,领导满洲人在东北 的民族国家。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欺瞒之处,并非是 纯正的满洲人是否真的存在(此时这样的群体的确存 在),而是谎称满洲人会有真正的民族自决。 这样的新叙述本身可能言过其实。第二代的“满 洲中心”研究主张从清朝肇始,至少在当代人眼中, 即存在着族群或种族区别的现实。例如一项对清代满 营的研究显示,满营中的居民与周遭汉族人群始终具 有显著的族群紧张关系。然而无论是那种形式,现在 多数史学家喜欢新的叙述胜于旧的,而新叙述的假设 即为我们故事的基础。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