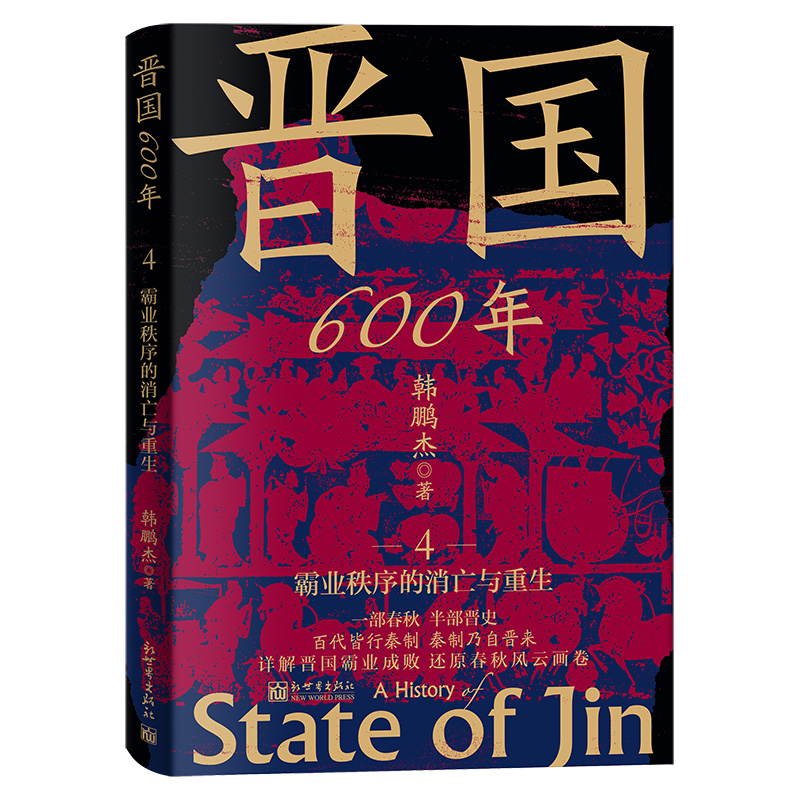
出版社: 新世界
原售价: 62.00
折扣价: 36.60
折扣购买: 晋国600年4:霸业秩序的消亡与重生
ISBN: 9787510479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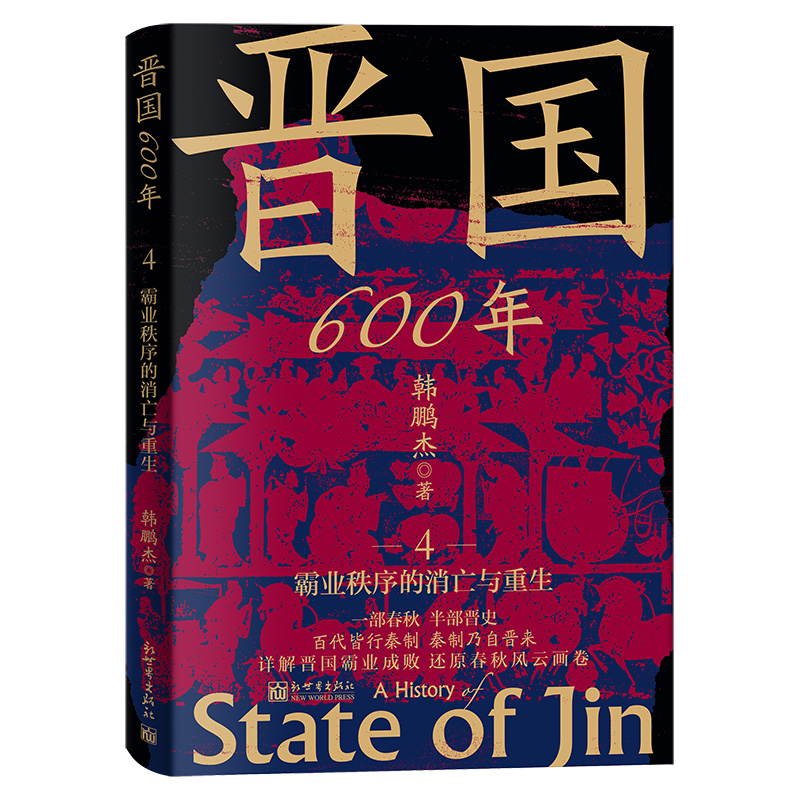
韩鹏杰,晋中人士,新锐历史作家,多年来深耕历史地理领域,对晋地历史尤为精通。历史博主、今日头条签约作家,在网络上集结了大量先秦历史爱好者群体。
第一章?晋国霸业的衰落 第一节 寻盟之会 韩起出使 晋平公十八年(前 540 年)春,刚刚接替赵武担任中军元帅的韩起,顾不得举行烦琐的就任仪式,就迅速打点行装奔赴东方,马不停蹄地对鲁、齐、卫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向列国通报自己执政的消息。 在拜访鲁国时,韩起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大史氏负责管理的宫廷藏书。在翻阅了《易》《象》《春秋》等典籍之后,不由称赞道:“周朝的礼仪都在鲁国了,看了这些我终于明白了周公的德行,理解了周朝之所以能够成就王业的缘故。” 在随后鲁昭公专设的享礼上,鲁国正卿、季孙氏宗主季孙宿赋《绵》之最后一章。这首出自《诗经·大雅》的诗讲述的是周朝先祖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徙到岐山后,在一片荒原中开辟土地、疏通道路,组建军队、营建城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得周人族群发展壮大的故事。 至于诗的最后一章,则带出了周文王平虞、芮两国争讼的事情,预示着周人的德行日渐昌盛,已经逐步具备了翦灭殷商的能力。其中“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四句,据说象征的是文王有四名贤臣,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周人才得以星星之火绵绵不绝,终至于发展成燎原之势。季孙宿在这里赋《绵》之卒章,其意是将晋平公比作周文王,将韩起比作文王“四辅”,恭维的意味浓烈而厚实。 韩起听了之后,回之以《诗经·小雅角弓》。这首诗据说是在讽刺周幽王近奸佞而远亲族,导致骨肉相怨、纲纪崩坏之事。韩起取诗中“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之句,意指兄弟之国应当相互亲近和睦,这样才能团结民众,避免怨怼集聚以生出祸乱来。 季孙宿当即拜谢:“有您的这番心意,寡君就看到希望了!” 紧接着,他又赋了《节》之最后一章。《节》即《诗经·小雅节南山》一篇,其所指的时代历来众说纷纭,但就诗中所述的情景来看,显然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当政的天子和官员不能持平,导致天灾人祸不断,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诗的最后一章,是作者“家父”说明自己作诗的本意,是为了追究这场祸乱的元凶,希望他们能改变邪心。 单从诗歌描述的情景来看,其中包含着很大的怨气,与当下赋诗唱和的场景显然是不相称的。但季孙宿所取的仅是“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一句,意在夸赞晋国君臣德行高尚,足以造福天下诸侯惠及黎民百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人们在社交场合上运用诗歌时并不完全遵循其本意,更多的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截取自己需要的片段来表达心志即可。 享礼结束后,鲁人又在季氏府中设下饮宴。韩起看到院子里栽植的一棵树长得十分挺拔,于是便情不自禁地赞叹了几句。季孙宿当场表示以后会悉心管护这棵树,以感谢韩起赋《角弓》对鲁人的勉励,并赋《甘棠》一诗。 《甘棠》是一篇怀念召公的诗作。相传当初召公巡行乡邑,所到之处不占用民房,只在一棵甘棠树下停车驻马、搭棚过夜,决断曲直、教化百姓。国人感念其德、服其教化,所以爱屋及乌,以甘棠树作为寄托而不忍翦伐。 季孙宿前以文王四辅来作比,后又以召公之德逢迎,马屁都快拍到天上去了,让韩起自己都感到无地自容,于是急忙推辞说:“起愧不敢当,哪里敢跟召公相提并论?” 离开鲁国后,韩起旋即奔赴齐国,代表晋平公向齐景公送来了两国缔结姻亲的聘礼。逗留期间,他分别拜会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公族权臣子雅(公孙灶,栾氏)与子尾(公孙虿,公族高氏)。 不久前,齐国刚刚发生了几场内乱。先是在晋平公十二年(前 546 年)时,崔氏家族因继承人问题出现纠纷,一直觊觎崔杼地位的庆封从中浑水摸鱼,诱导崔氏二子发动内乱,随后又凭借崔杼的信任出兵平乱,致使崔氏家破人亡,崔杼也在绝望中自尽。 庆封掌握朝政大权之后,担心有人会兴风作浪,故而征召在外流亡之人举发崔杼余党,齐庄公的近臣卢蒲癸、王何由此得以返回齐国。这两人一面假意侍奉庆封之子庆舍,一面秘密联络了与庆氏有怨的公孙灶、公孙虿以及陈氏等宗族,于次年十一月发动政变,迫使庆封经由鲁国逃到了吴国。公孙灶和公孙虿本身就有公族身份,此番又借迁葬齐庄公、将崔杼尸体示众等举措迅速获得了国人的支持,同时还进一步打击了反对势力,逐渐取代了崔氏、庆氏在国中的地位,成为齐国真正的“话事人”。 两位公孙得以执政时均年事已高,都有心将权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如今韩起来聘,他们就分别将自己的儿子栾施(子旗)、高强(子良)叫出来见礼,其意大概是想让韩起以后能关照着些。但韩起对他们的评价却出奇地一致:“这不是能够保得住家族的人,实在不像个臣子。” 其时齐国大夫多嘲笑韩起,认为他身为大国执政,看人的眼光也不过尔尔。只有晏婴对这个判断深信不疑,他认为韩起是个君子,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人暂时看不出其中的蹊跷罢了。 回程途中,韩起又拜访了卫国,卫襄公同样设下享礼款待。其间,卫国大夫北宫佗(北宫文子)赋《淇澳》。这是一首赞扬卫国先君卫武公的诗作,北宫佗以卫武公之德来夸耀韩起,其溢美之情不言而喻。韩起则赋《木瓜》一首,诗中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之句,所要表达的寓意亦是不言自明。 这是一次波澜不惊的外事活动,然而细想起来却很是耐人寻味。 以往的晋国执政,其上任之时虽不需要像国君登基一样让各国君臣前来朝贺拜会,但通常都会巧立名目举行一次诸侯会盟,以向天下人宣示自己的地位,在位期间也很少会专门到列国访问。韩起以霸主执政的地位却要屈尊纡贵,以拜会诸侯的方式来通报自己为政的消息,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奇闻一桩。 对于这样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动,《左传·昭公二年》的叙述可谓平淡无奇。除了那些看似可有可无的细节外,我们只知道韩起到齐国的目的,是为了给晋平公行“纳币”之礼。至于到鲁国和卫国的行程,就好像纯属顺道路过一般。但实情果真会这么简单吗? 郑人朝楚 想要搞清楚这其中的因由,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晋平公十二年(前 546 年)七月,在宋国都城商丘西门外盛大的会盟仪式上,晋、楚这对春秋时代最强劲的对手终于握手言和,中原大地持续了百余年的争霸战争也戛然而止。第二次弭兵会盟的顺利举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更为中原大地带来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局面。 然而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在同一个政治圈里出现了两强共霸的局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不过,在当下的时节里,人们似乎还来不及去想这些高深莫测的议题,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那就是促成盟约尽快落到实处。 这次会盟所签协议中有一项重要条款,是让原先隶属于晋楚两国阵营里的诸侯分别到对方的盟主那里朝见,也就是履行“交相见”的义务。 这样的条款对于楚国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放弃过兼并的战略,但凡与楚国接壤的国家不是变成了楚王治下的一个县,就是沦为了彻头彻尾的附庸。因此,当中原各国举行弭兵会盟的时候,从属于楚国的诸侯实际上也就只有陈、蔡、许等区区几个小国了。 而作为中原诸侯的盟主,晋国则一直遵循齐桓公“尊王攘夷”“兴灭继绝”的争霸策略,其所笼络的宋、郑、鲁、卫等诸侯都是响当当的中原大国。东方的强齐、西方的秦国虽不能真心归附,可在晋国的压制下也始终不能有所作为;在南方,与楚国毗邻的吴国也与晋国为善。 在双方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正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晋国竟主动提出共享霸权的弭兵之约,将楚人为之争夺了上百年都没有得到的中原列国拱手送上,这份大礼着实已经大大超越了楚人奔放的想象力,让楚国上下都精神恍惚了好几个月。 好在这些楚人也都是经历过大阵仗的,很快就从惊喜中回过神来,并急不可耐地开始安排履约的事情。会盟当年冬天,楚康王就安排薳罢到晋国去商定具体细节;紧接着到第二年(前 545 年)夏天,从属于楚国的陈、蔡、胡、沈四国国君就手拉着手到晋国去朝见了。 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齐、北燕、杞、“白狄”等国的君主。这其中北燕国和“白狄”地处北方,在当时还算是中原秩序之外的国家,听闻中原各国弭兵休战,都纷纷前来向晋国示好。齐国自外于晋楚盟约,本来没有前来朝见的义务,但由于此前的两任国君多次冒犯晋国,如今两国刚刚交好,自然要来巩固一下关系。 八国国君呼啦啦地同时来朝,搞得晋平公也有些应付不过来。好在楚国的盟友也不多,晋平公端起架子支应几天也就算过去了,可楚康王就没那么好应付了。 多年以来,楚康王一直幻想着自己能跟晋国国君一样,做一回货真价实的诸侯盟主,如今梦想就要实现了,心里还真有些小激动。也正因为如此,刚刚转过年来,他就催促着陈、蔡、胡、沈四国国君率先朝晋,楚国方面也就履行了盟约的义务,接下来就该看晋国方面的表现了。 然而让楚康王大感意外的是,左等右盼到眼睛都快望穿了,却没有等到哪怕一个诸侯国的君主前来朝见。好不容易到了夏天,边境上传来郑国来朝的消息,仔细一询问却发现,对方派来的只是一个名叫游吉(子大叔)的大夫,这可叫怎么回事? 楚康王当时就脸色铁青,命人到汉水阻拦郑国使团。游吉风尘仆仆赶到楚国,未曾想遭到如此待遇,心中自是愤愤难平,故而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在宋国举行盟会时,贵国口口声声说要实行对小国有利的政策,以使得小国可以安定社稷、镇抚百姓,用礼仪来承受上天的福禄。这不仅仅是贵国的法令,同时也是与会各国共同的心愿。如今敝邑屡受天灾侵袭,国家疲弱、民生凋敝,寡君不敢在危难时刻丢弃国家职责,因此才派游吉前来奉上财礼。可执事却一意孤行,执意让寡君餐风饮露、跋山涉水前来朝见以满足您的欲望,这恐怕不合适吧?” 但楚人根本不理会这些:“你们这些事情我们管不着,我们只知道在宋国举行会盟的时候,你们的国君是参加了的。如今你们的国君窝在家里不肯来朝见我王,这是瞧不起我们楚国呢,还是压根就没拿盟约当回事?寡君说了,您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倒想问问晋国是否真的有履行盟约的诚意!倘若晋国真是这么要求的,您再回来也不迟。” 游吉还一心苦劝,说:“如果楚国一定要寡君亲自朝见,郑国只能唯命是从,只是担心会因此败坏了楚王的德行,影响楚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既然你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又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多走几步路的事嘛!” 临到楚国却吃了个闭门羹,游吉的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回国之后,他向同僚们大倒苦水,还愤愤然地诅咒道:“这样一个不守信义只顾满足自己私欲的人,恐怕是活不了多久的。要我看,国君大可以到楚国走一遭,只不过,这一趟恐怕不是要朝见,而是给楚王送葬。楚人如此行事,显然不能号令诸侯了,这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没好气归没好气,楚国的事情还真不能不放在心上。郑国已经受够了晋楚拉锯的夹板气,这个时候就算是再多受一些委屈,也应该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维持下去。不久,游吉就再次踏上旅途,风尘仆仆地赶到晋国,向晋人报告国君将要到楚国朝见的消息。与此同时,郑简公也在子产(公孙侨,国氏)的陪同下踏上了朝楚的道路,以期尽早完成履约的义务。 然而事与愿违,郑人的诚意显然没能打动楚康王的铁石之心。他渴望的是万国来朝的虚荣景象,仅仅一个郑国前来朝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当郑简公抵达楚国行完了朝聘的礼仪,楚人却迟迟不肯放行。郑简公虽懊恼,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满心焦虑地望着北方,等待着那些难兄难友们尽快赶到,好让自己早日重归自由。 祓殡而襚 相比起内心急躁的郑国国君,其他诸侯就从容了许多。当决定要履行交相见义务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直奔楚国而去,反而是“南辕北辙”地先跑到晋国去了。就比如鲁国,早在游吉出使楚国之前,就已派出孟孙氏宗主仲孙羯(孟孝伯)到晋国去汇报工作。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游吉从楚国回来又去了晋国,郑简公也早已启程到了楚国,鲁襄公竟然还躲在自己的宫殿里没有出发。 诸侯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其用意无非是两点:首先是要消除晋国的猜忌,毕竟这种事情之前从未发生过,他们也不清楚晋国对此究竟持何种态度。倘若未经请示就去楚国朝见了,日后晋人责问起来,你就是有理也说不清楚。其次是想要让晋人为自己撑腰,一个过去屡屡欺辱盟国同时在诸侯会盟时带甲上阵的国家,很难让中原诸侯放下芥蒂、产生毫无保留的信任。万一楚人又像孟渚之会那样刁蛮起来,有晋人在背后伸张正义,结果也不至于太让人难堪。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手续后,这一年也就快过到头了。到了这年十一月,鲁襄公才不紧不慢地带着庞大的使团踏上了前往楚国的旅程。在此期间,他还“不辞辛苦”地特意绕道郑国,打算和郑简公一起携手同行。得知郑简公已经出发,就又掉头回来与宋平公搭了个伴儿,相扶相守共同上路。前往楚国的行程道阻且长,餐风饮露的滋味并不好受,可他们却故意放慢步伐,磨磨蹭蹭,能耗得一时是一时。 经他们这么一折腾,郑简公可就遭罪了。他在楚国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等了将近三个月,却还是没等到自己的难友们前来相会。而楚康王或许也是焦躁过度,还没来得及等到那个让他走上人生巅峰的荣耀时刻就去世了。这样一来,游吉一语成谶,郑简公的朝聘之旅果真就变成了送葬之旅。 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传出的时候,一直游山玩水故意拖延的宋、鲁两君才刚走到汉水边上。望着奔腾而过的汉水,两国君臣都停了下来,就是否该继续前往楚国朝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宋国是一个君权相对集中的国家,一切行动以国君本人的意愿为准绳,因而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在他们看来,宋人此番前来只是为了满足楚康王的虚荣心,又不是因为跟楚国有多好的交情。当前宋国国内还在闹灾荒,百姓还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哪里能顾得上楚人的感受?随即他们扯了行李就掉头回去了,留下鲁国人接着争论。 与宋国不同,鲁国公室的权力已经被三桓瓜分一空,大夫们做出决策时通常也都以私家利益为准绳。随行的叔孙豹(叔孙穆子,叔孙氏宗主)、叔仲带(叔孙昭伯)、荣驾鹅(荣成伯)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次远行为的就是与楚国搞好关系,楚康王人在不在都不影响他们的目的。当时年纪尚轻的子服湫(一作子服椒,子服惠伯)有不同意见,谁料却遭到叔孙豹的嘲笑,说他是“始学者”,也就是刚刚开始接触政务,还不够资格发表意见。最后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议定继续前往楚国履行朝见义务。 丝毫不出意外的是,在抵达楚国之后,他们果然就和先行到达的郑简公、陈哀公、许悼公一起被楚人给扣下了。这个时候,鲁襄公大概才想起了宋国左师向戌这个“老油条”,这个多年以来一直奔波于晋楚之间的卿大夫,对于楚人的认识是多么深刻,自己真该多听听他的意见啊! 事实容不得假设。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该坦然接受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鲁襄公只好和他的难友们一起,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个最难熬的新年。在朝的鲁国大夫等到新年的钟声敲响,终于确认自己的国君是无法回来过年了,只好取消了原定在祖庙举行的听政朝会。 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消息。等到正月里一切的事务都结束后,楚人大概是为了惩戒鲁国的迟到,竟然又提出了一项非礼的要求:让鲁襄公为楚康王“亲襚”,也就是亲自将鲁国赠送的衣物放置在灵柩的东侧。 通常来说,“致襚”是使臣前往盟国吊丧时的礼仪,楚人让鲁襄公亲自“致襚”,就等于是把他当成一个臣子,而不是地位平等的诸侯。这就让鲁襄公感到很是为难:不听他们的吧,楚人这么无礼,谁知道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可听他们的吧,就等于是承认了楚国的预设,如此贬低身份又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这种两难的处境如果是让旁人遇到或许注定无解,可鲁国毕竟是礼仪之邦,楚人给他们出的难题,很快就被熟稔礼仪制度的叔孙豹给化解了。只见他将鲁襄公拉到一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派人把随行的一个巫师叫了过来。巫师听到吩咐,就用桃木棒和笤帚在灵柩上不住地挥舞着,口里还念念有词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明白的咒语。作法完毕,鲁襄公才缓步上前完成“亲襚”仪式。 初看到这个情形,楚人还真搞不懂这是在玩什么花招,就由着他们去了。事后才知道,原来巫师耍的那一套把戏,在中原被称作“祓殡”,也就是扫除不祥,是国君莅临臣属丧事时所用的礼仪。这样一来,楚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却让鲁襄公占了自己的便宜。 四国国君在楚人胁迫下这时已是这年(前 544 年)的四月了,亲自将楚康王的灵柩送出郢都西门外,其随臣则一直送到墓地。葬礼结束后,他们又参加了新君郏敖的即位典礼,这才被楚人释放而重获自由。 当诸侯纷纷到楚国朝见的时候,流亡归国的卫献公正因国内乱局而悲伤不已,不久就撒手人寰了。一直到两年后(前 542 年),新继位的卫襄公才在北宫佗陪同下到楚国朝见。直至此时,第二次弭兵会盟约定的“交相见”义务才算是完成了。 1.详解晋国六百余年云谲波诡历史全貌,还原春秋争霸画卷底色。捋清晋国制度演变的底层逻辑,深刻剖析晋国兴盛衰亡的历史原因:作为先秦时期最强盛国家的代表,晋国的历史支撑起了整个春秋的历史脉络,同时也构成了战国政治格局的基座。本书以晋国视角梳理了春秋历史的总体框架,对于渴望了解先秦,但又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通读古籍的历史爱好者很有帮助。 2.说史严谨,广泛吸收《左传》《国语》《史记》等有关史料和当代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历史分析丝丝入扣,时有精辟见解:作者熟读经史,各种古籍史料信手拈来,引用皆有来处。对当代研究晋国及先秦史的学术论著、论文多有研读思考,而后成一家之言。 3.行文通俗流畅,叙事生动曲折,文风轻松幽默:先秦是一个风云激荡、群星闪耀的时代,有太多精彩有看点、值得玩味细究的历史事件、人物出现在这一时期。作者叙事简明生动,点评一针见血,不设阅读门槛,没有相关历史背景知识的读者也能读得津津有味。 4.晋人说晋事,述群雄纷争三百年春秋、品经天纬地六百载晋韵:作者生于长于山西,对晋地历史文化研究深入,重点说“晋”,又述尽三百年春秋史,饱蘸家国情怀。 5.书后附作者精心绘制的详解各时期晋国人物关系图谱: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一经图解豁然开朗。 插图示例:晋国公族羊舌氏及芈姓邢侯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惊心动魄春秋画卷徐徐展开,六百余年晋国风云胸中了然。读完本书,相信下面的问题您会有自己的答案: ○为什么春秋时期会出现诸侯争霸这种独特的政治模式?晋楚争霸的实质是什么?站在春秋时人的立场上,“春秋五霸”的盛名究竟该花落何处? ○为什么晋国可以在列国争雄的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响当当的中原霸主,并能够将这种优势长期维持下去?这是由晋文公本人“仁德”所带来的偶然结果,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到了春秋末期,这种政治模式又为何会突然退出历史舞台?吴越争霸的昙花一现,与晋国霸业衰退又有何关联? ○晋文公创设的三军六卿制为晋国的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可为何到最后却演变成了导致君权下移和国家分裂的元凶?究竟谁才是晋国公室真正的掘墓人? ○作为一名复兴霸业的中兴之主,晋悼公的伟业究竟实至名归,还是徒有虚名?晋国霸业的逐渐消亡、国君权力的突然衰退跟他有没有关系? ○从晋文公称霸,到晋平公失霸,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晋国的霸业如同坐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而晋国的君权却似水落悬崖飞流直下,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演变的? ○为什么晋国最后会走向三家分晋的结局,而不是如齐国的“田氏代齐”一般归于一家?参与了世纪决战的智、赵、韩、魏四家都扮演了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