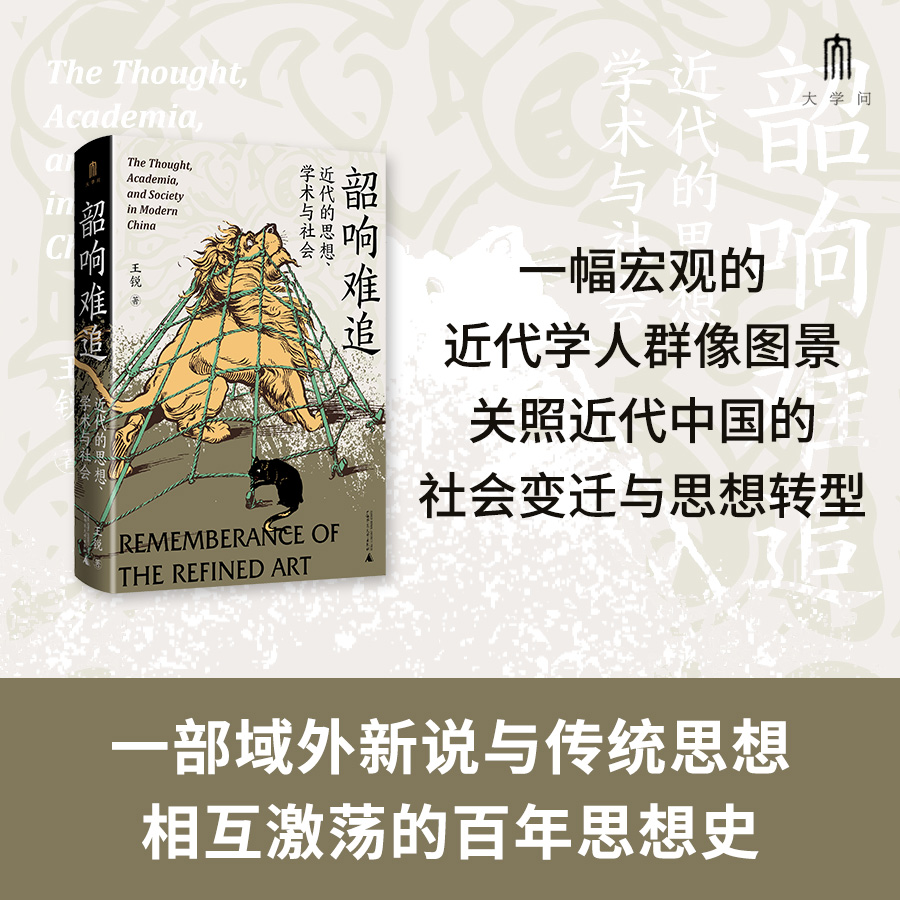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9.40
折扣购买: 韶响难追:近代的思想、学术与社会
ISBN: 9787559875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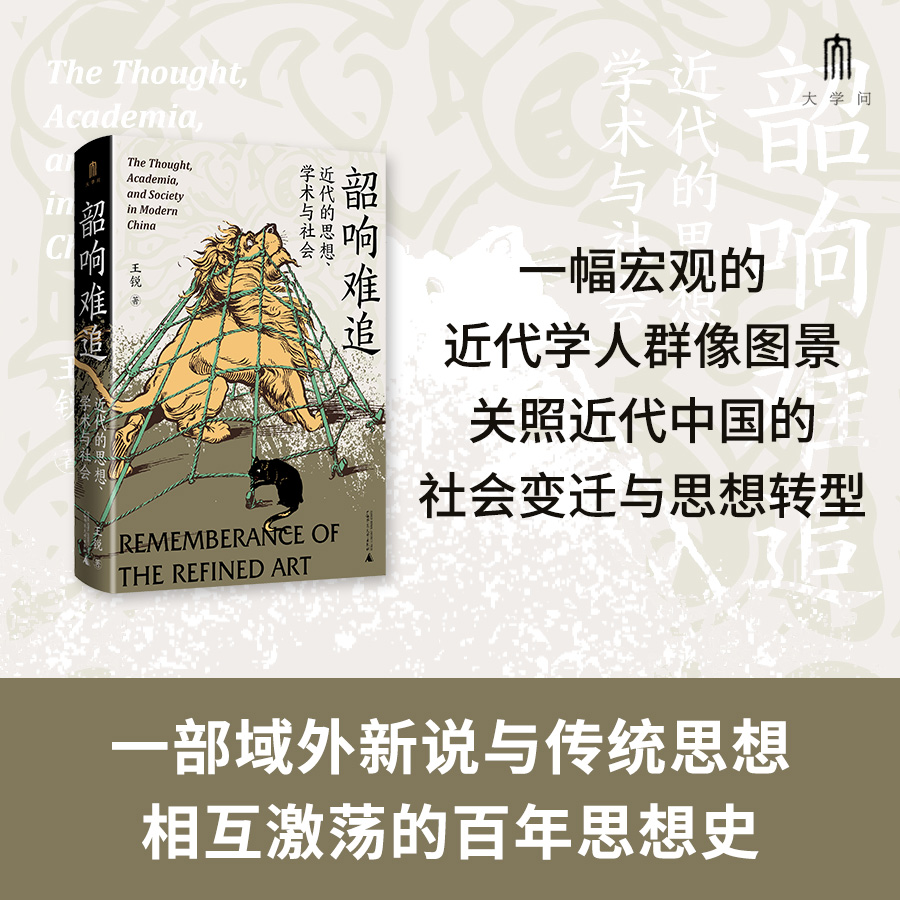
王锐,1987年生,广西南宁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出版《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履正而行: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异代先知:国家主义视域下的法家学说 晚清以降,面对东西列强之间越发激烈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希图瓜分中国的局面,人们多认为此刻世界政治犹如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之重演。这背后体现的是时人认为近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就是大国之间依据相似的发展道路纷纷崛起,然后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争霸,广大的非西方国家与地区除非能够效仿西方列强之所为,在短时间内实现富强,否则都难逃被侵略与殖民的惨境。关于这一点,对时代变局有着敏锐观察的梁启超体会尤深。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阅读了大量由日本学者译介的近代社会科学与历史学著作,使他对19世纪以降的国际政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梁启超认为,19世纪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要求一国内部实现政治变革,推翻封建王权,增加国家实力,保障民众利益,对外则以防止他国侵略始,至对外扩张为本国夺取更大利益终。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认为强国侵略弱国实乃天经地义之事,并无不道德之处。弱国被侵略或殖民,实属咎由自取。一国要想在优胜劣汰的国际环境中自存,唯有不断扩充国力,使国内政治、经济与文教建设皆以国家为本位,国民的权利要建立在为国家做贡献的义务之上。甚至天赋人权论也已为过时之物,国家有机体论方为此刻流行的学说。 尤有进者,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成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地。”“民族帝国主义”的流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在“民族帝国主义”之世里,除了传统的军事征服,列强还善于运用经济手段去控制非西方国家,如借款、倾销商品、修筑铁路、派遣财政顾问等。因此梁启超提醒国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又言:“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此中消息,不待识微者而知之矣。”1903年他赴美游历考察,一方面目睹了以托拉斯、康采恩为代表的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垄断生产,另一方面对美国唐人街里的中国人如散沙一般缺乏组织能力痛心疾首。凡此种种,再加上先前对于世界大势的剖析,梁启超遂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立即施行民主政治,天赋人权论也不适合在中国过度传播。中国需要由具有现代意识的统治者厉行“开明专制”,一方面提高行政效率,建立现代的内政与国防体系;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经济,使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提升;同时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使民众具备政治能力与国家意识。因此,在与革命党进行政治论战时,梁启超明确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 梁启超向来认为,历史学是培养国民意识与政治能力的利器,他的“新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借助历史著作的普及化来宣扬他心目中当时中国人所需掌握的政治观念。因此,梁启超在清末写了大量历史著作,或是将“民族帝国主义”的内容投射到古人身上,或是秉持建设现代国家的立场来批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或是借由叙述与中国命运相似的亚非国家的“亡国史”来警示国人。除此之外,梁启超相信学术为“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可以“左右世界”。那么为了更好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绝不会忽视从中国传统政治学说当中汲取可供阐扬的资源。其中,他注意到了先秦法家。 1909年,梁启超出版《管子传》。从书名就能看出,他是在叙述被视为法家人物的管仲的生平与思想。在“例言”中,梁氏声称该书“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此外,他特别强调在“发明管子政术”时,自己“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这就表明,他在书中并非以复原管仲的生平与思想为目的,而是要以新学说为视角,去解释管仲的“政术”。 关于管仲的历史地位,梁启超认为: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 梁氏又言: 至最近二三十年间,然后主权在国家之说,翕然为斯学之定论。今世四五强国,皆循斯以浡兴焉。问泰西有能于数千年前发明斯义者乎……有之则惟吾先民管子而已。 基于此,梁启超将管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分为“法治主义”“官僚政治”“内政”“教育”“经济政策”“外交”“军政”等几个内容,分别论述管仲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壮大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力,整合齐国内部的人口资源与经济资源,让经济生产为政权服务,使齐国具有逐鹿中原的资质,并在春秋诸侯国中间长期居于霸主地位。在梁启超看来,“管子为忠于国民之政治家,为负责任之政治家,为能立法之政治家,为善于外交之政治家,为能实行军国主义之政治家”。 在《管子传》中,梁启超毫不讳言自己的国家主义立场。他说: 夫以一国处万国竞争之涡中,而欲长保其位置毋俾陨越,且继长增高以求雄长于其侪,则必当先使其民之智德力,常与时势相应,而适于供国家之所需。国家欲左则左之,欲右则右之,全国民若一军队然,令旗之所指,则全军向之。夫如是乃能有功也。 基于此,他认为管仲的内政举措类似19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当中的“干涉主义”,即通过建立法度来最大程度地组织、调度国内各种资源,使国家机器能够极有效率地运转起来,并借助国家力量形成经济托拉斯。在论述管仲时代的相关史事之后,梁启超指出: 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又当为国家自身谋利益,故以图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何也?国家毁则个人且无所丽,而其幸福更无论也。是故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试观我国今日政治之现象与社会之情态,纪纲荡然,百事丛脞,苟且偷惰,习焉成风。举国上下,颓然以暮气充塞之,而国势堕于冥冥,驯致不可收拾者,何莫非放任主义滋之毒也?故管子之言,实治国之不二法门,而施之中国尤药之瞑眩而可以疗疾者也。 很明显,在梁启超眼里,以管仲为代表的先秦法家之所以值得提倡,主要是因为后者与近代的国家主义颇为相近,都强调国家本位、国家优先,相信只要做到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就能让国家实力大增,改变先前的涣散凌乱之象。 更有甚者,梁启超认为“民族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为了更好地使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强调:“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在他看来,管仲是可以与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齐名的大政治家: 昔克林威尔当长期国会纷扰极点之后,独能征爱尔兰,实行重商主义,辉英国国威于海外;昔拿破仑当大革命后,全国为恐怖时代,独能提兵四出,蹂躏全欧,几使法国为世界共主。盖大豪杰之治国家,未有不取积极政策而取消极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诚大国民之模范哉! 这一论调的关键之处,不在于管仲是否有资格与这两位西洋人相提并论,而在于梁启超之所以对此二人予以极高评价的理由。在他看来,克伦威尔与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既不是因为前者发动革命,组建新模范军,处死英国国王,建立共和体制,撼动欧洲王权,也不是因为后者巩固并传播了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同时用法典的形式将这些诉求确立下来,而是由于这二人都善于进行对外扩张,符合“民族帝国主义”的标准。依梁氏之见,管仲的政治实践也与此标准颇为相契,所以他堪称“大国民之模范”。总之,梁启超对于管仲的诠释,基本是在国家主义的维度上进的。 ——节选自王锐《韶响难追:近代的思想、学术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 编辑推荐一 本书剖析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转型中的一些产生深刻影响的问题,透视那些思想学说背后的渊源与流变,呈现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那些复杂而曲折的内容。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与对国内问题的分析之间的紧密联系,梳理那些看似相近但却颇有歧异的思想主张。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钱穆、蒋廷黻、吕思勉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思想,都在本书中有所呈现。 编辑推荐二 本书试图分析,为什么从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界一直有一股追求国家主义的风气。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主义的理解有何异同,这些理解,如何在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论述中表现出来。为什么从梁启超主张的“开明专制”,到蒋廷黻倡导的“新式独裁”,都难以真正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类矛盾与症结。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的大量负面遗产,为什么需要被不断地予以正视与剖析。章太炎在清末呼吁的“恢廓民权”与“抑官吏伸齐民”,为什么会在实践中遭遇如此多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