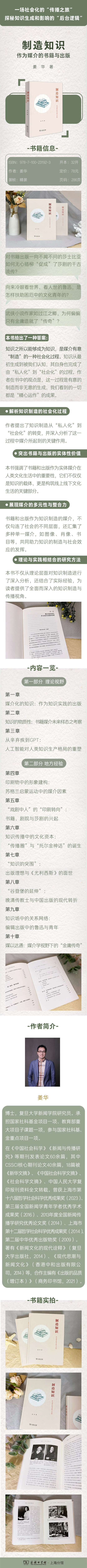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7.00
折扣购买: 制造知识:作为媒介的书籍与出版(精)
ISBN: 9787100231923

姜华,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CSSCI核心期刊论文40余篇,18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曾获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23)、第三届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奖(2016)、2013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优秀论文奖(2014)、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09)。著有《新闻文化的现代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现代思潮与新闻文化》(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4)等,合作主编有《出版的品质(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1)。
知识是人类在对置身于其中的周遭世界认知的过程中沉淀而成的经验,它往往以观念总和的形式呈现出来。凭借知识,人类可以在世界之中生存、协作,创造出更多属于人类才可达成的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生成、演化的历史,也是持续制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借由知识的生成与制造,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并正常运行。 在探究人类知识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作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创造者的写作者,其实这种知识仅仅是一种“私人化知识”。所谓“私人化知识”,乃是社会个体通过对周遭世界的观察、感知而形成的知识,个体将其写作出来存在于世,但并未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对于人类社会演进而言,更有意义的其实是“社会化知识”。所谓“社会化知识”,乃是指以“私人化知识”为基础,经由一系列社会化过程,最终进入社会领域并获得广泛传播,进而对他人智识、社会运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私人化知识”是“藏之名山”的存在物,公众是不知晓的,也无缘一睹风采。这些“私人化知识”由于存于“名山一隅”,未能触达公众,对于公众和社会而言,它犹如虚无缥缈的东西,于个体精神生活和社会的走向没有任何影响,其价值到底几何,也是无从判断的。 在过往的知识史、文化史研究中,我们更加看重“私人化知识”,也就是与某个写作者直接相关的知识文本,而对于这些“私人化知识”如何从个体的写作者手中,一步步走向社会的过程,是不太关注的。与此相关,我们在研究中,也就将更多的力量投注到古往今来的“文化英雄”——写作者身上。这当然没有错,因为“私人化知识”是“社会化知识”的前提和基础,若没有“私人化知识”的奠基作用,就没有“社会化知识”的形成和累积。不过,进一步深究会发现,若仅仅关注“文化英雄”,对“社会化知识”的理解则一知半解,就会有失偏颇——因为,“私人化知识”并不能涵括“社会化知识”的全貌。举个简单的事例,在古希腊,像柏拉图这样的“文化英雄”虽不能说如繁星点点,但肯定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古希腊时代,有众多的“柏拉图”创造了可观的“私人化”的知识文本,但传之后世的只有柏拉图这样的幸运儿,原因何在?撇去其他原因不说,柏拉图比其他写作者有识见、有能力的地方在于,他能够顺利地将其“私人化知识”转化为“社会化知识”。据有关研究,柏拉图曾经花钱购买其他作者的作品,然后七拼八凑成“新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卖给出版商。经由这个“从私人到社会”的过程,其他真正的作者消失了,善于“转化”的柏拉图留在了历史长河中。还有更多的写作者,可能作品并没有被如柏拉图这般的“作者”购买,但穷于将“私人化知识”转变为“社会化知识”,也消失在了历史星汉之中。 与之相似的,还有卡夫卡。有研究者就指出:“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堪称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状态。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上发表,不是为了大众,也不是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换言之,卡夫卡“纯粹的个人写作”所提供的知识文本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私人化知识”。若没有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违背他的遗愿(将所有作品付之一炬)这样的意外发生,世间便不会有“卡夫卡”,也不会有精细描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作为“社会化知识”的“卡夫卡”流布于世。布洛德在“形塑卡夫卡”的过程中,“极力把卡夫卡塑造成一个虔诚的思想家。通过出版卡夫卡的遗作,写作卡夫卡传,布洛德对卡夫卡声望的确立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其实,熟悉文学史的人会知晓,使卡夫卡的个人书写变为社会化知识的, 不仅仅是布洛德,还有文学圈的其他知名人物,如阿道司·赫胥黎、阿尔贝·加缪、威斯坦·奥登,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崇卡夫卡。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卡夫卡作品各个语种的译者以及所有被遮蔽在幕后的出版商们——卡夫卡为世人所知,所震惊,所敬仰,首先是在捷克之外(捷克的阅读者很长时间对他视而不见,即使他在域外声名鹊起时亦如此)。 从更宏观的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将“私人化知识”转化为“社会化知识”,使知识涵盖的“社会范围”逐渐扩充,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社会过程。古代社会的知识,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但大都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中,知识生产、加工和传播的这种状况,介于完全的“私人化知识”和“社会化知识”之间,是一种“半社会性质的知识”——其生成、制作和传播始终局限于社会中很小的一部分群体之中。依照迈克尔·曼的说法,“人类是在无休止地、有目的地并且是有理性地为增进他们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而斗争,为此,他们有能力选择和追求适当手段。……他们是权力的来源”。“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权力是通过支配人们的环境以追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因此,追求“个体性权力,即社会的分层也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制度化特征”。安东尼·吉登斯也指出,手段或资源乃是“包含在支配结构中的权力的‘基础’和‘途径’”。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对知识生产和传播权力的掌控,就成为个体或者集团拥有和运用权力、维系社会分层并保持权威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正因为如此,古典世界的书籍生产主要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在古埃及如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依然如此。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看,书籍加工使用的材料非常昂贵,远非一般民众所能负担。“纸莎草纸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价格高昂,比现在最优质的纸张也要贵得多。公元3世纪的菲尔穆斯皇帝曾说,可以用纸莎草纸的收入供养整个军队。” 为了竞争,托勒密禁止纸莎草纸出口帕加马,导致帕加马最终发明和使用了羊皮纸。无论是纸莎草纸,还是羊皮纸,均价格不菲,这就使得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与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层合二为一。这在图书的流通传播环节也可见一斑。纸草书不易保存,需要干燥的环境,而且不抗虫害。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曾经感慨地说:“飞蛾不识字,何以食我书。”这对书籍文献的保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当时最为知名的两大图书馆(同时也是书籍的编辑出版机构和研究机构)——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帕加马图书馆,都是由托勒密王朝和帕加马王朝举全国之力而筹建的;虽然也存在一家“民间图书馆”——私人设立的吕库吕斯图书馆,宣称对全社会开放,但事实上,能够进入并使用这家图书馆的也是上层社会的文化精英。 基督教兴起后,教会系统成为与世俗政权并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世俗政权,在欧洲历史上绵延一千五百余年、垄断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强大力量。“在许多时间和地点,意识形态延及的社会空间比国家、军队或经济生产方式的覆盖面更广。”在迈克尔·曼看来,宗教,正是一种非凡的意识形态权力。在欧洲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它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知识传播网络。它不是国家,却形似国家,跨越了疆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最终形塑了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播结构。基督教对知识传播的控制是通过教会的修道院书写系统建立的。“在六七世纪,意大利是修道图书馆建造的主要舞台。”“在一个几乎由口头文化独霸的世界中,修道院成为书面文化和古代传统的庇护所。”之所以说修道院书写系统是一个全新的知识网络,原因在于它改变了知识的内容,垄断了知识的生产:“识文断字的能力,不管是对于一个以圣经为经典的宗教来说,还是对作为罗马帝国灭亡后诸王国管理者的教会来说,都是必须的,所以它现在几乎成了教会的专利。”在这个垄断性的知识生产体系的运作下,古希腊和古罗马早期的很多文献,虽然有些得到保存,但古典世界的知识,在这个全新的、封闭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不是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就是被束之高阁。旧经典的消失,显然与阅读市场的变化密不可分,上流社会的精英读者逐渐演变为基督教文献的读者,也很少再阅读古典文献。 罗马帝国建立后,基督教很快成为国教,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因此进入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中。古希腊的诸多世俗知识或被掩盖在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的宗教文化之中,或在罗马帝国的文化版图中消失不见。在这漫长的千年中世纪里,很多在西罗马帝国销声匿迹的古希腊经典文献被阿拉伯人翻译为阿拉伯文,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大量精通古希腊文的知识阶层被迫离开了东罗马帝国。这些西迁的知识群体将留存于阿拉伯文世界的大量古希腊文献重新翻译成希腊文出版,并使之在欧洲大陆广泛流传——文艺复兴的时代由此来临,诸多久已消失在人们精神世界之中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几乎失传的古希腊智者的作品,遂得以重见天日。在此过程中,如何将这些被束之高阁的“私人化知识”转化为“社会化知识”,绝非原著者和翻译者的一方之功(当然,这个过程中,翻译者居功至伟,是他们重新发现了尘封的古希腊文明和被弃之不顾的众多优异的知识文本),乃是诸多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出版商作为“私人化知识”走向社会的“媒介”,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文艺复兴的兴起,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在时间上有很大的重叠性,这并非偶然,三者之间实在是存在异常紧密的相关性; 在三者之间,促使知识社会化的出版媒介的重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柏拉图、卡夫卡的事例以及古希腊文明的再发现和文艺复兴的开启表明,社会化知识不仅仅是个体书写的私人化知识这么简单的事,它们的形成,经历了从“私人”到“社会”的复杂过程;社会化知识不是“创作”出来,而是“制造”出来的。本书的目标,即力图从两个层面揭示“制造知识”的过程:其一, 社会化知识制造时人类要素之外的非人类要素的作用;其二, 社会化知识形成过程之中写作者之外的力量。 人们考察人类知识史的时候,过多地将注意力投注在了人类自身,仿佛只有人类才是人类知识史得以形成的唯一因素。此种现象的出现,或许是人类对自身过于自信,也或许是思想史对主体性力量的过分强调,掩盖了人类要素之外的非人类要素对人类知识积累的重要作用。诚如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所言,“现代性通常都是以人类主义(humanism)为基础进行界定的……这一惯例本身就是现代式的,因为它保持了一种不对称性。它忽视了‘非人类’——物,或者客体,或者兽类——的同时诞生”;“现代人自认为,他们成功地进行了这样一种扩展,仅仅是因为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自然和社会(以及那被搁置的上帝)分割开来,而事实上,他们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将更大量的人类和非人类混在起来,他们并没有搁置任何东西,也没有排除任何结合”。依照拉图尔的思路,重新考察人类知识史,我们也会发现,人类知识形成或者说人类制造知识的过程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非人类要素。中国的笔墨纸砚,埃及的纸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都是制造知识中必不可少的非人类要素。进而观之,城市这种人类居住的场所,也可作为影响知识制造的重要非人类要素。至少在欧洲,制造知识的中心,往往都是威尼斯、巴黎、里昂、法兰克福;或者依河傍海,或者身为交通枢纽,或为纸张加工提供便利,或为知识产品扩散减少开支,都是制造知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非人类要素。其实,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中国书籍史家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中就提出,人类思维能力与文字载体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他虽然未曾明确地提出人类要素与非人类要素这样的对等学术概念,但“人类思维的能力”与“文字载体的方式”,在学理上与上是相通的。 一场社会化的“传播之旅”——探秘知识生成和影响的“后台逻辑” 。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中,大卫·休谟如何“媒介化”自己,在文坛暴得大名,并引来英国一代文宗约翰逊的讥讽?对书籍出版一向不闻不问的莎士比亚又如何无心插柳“促成”了莎剧的千古流传?曾经作为家庭晚间口述故事的《霍比特人》,又是怎样走向英国民众,并最终成就了“托尔金神话”的?当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四处碰壁的时候,又是谁雪中送炭,成就了文学经典?向来冷眼看世界、看人世的鲁迅,是怎样扶助困厄中的文化青年的?武侠小说作家如过江之鲫,为何偏偏只有金庸造就了“传奇”?本书给出了一种答案: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是媒介有意“制造”的一种社会化过程。知识从最初生成到被我们认知,其自身也完成了由“私人化”到“社会化”的过程。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这一过程是有意的制造而非无意的生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精心运作”的成果。 本书聚焦于“制造出”知识的媒介: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和推动知识传播的出版。相较于信息网络的虚拟性,书籍和出版如今似乎处于没落的“危机”中,但其实体性的特质又是构筑人类线下线下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索知识如何被“制造”,会让我们更加了解书籍和出版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