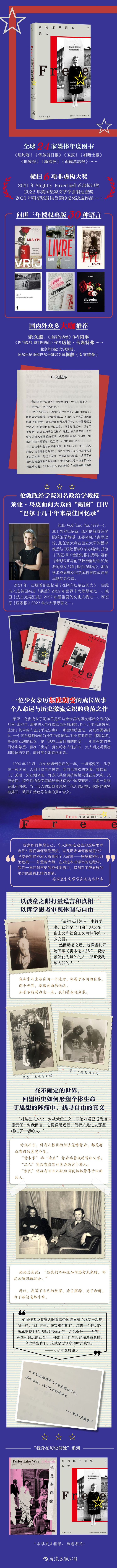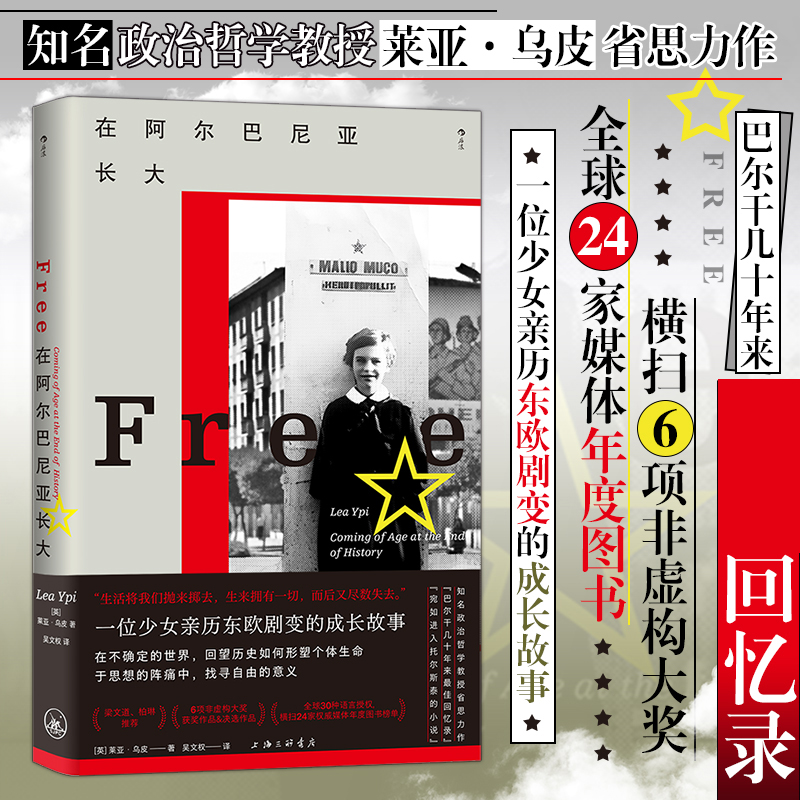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20
折扣购买: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
ISBN: 978754268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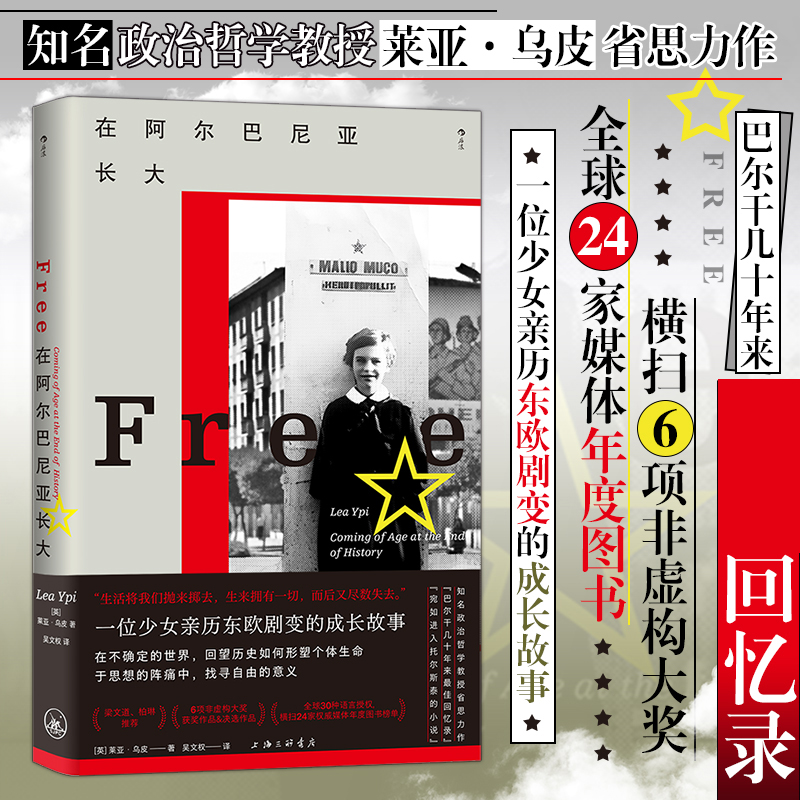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莱亚·乌皮(Lea Ypi,1979— ),生于阿尔巴尼亚,拥有罗马拉萨皮恩扎大学哲学和文学学位、欧洲大学研究所博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博士后奖研究员。现为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理论,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哲学教授。 著有《全球公正与前卫政治能动性》《党派的意义》和《理性的建构》。她的学术成果曾获得英国科学院政治学卓越奖和利华休姆杰出研究成就奖。她也是《政治哲学》杂志的编辑,并为《卫报》和《金融时报》撰稿。 2021年,她面向大众的回忆录《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一经出版即成破圈经典。她也因此书入选英国杂志《展望》2022年年度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22年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西班牙《国家报》2023年六大年度思想家之一。 译者简介 吴文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译有《呼吸秋千》(第二译者)、《文学的读法》《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幽默》《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第一译者)、《唯物主义》《我桌旁的天使:珍妮特·弗雷姆自传三部曲》等。
第 12 章 雅典来信 大约是1991年1月,首次自由公平选举之前,奶奶收到一封来自雅典的信,署名者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是个叫卡塔琳娜·斯塔马蒂斯的女人。打开之前,我们把信拿给邻居们看。帕帕家聚了一小群人。多尼卡一辈子都在邮局工作,信顺理成章地交到了她手上。她站在客厅中央,周围是一张张好奇的面孔,眼睛盯着那薄薄的奶油色信封,上面是几行墨水书写的希腊文,宛如预言未来的象形文字。 我知道多尼卡不懂希腊文。就在几周前,她还请奶奶帮忙翻译了一瓶黄色液体标签上的配料表。这瓶东西是一位表亲最近从雅典旅游回来带给她的礼物。她还以为是外国的柠檬香波,洗头后才发觉有点刺痛,很不对劲,然后头皮瘙痒起来。经奶奶一翻译,方才真相大白,原来那是国外才用的玩意儿,叫什么洗碗机清洁液,以前真没听说过。 有那么几分钟,多尼卡一言不发,仔仔细细、翻来覆去地端详着信封,那严肃的样子令整间屋子都笼罩在静默的期待中,能听到的只有炉火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她把信封拿到鼻子下,不同的位置都嗅了嗅,每嗅一次,便用力呼一口气。她摇摇头,咂咂舌头表示不屑,然后将食指探入封盖下,拇指摁住外侧,接着,两指沿着信封边缘向前滑动,动作缓慢而凝重。她聚精会神地紧锁着眉头,仿佛这让她感觉到疼痛,而她却不得不忍耐。检查结束后,她抬起头,脸上写满了沮丧,开口说话时,沮丧又渐渐变为愤怒: “信拆开过,”她一边宣布,一边将目光投向门口, “那些人拆开过。” 安静的房间里突然充满了众人的低语声。 最终妈妈爆发了:“浑蛋。” “还不止拆了一次呢,有好几次。”多尼卡说。 “是啊,这不明摆着嘛,”她丈夫米哈尔抢白道,“邮局好像也没有雇新人吧?老人儿可不就是老一套做法。” 几个邻居点点头,其他人却不以为然。多尼卡反驳道:“应该规定邮局员工不能再拆信。”我妈跟着说:“那是隐私啊,隐私多重要啊。以前哪里有什么隐私。”她觉得,除非邮局私有化,否则还是老样子。只有私有化才能让人尊重隐私。 大家都觉得隐私很重要。“岂止重要, 那是你的权利,是一种权利。”多尼卡阐述道,嗓音中透出多年拆信积累起来的智慧与权威。 随后,在众人的请求下,奶奶大声朗读了信中的内容,并逐字逐句地翻译。寄信人卡塔琳娜·斯塔马蒂斯自称是我曾祖父的生意伙伴尼科斯的女儿。信里写道,50年代中期,奶奶的父亲去世时,尼科斯就陪伴在侧。那女人想知道,奶奶有无兴趣诉诸法律手段,收回她家在希腊的产业和土地,并提出可以帮着办理此事。奶奶说那女人的姓氏听上去有些熟,应该不是个骗子。 尼尼最后一次见到她父亲还是在她的婚礼上,1941年6月,在地拉那。照她的说法,战争结束后,“道路都被关闭”,她虽然记得自己收到了从雅典拍来的通知父亲死讯的电报,但她没有将护照申请下来,无法参加葬礼,也不清楚他过世时的情况。她回忆起大约四十年前收到父亲死讯的情景。当时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给一个男孩上法语课,他爸是高级官员。收到死讯的那天,他们正在复习属格,她让那孩子用“你的”造句,孩子说:“你的眼睛红了。”小男孩后来也成为高级干部,就是那个教育小组里的穆罕默德同志。没有他的许可,当年我就没法提早上学。 信中,卡塔琳娜动情地写到父亲尼科斯对奶奶的父亲的忠诚。她回忆说,在尼科斯弥留之际,她答应只要阿尔巴尼亚的局势有所缓和,就会联系我奶奶。接着她用稍微冷静一些的语气说,这件事会给双方家庭带来巨大的利益。她已准备好在雅典接待奶奶,陪奶奶去查询相关档案,协助联系律师,律师会帮着调查的。 奶奶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就仿佛一辈子都在排练这个角色,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有一天人家希望她扮演的角色。不过,她考虑的是另一项财务问题。自从获得批准,在我长大的那条街上建了一栋私房,爸妈就深陷债务之中,欠了很多人的钱:我舅舅的、妈妈同事的,还有几个外地远亲的。那天,奶奶、爸妈和邻居们坐下来讨论奶奶有无可能拿到签证,还左算右算,看家里还欠多少钱、每个月底爸妈能剩下多少、奶奶的养老金能到哪个数、够不够远赴希腊的开销。他们尽量将每一项明细都列出来,很快就发现,家里的余钱仅够在雅典待一天, 更别说签证费和两周的旅行花销了。 奶奶给我看过一本旧护照,是国王统治时期签发的,纸壳上订着一张她的黑白照片,下方是几行字,注明了她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出生地与日期,以及身上的胎记情况。护照存放在抽屉里,与埃菲尔铁塔明信片、 爷爷获释后给恩维尔·霍查的信在一处。 照片 里,奶奶表情严肃,如果不是那副十七岁的青涩面容,会给人自命不凡的印象。她的头发剪得极短,似乎是刻意想让人觉得,这什么发型都不是。她嘴唇紧抿着,似乎在尽力绷住笑。整个人的姿态都是在努力让观者相信,性别一栏的那个“女”字如果不是经办人填错了,便只是偶然。 奶奶过去常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这叫护照。”她解释说,护照决定路是畅通的还是关闭的。有护照的话,就能远行;没有的话,就只能困在原地。只有少数阿尔巴尼亚人可以申请,通常是为了去国外工作,而决定什么算工作的是当局,所以我们只有等。她曾说:“护照里可以添加一张儿童照片,要是哪天我拿到旅行护照,就把你带上。” 1990年12月,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盼望的不是上面批准护照,而是盼着护照可以挨到他们下台,就像当年挨到国王流亡那样。然而,收到雅典来的信时,听着大人们在多尼卡家客厅里耐心计算,看家里的钱够不够我和奶奶出行,一种从未有过的困惑攫住了我。我才发现,光有护照是绝对不够的,护照只是最为迫切的第一关,后面还有一连串障碍,它们变得越来越抽象,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真要打开通往外界的路,签证必不可少,然而事实上,获得签证不是旧党能保证的,它已奄奄一息,新组建的那些党派也没法打包票。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便我们顺利拿到护照和签证,旅行的钱也没着落。那这趟国该怎么出呢?家人花了出奇久的时间才得出结论:我们去不了。 几天过去了,雅典来的信被仔细折好,塞回了信封里,置于客厅的矮桌上,旁边是一个花瓶和一包用来招待客人的香烟。谁也没有勇气把它收进抽屉,因为抽屉里收藏的是我们的过去;我们还不愿将雅典来信视为过去,它属于当下,甚至属于未来,即便那未来依旧遥远。妈妈仔细看顾那封信,仿佛它是新近驯服的野兽,仍然会咬人。她细致地擦拭桌上的灰尘,确保花瓶里的水不会滴在信上。我们还称那封信为“卡蒂”,那是寄信者的昵称。除了妈妈,其他人都不愿靠近它。我们会蹑手蹑脚地绕过去,偶尔偷瞄一眼,但多数时候,都装作它 不存在。有一两次,它引发了家人的争论:该如何回复,才不会一下子断绝未来出行的可能;它会让我们指责对方以前本可以更好地管理家里的财务状况,或是幻想会不会还有一些我们没欠债的人能借些给我们。 就在我们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我外婆诺娜·弗齐伸出了援手。她来给弟弟庆生,注意到放在桌子上的“卡蒂”,就问雅典之行准备得如何了。尼尼只是叹气。 “我们去雅典, 比加加林上太空还难呢。” 爸爸打趣道。 “斯塔马蒂斯同志答应出机票钱,”我慌忙打断他说,“签证费也筹到了,可大老远跑去希腊,身上没有备用的钱可不行,万一出什么状况呢?” “是斯塔马蒂斯太太,”妈妈纠正道,“不是斯塔马蒂斯同志。她才不是你同志呢。不过其他说得没错。”说完转向她母亲。 诺娜·弗齐急匆匆出屋去了,咖啡没喝完,生日蛋糕也没怎么吃。她半小时后回来时,右手紧紧攥着什么东西,大老远就挥动着,像共产党员行礼一般。等到了放“卡蒂”的桌边,她伸开手掌,眼中流露出傲色,将五枚拿破仑金币撒落在信封上。它们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与列克掉落地板时发出的闷响不同,那声音是如此陌生,离我们是如此遥远,就如铸造金币的那个国度。没人知道诺娜·弗齐还有黄金。妈妈有时会想,家里的财产被没收前,她父母是不是私藏了些黄金。她觉得不可能,因为即便是饿到绝望时,大家说起藏匿的黄金也完全是以假设的口吻,就好像说说黄金就能填饱肚皮。诺娜·弗齐这会儿说,财产被没收时她设法留下了一些,妥善保存了起来,就等着道路开放的那天。“瞧瞧,”她跟尼尼说,脸上明显带着因自己的远见而颇为得意的神情,“现在可以出发了。愿神灵保佑你的黄金成倍增长!” 爸爸拿着金币去银行换钞票,很快就攥着张一百美元的纸币回来了。大家纷纷建言,这张钞票该藏在哪里,才不会被偷或轻易花掉。一度十五个邻居挤在我家客厅里,拿出各个时期、各种尺寸的钱包供我们挑选,但仔细查验后,我们觉得没有一个是安全的,因为“谁都知道西方满大街都是扒手”。接着大家又否定了几项建议,包括藏在箱底、夹在书中、塞进护身符里,最终一致决定,将钞票缝进奶奶衬裙的下摆,除了睡觉,平时不脱,而且绝对不能洗。 出发那天,整条街的人都来送行,每户邻居都拿出了一些东西,指望着旅途中或许能派上用场:用报纸包好的馅饼、带来好运的大蒜球、失联已久的亲属名单(但没有地址)——万一斯塔马蒂斯家没人来接,便可以去找他们。坐在轿车里,奶奶不停整理裙子,确认百元 美钞还原处。这么做的时候,她神色庄重,带着一丝挤出来的微笑,仿佛是在说:“我懂我懂,一位女士不该边进机场边摆弄裙子。”在出发大厅候机时,有一瞬间,最担心的事差点就发生了。“我觉得那东西不在了。”奶奶惊恐地说。两人忙不迭地冲进卫生间,她没法弯腰看下摆上的小孔。我只好仰卧在地上,瞧那张纸币是不是还在。还好,只是有些皱了,它仿佛在表达不满,好好的为何要离开外汇商店,沦落到被藏在奶奶的裙子里。候机厅里空空荡荡的,有几个外国人在等航班,还有几个在入口处的小店里购物。那家店很像外汇商店, 不同的是,人们可以直接从货架上选商品。奶奶说店员笑起来像个暗探。“暗探怎么笑 啊?” 我问她。“就这样啊。”她嘴角向两边撇了撇,没有露出牙齿。“也没什么特别的呀,都是这样笑的嘛。”我说。“没错,”奶奶回答道,“问题就出在这儿。”大厅各处站着些穿蓝色制服的警察。一位工作人员查看了护照上贴的条子,随即便盖了章。我知道那小条子是签证。我们放下行李接受检查的时候,其他人则在一旁等着。“浑蛋。”我小声咕哝道,想起妈妈发现雅典来信给人拆开过,当即就骂了这句话。奶奶看上去不知所措。检查结束后我说:“这个国家就没人在乎别人的隐私,不是吗?我猜啊,机场这儿肯定没雇新人。” 在飞机上,我人生中头一回见到了彩色塑料袋。空姐问我们是不是第一次坐飞机,然后便递过来一个彩色塑料袋,告诉我想吐的时候该怎么用。旅程结束前,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忍不住要吐了,看到最终也没吐,心里还有些惴惴不安。午餐上来了,用的是塑料餐具,不过我们吃了自己带的馅饼,午餐没有动,一来怕晚些时候肚子饿,二来塑料刀叉和盘子挺稀罕,打算带回家,特殊场合再拿出来用。“真是好看啊,”奶奶赞叹道,“战争前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不记得有这种材料。” 到了雅典,奶奶鼓励我开始写日记。我列出头一次看到的新鲜事物,细致记录自己的感受:手心第一次感受到空调风,第一次品尝香蕉,第一次看到红绿灯,第一次穿上牛仔裤,第一次不必排队就能进商店,第一次遇到边境检查,第一次目睹车辆排长龙而不是人排长队, 第一次坐上马桶而不是蹲着解决,第一次看到人牵着绳遛狗而不是流浪狗尾随着人,第一次拿到口香糖而不只是糖纸,第一次看到大厦内外商铺云集、商店橱窗塞满玩具,第一次看到坟茔上竖立的十字架,第一次凝视贴满广告而非反帝国主义口号的墙壁,第一次观赏雅典卫 城却因买不起门票只能在外面欣赏。我花了很多笔墨描写我这个小游客与其他小游客的第一次邂逅。我惊讶地发现,看到雅典娜和尤利西斯的名字时他们毫无反应,而他们也会笑我,米老鼠那么有名,可我看见就像没看见,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 我们落脚在卡塔琳娜夫妇家。他们住在埃卡利的一套顶楼公寓,位于雅典北郊的富人区。透过将独栋别墅与外界隔开的大门望进去,只见带泳池的大花园里,草坪修剪得十分整齐。斯塔马蒂斯夫妇家没有泳池,却有更古怪的东西:五台大小不一的冰箱,分别放在几间房 内,无一是南斯拉夫的奥博丁牌。其中两台只放酒,一台放包括可乐在内的软饮料。装可乐的不止我熟悉的罐子,还有塑料瓶。我养成了半夜醒来开冰箱喝可乐的习惯,不仅因为对那味道很上瘾,更因为一直拿不准罐装与瓶装可乐口感是否一样。如果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搞 两种包装?主人请我们不要客气,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自己拿,但奶奶绝不允许我这么做,说绝不能要人家请吃请喝。如果注意到我想多要根香蕉、多要杯饮料,她会在桌下拧我的大腿;如果离得比较远,她会绷着牙挤出几句阿尔巴尼亚话,脸上却装出笑容,好让别人看不出她在警告我。真像个暗探,我心里说。她自己吃得很少,每到吃饭时,卡塔琳娜的丈夫约戈斯便会大声说:“给霍查统治了四十五年,您的胃都缩成橄榄那么大了!”约戈斯那样的大块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经营着一家生产丝瓜海绵的工厂,体形也颇具丝瓜海绵的风范。 我们去了趟萨洛尼卡,找到了奶奶以前上过的法文学校。那栋建筑如今成了写字楼。我觉得它像一家银行,跟在西方电影中看到的很像。班上那些最吃香的男孩,谁叫什么,尼尼都记起来了。课间她还曾同他们一起抽过雪茄。她还记起了以前的老师,特别是某个伯纳德先生。他曾预言,只要不笑太多、一直保持短发发型,她一定会前程似锦。此话她谨记在心,严格遵行,可到头来却证明,那预言有些不靠谱。 我们造访了她父亲的坟墓。她心里一定很痛,却能尽力克制,保持尊严。也只有她能做到。从头至尾她都一言不发,只在离开时躬身轻吻了墓碑上的照片,同时催我照做。我挺不情愿的,毕竟我没见过他,他也没见过我。不过我还是依了她,不想让她失望。她执意要找到老保姆达芙妮的墓。她最后一次见到老人,还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她僵立在白色十字架旁的时候,眯缝起眼睛,死死攥着手包,脸色苍白,形销骨立,似乎这中间的岁月已经让她的肉身枯萎,唯余一根根骨头。几滴泪水滚落在大理石墓碑上,很快就会被冬日的阳光晒干。她察觉到了,转向我,忧郁地勉强一笑,说:“看到了吗?达芙妮以前总是帮我拭泪,如今也还是啊。” 我们在城里的土耳其人区找到了她家的祖屋,是一栋带花园的白色大房子,花园里各种果树正芳华初绽。尼尼两岁时,这栋房子曾失过火,这是她最早的记忆。她记得自己给人抱着冲到屋外,身上裹着的毯子灼烫着皮肤。她说,现在似乎都还能听到尖叫声,记得当时看 见妈妈头发上燃着火苗。房子正面,过火的痕迹依稀可辨。奶奶说如果可能,想带我看看屋内的样子。走近前门时,露台上出现一个女人,问我们有什么事。奶奶说了此番前来的目的,请求进屋看看。那女人回答说,她倒是愿意相信我们,不过她只是来打扫的,让外人进屋她可负不了责。奶奶表示了理解。“邻居们还互相帮着打扫屋子吗?”我很是纳闷。“她是花钱请来的。”尼尼解惑道,然后再次转身面对清洁工,熟络大方地用希腊语喊道“谢谢你”,就好像两人以前见过面。 奶奶早就知道收回产业断无可能了。她同意来一趟,有尽义务的考虑,不想让抱有希望的人失望,同时也想重温过去,让我对它有所了解。对遇到的人她诚挚而友好,只是也许他们觉得她是冲钱来的,尽管其实对钱她没那么上心。她找了不同的律师,都说想收回她家过去的公寓和田产,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他们说奥斯曼帝国崩溃后,人口开始流动,还着重指出,财产法改了,要拿到所需的文件绝非易事,而且两国理论上仍处于交战状态,从40年代起未变,再加上希腊军人独裁政权流毒未尽,等等。奶奶点点头。斯塔马蒂斯夫妇开车送我们去了大大小小的办公室,赴了各种约。他们总是在旁边仔细听着,同时做着笔记,有时会插上一两句我听不懂的话,有时会做出激烈的动作,挥舞胳膊,摆动手指,无奈地摇头。 最后一天商谈时,约戈斯怒不可遏,用希腊语冲房间那头的一个律师咆哮,同时手指指向我,仿佛想借此表明论点,他声音越提越高。接着他跨步过来,扯起我的胳膊挥动起来,就好像那是他自己的,与此同时吼声不断。我的目光投向奶奶,她一直在点头,听着律师的解释,听着约戈斯的喊叫。我想,不抽回胳膊或许明智些。 “他们争论的是一份叫‘遗嘱’的文件,”那晚奶奶跟我说,“人们在里面写下自己去世后财产留给谁。” “我们有吗?”我问道。 “遗嘱吗?”奶奶笑道,“比它更要紧的信件,警察抄家时我都没能保留下来。” 远离希腊的五十年里,奶奶只跟科考特争论政治话题时说过希腊语,因为不希望我听懂。斯塔马蒂斯夫妇有时跟我说法语,磕磕巴巴的,比我差远了;有时又同我讲英语,也是磕磕巴巴的,倒是比我强很多。他们发现,奶奶的希腊语一点没忘,不过带有旧时上流社会的味道,听上去挺好玩,而且语调低缓,不似我见到的普通巴尔干人讲话那般粗声大气。同人交流时,她不断使用另一种语言,将我严挡在外。就好像我与两个人同行:一位是我最信任、最崇拜的尼尼,另一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神秘女人。 奶奶始终坚持说自己没变。出发去雅典前,我还是相信她的。她的话总能让人心安,有她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特别是 1990 年冬天,身边的一切都波动不定,爸妈也一样,上一刻还紧张焦虑,下一刻便热情洋溢,中间几无过渡。奶奶就不同,她总是镇定自若,波澜不惊,至艰的苦境都能适应,天大的困难都能克服,而且应对自如,让人觉得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障碍才最可怕,唯一需要的是获胜的意志。她令我相信,我们的现在总是过去的延续;在每一组看似随机的情形中,我们都会发现理性的人与动机。她的表情、姿态与言谈方式,无不传达着这种印象。 可在雅典之旅期间,我感觉到了变化。我们凝视着泛旧的照片,上面是早已过世的人、奶奶所爱之人,我却毫无感觉。他们应该都是我的先人和亲戚,对我却几乎没有意义。有一天,卡塔琳娜给奶奶拿了一把曾祖父留下的旧烟斗,我随手拿起来玩,奶奶却突然发火,劈手夺了过去,从没见过她那么粗暴。她吼道:“这不是玩具!只顾自己玩吗?!”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对这么一个物件如此敬重有加,为什么将它拿回手中对她如此重要。“好吧好吧,”我说,“不就一把烟斗吗?你都不抽烟了。” 奶奶以前总说,我和弟弟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我们对她的生命却知之甚少。当她真情流露,不论是站在达芙妮墓前、思念学校同学,还是与斯塔马蒂斯夫妇回忆她父亲时,她的话便没那么可信了。我感觉到了疏离与冷漠。我意识到,正是让我出生的这一系列事件 迫使她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多年来遭受艰辛、孤寂、丧痛与悲戚的诅咒。倘若当初她没有离开萨洛尼卡,就不会遇到爷爷,没有遇到爷爷,就不会生下爸爸,没有爸爸,就不会有我。这桩桩件件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她一向都是这么说的。我如果能像她跟我解释别的事情时那样,理解其中的因果关联,就会认同有决定就有后果。在别人眼中的断裂处,我就能察觉到某种性自由选择的产物,而非必然性的产物。 当我们在希腊时,难以相信她一直以来都在为自己的所有决定承担后果,她居然找到了与返回阿尔巴尼亚后遭遇的一切达成和解的办法。我们无法理解,战争结束时,移居希腊的机会就摆在面前,她是如何做到选择留下的。或许她无从得知即将降临的一切。可她一定感受到了什么,就算她不恨,不想报复,至少也有深刻的怨怒。在被迫抹除了自己的过去后,她还能体会到新的爱吗?她总说为我骄傲,爱我,在那个异邦,那个我至为陌生而她却至为熟识的异邦,我无法将自己同骄傲和爱联系起来,我只与她丧失的一切的痛苦有关。我想离 开。我想回家。我渴望家带来的安全感。 “我身在历史何处”系列002 知名政治哲学教授莱亚·乌皮省思力作 一位少女亲历东欧剧变的成长故事 在不确定的世界,回望历史如何形塑个体生命 于思想的阵痛中,找寻自由的意义 —————————————————————————————— ?权威大奖×大咖推荐×重要媒体×读者口碑,掀起全球热议的纪实文学力作。 6项非虚构大奖得奖&决选|全球30种语言翻译授权;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塔拉·韦斯特弗、梁文道、《边界的诱惑》作者柏琳推荐;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研究专家柯静专文推荐; 横扫《纽约客》《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全球24家媒体年度图书榜单; Goodreads过万人打出4+高分|原版豆瓣读者评论9.6高分,好评如潮。 ?个人命运与历史激流交织的典范之作,“巴尔干几十年来最佳回忆录”。 享誉国际的政治哲学家莱亚·乌皮面向大众之作,一经出版即成破圈典范。有人说,她简直是被哲学家身份耽误的好莱坞编剧潜力股!她新颖的讲述,令家国历史栩栩如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视角。阿尔巴尼亚,那个我们可能知之甚少,又与我们有诸多相似的国家,从此不再遥远。 ?以小说大师之笔,勾勒一段亲历东欧剧变的非凡成长往事。 寓言般的小故事,再现生动场景和对话,串联起童年与少女时代的困惑与领悟。读者化身为孩童,一起在谎言与真相中打转,沉浸式经历种种黑色幽默,感受荒诞与悲怆。读来宛如《乔乔的异想世界》遇上《我在伊朗长大》,也堪比“阿尔巴尼亚版《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在巧妙铺陈中,她的故事,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跟随哲学家,穿过时代的迷雾与废墟,身临一场生命与观念洗礼。 曾经天真的女孩、如今的学者,带我们重访洪流中裹挟的具体面孔,体悟种种观念的幽微内涵,看历史的翻云覆雨手如何形塑个体生命。生长自切身经验的智性思考,跨越时空仍掷地有声,给人启迪。 ?一部犀利而正当时的警醒之作:在历史远未终结的今天,我们要如何有意义地生活?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未来,那就必须回顾过去。”回首人生,关照当下和未来,莱亚在对自由意义的叩问中,也发出沉落年代的希望之声:“如果我无所作为,他们(先辈)的努力将会白费,他们的一生将会显得毫无意义。” 获奖记录 2024年里登奥尔图书奖(Ridenhour Book Prize) 2022年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翁达杰奖获奖作品 2021年Slightly Foxed最佳传记获奖作品 2022年戈登·伯恩奖决选作品 2021年科斯塔年度最佳传记决选作品 2021年贝利·吉福德奖决选作品 《纽约客》《华尔街日报》《卫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全球24家媒体年度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