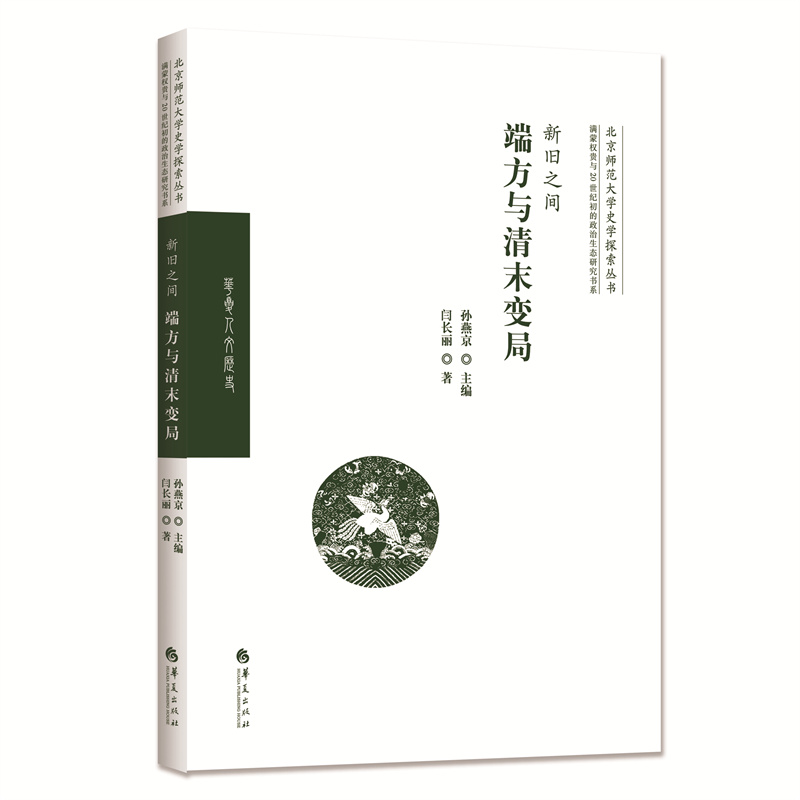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新旧之间:端方与清末变局
ISBN: 9787522202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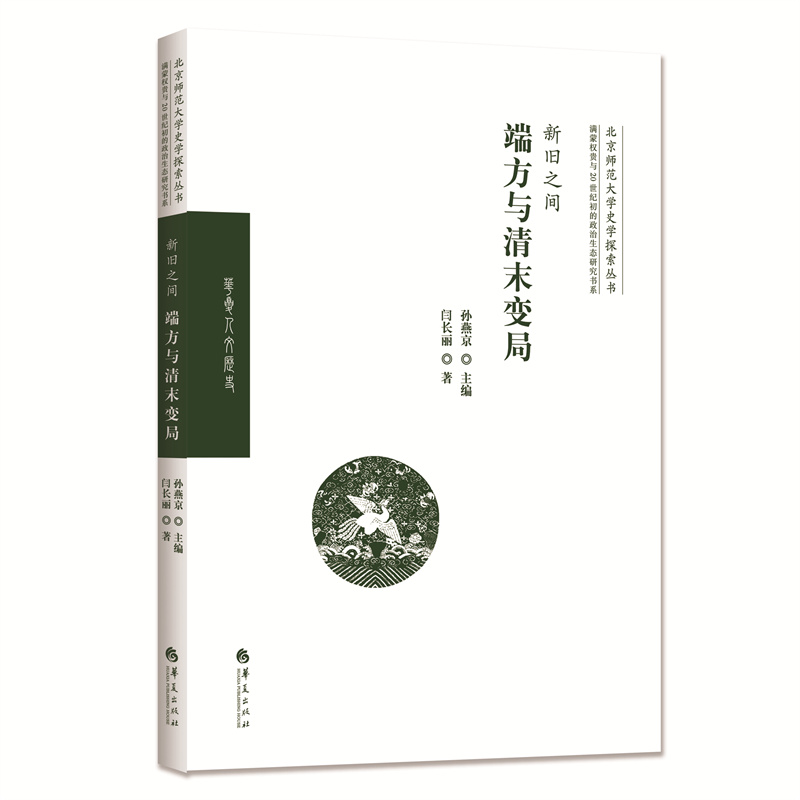
闫长丽,1983 年生,山东菏泽人。2004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得 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2010 年就读于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 博士学位。2010 年至今,就职于北京交通大 学,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共党史研 究,先后主持北京市省级课题多项,入选北 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在《治理 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满族研究》 等刊物发表文章数篇。
善政变暴政:载沣、载泽与干路国有风潮 皇族内阁出台后,清廷已尽失人心,危如累卵之际又贸然推行干路国有政策,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湘、鄂、川、粤诸省保路风潮,清廷应对失当,致使绅民与之决裂。《清史稿》有谓:“辛亥革命,乱机久伏,特以铁路国有为发端耳。”[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二五八·瑞澂》卷471,第12814页。]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有关保路运动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早年研究者多以绅民为中心探讨从绅商抗争到人民起义的基本史实,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探究清廷推行干路国有与应对保路风潮的正当与失当之处,[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廷湘《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陈晓东:《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孙自俭:《晚清干路国有政策再认识——以政府决策为中心》,《兰州学刊》2010年第8期;苏全有:《论清末的干路国有政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马勇:《正当与失当:清末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再检讨》,《史林》2012年第3期;葛风涛:《清末保路风潮何以激化》,《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并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总体而言,研究者多认为清廷推行干路国有从政策上看并不错,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失误。 关于清廷推行干路国有和应对保路风潮仍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虽然清廷对干路国有和保路风潮的处理意见均以朝廷名义发出,但彼时清廷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诸王大臣并非“一致对民”,朝廷最终决策系不同政见、不同派别之间相互商议、争执与妥协的结果;有关清廷出台决策的来龙去脉、各种政见及其间重要人物对朝廷决策的影响、诸王大臣之间的分歧与妥协等等,均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研究。少壮亲贵中,载沣作为最高决策者,载泽作为干路国有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盛宣怀的政治后台,在保路风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本节拟对此做一番探讨。[据笔者管见所及,专门探讨载沣与保路风潮的论著仅有李学峰《载沣与清朝末年的铁路政策》(《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一文;关于载泽与保路风潮尚未见专门研究,可见拙文《“路事”与“乱事”:载泽与辛亥年干路国有风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一、少壮亲贵与盛宣怀的关系——以载泽、载洵为例 盛宣怀系引发保路风潮进而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他办理铁路国有事宜一意孤行,颇受时人指摘,但彼时他仅是邮传大臣,并不代表清廷的最高意志,因而有必要首先探讨宣统年间清廷重用、信任盛宣怀的原因。盛以办洋务起家,曾是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光绪朝末年袁世凯柄政后逐渐失势赋闲。进入宣统朝,盛的仕途迎来转机,宣统二年七月清廷谕令其回邮传部侍郎任上,数月后升任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出台后继续担任邮传大臣,一时炙手可热。 盛宣怀能在宣统朝重新崛起主要由于载泽的信任,载泽力主重用盛宣怀则主要看中其出众的理财能力。盛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办理路矿、电报、银行、航运等实业颇有成绩,不仅为清廷及南北洋创收颇丰,自己更是获利千万,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富豪。清代最后几年,各项改革全面提速,推行新官制,改革币制,清厘财政,振兴实业,整顿陆军,兴复海军……无不需要以丰厚的财力做保障,而清廷财政捉襟见肘;其时载泽主管度支部,对朝廷财政状况有较深刻清晰的体认,各部院无不向度支部伸手要钱,载泽囿于穷困的财力不得不推行撙节政策,尽量削减各衙门开支,避免糜费。这势必引起各部院的不满,也不利于清廷立宪的推进,尤其制约了载洵、载涛等人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载泽认识到,欲解决财政困境仅靠“节流”显然不够,充裕国库更需要“开源”,于是盛宣怀作为当时官商两界公认的理财好手正能投其所需。时人恽宝惠认为,“载泽亦看出这种情况,认为盛宣怀是筹款好手,遂彼此互相利用”。[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6页。] 载泽在光绪朝末年担任度支部尚书后即向朝廷建议起用盛宣怀。光绪三十三年,江浙绅商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一度使清廷极为棘手,载泽立即向慈禧太后面保盛宣怀办理此事,声称:“盛宣怀熟悉路事,令与英使直接磋商或可就吾范围,且铁路、电报、招商各事急应整顿,请加恩将盛宣怀起用,予以邮传部尚书之缺,必能日有起色。”[《泽公力保盛宫保》,《大公报》1908年1月6日,第3版。]载泽颇赏识盛宣怀办理实业的本事,在他看来,值此开支激增而国库奇绌之际,盛出众的理财能力无疑对朝廷有重要帮助。慈禧太后听取了载泽的建议,召盛宣怀进京参与办理浙省铁路事宜,事毕授之以邮传部右侍郎。不过,彼时正值庆袁一派炙手可热,他们显然不希望盛宣怀分割其邮政、交通、电报等方面的既得利益,两天后即以赴上海办理商约为由将盛排挤出京。[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0—881页。]盛宣怀在京的短暂时日内得以与载泽建立起频繁的直接联系。其时载泽正着手改革币制,拟仿照西方惯例铸造七钱二分银元,然而枢臣张之洞、袁世凯、鹿传霖皆主铸一两银元,唯有盛宣怀赞成载泽之见,二人遂得以密切往来。盛归沪后,二人常有书信联系,盛宣怀提出诸多币制改革建议,颇受载泽认可。[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4—95页。] 载沣摄政后,少壮亲贵掌握了国家大权,载泽更是“势要冠亲贵”,不少内外大员竞相攀附以求进用。盛宣怀向来以长袖善舞著称,加之遏制其权势的袁世凯已经被罢黜,他自然不会错过向上攀登的机会,用金钱运动亲贵对这位家缠万贯的富豪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宣统二年七月,清廷起用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这一调整即与载泽有关,据《凌霄一士随笔》载,“载泽长度支部时,在政府中独树一帜,以集中财权为务,犹载涛之集中军权也。盛宣怀希进用,厚结载泽,志在邮部。载泽以邮部为富有收入之机关,为扩张势力计,遂言于载沣,召用宣怀,授邮部侍郎”。[《争财神》,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633—634页。]由此可见,宣统朝少壮亲贵柄政后,载泽起用盛宣怀已不只是着眼于财政困境,还有引用私人、扩充己派权势的意图。 不仅如此,在载泽的建议之下,清廷任命盛宣怀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6册,第255页。]在币制改革中,载泽相当信任、支持盛宣怀,二人通力合作,币制事宜颇有成效。[详见易惠莉《盛宣怀与辛亥革命时期之政治(1909—1911)》,《近代中国》第12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82—151页。]数月之后度支部新官制即将实行,载泽甚至一度表示不再继续担任督办币制大臣,愿意让位给盛宣怀。[《将来之督办币制大臣》,《大公报》1910年12月13日,第5版。]宣统二年底,清廷筹划设立责任内阁,载泽一度有望担任总理大臣,据报传闻,载泽曾保举盛宣怀继其度支部尚书之任。[《泽公何亦萌退志耶》,《申报》1911年2月14日,第1张第3版。]后因载泽放弃总理之争而作罢。载泽对盛宣怀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在时人看来,盛俨然已经是载泽的党羽。 邮传部为全国交通总汇之处,朝廷利权之所在,然而自陈璧、徐世昌到唐绍仪,连续三任邮传部尚书皆为奕劻、袁世凯一派人物,载泽极欲染指该部,并不满足于仅将己派亲信盛宣怀安插在侍郎之位,更想要拿下尚书一职。时任邮传部尚书唐绍仪在本部中大量起用广东籍同乡担任要职,形成一派“粤党”,载泽对此极其不满,遂计划扳倒唐。[《盛杏荪办洋务》,胡思敬:《国闻备乘》卷1,第15—16页。]他首先嗾使其姻亲瑞澂弹劾唐绍仪,指称:“唐绍仪不过为盛宣怀一翻译,并无才具之可言,历办外交无不着着失败,经手款项徒以冒滥为能。”[《鄂督连参唐尚书之严厉》,《申报》1910年9月22日,第1张第5版。]显然是在扬盛贬唐。接着,度支部在财政上对邮传部百般掣肘,唐自知难敌载泽,遂自请辞职。[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下册,第201页。]盛宣怀见有机可乘,乃向载泽行贿六十万金,企图夺取尚书一席。[《盛尚书诱骗泽公》,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第85—86页。]其时邮传部另一名侍郎沈云沛亦有希望晋升尚书,他在唐绍仪上任之前曾有过署理邮传部尚书的经历,论资历当在盛宣怀之上,“宣怀捷足先登,兼有载泽之助,云沛仅恃奕劻,遂相形见绌”。在载泽的提携之下,盛宣怀得以晋升邮传部尚书,沈云沛仅调吏部侍郎,“吏部昔称六曹之长,而此时已成闲署,且行将裁撤矣。云沛由绚烂而平淡,觉鸡肋之寡味,未几即乞休。宣怀如愿以偿,意气发抒,遂贯彻其主张”。[《交通系》,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6第10页。]十七日,赵尔丰回电表示:“日内即拟起程,到川后查度情形,相机劝导。当此时局艰难,万不可使民气再乱。”[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766页。] 闰六月初三日,端方电致载泽和盛宣怀汇报川路风潮情形,称:“川人对于路事,确定于初十日开会,所刊《蜀报》暨各种传单嚣张狂恣,无可理喻。近又纷电李姚琴(即后文的李稷勋——引者注),有速将外间存款数百万汇回成都,免为邮部所夺等语。并派人分赴湘、粤,极力鼓煽。”端方还向泽、盛控诉王人文“违道干誉,专主附和,不加裁抑,颇有幸灾乐祸、藉实其前言不谬之意”。建议设法阻止川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尽快拿办首要人物。[盛宣怀:《愚斋存稿》卷7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27—28页。]载泽和盛宣怀甚为恐慌,翌日将此事商诸总协理大臣,建议内阁速发电旨阻止股东大会,奕劻等人认为应待赵尔丰到任后再发。然彼时川路股东大会已定于初十日召开而赵尔丰到任之期未定,泽、盛二人对此颇为焦虑,遂电致四川藩司尹良探明赵尔丰何日可到,迅速电复,并密告尹良,如赵不能赶在股东大会之前到任,即与王人文“平心办事,刚柔互用,总以设法解散为是”。[国史馆史料处编:《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上册,第362页。] 眼见川路风潮愈演愈烈,载泽对督办铁路大臣端方也极为不满,他在信函中有谓:“惟闻午桥(即端方——引者注)在武昌行辕每日请客,不甚关心路事,大有醉翁之意,奈何,奈何。”其所谓“醉翁之意”,实指端方欲谋求湖广总督之位,而彼时的湖广总督瑞澂乃是载泽姻亲。初五日,瑞澂函致载泽,“痛言陶斋(即端方——引者注)举动谬妄,于路事毫无布置云云”,载泽对其委任梁鼎芬等人为铁路总办亦早有不满。作为一名“谊属宗支,休戚与国”的亲贵,载泽对国事的热情显然要比端方这样的异姓大臣高,在他看来,川事糜烂之际端方的所作所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当日致盛宣怀的信函中申明了自己的政见: 伏念此次借款造路,稍有不慎,既无以对朝廷,更无以对拒款之百姓。泽管财政,尤不能不格外关心。前日林炳章说帖诚不为无见,曾肯代拟奏折,未知脱稿否。鄙意此折必须呈递,严为限制,陶斋见罪与否在所不计,如或奏奉谕旨后仍无效果,则彼时当用野蛮手段矣。[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34—2837页。] 闰六月初六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赶即前往川督任上,务必于初十日股东会议召开之前抵达,“届开会日期,多派员弁,实力弹压。除股东会例得准开外,如有藉他项名目,聚众开会情事,立即严行禁止,设法解散,免致滋生事端。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以销患于未萌。该署督务即遵旨,迅速赴任,毋稍延缓,并将对待办法预为妥慎筹划”。[《宣统政纪》卷57,《清实录》第60册,第1018页。]初八日赵尔丰抵达成都,初九日正式接印上任。清廷欲以“悍吏”赵尔丰强力推进干路国有,然而赵到任后立即与朝廷意愿相悖,他有感于川省民意愤激,认识到川路风潮不可强行压制,主张采用安抚策略,不但未强力干涉川路公司股东大会,还向清廷建议俯顺舆情,暂缓办理,但清廷仍不为所动。 连续两任川督的建议均无法阻止清廷收路的决心,与此同时,盛宣怀又强要留用已被川路公司辞退的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这彻底激怒了川省舆情,七月初一日,成都全城爆发了大规模的罢课、罢市行动,米价飞涨,各街居民沿街供奉光绪皇帝牌位,写有“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字样。[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889—892页。]此时绅民虽采取和平方式争路,但愤怒情绪已逼近极点,清廷若能俯顺舆情,做些许让步,仍有可能将保路风潮控制在和平范围内,而一旦再次激怒川人,即将激化矛盾,酿成流血冲突。 然而,载沣、载泽未意识到民愤已经到了即将激化的危险关头,并不打算延缓干路国有计划。载沣接到赵尔丰关于川省保路情形的汇报后首先考虑的是“此次该省激动情形,有无匪徒从中煽惑”,并下令“严行弹压,毋任再滋事端。所有各领事馆、教堂及重要局库,务须尽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宣统政纪》卷58,《清实录》第60册,第1038页。]不过载沣此时严旨弹压针对的是煽惑的“匪徒”而非保路的绅民,其时盛宣怀主张立即调兵镇压保路运动,载沣并不认可,声称:“川人亦朝廷赤子,只宜善言劝导,如果系为路政争执,宁可朝廷稍受委曲,断无与百姓为敌之理。且路归国有政策系出自盛宣怀,已经滋怨,贻误大局,若再用强硬手段,以致激成祸端,试问该大臣能当此重咎否?”[《川路风潮危迫之现状》,《大公报》1911年9月11日,第4、5版。]可见载沣此时已经对盛宣怀颇为不满,另据时论报道:“川民抗争罢市,阁臣相顾错愕,监国颇咎盛(宣怀)主张借债收路,坐失人心,致有今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99页。]七月初六日,载沣发布了一道语气相对和缓的上谕: 铁路收归国有系为减轻小民担负起见,叠经降旨宣布,乃川民仍多误会,相率要求,其词虽激,其愚可悯,朝廷亦何忍重负吾民?着邮传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将路款轇轕纠葛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群疑。赵尔丰身任疆圻,保卫治安,是其专责。务当仰体朝廷爱民之隐,剀切开导,设法解散,俾各安心静候,照常营业。[《宣统政纪》卷58,《清实录》第60册,第1040页。 ] 载泽坚持认为闹事的只是部分“莠民”,多数川民不支持保路,主张强力弹压保路运动。七月初六日上谕,载沣命载泽列衔署名,载泽以载沣未能对川路风潮采取强硬举措颇感愤懑,乃向盛宣怀抱怨称:“今早居摄(指载沣——引者注)又令邮部拟办法电致季帅(即川督赵尔丰——引者注),今忽加入度支部殊觉刺目……鄙意不愿列衔决非不负责任,总以为此等办法甚不满意也,将来如用强硬手段泽决不推辞。”[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53—2854页。]其时湘、鄂、粤三省风潮在地方督抚的强力弹压之下已逐渐归于平静,这益使载泽相信高压政策才能平定风潮,而川省局势的恶化正是由于两任川督的纵容。[其时端方致电载泽、盛宣怀有谓:“前者湖南反对铁路国有,经湖广总督瑞澂电致湖南巡抚杨文鼎,禁止刊刻传单,开会聚众,登时解散。今则群情帖然,收路在即。”(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85页)载泽极表赞同,并拟将端方意见密告载沣。(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0,第16页)]为了争取载沣的强硬态度,载泽于初九日专门上了一道说帖,要求严饬赵尔丰,强力弹压保路运动: 铁路国有政策,中外同钦,朝廷断无反汗之理。四川莠民抗拒谕旨,实为国法所不容,全赖政府主持于内,地方官弹压于外,乃能相安无事。今川督电奏沿街搭棚供奉德宗万寿牌,藉图煽惑,此等举动实近于义和团。川督不但不能禁止,转有不敢禁止之意,实属糊涂谬妄。试问强盗头顶万岁牌到处行劫便不敢拿办乎?此事在川民为亵渎先朝,在川督为戏侮监国,情节万分可恶,无如川督柔懦无能,政府又不负责任,且有幸灾乐祸者盘踞于中,势不至酿成大患不止。监国若不极力主持,大局不堪设想。拟请严旨切责赵尔丰,以期消患未萌,勿听政府之恐吓,要知刁风不可长,莠民不足畏,是在监国纲断,毅力主持,无惑人言至要。[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51—2852页。] 可见载泽的态度要比载沣强硬得多,他上此说帖提醒载沣勿为人言所动,显然是担心载沣举棋不定。说帖上奏后,载泽仍心里没底,唯恐载沣不能听取他的建议,在当日致盛宣怀的信函中言道:“今早业将说帖呈阅,究竟采纳与否不可得知,殊觉闷损,惟向来召见内阁在先,外起在后。今忽改后见内阁,意似酌留写字工夫亦未可知。”[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56页。] 川省局势日益糜烂进一步加深了内阁中载泽派与奕劻派的矛盾。起初奕劻等人便不主张遽行铁路国有政策,但拗不过载泽等人一意孤行;保路风潮发生后,在奕劻等人看来此系载泽派一手造成,正是打击其权势的绝好时机,因此并未极力干预,而是隔岸观火,任由载泽等人行事,坐看其如何收拾,载泽说帖中提及的“盘踞于中,势不至酿成大患不止”的“幸灾乐祸者”即意指奕劻。时论注意到,“某公(指载泽——引者注)在政府中意气颇盛,大有旁若无人之势,庆邸本甚不满意,川路风潮初起,庆邸即谓对于川人终须和平,否必决裂。某公信用盛宣怀、郑孝胥之言,主张强硬,遂致酿不可收拾之局。警电到阁,庆邸曾叹曰:‘吾早料及此,奈诸公不听耳。’”[《川乱声中之朝局》,《民立报》1911年10月1日,第2页。]又有谓:“庆则更事已多,固灼知此政策一行,必酿成非常之大变,特知之而不欲遽发之,必俟其溃败决裂之后,束手相顾,靡所为计,则两公之名誉与扆眷俱为之扫地以尽,自不敢复为觊觎政地之谋,而以己之地位势力乃巩固而不可稍撼。”[《川乱危言》,《民立报》1911年9月22日,第1页。] 川路风潮激化后,奕劻等人主张善待民意,采用和缓办法办理。载泽和盛宣怀,“他们也深知在此危机时期,去迎合地方民意,不但可能停止国营铁路建设,而且还可能导致清帝国的瓦解,因为四川、湖南、广东和其他省份皆已借机进行反清活动”。于是泽、盛派遣邮传部侍郎李经芳去见英国公使朱尔典,希望朱尔典能帮忙游说奕劻,“以强烈的言词劝告他不要采取那种可能暴露中国弱点而导致中国灭亡的政策路线”,并建议朱尔典“应当表示要积极干涉,借此作威吓,才能使这位‘糊涂’的老官僚有所醒悟”。[《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55页。] 其时总协理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主持阁务,他们反对载泽的强力弹压主张,并且不将四川来电交载泽查看,在奕劻等人的建议下,载沣发布了几道语气和缓的上谕。载泽对此极为不满,在他看来,总协理大臣此时主张缓和只能令川事更加难以收拾。载泽向盛宣怀抱怨:“近日政府所拟谕旨,一次比一次松懈,不知是何居心,或者有意酿乱亦未可知。”并直斥总协理大臣:“邸座(指奕劻——引者注)开口第一句即出人意外,可见不足以有为,大势去矣,可胜憾哭。那、徐二人私心充斥,想更无办法,亦不足与谋。”[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52、2836页。]由于总协理大臣主张和缓办理,载泽一度未能争取到朝廷的强硬举措,颇有怨言,竟致拒绝参与内阁商议。据报载,“川省抗路风潮现已连电到京,昨内阁总理邀集泽盛两大臣在内阁密议,熟商正当办法,泽公对于此事声辩:‘本大臣虽曾参预借款,然并未干涉路事,现川省所纠葛者为路事,非为借款。其中应如何筹办之处,本大臣不负责任,故亦不便与议。’言讫竟自行退出,各王大臣亦随即散班”。[《泽公不负路事责任》,《大公报》1911年9月8日,第4版。]川事糜烂已危及国本,奕劻、载泽两代亲贵不仅不能通力协作,反而互相诿过、倾轧、拆台,致使清廷决策首鼠两端,难以形成对待川事的统一意见,朝局日趋失控。 在宣统朝政坛上,奕劻和载泽是老少亲贵的代表人物。奕劻虽老髦保守,无意开拓,但政治阅历丰富,处事谨慎;载泽虽趋新求变,进取意识较强,但阅历不足,行事近乎操切。在速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强军富国等诸多问题上,民众普遍希望朝廷能够锐意进取,彼时朝廷“有为”才能顺应民意,因而少壮派更受舆论青睐,奕劻则以其立场保守屡被舆论攻击。川路风潮激化后,舆论希望的是朝廷能够退却,此时“无为”或“少为”才能顺应民意,于是“一味进取”的载泽逐渐为时人诟病,奕劻的“老成持重”受到舆论认可。其时有时论将川事糜烂归咎于载泽与奕劻的纷争:“泽之欲取庆而代之也,非一日矣。庆虽昏髦贪婪为天下所不与,而凭借既坚,根底深厚,非可以旦夕倾之者。故非有非常之大政策足以震动海内外之心目者,必不足以收战胜之效果,此盛之所以伺间乘机而得行其大借外款之计划者也。泽年少而勇于任事,顾艰难险阻曾未少尝。盛虽阅历较深而垂暮年华正当戒得之候,徒知目前有什伯之大利,而不晤将来有邱山之巨害,所谓攫金于市,但见金不见人者,两公之为矣。”[《川乱危言》,《民立报》1911年9月22日,第1页。]对于奕劻则有谓:“庆内阁自此次川乱后,舆望增进,足见政界情事之无常。然平心而论,此次若非总协理之力主和平,则川事将不可问矣。”[《阁部现形记》,《时报》1911年10月11日,第2版。]足见老少两亲贵的政坛口碑由于川路风潮而发生了反转。 四、激起民变与镇压保路 七月初一日罢市罢课事件发生后,虽然清廷未采纳载泽的强力镇压主张,但彼时川人的怒火已经被激进派带有煽动性的宣传鼓动起来,所争已非只在收路办法一端,清廷仅以“剀切晓谕”“明示办法”之类的上谕难以平复川省民愤,“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捐杂以为对待”。[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964页。]继成都之后,四川其他州县相继发生罢课、罢市、抗捐等活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暴力事件。 眼见局势日趋失控,川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昆屡向清廷上折痛陈川省的危险情势,建议将干路有一事交资政院商讨,资政院议决之前铁路暂归商办,并要求惩办盛宣怀,如此才能安抚民心,消解风潮。不过载沣并不打算就此收手,坚持“干路收为国有,早经降旨允行,决无反汗之理”,并斥责赵、玉“殊属不知朝廷维持全国路政之深意”,仍令赵尔丰迅速解散保路组织,切实弹压暴力行为,不得再使风潮蔓延,否则将治其罪。[《宣统政纪》卷58,《清实录》第60册,第1044页。]至于已成为众矢之的的盛宣怀,载沣对其虽有不满但尚不打算严惩,据报载,“监国于初九日午后特在本邸传见民政大臣桂春及邮传大臣盛宣怀,情形甚急,随即交出一折着盛阅看,阅未竟,盛面有惭色,该折内容系川省人士为铁路借款事参劾盛之丧权误国,有迕先皇谕旨。监国见盛踧踖状况,略加训慰”。[《监国传见桂盛两大臣之述闻》,《大公报》1911年9月6日,第3版。] 局势的恶化使主持收路事宜的载泽、盛宣怀、端方三大臣极为恐慌。七月初六日,端方致电泽、盛,痛斥赵尔丰举措乖方,纵容川乱,一旦酿成暴动,以赵之手段势难敉平,建议朝廷派重臣入川查办,请泽、盛二人从中维持。翌日,盛复电极表赞同,称载泽此时正准备上呈说帖力劝载沣,端方电奏到京后即交于载泽密奏监国。初九日,载泽面见载沣,因端方电奏没能及时到京,载泽未得将该奏进呈,只提及派员入川查办问题,载泽“又切实面奏”,载沣“遂稍动容”。[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997—998页。]随后,载泽得见端方奏折,认为“端方来电抄送电参赵尔丰原稿,语语痛切,有关大局,朝廷断不能不为主持。又有请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之语,与昨日面陈办法不谋而合,应请独断,及早发挥”。[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58页。] 至于所派入川查办之大员,盛宣怀曾向载泽提议或可派遣端方前往,“仍以路为名,到彼再将事实揭晓”。但端方以为川省风潮因路政而起,自己是办理路政之人应当回避。[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998页。]载泽亦不赞同派端方入川查办,建议起用岑春煊。岑系彼时少有的政治能人,素以善于用兵平乱著称,又曾署理四川总督,在川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清廷若起用岑春煊办理川事极有可能缓解川民与朝廷的对立情绪。载泽将此意禀报载沣后,载沣竟陷入为难,以岑春煊系奕劻政敌,二人交恶已久,若此时起用岑恐怕会伤及奕劻颜面,有意派遣瑞澂入川。载泽认为“瑞澂前往,亦必能济事,但瑞澂身体多病不定,能耐此蜀道艰难否?万一半途患病,不利遄行,亦恐有误事机,不可不虑”。[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58页。] 载沣采纳了载泽部分建议,同意派员入川查办,但不打算起用岑春煊,“某中堂”建议派前任邮传部尚书唐绍仪前往,载沣不以为然,认为唐“为人轻率,虽有杰才,然办理此事终恐不洽舆论”。[《监国不重用唐绍仪》,《大公报》1911年9月11日,第3版。]七月十三日,清廷发布上谕,简派端方赴川查办路事,理由是“以其系原参之人,必不致有回护隐饰情事,且川鄂交界,路途并不甚远,再近实无可派之大员”。[《宣统政纪》卷58,《清实录》第60册,第1044页。]其时端方早已因强行收路得罪川省绅民,以端入川必定再度激化风潮,这显然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 载泽等人对这一任命极为不安,盛宣怀怀疑此系总协理大臣从中作梗,以致载泽的建议没能被载沣全部接纳,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2页。]端方极不愿担当此任,乃致电载泽,求其在载沣面前设法挽回,另简其他大员入川;如不能获允,则奏请朝廷先饬赵尔丰严厉弹压,而后准许他带鄂省军队入川并有权随时调遣川省各军。该电末谓:“初十日寄谕季帅,词稍严厉,窃揣非荫弟(即载泽——引者注)之力不及此,仍恳始终维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999—1000页。]端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载泽身上,在他看来只有载泽才能说服摄政王收回成命,有关载泽将端方意图转达给载沣的具体情形,囿于史料有限难得其详,据载泽事后的信函披露:“陶斋赴川为不宜,人所共知,前于独对时反复痛陈,未置可否,更不知政地有何措施,殊为闷损。”可见在载泽看来,以端方入川绝对是下下策,他在载沣面前已经力争过多次,但并没能使载沣收回成命,以致感叹“大好河山如此断送甚为可惜”。[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60页。]最终,清廷不允端方推诿卸责,仍令其赴川查办,准许其调动川省各军。[《宣统政纪》卷58,《清实录》第60册,第1043、1046页。] 清廷以端方入川激起了绅民更激烈的反抗,其间有人散布《自保商榷书》,号召川人停止输捐、纳税、协饷,激进派已经有意与清廷决裂。总协理大臣以川事危急,向载沣提议电饬赵尔丰来京面商办法,载沣反对,“以川省风潮正赖赵尔丰随时镇压,若遽召来京,既恐迁延时日,且虑滋生他变,此举殊于路事无益,着不准行”。[《奏请赵尔丰来京不准》,《大公报》1911年9月7日,第5版。]赵尔丰迫于压力,最终改变方针,于十五日诱捕了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人,川民得知后怒不可遏,数千人涌向总督署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卫兵射杀群众数十人,激起民变,保路同志会组织川省各地发动起义并有革命党人参与其中,川路风潮最终在清廷的高压之下,从绅民和平请愿演变为武力反抗清廷的斗争。载沣认为赵尔丰查拿首要人物的办法尚属妥恰,但川民的武装暴动还是在他意料之外,据报载:“川督赵尔丰昨有急电到京,称川民数千人,于十五日围困督署(此一层),情形紧急,各属匪党(此又一层)又乘势暴动。用兵不敷分布,大局异常危险。监国呈毕,叹曰:不图盛宣怀误国至此。”[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409页。]其时赵尔丰以川省兵力不足向朝廷求助,载沣下令“瑞澂就近遴派得力统将酌带营队,迅即开拔赴川,暂归赵尔丰节制调遣。当此事势急迫,该署督务当督饬兵队相机分别剿办,一面出示解散胁从,以安人心。一面严饬省外州县妥慎防范,悉心安抚,免致勾结为患”。[《宣统政纪》卷59,《清实录》第60册,第1050页。]十六日载沣召见总协理大臣,“着即赶速设法解散风潮,否则诚恐牵动大局,益至不可收拾。且此亦系中央政府应负之责,未便尽委诸赵尔丰、端方。务尽五日之内拟定切实办法,不得延缓”。[《监国勒限办理川路风潮》,《大公报》1911年9月12日,第3、4版。]十七日,载泽面见载沣,认为铁路国有系朝廷既定政策,川民竭力反抗,始则罢课罢市,继则抗捐拒租,如今竟致谋求自立,必须严厉镇压。[《川乱中之京师》,《时报》1911年9月22日,第2版。] 七月十九日,载沣召集总协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在勤政殿商议应对川事办法,载沣阐明了对川省保路风潮的看法: 铁路国有定为政策,借款办路实出万不获矣。湘粤两省士绅初虽误会,今已帖然,不料川人始终反抗,聚众要挟,不听劝导。观近日种种情形,如成都士民之围扰督署,来京代表之滋闹王府,殊属不成事体。若再事姑容,效尤将伊胡底?且借款筑路之议创自故相张某,朝廷对于国势民力审慎再三,迁延至今始经定议。该省绅民岂毫无闻见,奈何不谅朝廷苦心,但凭一二不肖士绅之怂恿,恃众呈蛮,目无法纪。该省大吏不能善为开导,尚有附和渎奏者,真不解事。卿等速电川督,一俟督办端方到时,会同妥为解散。并访拿首要,请旨办理。[《川路枪声记(五)》,《时报》1911年9月18日,第2版。] 总协理大臣对绅民的暴动仍不欲操切行事,载泽则认为:“祸乱已至如此,若再优容,后果何堪设想?”徐世昌认为川事虽不能再优容,然没有谋逆确实证据不可轻言杀戮。[《川路滴滴血》,《申报》1911年9月22日,第1张第4版。]当日拟旨时采取折中办法,分别“路事”与“乱事”,于“乱事”中又分别剿平匪乱与解散胁从,谕旨草案由阁臣拟定完毕后进呈,载沣又做了些许修改,意在避免言辞过于激烈[“二十日宣布川路乱事之谕旨,阁臣恭拟草案时其中应行宽严并用之处,措词煞费踌躇,经总协理研究多时始能得体。迨草案呈进后,复由监国添改多语,始行颁布。闻旨内‘不得稍有株连,免致地方糜烂,如有为逆党强迫列名会簿者,即将各册全行销毁,一概不究’等语,又‘端方带队入川后,务须申明纪律’句下‘严加约束,不准骚扰’八字均为原拟草案所未有,经监国指饬增入者。”见《川乱谕旨曾经监国参改》,《大公报》1911年9月16日,第4版。],二十日正式发布。[七月二十日上谕全文:“谕内阁,自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凡从前商股民股均经饬部妥定办法,明白宣示。既已减轻民累,复不令亏损民财,朝廷体恤闾阎,实已仁至义尽。乃川人未明此意,开会演说,藉端争执。始不过无知愚氓群相附和,继则罢市罢课,迹近嚣张。屡经电饬赵尔丰弹压解散,并饬邮传部将路款轇轕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群疑,原冀早就敉平,各安生业,迄不忍加罪吾民。不料抗粮抗捐之议相继而起,惟恐有匪徒从中煽诱,别滋事端,特派端方前往查办。仅准酌带兵勇两队,俾免惊疑。旬日以来,该省突有人散布自保商榷书,意图独立,并有约期起事之举。经赵尔丰先期侦悉,将首要擒获。本月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毙弁兵,似此目无法纪,显系逆党勾结为乱,于路事已不相涉,万难再予姑容。已电饬赵尔丰相机分别剿办,该署督迅即懔遵前次电旨,严饬新旧各军。将倡乱匪徒及时扑灭,勿任蔓延。其被胁绅民均系无辜,尤当妥筹安抚,不得稍有株连,免致地方糜烂。如有为逆党强迫列名会簿者,即将该名册全行销毁,一概不究。端方带队入川,务须申明纪律,严加约束,不准骚扰,并沿途晓谕居民,宣布德意,俾皆晓然朝廷不得已而用兵,纯系为除莠安良起见,以定众志而遏乱萌。至该省商民一切路股,仍着邮传部督办会办铁路大臣遵旨妥速办理。经此次申谕之后,该省绅民等勿再轻信浮言,徒滋扰乱,应即照常开市开课,各安本分,用副朕谆谆诰诫之至意。”见《宣统政纪》卷59,《清实录》第60册,第1054—1055页。]过往研究者多认为载沣在川省暴乱发生后采取强硬态度对待,[例如,李学峰《载沣与清朝末年的铁路政策》(《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一文指出:“此时,载沣已无退路,只有硬着头皮,强硬到底。”]不过从二十日谕旨措辞看来,载沣并没有完全采纳朝中较为强硬的载泽一派的建议,总协理大臣的和缓主张对朝廷决策有较大影响。时论注意到:“二十日之上谕,乃参合两派意见而成之者。故一句一开,一句一阖,既曰分别剿办,又曰妥筹安抚;既曰及时扑灭,又曰销毁名册,一概不究。”[《川乱中之京师》,《时报》1911年9月22日,第2版。] 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朝廷和皇帝必须是一贯正确的,一旦政策有失往往首先要诿过臣下。川路风潮发生后,盛宣怀早已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而暴动的发生使载沣认识到有必要与盛宣怀划清界限。在他看来,朝廷的干路国有政策没错,只因盛宣怀办理不力才酿成风潮,其时已有御史弹劾盛宣怀误国,载沣若再听信泽、盛一派的强硬主张显然不合时宜,他认为:“此事本由盛宣怀酿成,如再操之过急,乱更难解,奈何欲以意气糜烂大局耶?速电各该督抚,妥为劝谕,俾待后命云。”[《监国恻隐之心》,《民立报》1911年9月16日,第3页。]对盛宣怀失去信任应是载沣不愿采纳载泽强硬建议的一个原因。 此时川省局势发展早已脱离清廷掌控,载沣一纸“温谕”根本无济于事,翌日即有报告称成都已被保路军民围困,电报中断,清廷只能寄望于武力镇压。然而勉强受命入川的端方逡巡不前,坚称自己的职责是督办铁路事务,不宜参与弹压,并且曾参劾过赵尔丰,入川后恐多误会,仍寄希望于朝廷能更换大员。[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48页。]载泽早就认为派端方入川不可取,“午帅畏川如虎,其行程延缓,事所必然”[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62页。];端方既畏葸不前,载泽遂极力运作岑春煊出山。 此时有意保荐岑春煊的不止泽、盛,还有鄂督瑞澂和东督赵尔巽。载泽、盛宣怀认为“须有外省督抚之电奏,而后监国能允起用岑春煊”,遂联络瑞、赵二督共同吁请。[《岑春煊受命记》,《民立报》1911年9月23日,第2页。]据盛宣怀致赵尔巽的电文披露:“泽公接莘帅(即瑞澂——引者注)函,请改派西林(即岑春煊——引者注),似与尊见相合,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如公以为然,可否电商莘帅,会同电奏?”同日,盛在致瑞澂的电文中又谓:“次帅(即赵尔巽——引者注)来电亦商改派,事已急切,公可否电商云帅(即岑春煊——引者注),会同电奏?逊敷(即载泽——引者注)必为内应,弟以将此意电复次帅矣。”[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3页。]由此可见泽、盛、赵、瑞四人为推动岑春煊出山,以盛宣怀为中心相互联络,制定了内以载泽面劝载沣,外以瑞澂、赵尔巽两督联合电请的计划。 二十一日,载泽函致盛宣怀称:“明日进呈宪法条文,本拟请起,惟与伦贝子同见,不便开谈,拟于事毕留后刻许工夫痛切一言,采纳与否,付之天命而已。”二十二日,载泽独对,再次向载沣力荐岑春煊,但载沣“未置可否,意似有为难”,载泽对载沣在如此紧要的时刻竟依然犹豫不决颇感失望,在当晚致盛宣怀的信函中认为:“大约仍归无效,此则关乎天心国运,非人力所能为矣。”[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64页。]不过,由于有了瑞、赵两督联合电请,结果并非载泽想象的那般糟糕,据报载:“瑞督来电,力请另简重臣,帮同办理;赵督亦请起用岑春煊,并力陈岑在广西剿匪之事迹,监国大为动容。”[《岑春煊受命记》,《民立报》1911年9月23日,第2页。]盛宣怀甚至乐观地向岑表示:“莘帅、次帅电商改派,上公(指载泽——引者注)仍请派公。事棘,当局似难再执私嫌。”[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50页。]二十三日,廷议商讨改派岑春煊事,“监国对于川乱极为焦灼,满冀从速解散,端方、赵尔丰均系川民之所反对,恐增恶感,故另派威望素著之大员前往相助为理,以期得力”。[《岑西林将继任川督》,《大公报》1911年9月19日,第4版。]奕劻见载沣心意已决,遂请假以图规避署名。当日,清廷发布上谕,派岑春煊前往四川与赵尔丰共同办理剿抚事宜,命其即日由上海乘轮起程,不得延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26页。] 清廷起用岑春煊使载泽喜出望外,他认为,“云帅明日即行,可谓迅速之至,此去必能有效,但希稍迟数日耳”“西林此番入蜀,必立于不败之地”,载泽还函告盛宣怀“于晤西林时切实筹商,期有把握”,并要求邮传部电告岑春煊川省匪患严重,“从前感情未必足恃也”,言下之意,希望岑春煊能严厉弹压。[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68、2880页。]端方以朝廷已起用岑春煊,遂电告载泽有意辞去查办之差。二十四日,载泽将端方辞意密陈于载沣,载沣准其所请,下令将端方节制军队全部交岑春煊指挥,以便划一事权。载泽还因岑此次入川,仅奉命与川督共同办理剿抚事宜而无正式名号,建议授予岑钦差大臣以示隆重,不过载沣当时对此并未表态,载泽在信函中向盛宣怀抱怨这是总协理大臣从中作梗:“起用西林,只令会同办理剿抚,既无兵权又无名分,倘亦别有用意,不欲其成功耶?”[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77页。] 川路风潮激化后,载泽日益受到朝臣和舆论的攻讦,甚至已经引起了载沣的不满。[“监国近来对于川省乱事极为注意,连日召见阁臣密筹办法。昨二十五日复行召见,密议此事,详情虽不能悉,只闻曾谓阁臣云:‘此次川乱虽由于王人文、赵尔丰办理之不善,然追原祸始,载泽、盛宣怀实皆不能辞责。’”见《监国不满意泽盛两大臣》,《大公报》1911年9月20日,第3版。]载泽将平定川事、挽回声誉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岑春煊身上,他在载沣面前保证岑二十五日即可起程,“一往直前,较之逗留不进者,奚啻天渊”,载沣嘉许;然而岑受命后并没有回电汇报起程日期,反而在成都围困之时奏请调粤省军队入川解围,这使载泽一度极为尴尬。其时朝中反对者多谓“端在鄂迟延,尚与瑞商征调。沪有何事?并以调粤军,何能济急?临敌易帅,辗转担延,成都危矣”,指责载泽应对无方。[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第1562页。]为促使岑春煊迅速起行,载泽向载沣建议,岑入川后立即授以四川总督,[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85页。]载沣应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第1562页。] 载泽力保岑春煊,原本希望借助岑在川省的声望及强力手段迅速平定乱事,并震慑其他省的反抗活动,即其所谓“各省之观坐待隙而动,固意中事,惟愿川事早了,则诸怪自绝”。[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79页。]然而令载泽失望的是,岑春煊竟依然如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采取安抚政策,主张和平办理。二十六日,岑春煊在上海发表《告蜀中父老子弟文》,劝绅民各安本业,朝廷不会妄开杀戮,表示将会为川人请命。载泽、盛宣怀有意将“路事”与“乱事”区别开来,欲以岑负责平乱而不令其参与路事,但岑坚称川路风潮因收路不公而起,必须先使还股办法不负川民,才能将仍不听命者视作乱民剿办。[岑春煊:《乐斋漫笔》,第36页。]载沣遂下令“凡川省路务事宜,均准该大臣参酌办理,并嘱与端方和衷筹划,毋得稍存意见,以期成效早收”。[《特准岑督干预路事》,《大公报》1911年9月30日,第3版。] 七月二十七日,岑春煊向清廷电奏处理川路风潮的“标本兼治”之策,建议清廷释放保路士绅,以现款发还川人股本,国家补偿铁路亏损,朝廷下诏罪己。岑春煊认识到川省乱事全因收路而起,从路事下手方为治本之策;况且即使武力镇压,彼时端方和岑春煊尚在途中,先以此安抚民心仍可能防止动乱扩大。[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4—6页。]岑春煊的政见无疑是清醒的,清廷若能采纳仍有可能缓解局面。然而,载泽此时一味迷信武力镇压,对岑的政见极不满意,在致盛宣怀的信函中言道:“岑电读悉,所谓每下愈况,罪己二字尤属不伦,一念沽名,遂不觉措词失当,私心之为害大矣哉!”自己极力保荐之人竟与自己唱反调,载泽对此极度失望,感叹“鄙人所保非人,真堪罪己也”。[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88页。]载沣亦认为朝廷引咎罪己之策极不可取,载沣、载泽只能先将镇压的希望寄托在端方身上,命端“一面赶程,一面听命”。[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第1608—1609页。] 岑春煊见朝廷无意采纳自己的政见,颇不愿前往,七月二十八日,赵尔丰电告成都解围,岑遂以川事渐有好转为由请辞。随后,清廷就是否有必要仍派岑春煊入川进行磋商,奕劻原本就反对起用岑,认为“岑既力辞,若始终强其前往,事与心违,措置必不尽善,似不如准如所请”。[《岑三滞武昌记》,《民立报》1911年10月12日,第3页。]岑春煊系载泽极力保荐,若甫经任命便准其辞职,再次临阵换帅,无疑会让载泽受到更多攻讦。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成都之围虽解,但川乱仍在发酵,应当继续强力弹压,遂向载沣建言:“现在叠奉谕旨,饬令分别良莠,剿抚兼施,此不过暂救目前,以防大局之糜烂。惟是乱民固宜分别剿抚,而肇事罪魁亦当候乱事平定按律严惩,以昭平允而符立宪国制体。”[《泽公奏陈对于川乱之政见》,《大公报》1911年9月23日,第3版。]载沣听取了载泽的建议,翌日发布上谕,仍令岑春煊迅速入川弹压;其所奏还股办法,“尚得要领,与朝廷前次谕旨,亦相符合,其中详细条目,着邮传部速议具奏”。[《宣统政纪》卷59,《清实录》第60册,第1062页。] 这一上谕对岑春煊所奏还股办法采取模糊对待,表面上看朝廷有意允准,然而又要交邮传部议复,实际上不过是为催促岑春煊立即起行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八月八日,岑春煊行抵湖北,当日邮传部否定了岑的还股办法并获得载沣批准,鄂督瑞澂劝岑改变主张,但岑坚持商股必须发还十成现银,并且不能惩办保路首要人物。[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496页。]载泽得知岑春煊仍坚持发还现银、不惩首要极为恼怒,表示:“川匪如此大弄,当与路事何干?岑云阶力主不办首要,真为谬妄。销假之日如蒙召对,自当痛切言之。”[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815页。]本来被载泽寄予强力弹压希望的岑春煊至此已完全成为强力弹压的障碍,载泽转而阻止岑入川。岑自知与强硬派大臣意旨不合,遂于十一日上折以“感受风热,触动旧症”为由请辞,载沣允准。[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第1599页。]岑春煊既辞,清廷失去了安抚川民的最后机会,数日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川省保路起义成为全国革命洪流中的一股。清廷因其处理保路风潮举措失当,彻底激怒民心,绅民与之决裂,随后在辛亥革命中被迅速抛弃。 综上,少壮亲贵载泽和载沣对干路国有及保路风潮的影响清晰可辨。干路国有政策系载泽和盛宣怀一手谋划,得到载沣支持;制定收路办法时载泽偏信盛宣怀,与绅民斤斤计较,导致保路风潮;风潮发生后,总协理大臣主张和缓办理,载泽一派主张强硬对待,载沣虽坚持干路国有政策不可改变,但又未完全采纳载泽的强硬主张;对于主持川事之人选,载泽和载沣始终在端方、赵尔丰和岑春煊之间摇摆不定,既用人又不信人,既不信人又不得不用,举措乖张,终致大局糜烂。干路国有本是利国利民的“善政”,却由于清廷内部纷争、主事者缺乏政治远见、用人举棋不定等因导致民众与清廷彻底决裂,至此,朝局已经完全脱离清廷的掌34—635页。] 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时已年近七十,身体时常抱恙,他如此费尽心机地攀附权贵并非仅为混个更高一级的尚书,然后像其他老髦大员一样浑噩无为,混天度日;相反,他仍想要在任上有所作为。《愚斋存稿》中有盛宣怀“行述”一节记叙了他执掌邮传部后的主要举措: 计受事数月,若收回邮政,接收驿站,规划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规制,靡不灿然毕举,逐件施行。又加币制改革,细极毫芒,振需追求,急于星火。余若度支部四国银行借款、川粤汉铁路借款,商订合同,尤为繁重。府君向以勇猛精进任事,当百端填委,一一应之以整暇,虽不遑寝处,而未尝言劳。[盛宣怀:《愚斋存稿·行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55页。] 可见,盛宣怀的做派并不同于一般老髦官员,他希冀有为,善于理财又主张中央集权,无怪乎载泽将他作为左膀右臂。时人刘垣认为:“载泽利用盛宣怀以反袁,可说赏识非虚。宣怀的能力,的确可以打倒唐绍仪、梁士诒而有余。假如他币制及铁路借款完全成立而不生枝节,亦许可以暂时延长清廷政权之生命。”[刘垣:《张謇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74—175页。]盛宣怀既得邮传部尚书又有载泽为靠山,在朝中话语权大大增加;责任内阁出台后,盛、泽二人分据交通、财政要津,办事擅专,动辄单独请旨办理,不以总协理大臣为然,为后来应对保路风潮一意孤行埋下隐患。 盛宣怀富可敌国又长袖善舞,少壮亲贵中爱财、求财之人难免被其金钱所俘获,他们虽不像前辈奕劻那样贪婪无度,但也时常拜倒在金钱之下。盛在官场上有求于亲贵,在钱财的问题上却是一些亲贵有求于盛。据胡思敬记载,“载泽知宣怀多财善贾,因出宿储合成百万,托其存商生息。宣怀极赞萍冶矿局之利,给以股票一张”。[《盛尚书诱骗泽公》,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第85—86页。]可见,载泽起用盛宣怀不仅因其政见相合、理财出众,同时也接受了盛的好处,时人刘体智的《异辞录》亦注意到载泽与盛宣怀的金钱往来: 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兼收而并蓄。武进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钧衡重任,当之无愧。然泽公拥有汉冶萍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虽不敢遽定为贿,抑无人能断其非贿矣。[刘体智:《异辞录》卷4,第230页。] 除载泽外,载洵与盛宣怀交往亦比较密切。与载泽的不同之处在于,载洵主持的海军部是个花费巨大的衙门,其个人行事又经常贪大图全,不喜撙节,因而更看重盛宣怀的钱财。宣统二年六月,日俄协约签订,清廷危机加深。其时载洵拟赴美考察海军,尚在上海未得进用的盛宣怀闻讯后立即致函载洵,大谈自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认为:“鄙见宜速筹外交良策,看来只有美德两国尚在局外,隐抱不平……殿下此次赴美,自宜设法与美廷妥议牵制日俄之策,匡时救国,在此一着。”并声言自己病情已经逐渐痊愈,能够进京面奏一切。[盛宣怀:《愚斋存稿》卷7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6页。]言下之意,请求载洵在朝中为他多多美言。 载洵出洋考察期间对西洋风物颇有好感,归国后建造了一座西式楼房,拟作为接待德国太子访问之所。该楼共需花费十万余金,但在将要建成之时尚欠款四五成,一时难以筹措,载洵乃直接致函盛宣怀求助,表示:“平夙引为知己者唯宫保阁下耳,拟请暂为假贷,俾于接待德储时不致误事。唯平生从未向人启齿,窃恐一经揭露,亦甚难堪,如蒙慨诺,即祈密函缄致,纫感无既。俟有充余,再行缴纳。”[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6页。]二人书信往来之间,颇有权钱交易之嫌。载洵还因本部一名医官薪水太少,请盛宣怀在油水丰富的邮传部为其谋一差事,[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62页。]俨然已经将盛视作钱袋子。 总之,载泽重用盛宣怀始于政见相合,欣赏其理财能力,继则有扩充己派势力的意图,其间亦不乏金钱贿赂。载洵与盛宣怀来往主要是权钱交易。 二、出台干路国有政策及筹划收路办法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为振兴实业起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建设,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商办铁路热潮,清廷“不分干支,比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然而,建设铁路花费甚巨,民间资本实际上无力承担,且各商办铁路公司管理混乱,技术落后,腐败丛生,效率极为低下,全然违背了清廷加快铁路建设的初衷。不仅如此,一些商办铁路公司为吸收民间资本,强行在本省摊派租股,进一步加重了民众负担。至宣统朝,商办铁路不仅未见成效反而成为一大弊政,于是将铁路收归国有的议论甚嚣尘上,载泽和盛宣怀均是铁路国有的力推者。 宣统元年,载泽向时任暂署邮传部尚书李殿林提出铁路国有建议:“目下全国铁路修筑费用甚大,皆从外国借得,然利权未至大损。若订借款条约,则期满而不能还清,该铁路将非我所有;若从他国借款收回,则与割肉补疮无异,最终对我不利,且遇干戈之事,国家无专有铁路之权,亦难免不利,故铁路当全归国有。”并要求度、邮两部部员将各省的省债发行额、铁路回收额、省债清偿年限及省债利息等做详细调查。[《铁路国有计划》,李少军编译:《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集》,第200页。] 盛宣怀亦赞成将铁路收归国有,与载泽的不同之处在于,盛更倾向于借用外债来加速铁路建设。据报载,盛宣怀曾向载沣提议:“粤汉铁路收回三年之久,而迄今一无成效,热心路事、保护利权、忠君爱国者固如是乎?当此国家百度待举之时,不但不知赞成,反固执己见,鼓动风潮,此等无意识之举动殊不可取。并闻其中常有暗受他人指使,苟为彼辈所云,恐再迟三十年,款亦不足,路亦不能兴办。”载沣闻后“大为动容”。[《盛宣怀主张借债之奏对如是》,《申报》1910年8月24日,第1张第4版。]主政邮传部后,盛宣怀立即着手将铁路收归国有,并就收回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事宜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进行谈判。此外,朱尔典信函中还提及“庆亲王、那桐和徐世昌三人,曾在今年4月当着盛宣怀面前向外国使节郑重保证,盛氏乃王朝之重臣,负责解决铁路问题”[《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10页。],可见盛宣怀的收路举动已经得到最高决策层的认可。 关于清廷出台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基本史实已经十分清楚:宣统三年四月初七日,给事中石长信上折建议将全国铁路分为干路和枝路,干路国有,枝路商办。[《石长信奏请干路收归国有原折》,《申报》1911年6月9日,第1张第4版。]载沣览奏,认为石长信所陈办法“不为无见”,饬令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83页。]十一日,邮传部上折赞成石长信方案,清廷随即发布上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销”。该上谕认为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流弊甚多,“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脂,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责成载泽的度支部和盛宣怀的邮传部筹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的详细办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92—93页。] 从石长信上折提出干路国有到清廷发布收路上谕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概,各界闻之,群相骇异”。[《铁道国有风潮未已》,《申报》1911年5月22日,第1张第4版。]清廷的决策看似颇为盲目,实际上在石长信上折的前一天,载泽在与盛宣怀的信函中已有言道:“石折明日是否呈递,当祈密告。”[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第2784页。]第二天便有了石长信奏请干路国有的举动,由此可见载泽与盛宣怀谋划干路国有已久,石长信上折亦是由于他二人的授意。恰在这短短四日之内,四月初十、十一两日清廷公布了责任内阁成员名单,总协理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正忙于“请辞”,无暇干预路事;及至总协理大臣就职,载沣已经通过了干路国有案,总协理大臣无从商讨,只得勉强在收路上谕上署名。可见干路国有政策系载泽、盛宣怀等少数人经过一番谋划后迅速促动朝廷形成定议,考虑到载泽派与奕劻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载泽、盛宣怀在总协理“请辞”之时迫不及待地促成干路国有政策,显然是在有意排除奕劻等人的干扰。时论注意到:“十一日邮传部奏请全国干事(当作“干路”——引者注)收归官办,消从前批准商办之案时,新内阁发表之第二日也。闻盛尚书以此种问题按照内阁官制系应阁议之件,但一经阁议恐生他种阻力,故乘总协理辞职未就之时先行入奏,以便川粤汉路及开海路两项借款交涉早日了结。”[《干路收归国有之主力》,《申报》1911年5月18日,第1张第4版。] 此外,清廷迅速发布收路上谕与载沣的支持密不可分,载沣自摄政伊始便将中央集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大宗旨,干路国有政策显然符合他中央集权的目的,盛宣怀在致瑞澂的电报中言及对于铁路国有一事,“上意甚坚”。[盛宣怀:《愚斋存稿》卷7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8页。] 收路上谕发布后,时论发现,“邮传大臣盛宣怀此次取消商办铁路,其事多由于泽公之暗中赞助,内阁总协理大臣并不与闻,故封折入奏之期适在总协理大臣辞职未定之日”,总协理大臣就职后,对泽、盛二人无视阁臣意见便促成朝廷收路决策的做法极为不满,其时盛宣怀将拟定完毕的收回商办铁路办法草案交内阁讨论,“某协理”冷嘲谓:“宫保为熟娴路政专员,所定办法谅能合宜,惟果能保全治安不至激成意外风潮,则各国务大臣又何不愿赞成之有?”[《阁臣不满意于盛宣怀》,《大公报》1911年5月20日,第5版。]他们并不反对干路国有政策,而是认为泽、盛二人在未经各国务大臣充分讨论、详细筹划的情况下贸然推动朝廷形成定议多有不妥,若办理不善必将招致风潮,即如某国务大臣声称:“干路收归国有固属正当办法,然须斟酌妥善方不负商民经营之苦心。今遽出此最激烈之手段,诚恐将来众情愤激,必难免风潮之迭生。”[《政界对于取销商路之不满意》,《大公报》1911年5月15日,第4版。] 至于总理大臣奕劻的态度,据朱尔典信函披露:“传说总理大臣庆亲王并未充分支持政府的政策,他与美国公使的一次面谈,更给人加深这个印象。本月2日,邮传部李侍郎代表载泽亲王与盛宣怀(邮传部大臣)来看我。他告诉我说,载泽亲王与盛氏是目前铁路政策的主要负责人,而庆亲王因为嫉妒载泽亲王势力的增长,一开始便对这个政策抱勉强同意的态度。”[《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55页。]可见,干路国有政策是在载泽、盛宣怀极力促动,载沣支持下推出的,而且出台伊始即与载泽、奕劻两派之间的纷争密不可分。由于载泽在内阁中较为强势并且获得载沣支持,又是政界公认的下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的最有力人选,奕劻等人对干路国有一事并未激烈反对,但他们又不满意泽、盛二人刚愎自用的做派,故只得消极对待。 载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