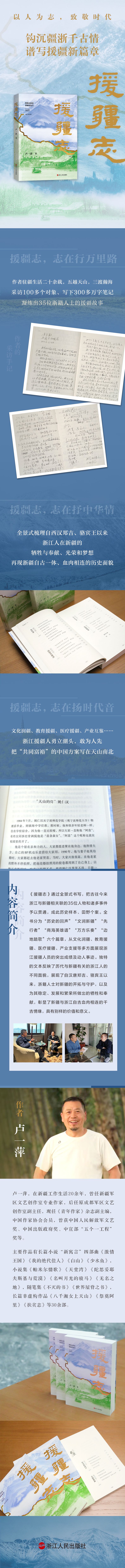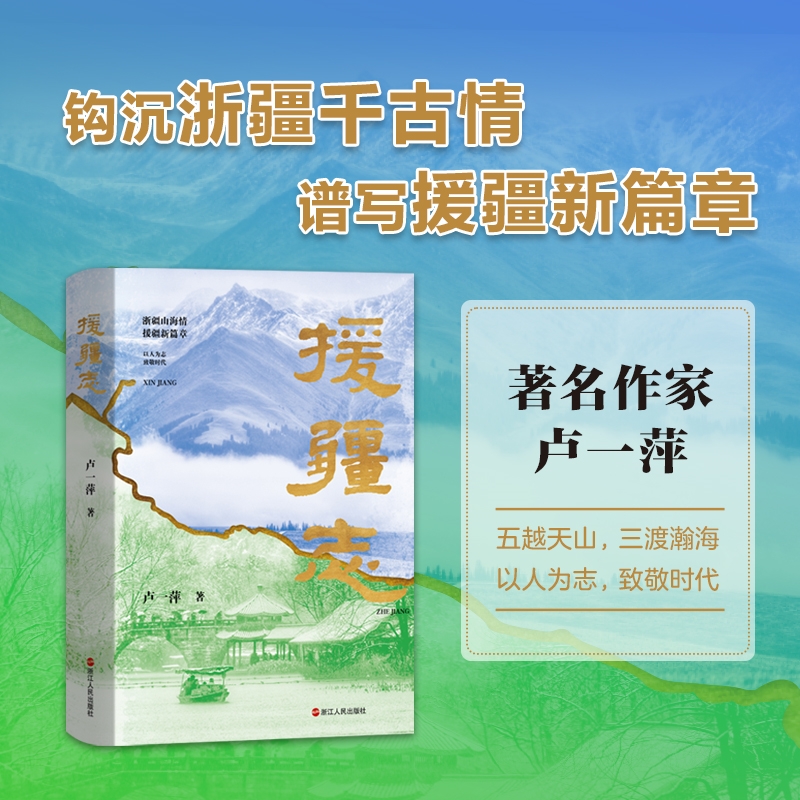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1.40
折扣购买: 援疆志
ISBN: 9787213114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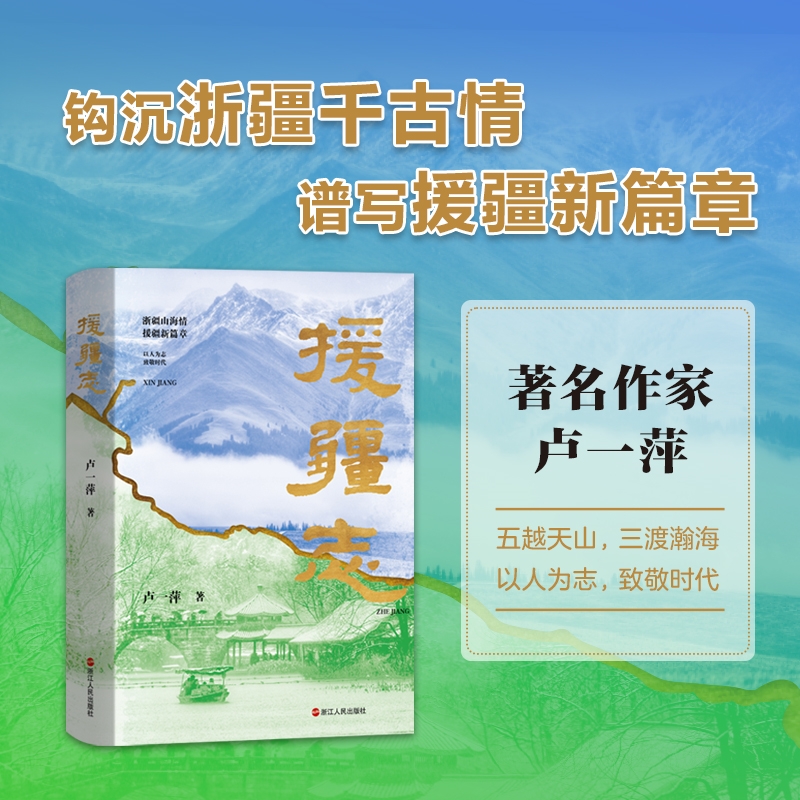
卢一萍,作家,1972年10月出生,四川南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军旅 26年,原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寓言”四部曲《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少水鱼》,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名叫月光的骏马》《无名之地》,随笔集《不灭的书》《世界屋脊之书》,长篇非虚构作品《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扶贫志》等30余部,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序章 大国构想与浙疆情缘 西域在古代泛指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在西汉正式归入我国版图。当时的疆域西至巴尔喀什湖,南至喀喇昆仑山脉南麓;至唐代,其疆域更为辽阔,西界直抵咸海;元朝的西部疆域较汉唐广阔;到清代强盛之时,其西界仍抵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而最早奠定这一基础、居功至伟者,除了张骞,还有浙江绍兴人郑吉——作为第一任西域都护,他在中西交通史和西域史上均具有堪与“凿空西域”的张骞比肩的重要地位。 疆域意味着治理之责,自西汉以来,历朝历代都重视对西域的开发和守护,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故城烽燧、屯垦遗址、古道驿站。疆域开发总与人口迁移紧密相连。在这些遗址的背后,有无数先民西出阳关、筚路蓝缕的身影。这种迁徙活动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古老悠久,也正是频繁的迁移从人种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促进了世界的交流,并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中国在上古就有“夏人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人东迁”的记载。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域成为人口往来迁徙的黄金通道。汉初,月氏人和乌孙人西迁;汉唐时期,汉人因屯田戍边进入西域;清代,也有锡伯族从东北西迁伊犁河谷、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新疆的实例。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一直是一个移民区,也带来了各种文化与观念、方言和习俗。它们兼收并蓄,形成了现代新疆自由开放、剽悍旷达、宽容大度的气派。 而新疆的屯垦,早在西汉就开始了。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2014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五家渠市主持召开兵团座谈会时,就说,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后的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新疆地区的屯垦活动,从汉武帝开始,已经有2000 多年的历史。“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 汉开封六年(前105)护送细君公主与乌孙王和亲的西汉军队在眩雷(今伊犁河谷中)屯戍,揭开西域屯垦史的第一页,自那时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102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西汉屯戍官兵最盛时累计多达2.5万余人。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西域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都护郑吉以屯垦为依托,使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它使许多地名从那时起,就以其浓郁的历史感流传至今,比如轮台、楼兰、伊循、和阗、焉耆、龟兹、高昌、交河等。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在西域大兴屯戍,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即有屯,使西域屯军最多达10万之众。屯田巩固了唐朝的辽阔疆域,同时也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清代的屯田规模最大。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有识之士如浙江人龚鉴即主张在西北兴屯,为此,清朝将屯田作为安边定国之策,不但兴办了军屯,还招募迁徙关内农民来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时,组织发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种,实行犯屯;并从南疆迁移500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谷垦荒种地,组织回屯。不足20年时间,就在西域开垦了近百万亩耕地。 作为改良主义的先驱,龚自珍很早就开始关注西北边疆问题。在国家面临危机之际,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积极筹边谋防,向朝廷进言献策,为西域的长治久安,写成《西域置行省议》,成为最早建议在新疆建省的知识分子。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觉到,那些有功于西域的人,无不被这片热土所铭记。这其中就包括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清代“中兴之臣”左宗棠。 英俄两国利用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作为吞并新疆的工具,使新疆陷入了国土沦丧的严重危机之中。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时,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在胡雪岩强有力的后勤支援下,从光绪二年(1876)至四年(1878)初,左宗棠所率大军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光复了除沙俄盘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随后又于光绪六年(1880)抬棺西征,白发临边,迫使俄国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具备的特殊的战略条件,而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和中国安全的军事基地。著名文学家茅盾来到新疆,开辟了民主阵线,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种子,所剩余粮难以糊口。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7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勒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300卢布,所需总价要数亿元人民币。除此之外,新疆商业几乎为空白。于是,浙江省响应中央号召,从全省各地挑选了500多名优秀青年,在1955年9月慨然进疆,分赴天山南北,肩负起了振兴新疆商业的使命。随后,有无数浙江人因为工作、经商,扎根于此。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浙江与新疆开始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三山逶迤,南有昆仑,中有天山,北有阿尔泰。天山以南,俗称“南疆”;天山以北,俗称“北疆”。在三山的臂弯里,夹着两个巨大的盆地,南疆为塔里木盆地,盆底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为准噶尔盆地,盆底为广阔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新疆地大物博,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330多万公顷耕地,5700多万公顷草原;发现和探明的有色金属矿种138种,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国陆地总储量的30%和34%,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40%。新疆因有特殊的水、土、光、热资源,成为“瓜果之乡”和全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及畜牧基地。新疆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环塔里木盆地为优势产区,种植面积1525万亩,盛产香梨、红枣等特色林果。克拉玛依、准东、塔里木和吐哈四大油田,使新疆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和石化工业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国际大通道。新疆计有边境线5600多公里,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接壤,自古以来都是我国连接西北亚、南亚、欧洲和北非的前沿通道。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西北的稳定,特别是新疆的稳定,事关我国发展和稳定大局。但受制于自然环境和地理交通的影响,新疆的发展一直较为落后。如何经营新疆,让它走上稳定、发展、繁荣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了以屯垦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的方法。 1950年2月,毛泽东命令驻疆大军“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这道命令宣告了在新疆铸剑为犁这一梦想的开始。驻疆20万大军除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以急行军的速度开到了与天地鏖战的新战场。他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当年开荒6.41万公顷,播种5.57万公顷,创办军垦农场13个。1954年10月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10万大军就地转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可称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最稳定、最庞大的援疆、固疆、稳疆力量。 到改革开放前,为解决区域发展和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中央政府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对各种资源进行全国性的调配。虽没有明确提出对口支援新疆的政策概念,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人员、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支援新疆建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疆发展再次进入中央决策层的视野。以次年4月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央对“对口支援”新疆首次有了明确表述。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国家将加强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增加资金和物资投入,并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第一次对我国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确定了具体的对口安排,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 1981年8月,邓小平在新疆考察时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当年底,中央政府决定恢复1975年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2001年2月28日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修正,第64条是:“上级国家机关应当组织、支持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多层次、多方面的对口支援,帮助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从此有了法律依据。 1988年,经过10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国家的发展需要平衡,在全力发展东部的同时,广袤的西部地区也要加快发展。他运筹帷幄,提出了东西部共同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第一个大局”基本实现,而西部的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7.1%,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排在全国与西部倒数第二位。 1996年,中央做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决策。由浙江及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江西、河南8个省市和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选派到新疆工作的首批200多名援疆干部陆续抵疆,进一步开展援疆工作。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东西部长期发展不平衡,必然带来社会矛盾。历史一再证明,对于文化多元、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复杂的新疆,要繁荣,则需长期稳定的环境,而边疆的稳定,也事关国家的发展。为此,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新疆又一次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 此后10多年,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在数批援疆干部的努力下,新疆民生财政投入增长了数倍以上,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持续改善。但新疆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新疆稳定仍面临严峻挑战,新疆的民生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南疆喀什、和田和克孜勒苏3个地州情况尤其令人担忧。为此,根据国家批准的《南疆三地州建设项目专项规划》,加大了对喀什、和田两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资金投入,2009—2013年,国家补助投资500亿元,建成大中小型项目超过1.3万个,以缩小南北疆的发展差距。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国际政治因素复杂、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在新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2010年,新疆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疆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新疆社会科学院《2009—2010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社会蓝皮书》指出,必须把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切实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为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构筑牢固的群众基础。新疆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发展与稳定已成为密切相连的两个要素。若不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新疆也很难实现真正的稳定。 2010年3月29日至30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借鉴2008年中央曾经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中“一省市帮一重灾市县”的方式,19个省市提出了“对口支援”的援疆模式,决心举全国之力援新疆发展。 与此前的援疆相比,新一轮的对口援疆战略是干部、人才、技术、教育、管理、资金的全面援疆。支援新疆发展的省市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和深圳,共19个,受援方由过去的新疆10个地州56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个师,扩大到新疆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受惠面遍及天山南北。其广度、深度和对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影响前所未有,其起点高、力度大、意义深远,受到世界瞩目。 党中央、国务院对援疆工作高度重视。2010年5月、2014年5月、2020年9月,三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2010—2023年,9次召开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 对于新疆,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20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就到过新疆。在浙江任主要领导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对口支援和田地区建设、推进浙江和新疆两省区经济合作,同新疆同志多次交流探讨。2003年,习近平同志带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8天,在天山南北都留下了足迹。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于2009年到新疆考察5天,身影留在了巴音郭楞、喀什、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的农村、企业、社区、学校。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新疆考察和调研。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赴新疆考察,到新疆大学、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等走访、调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新疆工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新疆考察,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审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审视、谋划、部署新疆工作,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治疆方略。 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对象也做了调整,浙江从原来的对口支援和田地区三县一市调整为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八县一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浙江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性,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为适应新一轮综合性援疆工作要求,浙江建立了“1+2”的援疆领导机构,“1”即省委、省政府建立省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2”即后方的省对口办和前方的援疆指挥部。省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指导、协调全省援疆工作,办公室(简称省对口办)设在省发展改革委,承担省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省援疆指挥部以及各市10个市指挥部形成“1+10”的前方工作体系。后方的省对口办和前方的援疆指挥部密切联系、紧密配合。各市分别参照这一组织指挥体系建立各自的领导机构,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有关部门牵头负责,形成了全省援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保障体系。 对于援疆,浙江人发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雷厉风行,浙江各市无不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第一时间发动援疆志愿人员,第一时间组建起“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指挥部”,第一时间踏上奔赴新疆的路途。这真正诠释了什么叫“浙江速度”和“浙江精神”。 自郑吉立功西域,成为首任西域都护以来,浙江人便为西域、为新疆的巩固、稳定和发展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从某种角度而言,浙江也代表了内地与西域、与新疆的血肉联系。自党中央把西部开发、对口援疆作为大国构想付诸实践,浙江与新疆因此成为结对省份。11批援疆干部秉持“忠诚报国,团结实干,倾情援疆,勇立潮头”的精神,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努力和包括浙江在内的19个省市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新疆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完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用一本书,把古往今来浙江与新疆相关联的人物和事件予以贯通,形成一个文本,从而反映历代与西域、与新疆有关的浙江人的面貌,是笔者的一个心愿。 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只有书写“人”在历史长河和现实中的所思所想所为,才能表现时代的巨变。也是这个原因,《援疆志》以“人”为志,将历史事件的复杂面貌和中央大政方针的实施过程转化成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内在应和“志”的精神主旨,由此更好地书写“人”的牺牲与奉献、光荣和梦想。 为创作《援疆志》,笔者钩沉了历代跟西域有关的古籍,从2022年末至2023年3月,五越天山,三渡瀚海,先后前往乌鲁木齐、石河子、塔城、伊犁、哈密、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寻访历代浙江人留下的踪迹,接下来又赶赴浙江杭州、宁波、温州、金华、湖州、绍兴、台州等地采访,走遍了新疆、浙江的绝大多数地方,寻找了郑吉在新疆的遗踪,根据骆宾王的诗作,重赴他在新疆的诗歌之路,去了浙江茅盾、艾青在乌镇、义乌的故里;寻访了20世纪50年代进疆的500多名浙江青年中10多位在世者、20多位浙籍政商人士,采访了70多位援疆的参与者,从数千分钟采访录音、3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中,选取自西汉郑吉以来35位浙籍人士的故事,用文学手法,细腻地描写了他们与历史和时代的关系,以图通过从古至今浙籍人士在新疆的事功,书写新疆与内地自古一体、血肉相连的历史样本和田野个案。这是笔者一次艰难却充满激情的采写,我希望,这个“中国样本”能因其独特性,而具有别样的价值和意义。 《援疆志》以人为志,致敬时代! 钩沉疆浙千古情,谱写援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