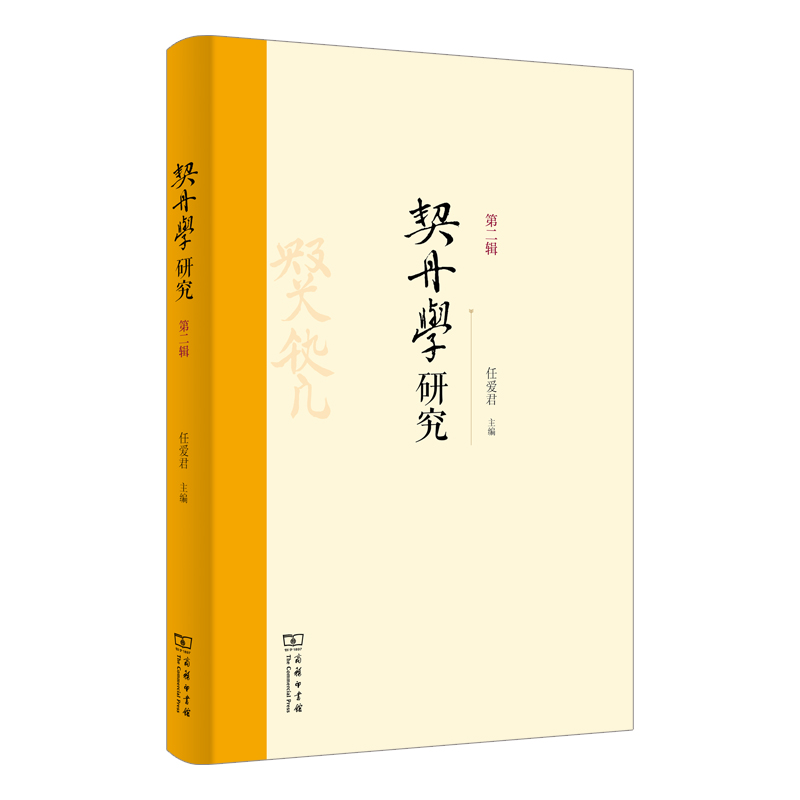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78.90
折扣购买: 契丹学研究(第二辑)
ISBN: 9787100215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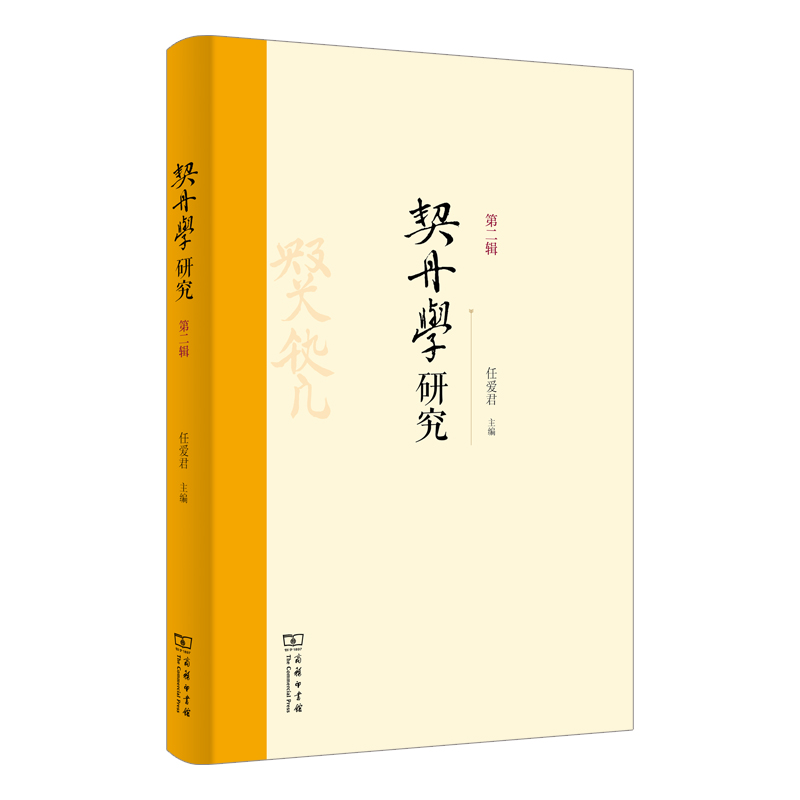
任爱君,赤峰学院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专门史及契丹辽文化。代表性论文有《契丹四楼源流说》(《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契丹“盐池宴”、“诸弟之乱”与夷离堇任期问题》(《史学集刊》2007年第4期)、《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建筑群落的属性及其功能》(《北方文物》2010年第4期)等论文百余篇;代表著作有《辽朝史稿》、《什么是契丹辽文化》等2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契丹及契丹人》等各级各类项目30余项。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草原地区形成权力真空,唐王朝(618—907)的崩溃更是为东北地区契丹—辽王朝(907—1125)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东北地区是其肇兴之地,契丹人以其南部的辽河为名,定国号为“辽”,此后迅速攻克邻邦渤海a,征服蒙古草原(monglia)。938年,在华北辽朝统治者从中原政权(nothern Chinese state)后晋(勿与后来的女真建立的金朝相混)手中攫取了现今北京地区的燕云十六州。947年,在短暂南侵并占据后晋都城开封三个月后,辽帝决意北归,把疆域限制在燕云十六州及其以北地区。随着中原王朝—大宋(960—1279)的建立,其统治者一直致力于统一大业,因而燕云十六州也就成为二者争议的焦点。 1005年,数十年的疆界纷争后,辽宋缔结和约。《澶渊之盟》明确划分了辽宋双方的疆界,并规定宋每年向辽输送大量岁币。这使双方在整个11世纪,除了在1042年以及1074—1076年间爆发过短暂冲突外,保持了长达百余年之久的和平局面。北南双方辽宋之间以兄弟之国的平等方式结约,也就意味着一南一北两个天子并存于天下已获认可,这与中原王朝的传统秩序是相违背的。辽的其他邻邦,如高丽和以今甘宁二地为基盘的西夏(1032—1227)也都最终正式承认了辽的宗主国地位,每岁向其纳贡。辽在宋岁输入大量金银和贡物的基础上,通过陆路与西方世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贸易。契丹语中“Khitan(契丹)”一词在突厥语中作“Khitai(契丹)”,该词恰是以这种贸易方式,在欧亚大陆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 辽朝最基本的特征即为南北二元体制。北面官系统管理契丹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事务,南面官系统管理汉、渤海等定居民众的事务。终辽一世,契丹人一直保持着游牧属性,辽帝终年都在四时捺钵和五京之间巡狩,其中枢机构始终相随左右。虽然迄今为止契丹大小字仍未被完全释读,但其仍能体现契丹人的文化特质。此外,随着一些考古文物在中国不断被发掘出土,契丹人的物质文化特质也逐渐显现b。 12世纪初,随着辽帝皇权旁落以及治下经济衰败,东北地区的属部—女真乘势而起反抗辽的统治。1114年,契丹与女真全面开战,女真大获全胜,遂于1115年建立了女真金朝(1115—1234),继之于1125年取代了辽的统治。在辽分崩离析前夕,耶律大石迫于女真势力之强,向西逃亡,从而开启了西辽王朝的纪元。 在中国西部,840年回鹘汗国的崩溃拉开了蒙古草原游牧民族衰落的序幕。随后,被击溃的回鹘人迁徙至新疆一带,在今吐鲁番(Turfan)地区建立了高昌王国(约850—1250)。打败回鹘人的黠戛斯(Qyrghyz)并没有在蒙古草原建立帝国的野心。因而10世纪时,他们已返回故土叶尼塞河(Yenisei)流域。也正因如此,辽王朝轻而易举便成为了蒙古草原的统治者。契丹人的兴起迫使突厥诸部西迁中东地区(Middle east),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祖先也被带至了蒙古草原。924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了鄂尔浑(Orkhon)地区,遂提议高昌回鹘迁回其在蒙古草原的故地。虽然回鹘人并未接受,但终辽一世,高昌回鹘一直都是辽的忠实藩属。 在更西的伊斯兰东部世界,随着9世纪中叶以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地位(Caliphate)的衰弱,伊朗东部(eastern Iran)和河中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独立的政权。其中,以不花剌为中心的萨曼王朝(Sāmānids,875—999)对草原政治秩序(steppe politics)的形成意义非凡。萨曼人不仅将伊斯兰世界的疆域拓展至草原地区,还常常从草原上掠夺突厥人为奴,并逐渐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此外,由于大力倡导传教活动,加之萨曼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威信,整个突厥部落在其治下逐渐伊斯兰化。10世纪中叶,统治喀什噶尔(Kashgar)和八拉沙衮(Balāsghūn)的突厥部族,也即现代文献中提到的喀喇汗王朝已皈依伊斯兰教。不久,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便开始向穆斯林世界扩张。999年,他们从萨曼人手中夺取了河中地区,与此同时,由萨曼王朝军中奴隶建立起来的另一个皈依穆斯林的突厥政权—哥疾宁王朝(Ghaznawids,994—1186)占领了萨曼王朝的西部疆域。 喀喇汗与哥疾宁之间的战争,加之10世纪契丹对蒙古草原的征服和1032年西夏的建立引发的人口迁徙,这些均促使了塞尔柱突厥王朝(Saljūq Turks)的兴起。塞尔柱人系出突厥乌古斯部落联盟(Oghuz),于10世纪末皈依伊斯兰教。1040年,塞尔柱在木鹿(Marw)附近的旦旦坎(Dandānqān)打败了哥疾宁,并再度西征,于1055年进驻巴格达(Baghdad)。他们在此推翻了白益王朝(Dailami Byid dynasty,935—1055),自封苏丹,成为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Caliphs)背后真正的操控者。1070年,塞尔柱人攻占了拜占庭(Byzantium)治下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随后他们又将目光重新投向了中亚地区。与此同时,自11世纪中叶以后,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汗国(western khanate)以河中地区为中心,东部汗国(eastern khanate)控制着怛逻斯、白水城、石城、费尔干纳(Fergana)东部和七河地区(Semirechye)。1089年,塞尔柱人接管了不花剌和撒马尔罕(Samarqand),西部汗国遂成为其附庸。直至1103年,东部汗国也一直臣服于塞尔柱王朝。 11世纪末,随着苏丹马利克沙(Malikshāh)以及名臣尼扎姆·穆勒克(Ni?ām al-Mulk)维齐尔的相继离世,塞尔柱王朝也祸起萧墙陷入诸子纷争。因此,西喀喇汗国力图夺回塞尔柱在河中地区的统治权。1102年,喀喇汗王朝的首领卡迪尔汗(Qadr Khan)为马利克沙之子桑贾尔(Sanjar,卒于1157)所败。桑贾尔时任塞尔柱王朝东部地区的维齐尔,后于1118年成为了其最高统治者苏丹。12世纪30年代,桑贾尔以相似的借口再次染指河中地区,随后任命侄子马赫穆德二世(Ma?mūd II,1132—1141)统治西喀喇汗国。塞尔柱的东部藩属花剌子模沙阿即思(Ats?z Khwārazm Shāh)也是塞尔柱的心腹之患。阿即思家族自1097年便控制着富庶且自治的花剌子模行省。由于阿即思自立的野心越来越大,与塞尔柱的关系也于1130年代日益恶化,终至双方在1138—1140年公开对决,后以桑贾尔的胜利告终。尽管其疆域东部遭到种种挑战,但塞尔柱王朝对东部的控制力依然比西部要强大得多,因为疆域西部的武将以及阿塔伯克(atabegs)把持着地方大权,从而架空了塞尔柱的官方机构。 恰是中亚世界的动荡与分裂,使得耶律大石能够率领辽朝遗众在此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首部契丹学研究辑刊——展现契丹学前沿成果,彰显绝学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