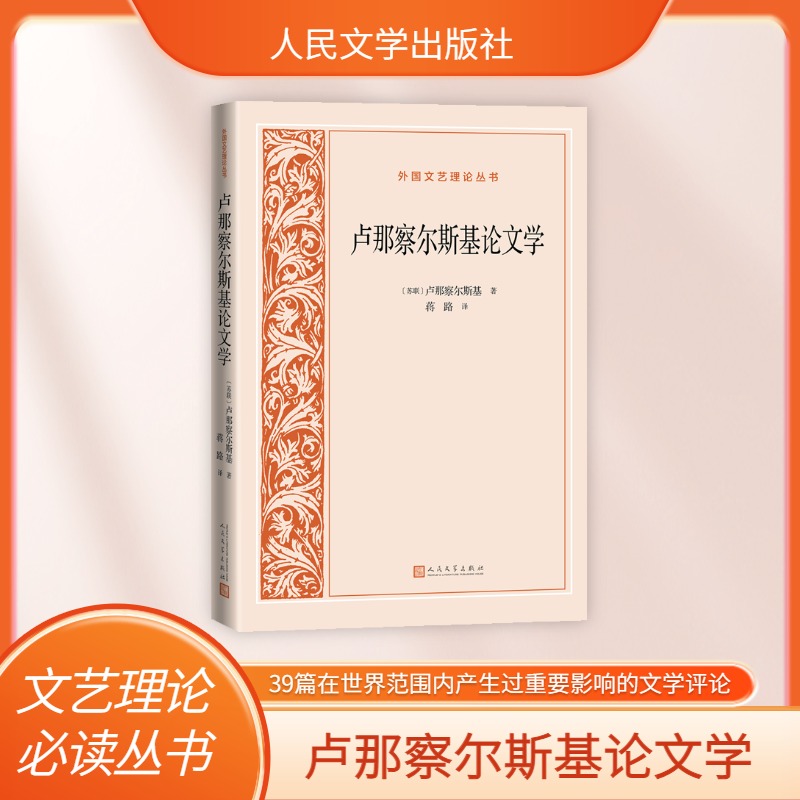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2.30
折扣购买: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ISBN: 9787020167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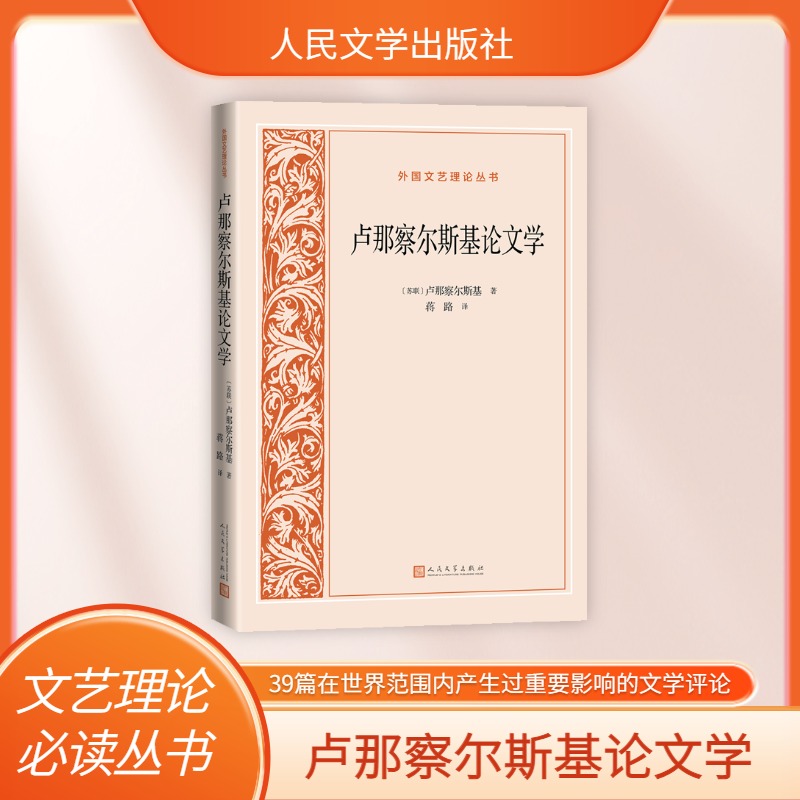
作者: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剧作家。一生著述丰富,门类繁多,涉及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外交、建筑、文艺等。在文艺领域,他不仅创作有诗歌和剧本,翻译过作品,而且撰写了两千多篇文艺评论类文章,涵盖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美学等。 译者:蒋路(1920—2002),1979年起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88年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荣获文化部出版局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俄国文史漫笔》、《俄国文史采微》、《蒋路文存》(两卷),译著《文学回忆录》、《星》、《怎么办?》、《俄国文学史》(三卷)、《论文学》、《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巴纳耶娃回忆录》等。曾获韬奋出版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节选) 卢那察尔斯基一生的著作,门类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了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外交、宗教、建筑、文艺等各个方面。在文艺领域内,撇开他的二十八个剧本、一些诗作和翻译不谈,仅以论著而言,他就在三十年间先后写了有关本国和西方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及美学的文章共约两千种,其中论述托尔斯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各达三十来篇。他不是坐而论道的评论家。他基本上是一个实践家;行有余力,而后为文,或者说,为文是他的行动的一部分。他的著作大都是在地下工作的余暇,在监狱里,在流放地,在亡命国外的时候写成的;十月革命以后,则是在内战的烽火中,在繁忙的国务和社会活动之余,利用周末休假的零碎时光,更多的是牺牲正常的睡眠和休息,临时急就的。在他的作品中,只有少数文章,而且是短篇文章,才是他亲手写成,其余都是由他口述,请他的亲人(十月革命前)或速记员(革命后)笔录的,其中一部分在发表前甚至未经他本人过目。这些著作价值高低不一。有的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动的现实意义;有的只适用于当时,事过境迁之后已经失效;还有的则即使在当时来说也并不正确。同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活动的记录一样,他的文艺观也经历过一条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 俄国三个主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当中,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几年已经停止他的理论活动;沃罗夫斯基的文学工作鼎盛时期是一九○七年至一九一二年,革命后他几乎完全搁笔,加之早在一九二三年就不幸殉难了;只有卢那察尔斯基一人得以亲身参加苏联文艺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积下丰富的经验,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卢那察尔斯基“追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巨人的脚印”,力求把文学现象摆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摆在具体的时间和社会环境之内加以考察,同时用阶级斗争作为基本的指针,因而他能在看似迷离混沌的复杂情势中发现规律性,比较确切地说明作家和作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卢那察尔斯基强调社会和阶级对文学的制约,却并不把这种制约加以绝对化。首先,就创作过程来说,文学是客体和主体相融合的结晶。其次,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不但处于青春期的资产阶级的伟大作家莫里哀和歌德有时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接近当时全民的或全人类的理想,而且人类本来有一些共同的情趣,诸如自然欣赏、爱情陶醉之类。 在有关创作方法的论述中,卢那察尔斯基仍然保持着他的强烈的现实感,同时又显出了他的广阔的视野和雄大的气魄。他赞扬那些“从现实出发,笔锋所及,处处回答重大的迫切问题”的作家,但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作家反映生活的途径的多样性,所以现实主义应该“是一个广泛的艺术范畴”。只要一种艺术形式“具有很大的、内在的、现实主义的确定性,它在外表上无论怎样不像真实都可以”。 在处理文学遗产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历来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关键是,卢那察尔斯基不但善于发现矛盾,并且善于总观全局,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所以他对遗产既能毫不留情地批判,又能理直气壮地继承。 对作品艺术性的评价是二十年代苏联文艺学中最薄弱的一环,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也有不少补偏救弊的劳绩。他深刻地缕述和分析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艺术成就,有时更将同时代的或创作上相近或相反的几个作家并列在一起,经过对照,使各人的特色益发显豁。 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也很值得一提。他的文学论著,有时信笔铺排,汪洋恣肆,有时却大题小做,用寥寥数千字概括作家及其时代的基本面貌(《安·巴·契诃夫在我们今天》《萧索时期的天才》《日出和日落之前》等)。不管是长篇还是短论,大都写得富有战斗热情,而不仅仅诉诸读者的理智。 总的讲来,正如鲁迅所说,卢那察尔斯基“是革命者,也是艺术家、批评家”,他“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 ——蒋路 托尔斯泰出身于一个很顽固的地主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个很顽固的地主。可以说,八十年代以前,虽然他也经常有他的传记作者们所讲的各种内心的裂缝,但他主要还是个有阶级自觉的贵族。当他初次写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向全俄国放出异彩的时候,涅克拉索夫邀请他到自己主持编务的那个著名的杂志即《现代人》。社来,把他介绍给俄国的优秀人物、以伟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先驱们。但是托尔斯泰为了刺激他们,竟然谈起一些黑帮的话题、十足的贵族的话题,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位尖酸刻薄的军官当时列夫·托尔斯泰在担任军职。,对待他们听来是如此离奇的、反动透顶的意见才好。事后托尔斯泰却说,涅克拉索夫使得他纡尊降贵,给他介绍了几个浑身臭虫气味的正教中学毕业生,不过他让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本分。这是属于两个绝对不同的、无法调和的阶级的人们之间的冲突。 这段时间,托尔斯泰对资产阶级、小市民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充满着同他顽固的绅士本性完全一致的阶级仇恨。在农奴制时代,他是乡绅,是仓廪充足的庄园主、一定数量的农奴的主人;农奴制废除以后,他又是农民依附的地主。他喜欢旧制度,喜欢这个稳固的、地主农奴主的制度。这个制度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摇摇欲坠,因此他憎恨资本主义关系。他去过西方,从游历中得到了极其阴郁的印象。他不仅全盘否定他所看见的、他觉得是真正市侩气的、不讲道义和不信上帝的欧洲,他还否定了这个欧洲的一切前途。他很早——还在六十年代——便开始说,有关进步的流言全都一钱不值。他说,这些进步只是造成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认为科学技术仿佛能带来幸福的一切言论,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科学技术只替富人服务,使他们能够剥削别人。其结果,我们看到一方面有被剥削者,另一方面又有一帮剥削者,他们害怕人家对自己造反,他们在他们所压迫的群众面前发抖,虽然群众受尽摧残,完全不像人的样子了。 托尔斯泰对西方和西方制度的看法,其实质大体就是这样。可是托尔斯泰本人究竟往何处去,他拿谁来同西方抗衡呢?早在史诗《战争与和平》里,在这篇俄国贵族的《伊利亚特》里,我们便发现他把他的阶级的自我意识发挥到了极致。他相信上层贵族是人类中最稳固、最优秀、蕴涵最丰富的一个阶级。他对此深信不疑。有人对他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里只看到俄国贵族大检阅,因为书中没有写农奴,难道这些贵族就不鞭打自己的农奴,不折磨他们吗?托尔斯泰回答道:第一,鞭打和折磨是被夸大了;第二,我不想写这些。他很直率地干脆说,他不愿描述贵族的这些消极面。托尔斯泰在《略谈〈战争与和平〉一书》这篇文章里写道: 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中看不到的那种时代的性质是什么,——那就是农奴制的祸害、活埋妻子、鞭打成年的儿子、萨尔特契哈,以及诸如此类;我们心里都记得那个时代具有这种性质,但我并不认为它是切合实际的,因此我不愿意表现它。 他只描述处于全盛时期的贵族,他疯狂地爱他们,他想使这群贵族永垂不朽。 贵族在其发展中的某个时期,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