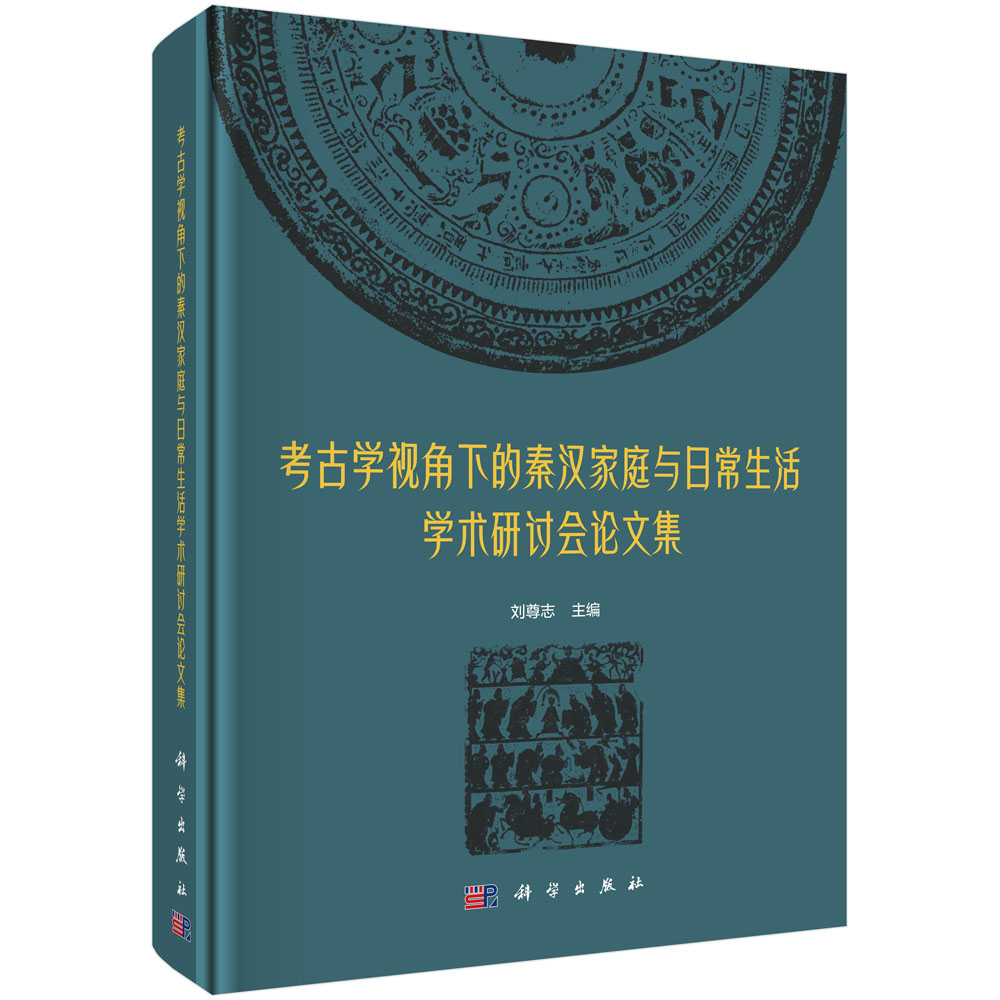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56.40
折扣购买: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精)
ISBN: 9787030625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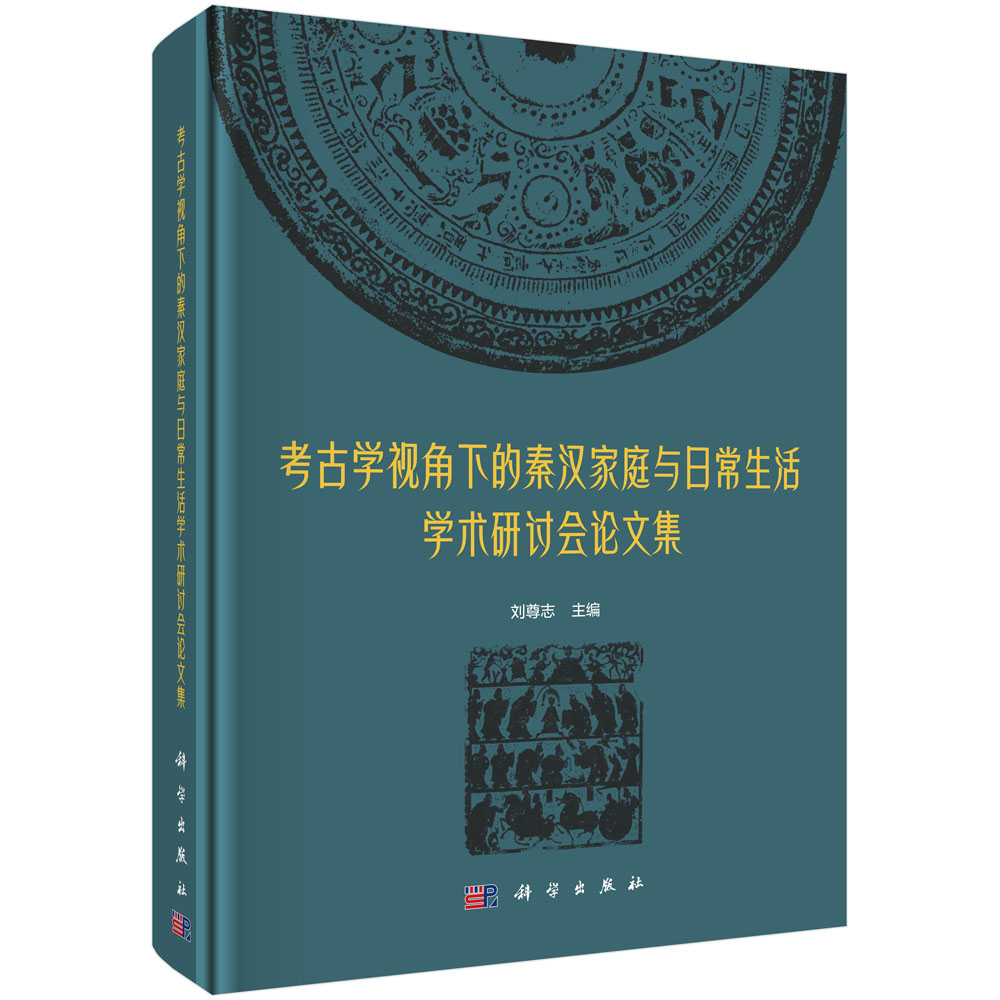
一 家庭与社会、日常生活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及其初步思考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
“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一般认为是指人类社会的生活系统,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上的社会生活,则是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1]。换言之,狭义的社会生活是指广义的社会生活中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应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
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即狭义上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从研究的实践看,社会生活的内涵是清楚的,但其外延往往因研究者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它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难以截然分开。但无论如何,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在史学界,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而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史学流派。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国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即1929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创办、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以及后来一系列研究成果,对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德国和意大利兴起了“日常生活史学”研究,甚至被称为史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2],并对其他国家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我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可以上溯到1911年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的出版。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缓慢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1986年10月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社会生活是其重要的讨论议题)在南开大学的召开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十卷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等为标志,我国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走向全面复兴,并且学术成果累累,逐步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一个热点和新的生长点。[1]在当今历史学界,社会生活史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学科分支。
在我国考古学界,“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考古学开始步入转型的阶段。所谓转型,就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心由前述的以年代学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占主导地位,逐渐向全面研究古代社会的方面转变”[2]。既然是全面研究古代社会,自然包括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新世纪以来,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学术理念被广泛接受。在关注和研究物质遗存本身的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遗存所反映的社会、人和人的活动等方面。
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之下,这里提出“社会生活的考古学”这一命题,并就相关问题略作思考和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近百年来,史学界关于社会生活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初主要是就社会风俗制度史等进行研究,同时也开始使用“社会生活”的概念[3];后来,又出现了“日常生活”的概念及其使用[4],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并称之为“社会生活史”;新世纪以来,有不少历史学者更倾向于使用“日常生活史”的概念和提法[5]。在笔者看来,尽管“社会生活”主要指的是“社会日常生活”,但使用“社会生活”的概念似乎更有利于理论的思考、研究的实践和体系的建设。因此,这里仍然使用“社会生活”这一概念,与社会史研究中的“日常生活”大致相对应。
二
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学科,其性质和任务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与文献史学一起构成古代史研究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众所周知,“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1]。就史前考古学来说,“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中,毫无疑问地包括史前时代的社会生活。就历史考古学来说,更是“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2]。因此,古代社会生活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毫无疑问的。
实际上,自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发现、研究和揭示,试举数例[3]。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史前彩陶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用陶器及其类型和特征。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和一系列发现,从多个侧面展现了当时人们从居住、储藏、饮食、车马、文字到祭祀、埋葬等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丧葬习俗。1954—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比较完整地揭露出一处仰韶文化的聚落,比较清晰地再现了6000多年前氏族公社时期一个氏族聚落的布局、结构、内涵以及从居住、饮食、人体装饰、娱乐等日常生活到丧葬活动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56年以来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量有关社会生活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当时长安城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各种珍贵的实物资料。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研究提供新的实物资料。也正是基于丰富多样、与日俱增的考古发现及近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史前时代到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考古学研究,并且不断取得成果,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更是成果丰硕。当然,既往的很多研究虽然与古代社会生活直接相关,但当时更多的是着眼于物质文化而不是社会生活,此不赘述。
毋庸讳言,囿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长期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更缺乏理论的思考和体系化建设。正如我国古代史研究长期关注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五朵金花”一样,我国考古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注的重点是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和分期、史前及夏商文化谱系构建、古史重建、物质文化史研究等方面——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转型”[1]。古代社会复原研究自然包括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很多考古学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古代的社会生活,如饮食生活、服饰生活、车马出行、文体娱乐活动等。譬如,黄展岳利用大量考古资料,对汉代人的饮食生活进行复原和勾勒[2]。又如,杨泓的《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中,根据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考察古代日常生活的16篇短文,构成了该书的“生活”篇[3];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4],虽然名为“物质文化”,但实际上对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明而系统的考察。再如,汉代车马的研究,无疑属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范畴,但同样也是社会生活研究的范畴,练春海的《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其内容已经不仅仅是从汉画图像上对汉代车马的研究,而是从车容扩展到车仪及卤簿等,实际上是车马形象、车马出行及其礼仪的研究,更接近社会生活史了[5]。也就是说,迄今很多物质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物质文化本身,而是开始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解读和阐释。当然,以往的研究仍然主要着眼于物质文化而非社会生活。尽管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但物质文化研究并不等同于社会生活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物质文化研究的长期积累,为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史学界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兴未艾、考古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考古学研究逐步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转型、“透物见人”的学术理念被广泛接受的今天,提出并系统开展“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或者简称为“社会生活考古”,应该是时候了。这不仅对于进一步完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充分发挥考古学的史学功能、更好地实现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讲好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等,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