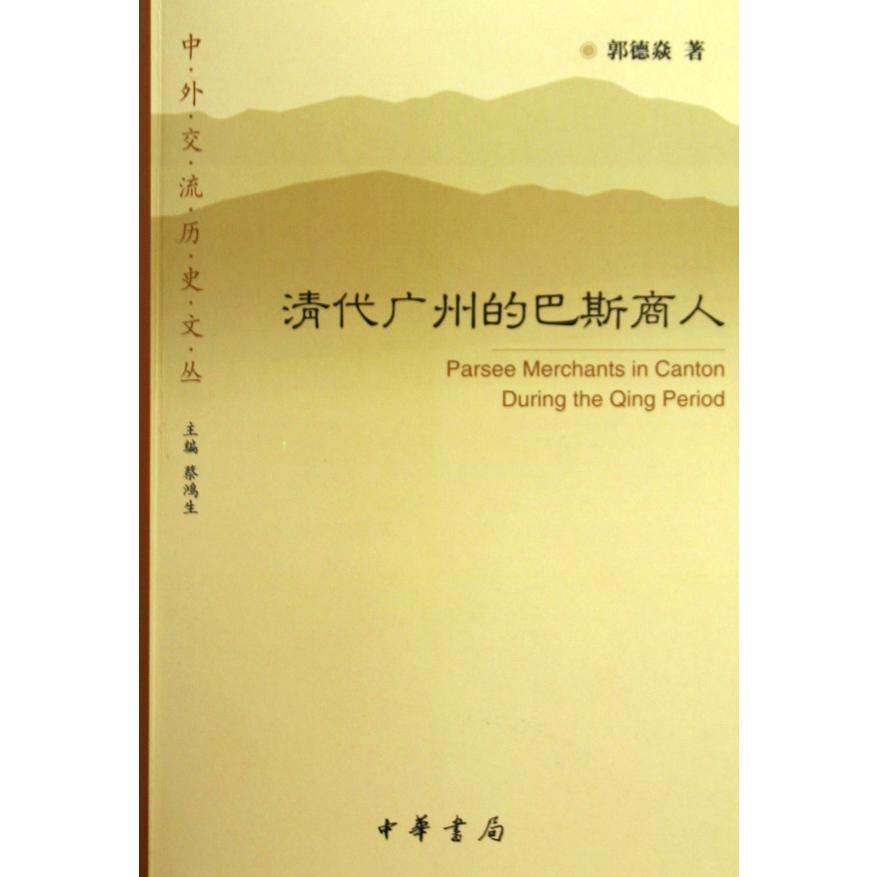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22.10
折扣购买: 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ISBN: 7101046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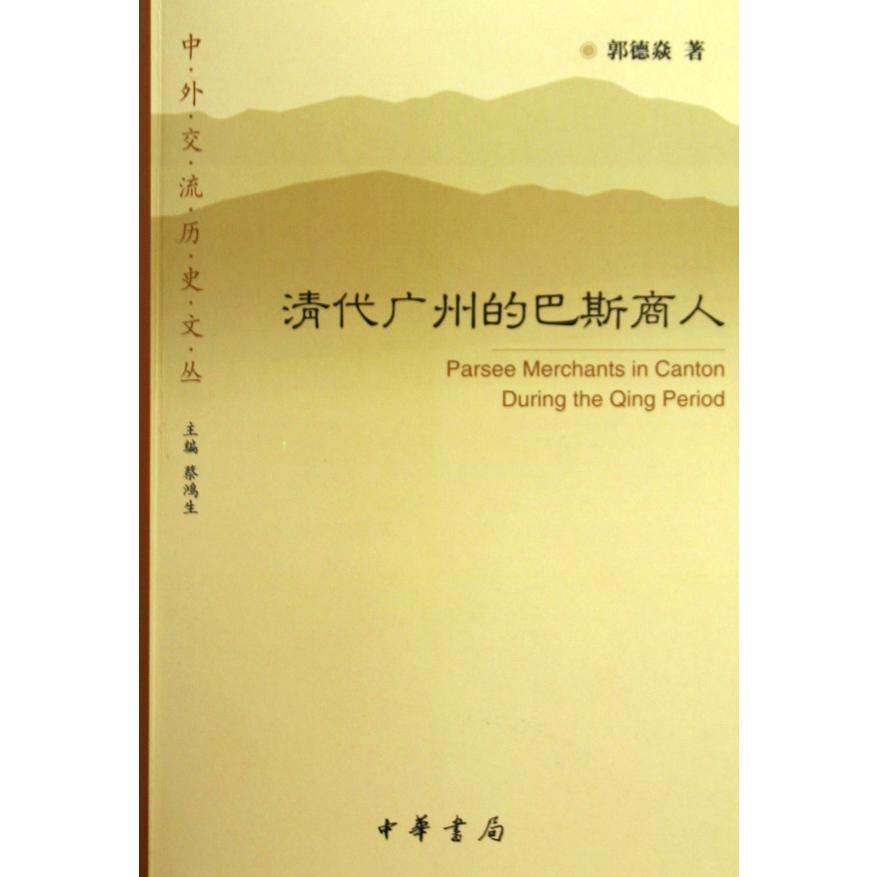
印度王公和土著的热情,使巴斯人得以生存。但这批兼难民和移民双重身份的巴斯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能够发生质的变化,却与欧洲人的到来紧密相关。本来,欧洲人到印度后,所有土著人的机遇是相等的,巴斯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土著人保持敌对和守旧时,他们却率先由浅入深地逐步“欧化”了。 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加强了世界范围的联系,但也是充满血腥的近代殖民掠夺和殖民瓜分的开始,它改变了印度的命运,也改变了东方的命运。最早献身这种探险活动的是葡P24萄牙人。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非洲西北角的休达港,1432年占领亚速儿群岛。1486年迪亚士抵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完成了航海史上的重要历程。1497—1499年,达·伽马沿着迪亚士航行的路线绕过好望角,由一位阿拉伯海员领航,迅速抵达印度。1502—1503年、1524年,达·伽马又第二次和第三次到达印度。从1505年起,葡萄牙放弃了每年派遣一次远征军的政策,在印度任命一位任期三年的副王,之后又设总督衔,以印度为据点四处扩张。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绝对控制了美丽的东方”。 但在17世纪,葡萄牙人的印度殖民地就逐一落到了荷兰人之手。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将注意力放在香料群岛,1641年占领马六甲,掌握了对远东的贸易。 之后,英国、丹麦(1616年始)、法国(1664年始)、奥地利(1723年始)、瑞典(1733年始)等欧洲国家先后在印度建立据点。印度成为欧洲人的大会堂。 欧洲人给印度带来近代文明,但欧洲人也带来了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得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因此,欧洲人与当地土著之间长时期的敌对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与众不同的是,作为印度“客籍人”的巴斯人却识时务,抛开一切包袱,开始了“欧化”的进程。这一过程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并持续到18世纪。如果说第一次社会生活的改变使巴斯人能够生存于印度,那么,第二次改变则使之崛起于印P25度,并走向世界。 “欧化”的第一步,是巴斯人与欧洲人进行简单的商务合作。从16世纪起,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在印度的各港口城市建立商业据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苏拉特,该地成为莫卧儿帝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中心。苏拉特的欧洲商业公司将巴斯人从印度其他地方吸引过来,这是巴斯人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提升的开端。他们非常善于同欧洲人打交道,适应欧洲人的习惯和要求,相互间建立起了信任关系。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均雇巴斯人作为他们的经纪人。具有经商天赋的巴斯人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离开了巴斯人,欧洲人无法开展商业业务。17世纪是荷兰人的天下,这时苏拉特荷兰馆中作为代理的著名巴斯人有曼车治·塞斯(Mancherji Seth)和那沙湾治·阔希亚(Nasarvanji Kohiyar)等。到了17、18世纪,苏拉特成为巴斯人最大的聚居地。1774年,据一位荷兰人估计,当地有十万巴斯人,占人口总数的十五分之一,他们精于商业,与欧洲人往来时比较灵活自如。 “欧化”的第二步,是巴斯人在生活习俗上学习欧洲。巴斯人的活力表现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不受社会和宗教禁忌的束缚。巴斯学者卡拉卡在《巴斯人史》中这样写道: 种姓制度、固有的风俗习惯往往成为民族发展的障碍,但是巴斯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思想束缚。当欧洲人到来时,他们抓住从未曾有过的商机。在葡萄牙、荷兰、法国人的商馆内,成为最主要的当地代理,成为欧洲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中介。这方面的商业机遇和空间,他们及时抓住了,毫不犹豫。 巴斯人在印度人当中,属于第一批生活方式走向近代化的民族。在印度,巴斯人也是第一个被英国模式(English style)所P26吸引的民族。他们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同,食猪肉、牛肉,与英人共餐,畅饮马德拉(Madeira)酒,建筑和服饰逐步英国化,普遍学英语。生活习俗上不固步自封,自然增强了与欧洲人来往的亲和力。 “欧化”的第三步,也是深层次的一步,是巴斯人接受欧式教育。这是欧化的重要标志,这一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与欧洲人在商业上打交道,使巴斯人意识到接受西方教育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1723年,第一位巴斯人劳罗治·那斯达姆治(Naorozji Rastamji)到英国,也是第一位到英国的印度人。之后,旅欧的巴斯人日益增加,有的经商,有的接受高等教育。从19世纪20年代起,在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影响下,印度陆续建立英国式教育制度。19世纪初,一些欧亚混血儿和退役老兵开办了语言学校,就读者多系巴斯人。1827年,包括巴斯入在内的孟买商人集资创办了爱尔纷斯顿学院,教授欧洲的语言、文学、科学和道德哲学。1840年,爱尔纷斯顿学院与一所学校合并为爱尔纷斯顿研究院,而入学者大多为巴斯子弟。当地耶稣会士创办的圣沙勿略学校和学院、传教士办的学校也以巴斯人居多。“事实上,可以说,巴斯人从国家和其他机构提供的教育中得到的益处,远较其邻人为多。”1884年,留学英国的巴斯人占印度留学生总数的24%,而穆斯林只占20%。 巴斯人的欧化,清代文献有明确的记载,《游历笔记》这样记述孟买的巴斯人: 在彼遇一波斯人,其父为该处官宪。邀至其家,款洽备至。自言曾至欧洲肄业,于西语、西文无不精熟,装束一如西人。其女亦皮鞋、手套,惟衣服则仍为波装。所居之屋高四层,华丽无比。 巴斯人得以接受欧式教育,与英国的殖民政策有关。1813P27年英国的有关法令规定:从东印度公司领地的盈余赋税中,每年至少应拨出10万卢比,用以复兴和促进文艺,鼓励印度本地知识分子在英属印度的居民中宣传和介绍各种科学知识。1824年的一份文书宣布:政府的目的不是讲授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学术,而是讲授“有用的学术”——换言之,也就是西方知识。用什么语言讲授也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梵语和波斯语自然都不合适。教印度人阅读英语书籍最实用。本廷克认为,“英语”是“一切改进措施的关键”。麦考利在一份讽刺性的备忘录中,嘲笑一般关于印度语言和东方学术的主张,他认为教印度人民学习英语的结果可能使印度发生一次文艺复兴:“印度人民需要我们的语言。”因此,总督在1835年作出这样的决定:“英国政府的伟大目标应该是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提倡欧洲文艺和科学;所拨出的一切教育经费最好完全用在英语教育上。”在以后十年中,政府任用公职人员时决定优先考虑懂得英语的候选人。用麦考利的话来说,这是“可以在我们和我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方面,却是英国人”。 “欧化”之后,巴斯人的商业精神与欧洲人十分吻合。他们的商业品质,欧人形容之为“慷慨、诚实、信用”。《海国图志》云“其人贵白头回,惟利是图”,“恒时买卖获益,亦好布施,厚周济,故令天下庶民景仰之也”。巴斯人的这种商业形象,与欧洲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十分接近。他们给欧洲人的印象,是十二分的诚实,其中毕哈治·伯拉治·班底(Bhikhaji Beramji Panday)被欧洲官员和商人评为“最忠诚的店主”。 这证明,巴斯人接受的欧式教育完全达到了欧洲人的要求和目的。巴斯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为以后与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长期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