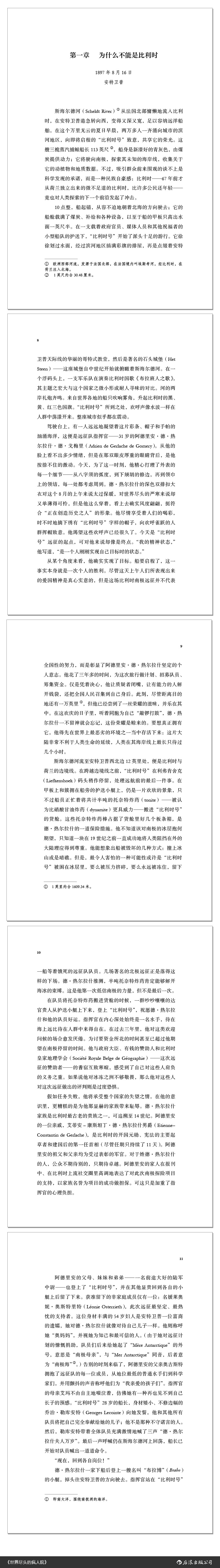出版社: 海峡文艺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世界尽头的疯人院:“比利时号”南极之旅
ISBN: 9787555035367

作者: 朱利安·桑克顿(Julian Sancton),作家、编辑,以文化和旅行书写见长,作品见于《纽约客》《智族GQ》《名利场》《时尚先生》等刊物。桑克顿对所有大洲做过报道,正是在为这本书做研究期间,他首次访问了南极洲。桑克顿在法国度过了童年大部分时间,后在哈佛大学攻读欧洲史,现与伴侣和两个女儿生活在美国纽约州。 译者: 李厚仁(笔名),青年编辑、译者,众多对语言感到亲近的人之一。
1926年1月20日 堪萨斯州莱文沃思 黎明将至,灰蒙蒙的天空被莱文沃思监狱医院的窗户格栅划成一个个小块。看着是个冷冽的早晨。16小时的轮班结束了,年迈的医生精疲力竭;他清理好工作台,向警卫示意,可以送他回牢房了。职责一经移交给正式的监狱医生,他便成了普通犯人——第23118号囚犯。 医生瘫倒在床上。刚刚过去的是很长的一夜。这时候的美国正深陷规模空前的鸦片大流行,入夜后,医院顶层就成了——用医生的话说——“毒品疯人院”。受着戒断之苦的成瘾者号叫着,还想再吸一口。医生的牢房在一幢三层高的砖砌建筑之中,照明良好,配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和自来水。墙上挂着一些精美的刺绣画,是他自己制作的。与他的一些狱友,包括芝加哥黑帮分子“大块头”蒂姆·墨菲(已成为他的朋友和保护人)和后来的杀人如麻、不思悔改的连环杀手卡尔·潘茨拉姆(不会成为他的朋友)相比,医生的牢房条件算是舒适的。不过话说回来,第23118号囚犯的罪过确实是另一种性质的。61岁的他被判犯有欺诈罪,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涉及某家石油公司股份的金字塔骗局。这是他服刑的第3年,刑期共14年——比对类似罪行的惩罚严厉得多,却与他的恶名十分相称。 在他记忆模糊的青年时代,远在他失宠沦落之前,医生曾是一名著名的极地探险家。他声称自己在1908年征服了北极点,一下被捧为国民英雄——直到人们怀疑,这件壮举(还有其他几件)是他杜撰的。“他将永远位居世界上最伟大的骗子之列,”《纽约时报》将如是断言,“他索要永垂不朽应是凭着这一点,而不是发现北极。” 当天下午,一名警卫告诉他,他有一位访客。自从一年前入狱以来,医生一直拒绝与亲友见面。今天在等他的这个男人,或许是他愿意破例会见的唯一一个人。几乎每一天,他都会想到这位前队友,一个身材魁梧、现年53岁的挪威人。近30年前,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如今回想起来仍令人胆寒的南极探险。挪威人曾是医生在极地探险方面的徒弟,现已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南极真正的征服者。他那些屡屡登44上新闻头条的事迹,以及他在完成这些壮举时所表现出来的轻松,赋予了他一种近乎神话的气质。为了一系列国际巡回讲座,他走遍美国,但是特意留出了时间来拜访昔日导师。 功绩显赫的探险家要与莱文沃思最出名的囚犯见面的消息不胫而走。没过几分钟,记者便一窝蜂地赶到了监狱。对名誉扫地的医生公开表示支持的举动,可能危及挪威人自己的名声。不过,这次访问的目的并不只是对一位处在危难中的老朋友表示同情。多年来,他一门心思地投入夺取地球上最令人垂涎的地理发现大奖的竞赛之中,这让他付出了代价。身体里的那团火把他燃尽了。他变得刻薄而偏执,没有几个朋友能像医生那样理解他——在更单纯的年代,当唯一要紧的只有生存的时候,他从医生那里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挪威人感到出于道义,他必须向救了自己一命的人致敬。 自最后一次见面以来,两个男人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一点也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出。监禁生活榨干了医生的活力,一张脸血色全无,青灰色的眼睛没了往日的犀利,曾经浓密的头发稀疏了不少,大鼻子则——如果可能的话——变得更大了。但是在他笑的时候(露出几颗金牙),人们似乎还是能看到他年轻时的影子一闪而过。 挪威人比医生高大不少。他的脸“是棕色的,被极地的冰雪所晒伤,布满深深的皱纹,但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清新活力”,医生后来回忆道。探险家“正处于光荣之巅,我则在刑事谴责的阴沟里……这种印象一开始让我震惊,但很快,往日的友好气氛就消解了一切阻碍。我们就像是兄弟”。 他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不愿放开。为了混淆视听,他们开始讲一种被医生描述为“比利时号混合语”的语言。“比利时号”(Belgica)是他们相遇时乘坐的船,那时他们都处在各自的黄金时代,正要第一次前往南极。科学家、高级船员和普通水手说各种各样的语言——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德语、波兰语、英语、罗马尼亚语和拉丁语,让人想起巴别塔停工之后人类社会的模样。那次航行让两人都见识到寒冷和黑暗是如何蹂躏人类灵魂的。正是在那次远征中,医生开始崇拜太阳。那时,他也曾沦为囚犯,只不过困住他的不是铁栅栏和锁,而是无边无际的冰原。那时,他也曾在夜里听到尖叫。 第一章 为什么不能是比利时 1897年8月16日 安特卫普 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从法国北部慵懒地流入比利时,在安特卫普港急转向西,变得又深又宽,足以容纳远洋船舶。在这个万里无云的夏日早晨,两万多人一齐涌向城市的滨河地区,向即将启程的“比利时号”致意,共享它的荣光。这艘三桅蒸汽捕鲸船长113英尺,船身是新漆好的青灰色,由煤炭提供动力;它将驶向南极,探索其未知的海岸线,收集关于它的动植物和地质数据。不过,吸引群众前来围观的谈不上是科学发现的承诺,而是一种民族自豪感:比利时——67年前才从荷兰独立出来的微不足道的比利时,比许多公民还年轻——竟也对人类探索的下一个前沿发起了冲击。 10点整,船起锚,从容不迫地朝着北海的方向驶去;它的船舱载满了煤炭、补给和各种设备,以至于船的甲板只高出水面一英尺半。在一支载着政府官员、媒体人员和其他祝福者的小型船队的护送下,“比利时号”开始了派头十足的游行。它徐徐划过水面,经过滨河地区插满彩旗的排屋,再是点缀着安特卫普天际线的华丽的哥特式教堂,然后是著名的石头城堡(Het Steen)——这座城堡自中世纪开始就俯瞰着斯海尔德河。在一个浮码头上,一支军乐队在演奏比利时国歌《布拉班人之歌》,其主题之宏大与这个国家之微小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河的两岸礼炮齐鸣。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吹响雾角,升起比利时的黑、黄、红三色国旗。“比利时号”所到之处,欢呼声像水波一样在人群中荡漾开来。整座城市似乎都在震动。 驾驶台上,有一人远远地凝望着这片彩条、帽子和手帕的汹涌海洋,这便是远征队指挥官——31岁的阿德里安·德·热尔拉什·德·戈梅里(Adrien de Gerlache de Gomery)。从他的脸上看不出多少情绪,但是在那双眼皮厚重的眼睛背后,是他按捺不住的激动。今天,为了这一时刻,他精心打理了外表的每一个细节——从八字须的弧度,到下颏胡的修边,再到领巾上的领结,每一处都考虑周到。德·热尔拉什的深色双排扣大衣对这个8月的上午来说太过保暖,对世界尽头的严寒来说却又单薄得可怜,但是他这么穿着,看上去确实风度翩翩,挺符合“正在创造历史之人”的形象。他尽情享受着人们的喝彩,时不时地摘下绣有“比利时号”字样的帽子,向欢呼雀跃的人群挥帽致意。他渴望这些欢呼声已经很久了。今天是“比利时号”远征的起点,可对他来说却像是终点。“我的精神状态,”他写道,“是一个人刚刚实现自己目标时的状态。” 从某个角度来看,他确实实现了目标。船要启程了,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次个人的胜利。尽管这天上午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是真心实意的,但是这场比利时南极远征并不代表全国性的努力,而是彰显了阿德里安·德·热尔拉什坚定的个人意志。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为这次旅行做计划、招募队员、筹集资金。仅是凭着决心,他让质疑者闭嘴,让有能力的人解开钱袋,还把全国人民召集到自己身后。此刻,尽管距离目的地还有一万英里,但他已经尝到了一丝荣耀的滋味,并乐在其中。在这欢庆的日子里,听着同胞为自己“敲锣打鼓”,德·热尔拉什一不留神就会忘记,这份荣耀是赊来的。要想真正拥有它,他得先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当中存活下来:这片大陆非常不利于人类生命的延续,人类在其海岸线上最长只个小时。 斯海尔德河流至安特卫普西北边12英里处,便是比利时与荷兰的边境线。在跨越边境线之前,“比利时号”在利弗肯舍克(Liefkenshoek)码头稍作停留,处理远航前的最后一件事。在甲板上和簇拥在船旁的护送小艇上,仍是一片欢欣的景象,只不过船员正忙着将共计半吨的托奈特炸药(tonite)——被认为比硝酸甘油炸药(dynamite)更具威力——搬进“比利时号”的货舱。这些托奈特炸药棒占据了货舱里好几个板条箱,是德·热尔拉什的一道保险措施。他不知道该对南极的冰层抱何期望,只知道一块在19世纪之前一直成功地将人类阻挡在外的大陆理应得到尊重。他能想象出船被毁坏的几种方式:撞上冰山或是暗礁。但是,最令人害怕的一种可能性或许是“比利时号”被困在冰层里,要么被压力挤碎,要么永远被冻住,留下一船等着饿死的远征队队员。几场著名的北极远征正是落得这样的下场。德·热尔拉什推测,半吨托奈特炸药肯定能够解开海冰的束缚。这是他第一次低估南极的力量,但不是最后一次。 在队员将托奈特炸药搬进货舱的时候,一群吵吵嚷嚷的达官贵人从护送小艇上下来,登上“比利时号”,祝愿德·热尔拉什和他的队员好运。指挥官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一名水手,待在海上远比待在人群中来得自在。在过去三年里,他对这类欢迎问候的场合愈发厌倦。为讨要资金所花的时间甚至已超过他期望在南极停留的时间。他与政府大臣、有钱的赞助人和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Société Royale Belgede Géographie)——这次远征的赞助者——的耆宿互致寒暄,感受到了自己对这些人肩负的义务之重。如果说他对冰冻之洲不够敬畏,那么他对这些人对这次远征做出的评判则是过度恐惧。 假如任务失败,他将承受整个国家的失望之情。在他的意识里,更糟糕的是为他那显赫的家族带来耻辱。德·热尔拉什家族是比利时最古老的贵族之一,可追溯至14世纪。阿德里安的一位亲戚,艾蒂安–康斯坦丁·德·热尔拉什男爵(Etienne–Constantin de Gerlache),是比利时的开国元勋、宪法的主要起草者和建国后的第一任首相(尽管任期只持续了11天)。阿德里安的祖父和父亲均为受过表彰的军官。对于姓德·热尔拉什的人,公众不期待别的,只期待卓越。阿德里安的家人在报刊中、在比利时上流社交圈里高调地表达了对此次南极探险项目的支持,以家族名誉为项目的成功做担保。可这只是加重了指挥官的心理负担。 阿德里安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名前途大好的陆军中尉——也登上了“比利时号”,并在其他显贵回到各自的小艇上后留了下来。获准留下的非家庭成员仅有一位:名媛莱奥妮·奥斯特里特(Léonie Osterrieth),此次远征最坚定、最热忱的支持者。这位身材丰满的54岁妇人是安特卫普一位富商的遗孀,她对德·热尔拉什就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他则称呼她“奥妈妈”,并视她为知己和最可信的人。(由于她对远征计划的慷慨捐助,队员们后来给她起了“Mère Antarctique”的外号,意思是“南极母亲”,与“Mer Antarctique”同音,后者意为“南极海”。)告别的时刻来临了,阿德里安的父亲奥古斯特拥抱了远征队的每一位成员,从地位最低的普通水手们到科学家们,并用颤抖的声音称呼他们为“我亲爱的孩子们”。指挥官的母亲艾玛不由自主地啜泣着,仿佛她有一种再也见不到自己长子的预感。“比利时号”28岁的船长,身材矮小、不修边幅的乔治·勒库安特(Georges Lecointe)向她发誓,他和其他所有队员将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她的儿子;他不是那种不守诺言的人。然后,勒库安特带着全体队员充满激情地喊了三声“德·热尔拉什夫人万岁”。最后一声呼喊仍在斯海尔德河上回荡,船长已开始对队员喊出一道道命令。 “现在,回到各自岗位!” 德·热尔拉什一家下船后登上一艘名叫“布拉博”(Brabo)的小艇,掉头往安特卫普的方向驶去。指挥官站在“比利时号”的甲板上用力挥着他的帽子。他勉强忍住了眼泪,但用一位观察者的话说,“猛烈的情感攫住了他的脸”。 “比利时万岁!”他对着水面大喊,看着“布拉博号”渐渐驶远。他以杂技演员般的敏捷疾速爬上牵拉船桅和风帆的绳索,只用了不到15秒就爬上了桅杆瞭望台——由一个酒桶改造而成——继续挥动帽子,直到那艘载着他几乎所有所爱之人的小艇消失在河道拐弯处。 ………… 意外陷入冰封绝境 被迫成为第一支在南极圈内度过整个冬天的探险队 悄然揭开南极探险“英雄时代”的序幕 忧郁的指挥官,冷峻坚毅的大副,足智多谋的队医 老鼠,坏血病,黑暗,饥饿,幽闭,猜忌,疯癫…… 惊心动魄的生存故事 极端环境下的人性考验 编辑推荐 ◎ 极地探险史上一个常常被遗忘,却极其重要的篇章 作为人类史上第一支在南极圈内度过整个冬天的探险队,“比利时号”南极探险成果丰厚,带回大量宝贵数据,对南极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包括:对数百个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数千份标本进行了编目,其中许多物种都是首次发现;发现了火地群岛和格雷厄姆地之间的深海沟;汇编了首份南极圈以南的气象学与海洋学全年数据,等等。探险队成员包括比利时人、挪威人、美国人等,为现代国际科考合作树立了典范。 ◎ 挪威传奇探险家阿蒙森的“青春修炼记”,1912年征服南极点史诗旅程的前传 1896年7月,时年24岁的罗阿尔德·阿蒙森恭恭敬敬地写信申请了“比利时号”水手的职位,却因为惊艳的履历直接被聘为大副。探险期间,阿蒙森以浑然天成的领袖气质和出色的判断力与责任心令“比利时号”上不同国籍的队员心悦诚服,并与极地探险经验丰富的队医库克成为至交,在实操和讨论中积累无数宝贵经验,为15年后征服南极点奠定了基础。 ◎ 小说家式的敏锐眼光,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 本书叙事生动细腻,融合了探险、生存与人性考验的元素。作者以小说家般的敏锐眼光,将读者带入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中。在南极恶劣环境下的生存挑战中,探险队员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要与自然力量搏斗,还要应对内心的恐惧和疯狂。“比利时号”的故事深刻展现了人性在极限处的光辉和力量。对喜爱冒险故事和非虚构文学的读者来说,本书将带来一次紧张刺激的阅读体验。 ◎ 35幅珍贵历史照片,重现百年前的南极风貌 照片来自挪威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及德·热尔拉什家族的私人收藏。铜版纸高清呈现,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