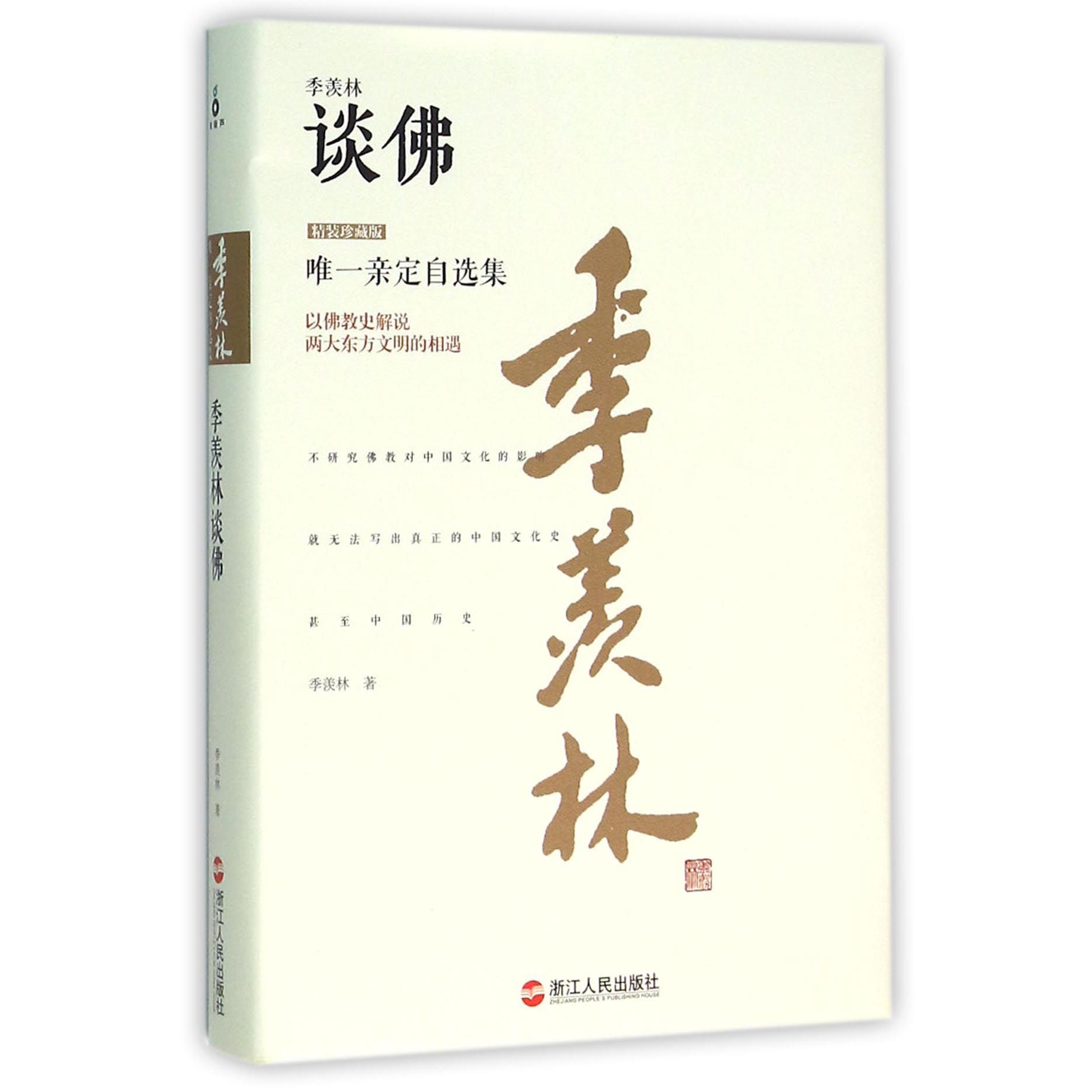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46.00
折扣价: 27.30
折扣购买: 季羡林谈佛(精装珍藏版)(精)/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
ISBN: 9787213069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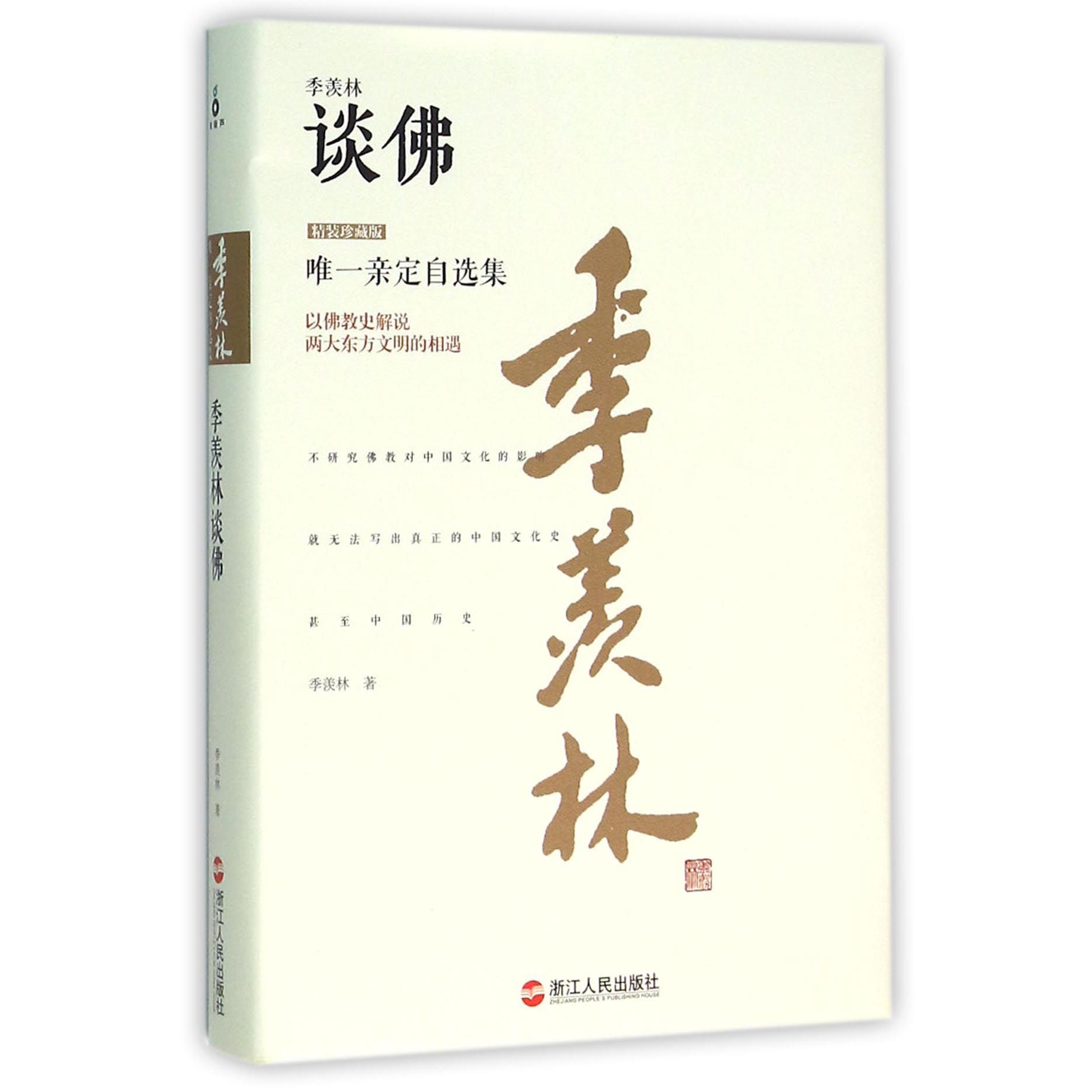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 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 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 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 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 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有人曾半开 玩笑地问过我。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 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 ,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 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 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 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 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 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 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圆满地回答这 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 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 确的。’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但是我感 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 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 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 。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 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平心 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 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 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 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 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 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 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 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 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 间一久,就会退化。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 ,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 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 ,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 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 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 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 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 ,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一 些史学家、哲学史家等,除了谩骂者以外,评价也往 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他们说,佛教是唯心主义, 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 过程。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佛教只是一个“反面 教员”。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今 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我们必须对佛 教重新估价。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 佛教有辩证思想。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言必称马恩 ,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任何社会 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 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 。我们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 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 再做出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因为它 符合客观事实。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 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 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 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 宗,最终发展到诃佛骂祖的程度,几乎成为佛教的对 立面,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深 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布时 间长,有的短。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流传 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冯定 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 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还是国家、阶级先消 灭呢?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 消灭,宗教后消灭。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 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 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类 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 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 “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 ,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 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 唯物主义者。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 神论了呢?不,不,决不。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 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 ,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 教张目。但是,唯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 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 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 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 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 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 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 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 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印度 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伊斯兰的侵 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 ,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 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绝不是 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大力打击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 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建立至今快七十年了。对无神论的宣传 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然而 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 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 “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绝不认为 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 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 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 不着故意去“消灭”。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 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 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 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 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操之过急,徒 费气力。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 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一 必过分地去考虑。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