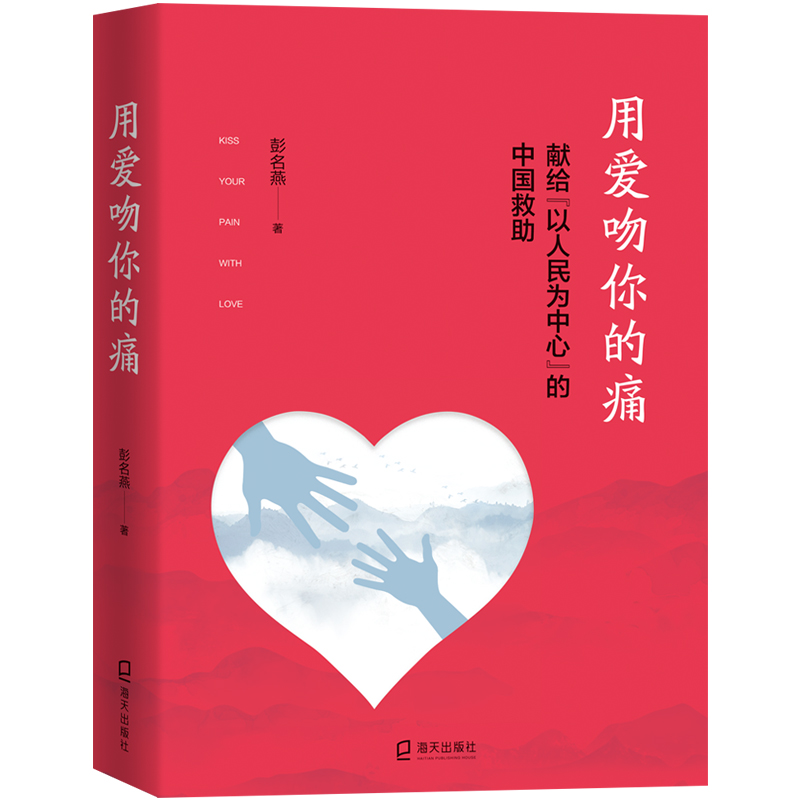
出版社: 海天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6.00
折扣购买: 用爱吻你的痛
ISBN: 9787550730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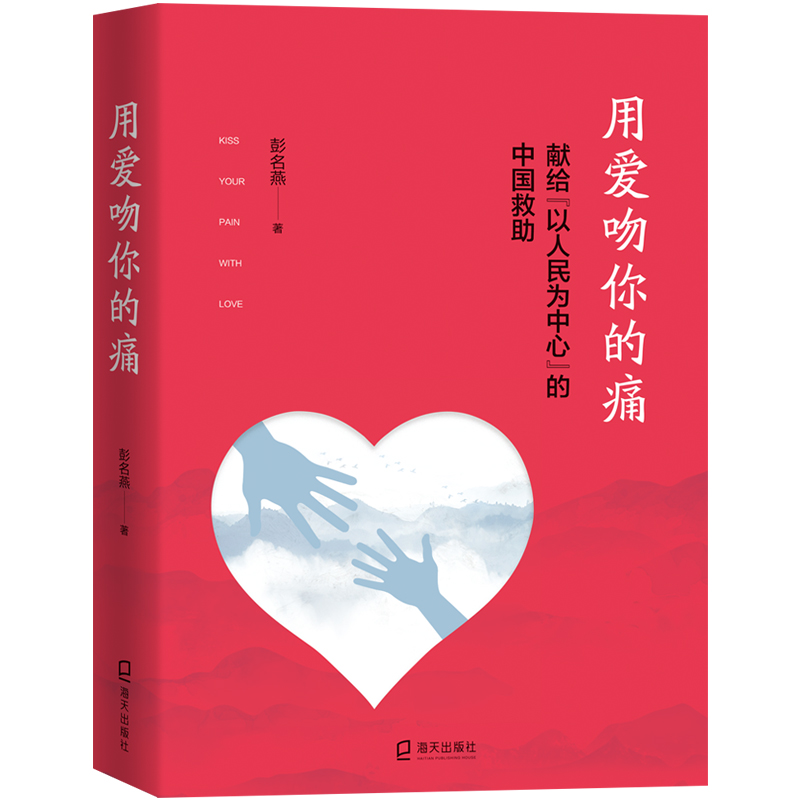
彭名燕,广东省作协原副主席,深圳作协原主席,深圳文联原副主席。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从事演艺1987年。1987年开始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从1980年起笔耕至今已有7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多次获国家和省级奖项。 已发表、出版长篇小说:《东方男性》《公关小姐外传》《世纪贵族》《日尔曼式的结婚》《大腕》《杨门家风》《为你心跳》《岭南烟云》《倾斜至深处》《高贵的混血儿》等。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从清华园到深圳湾》、散文集《瞬间与永恒》等。 著有散文随笔:《三笑》《送我一支曼陀罗》《母亲》《落地窗》《失眠的灯火》《心有余悸》《山河不会忘记》等八十余篇。
他们个个都配当主角 哪里去找一个铺天盖地的巨型舞台? 有家可归者生病了,落难了,救助他们,医治他们,责无旁贷。他们病情稳定和情况好转以后,按照国家的规定,是一定要把他们送回原籍,让他们与家人团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天地所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些生活不能自理,有些患了精神病,虽然出院了,但情况仍然很严重……送这样一批人回乡需要全程陪送。即便他们在天涯海角也要护送到位。 于是,一个不需要舞台聚光灯、不需要舞台布景、全靠自然情景构建的巨型舞台,在一个特殊人群的脚下自然生成。 这个舞台上的主角还有谁? 登台的人群中不乏失忆忘记家乡,之后又记忆复归者。他们不愿意回乡,救助者就要极力劝说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与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由救助方出面护送,由当地出面接应。所有的回乡者,都要救助方与当地事先对接好。送到了以后,救助方把受助者的档案及病历、目前状况等详细资料交给当地相关部门,在备忘录上登记,签字……整个交接的过程相当烦琐,也相当复杂,必须相当谨慎、细致地去完成。 于是,主角中,受助者和护送其回乡的救助方,必然共同携手登场。 这舞台上人影闪烁,吸睛程度不亚于电影。 担架上的袖珍舞台 护送回乡的全过程,有时要乘坐火车、长途汽车,有时开自己的私家车,有时需要四五天,最长的甚至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次次都是大考验和大挑战。 曾宇平科长曾送过吃喝拉撒全部需要护工护理的重病患者。冲着他年轻,有一把力气,还顶得住,才能揽了这重活。 知道吗?被护送者有些患了绝症,从医院里面刚刚出院,必须尽快送回家乡,让家人见他们最后一面。 常人无法想象一路上救助员工忍受了些什么。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曾进监狱三年,出狱以后就在街上流浪,后来被送到救助站。他在救助站反反复复出出进进十六年,闹事、打架、骂人是家常便饭。后来他摔断了腿,还是救助站把他抬进医院医治。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劝他回家乡去养伤。他在外面已经十六年了,对家这个概念已经很淡漠。他终于答应回家乡。因为行动不便,救助站派了四个人,其中一位是医生,专程护送他回乡。这个回乡过程太特殊,是用担架把他抬到飞机上的。因为老人无法行走,年龄又太大,身体太弱,怕经受不起火车加长途汽车几天几夜的折腾。这是唯一允许坐飞机的特殊个案。 满飞机的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四个护送者,真的像是在看一台戏。有人以为是传染病患者,吓得捂住鼻子,戴上口罩。医生解释道,老人是骨折,不传染的,飞机上的人这才放心了。于是大家纷纷猜测,送的人与被送的人的关系。看到曾宇平为患者擦脸,以为患者是他的父亲或叔叔或长辈。有一位旅客小声问曾宇平:“这位老人是你的什么人?”曾宇平悄悄回一句:“亲人吧。”那位旅客听懂了,又像没听懂,说了一句:“噢!他们几个……都是?”曾宇平反问:“你是这样觉得的?” 谁能猜得出来,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如果那位旅客知道实情,可能会惊掉下巴。 下了飞机,在人们好奇的目光中,救助站的四名护送人员轮流抬着担架,又去坐长途汽车,一直把老人送到老家铁岭。这一路,这一副担架,压得几个壮汉满头大汗,头发都滴水。 类似这样的受助者,不仅要送回乡,还要给他们办低保,送进养老院,向当地对接的相关部门详细交代受助者的情况,真的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不对,应该把“像”字去掉,换成“是”。 试想,把一个人们所不齿的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感动得他能掉一滴热乎乎的眼泪,这难道仅仅是一个老人被温暖了?当然不是,这也是对一个地区的温暖,也就是对整个社会的温暖。这种温暖的辐射力是很强的,一传十,十传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一个小举动是对党和国家的大维护! 临别时,当老人伸出手握住护送人员的手时,他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哽咽了。 抬担架来送行的人也哭了。 一副担架结成的缘,赛过血缘。这一个小舞台暂时拉下了大幕,自然旋转到另一个舞台。 12小时的120救护车舞台 有一名胃肿瘤患者手术后,要从医院直接护送回乡。这可是危重病人,上面插胃管,下面插着导尿管,带着尿包,一路还要输营养液,乘坐什么公共交通工具都不可能,只能坐120救护车,车程12到14小时,而且有很长一段路的路面情况非常不好。谁去送? 成人部部长王珲说:“我去!我体力好,经得住折腾,就这样定了!” 他和医生张小梅及另外一名护工上路了。 这一路,可是出现了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折磨。因为患者消化系统严重损坏,要不停地排气,说白了就是放屁,连呼出的气也是怪味,那是患者自己也无法控制的难堪。救护车是封闭式的,空间狭小,王珲和医生张小梅及护工挤在一起,脚都伸不开。加上不能开窗,臭气散不出去,差点把所有人熏倒过去。好几次,王珲这位高大威猛的汉子都觉得自己顶不住了,要呕吐。为了不刺激患者,不能捂鼻子,他强忍着从胃里翻上来的恶心感,还要笑着去安慰患者。因为他知道,患者的痛苦大过他们十倍都不止。 目的地总算到达了。王珲他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差点儿一头栽倒在地上,可能是车里空气太污浊,严重缺氧造成的身体不适。他们把患者送到了亲人的身边,还自己掏腰包给患者买了许多水果,这才离去。 患者的家属感动得眼泪汪汪,双手合十,连连说:“谢谢,谢谢,一路平安!” 120救护车颠簸的舞台暂时谢幕,旋转舞台又开始转动。 插尿管的火车舞台 王珲他们还送过一个从医院接出来的插着尿管的患者回乡。这次是坐火车。一路上患者如果要喝水,就得不停地排尿,就要不停给他拔尿管,倒尿包,再插尿管。患者的尿如果特别多,这一天一夜,送行人员根本无法睡觉,就怕尿包满了造成回流。王珲也是独生子,何曾干过这样的事情?好在有军事学院四年本科的基础,有驻港部队的风雨磨砺、摸爬滚打基本功垫底,尿管这点事又算什么?大丈夫一咬牙,什么难事不能扛得起?火车上人特别多,厕所总是没断人。患者上火车后特别自觉,尽量少喝水,少吃东西,否则他自己麻烦,也给王珲他们添麻烦。王珲有些心疼,几次把水递到患者面前,他几次用手轻轻推开。王珲很感动,说:“不要紧,我知道你好渴,你喝水吧,不就是给你倒尿吗?我们能做到。”但这患者只喝了两口就忍住了。难熬的24小时终于结束了。就这样,王珲他们充当了24小时的医生、父母、儿女、保姆。 到达目的地后,患者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感谢,恨不得把家里的鸡全部杀了、猪全部宰了来招待王珲他们。他们接受了患者父母的感谢,一顿饭没有吃,立即踏上回程路。 这方舞台落幕,他们准备走向另一个舞台。 悲喜兼容的舞台 有一个外省的中学生来深圳旅游,花光了钱,流浪时被城管送来救助站,因为马上要开学,如果从深圳坐火车回去,要转好多次车,起码需要五六天,孩子开学就在两天后。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业,民政局又特殊批准—坐飞机。 这名中学生高高兴兴回家了,没有耽误一天学习。虽然乘坐飞机行程只有几个小时,但是护工小赵等人回程却惨了。按国家规定,救助人员不得乘坐飞机,只能坐火车和汽车。但是,正值国庆期间,到广州的火车票一周内的全部售光,怎么办?只能坐长途汽车绕路,绕到广东的连南,下了车找不到北,人生地不熟,一迈腿就走错了方向,问路语言不通,听错了,又走了冤枉路,走到连公交车都没有的地方,只好招手坐了农民的马车、牛车,恨不得连环卫工人扫地的车也去搭一程,几经周折才坐上长途汽车到了广州,然后回到深圳,这一路足足用了九天。 他俩表面上说,这有什么,不就九天吗?私下里却苦笑说,早知如此,当初不如就等上一周,也比这样的折腾舒服得多。 ………… 送走的受助者,几乎都生长在农村,有的是偏远山区,哪能说通火车就通火车,说通汽车就通汽车的?救助站的护工,除了飞机,什么车都坐过。火车是习以为常,长途汽车更是小菜一碟,还有马车、牛车、货柜车……除了大粪车太臭不敢一试,什么交通工具都体验过。事后一回忆,能笑得肠子痛。 时过境不迁,桃花依然笑春风,这样的笑,永远是未完待续。 苦乐生涯,成就了一批真正的“时代主角”。他们扮演着大众父母、大众朋友、大众亲人的角色,却从不抢镜头,仅仅是把侧影或者背影对准观众。在城市大舞台上,该出现时会在前面为人挡子弹,该隐退时就退到人家背后当靠垫,这样的品质才配当真正的主角。 当然,这一切是他们应当做的,也是必然要经历的,没什么值得特别推崇。 但是,用这一正气压倒当前社会存在的歪风邪气,为什么要吝惜口舌和笔墨呢? 有一首歌《掌声响起来》不仅仅是献给演员的,更是献给谢笑、杨立君、付新生、张维文、王惠平、毛渝新、王珲、郭敏、吕老师等这些伫立在风雨之中,为弱势人群遮雨挡风的平凡大哥、大叔、大姐、阿姨的。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多少岁月已不在 多少情怀已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交汇你我的爱 一幅救助者的“大爱图” 一幅受助者的“众生图” 一条苦难与文明交叉的路 一曲爱吻别痛的离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