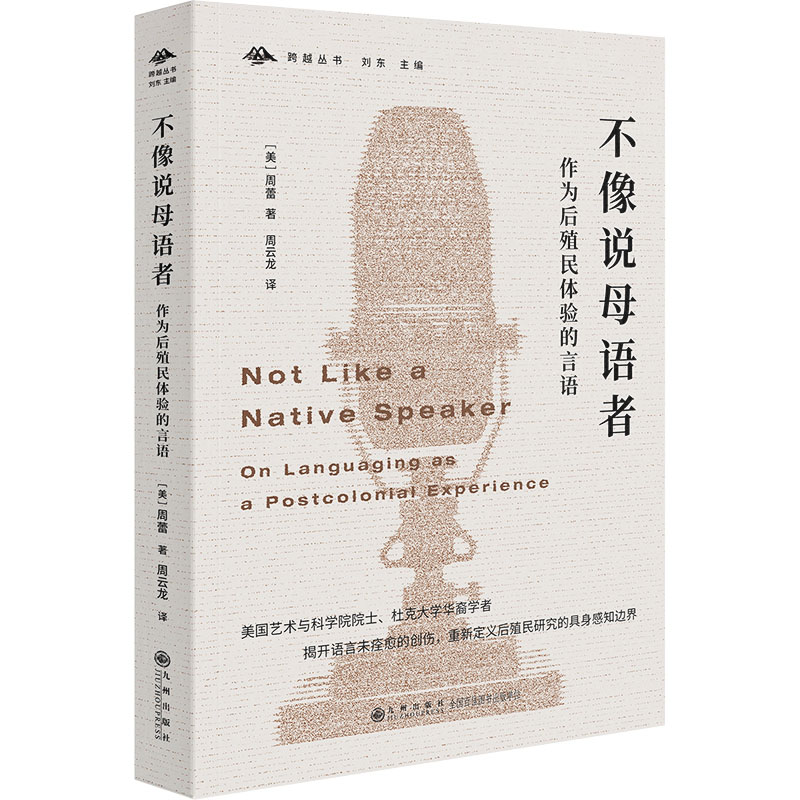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4.19
折扣购买: 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体验的言语
ISBN: 97875225335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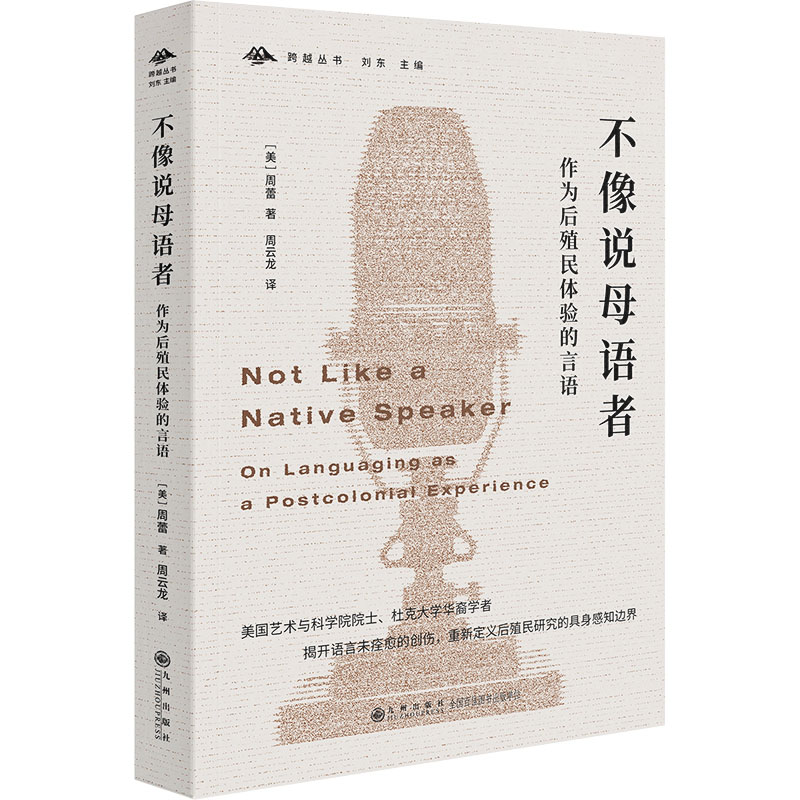
周蕾(Rey Chow),出生于香港,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任教于杜克大学。目前的学术工作集中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遗产、语言作为后殖民现象的政治,以及视觉技术与数字媒体时代生存经验和知识范式变迁。著有A Face Drawn in Sand: Humanistic Inquiry and Foucault in the Present,Entanglements, or Transmedial Thinking about Capture,The Rey Chow Reader等。已出版中译版的有:《温情主义寓言:当代华语电影》《世界标靶的时代》《原初的激情》《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等。 译者简介: 周云龙,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和跨文化戏剧研究。著有《别处的世界: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与亚洲形象研究》《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译作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一册)和《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合译)等。
导论 肤色——关于语言、后殖民性和种族化 巴拉克 · 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开始的地方,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一场遭遇: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大使馆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黑人双手的特写照片。他注意到,这双手“有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好像血液从肌肉中被抽掉了一样”。奥巴马继续讲述道: 我想,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病得很严重。一个辐射的受害者,或者,也可能是患白化病的人。几天前我在街上曾经看见过一个那样的人,我母亲是这样对我解释的。在我读了这张照片的配文后,才发觉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根据文章的解释,这个男人接受了一场医学处理以淡化其肤色。他用自己的钱支付了治疗费用。他对努力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表现出一些懊悔,他为事情出现如此糟糕的结果表示难过。但事情的结果是不可逆的。为了广告里承诺的作为白人的幸福,成千上万的黑人男女像他一样,回到美国做了同样的治疗。1 成年后的奥巴马仍然记得,当年那个九岁小男孩发自内心的感受:“我感到我的脸和脖子都发烫了。我的胃开始痉挛;这一页上面的字体开始模糊……我恨不得从椅子中跳出来……想要某人来给我解释并保证。”他的具身反应转变成了失语症:“像是在梦境中,我对自己新发现的恐惧发不出声音。”2这种失声正是我后面将要继续讨论的,是可被称作“极限体验(limit experience)”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说法来自福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已经抵达了其确信的事物的尽头,并触碰到了深渊的边缘。虽然这样的描述已经足够直接,但另一个问题又凸显了:失语症(发声或言说遭到限制)与种族化关联在一起时,该如何理解?种族化是这个故事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因素。 种族化作为与语言的一场遭遇 请允许我专门以一个著名的理论场景的谱系学方式,切入这个问题。奥巴马的叙述一开始就简洁地传达了那个年幼的黑白混血儿的创伤,这与弗朗兹 · 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的痛苦记忆一样引人注目,后者遭遇了他者从外部以武断的形式进行定性的过程:“肮脏的黑鬼!”“看,一个黑人!”3 在奥巴马和法农的境遇中,刻骨的震惊、自卑、脆弱和一无是处的感受,构成了强加于有色人种群体的强迫性反思的组成部分。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视的语域中,黑人不得不被自己和自己同类的客体化所惊吓。通过陌生人的习惯性方式凝视自己(法农),或在一次偶然中,通过一张另一个黑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照片(奥巴马),种族主要被理解并呈现为一出视觉上的戏剧,它强调了当一个社会蔑视黑人就像对待某些肮脏的东西时,被视为黑人 意味着什么。 虽然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第一章致力于探讨“黑人与语言”,但种族客体化和语言工作之间的关键联系,在当代学术研究中似乎被讨论得不够充分。对法农来说,殖民脉络中的语言,是把殖民者的语言强加给被殖民者,并要求后者掌握。如法农所言,这种对殖民者语言的掌握,甚至是其所谓的“种族表皮计划”中的另一种价值交换。“安的列斯黑人变白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将更接近一个真正的人——与他掌握法语的程度成正比。”4换句话说,(法语)语言知识的获得,就相当于白人性的获得。借助这种他者的生物符号学,掌握语言被翻译并接受为肤色的价值。这种生物符号学不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自明的东西,而是应当进一步阐述的东西。要开始这种阐述,我们必须问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简单问题:确切地说,这里的语言是什么? 我们再思考一下法农发出的感慨:“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这些言论被制造出来首先是为了给他者命名。沃尔特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人类语言的写作,使他在这个方面成为一名有趣的(如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话)对话者。和语言哲学传统中的一些前辈一样,本雅明在讨论语言时依据的是心理的内在性,即人类特有的一种内在的理解力。虽然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本雅明的思考具有启发性的是其矛盾的一面,这些思考具有雅努斯般的两面性——宗教性的神秘主义和 20 世纪早期革命性的乌托邦主义。比如,当论及语言,本雅明就特别关注命名的行为,正如他的文章所示,该行为变戏法般地带出一个神圣的创造性观念。与此同时,就像本雅明的思想特征那样,命名行为也是关于共同体形成可能的世俗化视角的关键。这里的关键节点是摹仿:作为语言中决定性的关键内容,命名与摹仿密切相关,它有生产相似性的能力。本雅明写道,名称(言外之意就是人类的语言)是相似性的非感性形式(因为和具体的物理性实体相比较,词语是抽象的);命名就是建立起“由事物构成的神奇共同体”的东西,它是“非物质的、纯精神性的”,它借助声音得以符号化。5 在命名与摹仿的等式之间,存在一个可以被认为是社会政治原型的步骤。本雅明认为,通过给事物命名,我们事实上是在摹仿它们,也就是说变得和它们相像。命名(他者),与(他者)相像,(和他者)形成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从世界获取知识的方式。 如果说本雅明的神学和浪漫沉思被转移到了一种社会政治框架中,那么,名称所指代的正是一个接触区域。从理想的角度说,名称是一个位置,在这里,象征性的相似、相遇、对等、交换以及整合,都由世界所创立。在人类与事物的无声世界之间的潜在联结,事实上是相似,这使我们可以把命名转变为一种非常有力的、述行性的姿态:通过命名某物,我们授予它一个原本不具备的身份——通过这个身份,被命名的事物作为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同等物、我们的共同体而变得生机勃勃;通过这个身份,被命名的事物可以接触(并影响)我们,就像我们能够接触(并影响)它一样。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潜在的共通性和相似性,名称才显得尤其危险。正如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样,当命名的姿态不仅仅被应用在沉默的物的世界,而且还被用于人类的其他群体时,在命名者和被命名的事物之间的那些不稳定且相反的对应和整合,就会变得不受控制。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类命名行为就不再仅仅是指定一个名称,同时还必须作为一种称呼、一种召唤被接受。6这就是法农的论述中的命名行为面临的情形。 通过被命名为“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这个黑人在视觉上瞬间被客体化,可以说在同一时刻,其存在感也得到召唤。法农的著作于 1952 年首次以法语发表,他在其中令人心酸地预示了主体的询唤,后来路易 ·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其广为引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 年首次以法语发表)中对此进行了论述。特别是,阿尔都塞为了分析得更加清晰,他把询唤的过程切分成两个连续的时刻,体现为两个沿着街道行走的人物。第一个是发出匿名召唤的警察(或其他陌生人),这个召唤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嘿,你!”然后,就有一个默认的转身,阿尔都塞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被召唤的人以 180 度的转身去回应这个召唤。这个转身的动作就是一种反馈,相当于在说“是的,那是我”,这就完成了匿名召唤发起的循环,主体由此生成。对阿尔都塞来说,当个体回应的第二个时刻,也就是“相信 / 怀疑 / 知道那是在叫他,比如,承认‘他的确是’召唤的对象”时,意识形态才成功地完成了其动员主体的任务。 ………… 《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体验的言语》是华裔文化批评家周蕾基于种族、语言、身份认同的研究作品。出于自身对身份认同的敏感,周蕾观察到语言带来的不平等与失语,反思不同肤色和阶级的语言与写作,认为语言实际上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秩序。 从德里达对法语的自传性反思入手,到与非洲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同等的对语言先天论的烦恼,继而“揭开语言尚未痊愈的伤疤”,作者潜入巴金、梁秉钧、马国明、本雅明、保罗·利科等人的文本,重新思索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与跨语言现象所带来的失落感。本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后殖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边界,还展示了如何将历史经验与基于声音和剧本的习惯、实践、情感、想象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