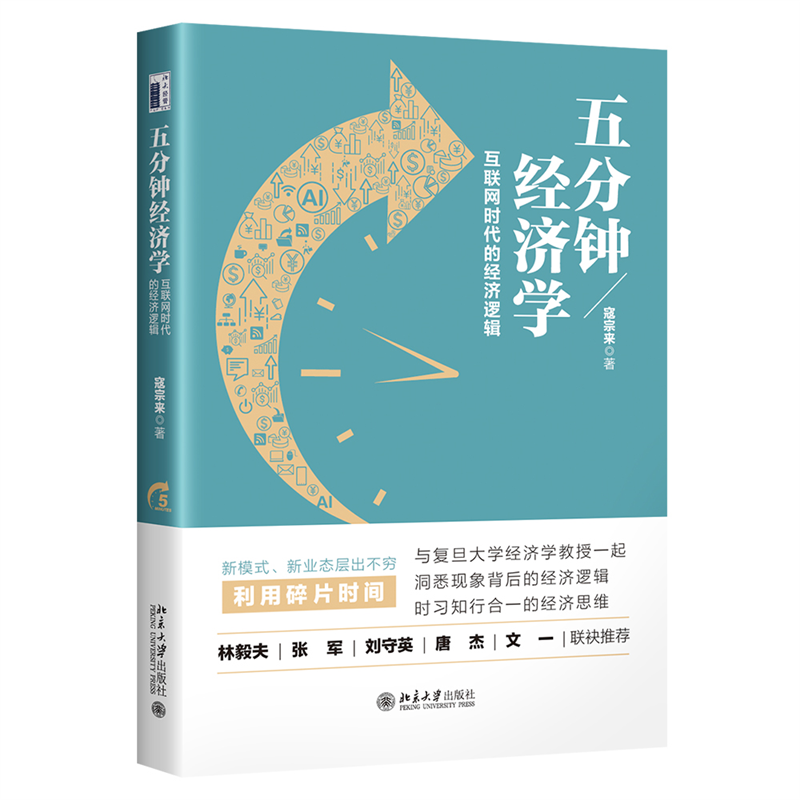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9.30
折扣购买: 五分钟经济学:互联网时代的经济逻辑
ISBN: 9787301321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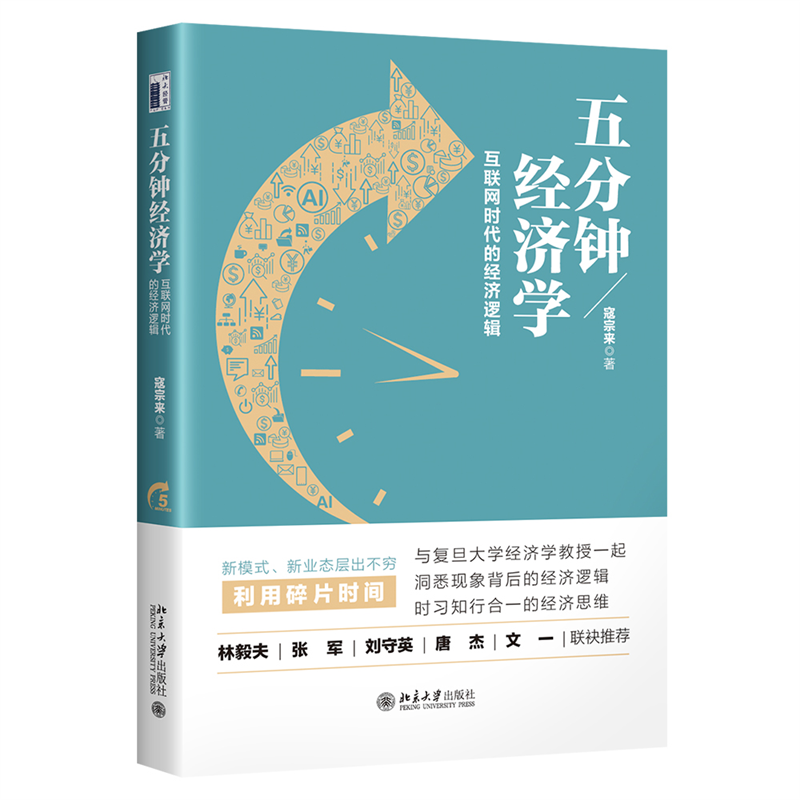
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创新发展、公司金融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及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知识定价中的产品思维与平台思维 知识定价中的产品思维与平台思维根据之前的文章,大家已经熟悉了互联网平台为何物,对于某种交易,市场中有许多潜在买家和潜在卖家,平台的作用就在于撮合买家和卖家达成交易。 关于平台的价值,通常的说法是,平台连接的买家和卖家的数量越多,平台价值越高。这背后是所谓的梅特卡夫定律(网络价值与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及双边网络外部性,移动出行是已分析过的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这种解释不能简单地移植到知识付费领域,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交易标的有很大差别。简言之,打车服务是一种搜寻品(search good),而知识产品是一种体验品甚至信任品。这三种产品为表述简洁,这里提到的产品都指产品或者服务。的差别,最好是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行阐释。 搜寻品是指消费者只要看到这种产品,就知道它的质量;体验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前不知道这种产品的质量,但消费之后就知道了;信任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前后都无法判断这种产品的质量。 一旦认识到知识产品(尤其是线性进程的音频产品)是体验品甚至信任品,我们就会发现,移动出行平台中的双边网络外部性并不能完全用于知识付费平台。主要原因是消费者购买知识产品,不但需要付出货币成本,更重要的是还得支付不菲的体验成本(主要是时间成本)。 对消费者来说,最不愿意得到的结果是花钱买了某个音频产品,听了半天,却发现里面讲的全是些无用的 “鸡汤”,或者全是些正确的废话。所以,撮合知识产品交易的互联网平台真要拥有高效率,就必须具有筛选的功能,或者说需要展现平台的眼光,在消费者中构建这样的名声——只要是我平台认可的产品,都是货真价实、物有所值的产品。 对此,有一个充分的例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知识的公开发布已经不再是难题。最初,有些人认为这会替代学术杂志,因为他们以为学术杂志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学术知识 “铅字化”,但事实证明,其言何其谬也。 以前,排版成本非常高,个人很难靠一己之力出版作品;而出版社因为出版很多书,可以摊销固定成本,因而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排版形式的作品都有其可展示的平台;在此意义上,杂志将知识 “铅字化”的功能就变得非常不重要。但现实表明,好杂志在学界的作用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强。为何?因为信息筛选! 如果说以前人们面临的问题是 “无书可读”,那么,现在人们面临的问题则是 “信息爆炸”。给定时间有限,如何才能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 做过研究的人都知道,许多学术文章看起来很高深,用了不少花里胡哨的技术,很有派头,但真正花时间看懂之后,会发现里面并无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有的甚至是错的。面对这种情况,读者自然有一种 “吃苍蝇”的感觉。因此,就在信息爆炸时代,好杂志变得日益 “赢者通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读者提供了筛选、背书和认证的功能。这样就能让读者把宝贵的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即所谓的好钢用在刀刃上。 所以,一个撮合知识产品交易的互联网平台,只要其定位不是一个人人想唱就唱的娱乐平台,就必须认清楚自己在本质上是个互联网讲台。三尺讲台, 能者上、 庸者下, 不在多、 贵在精。 简言之, “精益求精” 的产品思维一定优于 “狗吃牛屎——图多” 的平台思维。互联网时代,一个好产品,一定优于十个甚至一百个平庸产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做精品。做精品的核心,一是选对人,二是设定好的激励机制。选人,取决于眼光,至关重要,但又毋庸多言,历史上正反案例甚多,如三国时孙权重用书生陆逊而夷陵破蜀、孔明重用 “嘴炮”马谡而痛失街亭,等等。下面着重谈谈合约形式背后的激励问题。此处所谓的激励问题,既有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也有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现实生活中的合约,一般不会签得非常复杂,基本上用两部定价就足以解决问题。现实中当然还存在一些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定价机制,但契约理论分析表明,任何非线性定价原则上都可以用许多两部定价来逐步逼近。 买卖双方交易,两部定价的合约形式为:T=A+pQ,其中T为买方支付给卖方的总费用,A为固定费,Q为交易量,p为单位交易价格。A>0,表示买方为从卖方购买产品需要支付的 “资格费”。但原则上,A<0也是可以的,比如,商户为入住万达广场所支付的通道费(slotting allowance)就是这种情况。 几种常见组合: (1)A>0,p=0;这是 “自助餐”定价模式,在知识产品定价中,这对应于买断。 (2)A=0,p>0;这是最常见的线性定价模式,在知识产品定价中,这对应于简单分成。 (3)A>0,p>0;这是前两种定价模式的混合,在知识产品定价中,这对应于既有保底、又有分成的混合模式。 很容易理解,两部定价中,固定费A起的是保险作用,分成部分p起的是激励作用。由此,可以讨论买断制、分成制与混合制三种合约背后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买断制 买断制下A>0, p=0。 这是一种典型的 “弱激励合同”(lowpowered contract),因为卖方收益与后续的Q无关。这导致的结果是: (1)卖方对自己的产品评价越低,越愿意接受这个合同,此为逆向选择,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 (2)卖方后续收益与Q无关,但注意到Q的量取决于卖方的努力,而努力成本由卖方独家承担,故卖方有积极性偷懒,此为道德风险,结果是出工不出力,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分成制 分成制下A=0,p>0。这是一种典型的 “强激励合同”(high powered contract)。p越大,卖方激励越强(做好产品);反之,p越小,买方激励越强(平台促销激励)。 在完全信息下,这种合约是一种最优合约,卖方(制作者)和买方(平台)分别按照自己的贡献得到相应分成。但在非对称信息世界中,这种合约的最大问题是买方的道德风险。尤其是给定平台注意力资源稀缺,而平台产品鱼龙混杂,平台难以做出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会给予产品以合理的注意力资源,这使得卖方承担过度的风险。 混合制 混合制是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效果上也是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既有保险功能,又兼顾激励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平台产品数量比较少,每一种产品获得充分可见度本来就符合平台的事后激励,固定费的承诺功能就下降了。正因如此,站在平台的角度,给定注意力资源稀缺,产品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好的办法是分类,在 “平台严选”部分,产品数量少,每个都是精品,代表了平台眼光,以质取胜;而在 “自嗨部分”,平台可以除了进行常规的政策审查,允许人人皆可发声,借助于类似用户点评打分的方式,搭建平台,让市场自己玩,平台获取人气,收点流量费即可。 最后,简单讨论一下知识平台的定位问题。任何公司,做产品都必然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迎合市场还是引领市场?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每个公司肯定是希望两者兼顾,但本质上仍然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就知识产品而言,此问题尤为重要。这牵涉到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关于知识定价的三个难题。 第一是阿罗信息悖论。在此情形下,知识产品类似于一种商业秘密,是一种体验品,不存在用户看不懂、理解不了的问题。但对于商业秘密,消费者要知道自己愿意出多少价格,就必须先知道知识产品的内容;可一旦消费者已知知识产品的内容,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购买了。现实的解决办法是部分披露,比如音频课程中的 “试听三分钟”。 第二是认知不对称。在此情形下,知识产品介于体验品和信任品之间,消费者不是完全不懂,也不能完全懂。 一旦消费者无法知道知识产品的优劣,专家的认证和平台的筛选就变得至关重要。正因为多数知识产品都具有此类性质,平台的双边网络外部性受到很大的制约;也正因如此,对平台而言,知识产品并非越多越好。 第三是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对称,事前激励和事后奖励不对称。简言之,知识产品的创造成本很高,但复制成本很低。 所以,从事前角度看,为了让人们有积极性创造知识,知识产品定价必须为正;但从事后角度看,既然知识产品已经被创造出来,就应该免费共享才符合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牵涉到公共政策问题,此处不多谈。 对于平台企业而言,关键是前两点。如果知识产品定价更多地面临第一类问题,则企业策略主要应该是迎合市场,这时候平台思维占优;如果知识产品定价更多地面临第二类问题,则企业策略主要应该是引领市场,这时候产品思维占优。简言之,秉承平台思维的企业,其目的是迎合市场;而秉承产品思维的企业,其目的是引领市场。 2018年4月3日 这不是一本经济学的学术专著,书中也鲜有复杂的数学模型与公式。寇宗来教授凭借其多年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经验,以及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通过一篇篇基于时代热点的经济学短文,用通俗易懂且贴近现实的语言为读者阐释了知行合一的经济思维。 互联网时代的平台补贴到底是不是“免费的午餐”?网约车的安全隐患究竟是什么?“井喷”的知识产品该如何定价?AI与大数据将对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书中收录文章内容接地气且易阅读,读者可利用碎片时间随时翻阅。 林毅夫、张军、刘守英、唐杰、文一等知名专家联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