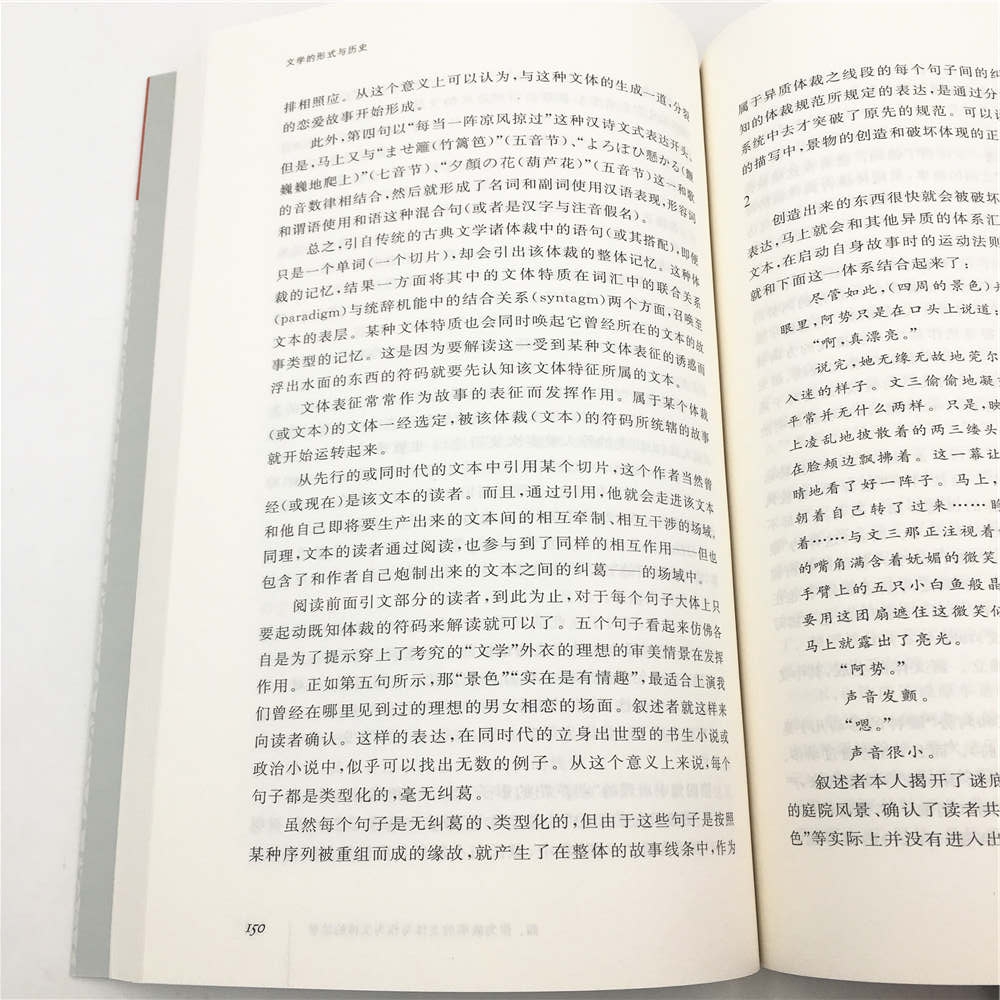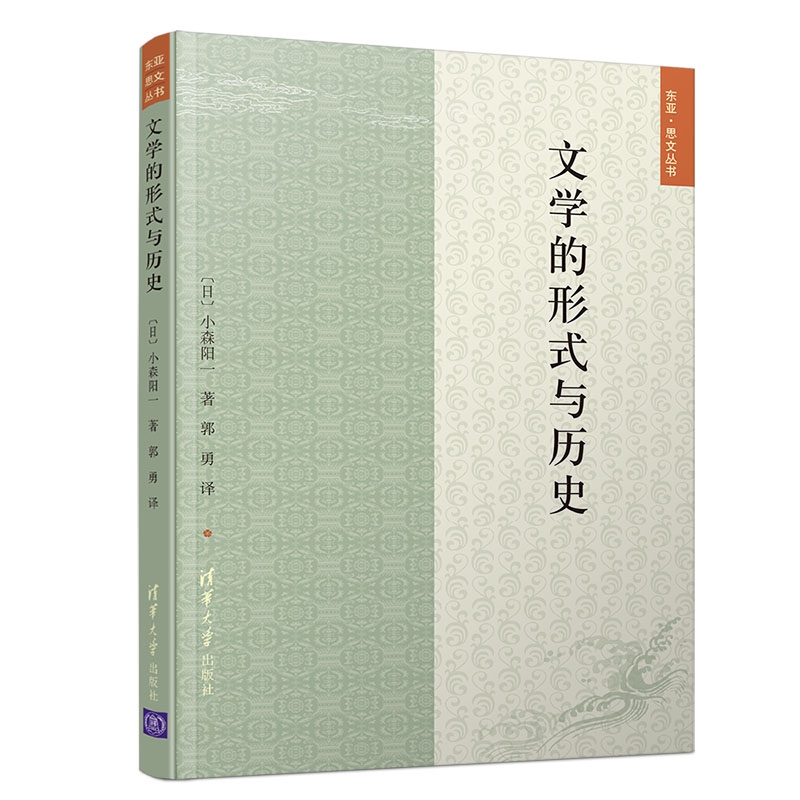
出版社: 清华大学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56.09
折扣购买: 文学的形式与历史/东亚思文丛书
ISBN: 9787302516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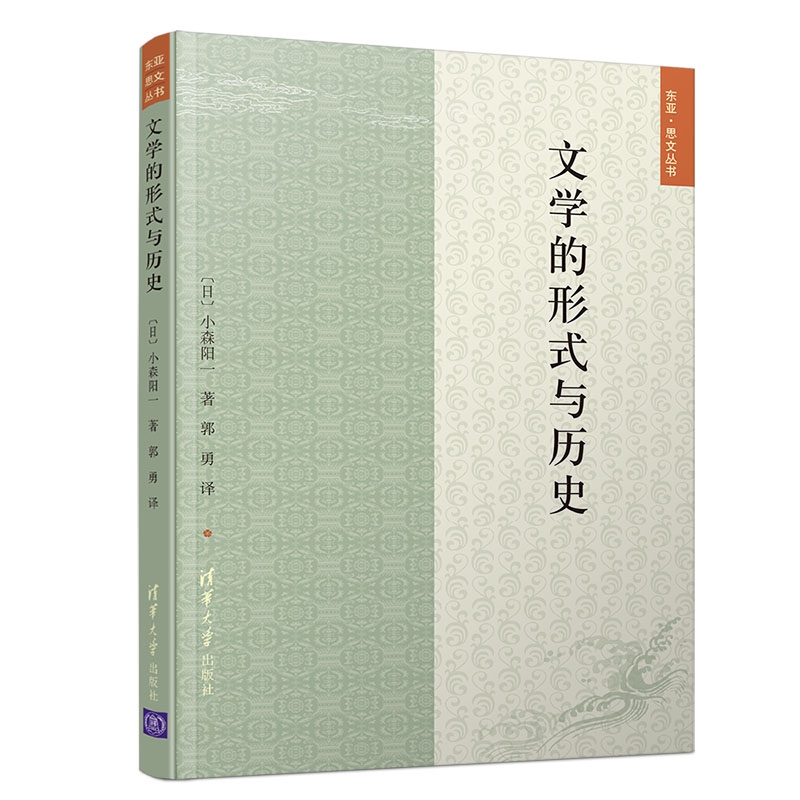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小森阳一(Komori Yōichi),1953年生。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现为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学术影响外,也是当今日本最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之一。自2000 年以来,一直是抵制日本右翼化方面的领军人物。他所领导、组织的捍卫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全国性的“九条会”运动,尤为人所知。作为小说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尤其关注作为历史记述装置的文学作品的特性。已出版的汉译著作有《天皇玉音放送》(北京,三联书店)、《现代日本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北京,新星出版社)。 译者简介: 郭勇,1967年生,重庆人,分别毕业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主要著述有《他者的表象: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等。 "
三、多声调交织的纠葛体“叙事”三、 多声调交织的 纠葛体“叙事” ——明治日本小说《浮云》的描述句1 在日本文学史中,从被认为是“言文一致体”创始时期的明治十年代至二十年代初的表达者们——其中也包括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绝对不单是想要通过口头讲的话(口语)来创造出崭新的小说文体。他们最终所关心的,是如何把在文学作品中“词”=作品中人物的对白和“地”=作者的话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起来。坪内逍遥(1859—1935,日本小说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译注)在《小说神髓》下卷(明治十九年〈1886〉四月)《文体论》中就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他把日本传统的小说文体分成“雅、俗、雅俗折中三体”,并按照文类类别分别进行了讨论。其时,他尤其留意的是作品中“词”与“地”的关系。 ……用马琴拿手的文体来写描写文,如果马上又采用为永所擅长的市井俗语写“オヨシナサイナ”(那就算了)这样的对白的话,地与词就会非常冲撞,句调本身也不平稳。但是,如果为了不出现这样的冲撞,过分地使描写句偏向俗文体,又必定会妨碍写出那种豪情跌宕的境况来。这可谓是第一难事。所以,如果用俗文体的话,应当会写出一篇有风骨的文章来。一定不要企图混合使用(江户时期通俗小说家)曲亭马琴和为永春水的句子来写描写句和对话句。(筑摩书房《明治文学全集》版)如果将很棒的“对白”与“描写句”连在一起就能产生出新的小说文体。但是,坪内逍遥并没有这种乐观。他认识到语言所具有的相互干涉作用,也就是,这两者越是出色,相互之间越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冲撞力量”。对他来说,所谓新小说文体的创造无非就是创造出“会话句”与“描写句”能够相互调和的崭新的“一篇文章”来。 站在这一问题意识上的坪内逍遥,尽管认为将“通俗语言”“原封不动地写进句子里”的“俗文体”“在充分地描写心底的感情方面是很妙的”表达,但是他并没有将其选作统一作品整体的文体。在他看来,“俗文体”在“摹写”“故事的台词”=“故事中出场人物的对话”上并无大碍,但是,如果要在“描写句”里使用它的话,则需要进行“一大改良”。正因为如此,当下他把“完全没有描写句和对话相抵触这种担心”的“雅俗折中文体”,尤其是“稗史体”选作“好文体”。 但是,坪内逍遥又发现了“俗文体”(俗语)中所含有的独一无二的性质。按照他的说法,“语言就是灵魂”。在这里“七情六欲全都不加修饰地显露了出来”,说是“如果原封不动地使用俗语,就会有一种如面对面地谈话的趣味”。这些就是与“雅俗折中句”相对照的“俗语”的特质。但是,倘若结合前面的“在表现出心头的感情方面是非常精妙的”这一观点来看的话,逍遥似乎是把“对白”(言)理解成毫无遮掩地表白了人(作品中人物)的诸如“灵魂”“七情”“感情”等内心的东西,从中发现了在“文”中所没有的“如面对面地谈话”的生动性。 ① 坪内逍遥∶《讨厌文学的作家》,《东京朝日新闻》,明治四十二年五月十日。 ② 二叶亭四迷∶《我的言文一致的由来》,《文章世界》,明治三十九年五月。由直接表白了人的内心的“俗语”所构成的“对白”,在坪内逍遥那里是通过其《当世书生气质》(明治十八年六三、多声调交织的纠葛体“叙事”三、 多声调交织的 纠葛体“叙事” ——明治日本小说《浮云》的描述句1 在日本文学史中,从被认为是“言文一致体”创始时期的明治十年代至二十年代初的表达者们——其中也包括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绝对不单是想要通过口头讲的话(口语)来创造出崭新的小说文体。他们最终所关心的,是如何把在文学作品中“词”=作品中人物的对白和“地”=作者的话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起来。坪内逍遥(1859—1935,日本小说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译注)在《小说神髓》下卷(明治十九年〈1886〉四月)《文体论》中就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他把日本传统的小说文体分成“雅、俗、雅俗折中三体”,并按照文类类别分别进行了讨论。其时,他尤其留意的是作品中“词”与“地”的关系。 ……用马琴拿手的文体来写描写文,如果马上又采用为永所擅长的市井俗语写“オヨシナサイナ”(那就算了)这样的对白的话,地与词就会非常冲撞,句调本身也不平稳。但是,如果为了不出现这样的冲撞,过分地使描写句偏向俗文体,又必定会妨碍写出那种豪情跌宕的境况来。这可谓是第一难事。所以,如果用俗文体的话,应当会写出一篇有风骨的文章来。一定不要企图混合使用(江户时期通俗小说家)曲亭马琴和为永春水的句子来写描写句和对话句。(筑摩书房《明治文学全集》版)如果将很棒的“对白”与“描写句”连在一起就能产生出新的小说文体。但是,坪内逍遥并没有这种乐观。他认识到语言所具有的相互干涉作用,也就是,这两者越是出色,相互之间越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冲撞力量”。对他来说,所谓新小说文体的创造无非就是创造出“会话句”与“描写句”能够相互调和的崭新的“一篇文章”来。 站在这一问题意识上的坪内逍遥,尽管认为将“通俗语言”“原封不动地写进句子里”的“俗文体”“在充分地描写心底的感情方面是很妙的”表达,但是他并没有将其选作统一作品整体的文体。在他看来,“俗文体”在“摹写”“故事的台词”=“故事中出场人物的对话”上并无大碍,但是,如果要在“描写句”里使用它的话,则需要进行“一大改良”。正因为如此,当下他把“完全没有描写句和对话相抵触这种担心”的“雅俗折中文体”,尤其是“稗史体”选作“好文体”。 但是,坪内逍遥又发现了“俗文体”(俗语)中所含有的独一无二的性质。按照他的说法,“语言就是灵魂”。在这里“七情六欲全都不加修饰地显露了出来”,说是“如果原封不动地使用俗语,就会有一种如面对面地谈话的趣味”。这些就是与“雅俗折中句”相对照的“俗语”的特质。但是,倘若结合前面的“在表现出心头的感情方面是非常精妙的”这一观点来看的话,逍遥似乎是把“对白”(言)理解成毫无遮掩地表白了人(作品中人物)的诸如“灵魂”“七情”“感情”等内心的东西,从中发现了在“文”中所没有的“如面对面地谈话”的生动性。 ① 坪内逍遥∶《讨厌文学的作家》,《东京朝日新闻》,明治四十二年五月十日。 ② 二叶亭四迷∶《我的言文一致的由来》,《文章世界》,明治三十九年五月。由直接表白了人的内心的“俗语”所构成的“对白”,在坪内逍遥那里是通过其《当世书生气质》(明治十八年六月至十九年一月)来进行试验的。但是,他不得不绞尽脑汁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契机,乃是和其弟子、小说家二叶亭四迷之间的文学讨论。二叶亭四迷曾携带《小说神髓》前来拜访他,在这本书里“每隔两三页就贴满了红纸条”①。和主张“俗语的精神存于兹”②的二叶亭相识数月之后,坪内逍遥就执笔撰写了《文章新论》(明治十九年五至七月)。在这篇文章里,《小说神髓》中的那种基于文类类别的文体论被修正,按照“智、情、意”这样的“心灵作用”来对文体进行分类,他断言“文以表达感情为主,不能表达感情的文辞不能算是完美的文”。尽管他认为“俗语”才是最适合表达“感情”的,但是,他将自己的主张同单纯的“言文一致”划清了界线,强调应该把握“俗语其物的精神”,去表达“感情”。进而,作为表达“感情”的具体方法,他提议通过“Elocution读书法”来再现作品中人物在此时此地饱含固有“感情”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对白”。 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明治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二年八月)就是在听取了带有这种问题意识的逍遥的各种建议后才执笔的。他们二人把关注的中心放在了直接表露作品中人物个性化“感情”的“对白”和与之并不矛盾的“描述句”的创造上。这完全是崭新的小说文体的摸索,在这里是要探究一种把对于人类“感情”的新认识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本章试图通过在与他关系紧张的先行文学或同时代文学中的“对白”(作品中人物=他者)和“描述句”(作者的话)的关系,来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二叶亭四迷于《浮云》里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2 同坪内逍遥交往时期的二叶亭四迷力图尝试一种彻底的俗语表达。他带到逍遥那里去的《果戈理某作品的一个断片》①是用一种被称作“街边小店用(无产阶级调)的粗鲁口吻”翻译出来的东西,据说逍遥对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① 坪内逍遥∶《柿蒂》,中央公论社,昭和八年七月。 ……我说: “若是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是中产阶层社会”。他回答说: “不对,国外的夫妻都是平等的。所以,不这样译就远离事实真相了”。夫妇间的对话完全采用去掉了敬语的“おまえ”(你)、“おれ”(我)、“そうかい”(是吗?)、“そうしな”(是的)等方式来写的。这和田口鼎轩的《日本开化的性质》的见解相同,作为理论我没有反对的余地。但是,这一旦成了艺术,人的联想动辄就会出来干扰。这样一来,就只会被认作是开小店的夫妻。如果把“おまえ”改成“卿”,把“そうかい”换成“乞う何々”等和文汉读方式的话,倒也还将就云云。我们谈论了很久。(《柿蔕》,中央公论社,昭和八年七月) 这段话历来被用来引证二叶亭是个多么彻底的“言文一致”的主张者。但是,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针对逍遥提出的最好是采用汉文训读的方式来书写这一建议,二叶亭站在与田口鼎轩(田口卯吉,1855—1905,日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相同的立场上而加以反驳。这次对话对于二叶亭似乎也印象深刻,他曾这样回忆道: 当时,坪内先生劝我增加一些美文要素,但是,我对此很反感。不如说我就是要努力排除掉美文要素,这样说或许更贴切些。而且,我正是要致力于推敲司空见惯的俗语。但是,这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我的月至十九年一月)来进行试验的。但是,他不得不绞尽脑汁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契机,乃是和其弟子、小说家二叶亭四迷之间的文学讨论。二叶亭四迷曾携带《小说神髓》前来拜访他,在这本书里“每隔两三页就贴满了红纸条”①。和主张“俗语的精神存于兹”②的二叶亭相识数月之后,坪内逍遥就执笔撰写了《文章新论》(明治十九年五至七月)。在这篇文章里,《小说神髓》中的那种基于文类类别的文体论被修正,按照“智、情、意”这样的“心灵作用”来对文体进行分类,他断言“文以表达感情为主,不能表达感情的文辞不能算是完美的文”。尽管他认为“俗语”才是最适合表达“感情”的,但是,他将自己的主张同单纯的“言文一致”划清了界线,强调应该把握“俗语其物的精神”,去表达“感情”。进而,作为表达“感情”的具体方法,他提议通过“Elocution读书法”来再现作品中人物在此时此地饱含固有“感情”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对白”。 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明治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二年八月)就是在听取了带有这种问题意识的逍遥的各种建议后才执笔的。他们二人把关注的中心放在了直接表露作品中人物个性化“感情”的“对白”和与之并不矛盾的“描述句”的创造上。这完全是崭新的小说文体的摸索,在这里是要探究一种把对于人类“感情”的新认识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本章试图通过在与他关系紧张的先行文学或同时代文学中的“对白”(作品中人物=他者)和“描述句”(作者的话)的关系,来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二叶亭四迷于《浮云》里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2 同坪内逍遥交往时期的二叶亭四迷力图尝试一种彻底的俗语表达。他带到逍遥那里去的《果戈理某作品的一个断片》①是用一种被称作“街边小店用(无产阶级调)的粗鲁口吻”翻译出来的东西,据说逍遥对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① 坪内逍遥∶《柿蒂》,中央公论社,昭和八年七月。 ……我说: “若是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是中产阶层社会”。他回答说: “不对,国外的夫妻都是平等的。所以,不这样译就远离事实真相了”。夫妇间的对话完全采用去掉了敬语的“おまえ”(你)、“おれ”(我)、“そうかい”(是吗?)、“そうしな”(是的)等方式来写的。这和田口鼎轩的《日本开化的性质》的见解相同,作为理论我没有反对的余地。但是,这一旦成了艺术,人的联想动辄就会出来干扰。这样一来,就只会被认作是开小店的夫妻。如果把“おまえ”改成“卿”,把“そうかい”换成“乞う何々”等和文汉读方式的话,倒也还将就云云。我们谈论了很久。(《柿蔕》,中央公论社,昭和八年七月) 这段话历来被用来引证二叶亭是个多么彻底的“言文一致”的主张者。但是,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针对逍遥提出的最好是采用汉文训读的方式来书写这一建议,二叶亭站在与田口鼎轩(田口卯吉,1855—1905,日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相同的立场上而加以反驳。这次对话对于二叶亭似乎也印象深刻,他曾这样回忆道: 当时,坪内先生劝我增加一些美文要素,但是,我对此很反感。不如说我就是要努力排除掉美文要素,这样说或许更贴切些。而且,我正是要致力于推敲司空见惯的俗语。但是,这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我的言文一致的经历》,《文章世界》,明治三十九年五月) 这里所谓的“排斥”“美文要素”是指“不成其为日语的汉语,一概不使用”这件事。对此,二叶亭证实说他选择了“诗性的”“在式亭三马(1776—1822,日本江户后期著名小说家,著有《浮世澡堂》等‘滑稽本’——译注)作品中常见的所谓深川方言”来创造新的文体。在二叶亭那里,“俗语”是作为与汉文体乃至汉文训读体相对峙的文体而被选取的。 作为二叶亭拒绝汉文体的理由而提及的田口鼎轩,其见解是这样的: ……或许因为汉语听声音很难懂的缘故,若原封不动地用它来演讲,听者又能听懂的话,那么,这样的句子仅仅是具有中等以上生活有所富余的人才能习得,不得不说其带有贵族性的成分。盖文章只是谈话,故能谈话之人也能马上将其记录下来。若不如此,也就不是真正的文章了。(田口卯吉《日本开化的性质总算是必须改革了》,《东京经济杂志》246号,明治十七年十二月) 田口鼎轩认为汉文体不是“真正的文章”,这有两点理由: 一是汉文体的内容很难通过音声来把握,另一点是汉文体只有生活“富裕”的人才能掌握的。于是,必然地就有了“贵族性的成分”。换言之,田口的批判就在于: 汉文体要求能够视觉性地理解汉字的识字能力,于是就成了有余裕学习它的特权精英的垄断之物,民众是望尘莫及的。言文一致的经历》,《文章世界》,明治三十九年五月) 这里所谓的“排斥”“美文要素”是指“不成其为日语的汉语,一概不使用”这件事。对此,二叶亭证实说他选择了“诗性的”“在式亭三马(1776—1822,日本江户后期著名小说家,著有《浮世澡堂》等‘滑稽本’——译注)作品中常见的所谓深川方言”来创造新的文体。在二叶亭那里,“俗语”是作为与汉文体乃至汉文训读体相对峙的文体而被选取的。 作为二叶亭拒绝汉文体的理由而提及的田口鼎轩,其见解是这样的: ……或许因为汉语听声音很难懂的缘故,若原封不动地用它来演讲,听者又能听懂的话,那么,这样的句子仅仅是具有中等以上生活有所富余的人才能习得,不得不说其带有贵族性的成分。盖文章只是谈话,故能谈话之人也能马上将其记录下来。若不如此,也就不是真正的文章了。(田口卯吉《日本开化的性质总算是必须改革了》,《东京经济杂志》246号,明治十七年十二月) 田口鼎轩认为汉文体不是“真正的文章”,这有两点理由: 一是汉文体的内容很难通过音声来把握,另一点是汉文体只有生活“富裕”的人才能掌握的。于是,必然地就有了“贵族性的成分”。换言之,田口的批判就在于: 汉文体要求能够视觉性地理解汉字的识字能力,于是就成了有余裕学习它的特权精英的垄断之物,民众是望尘莫及的。 "本书主要内容选自小森阳一先生的《作为结构的叙事》和《作为文体的叙述》两书。两本书互为“姊妹篇”,是作者重新解构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它把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后殖民批判结合起来,重新解读经典的文学文本,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小森认为,小说是永远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关系正是将作品活性化的能量。这些文章,以崭新的方法解读文学经典,在激活文学想象力的同时,为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人的处境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并提示了可能的突围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