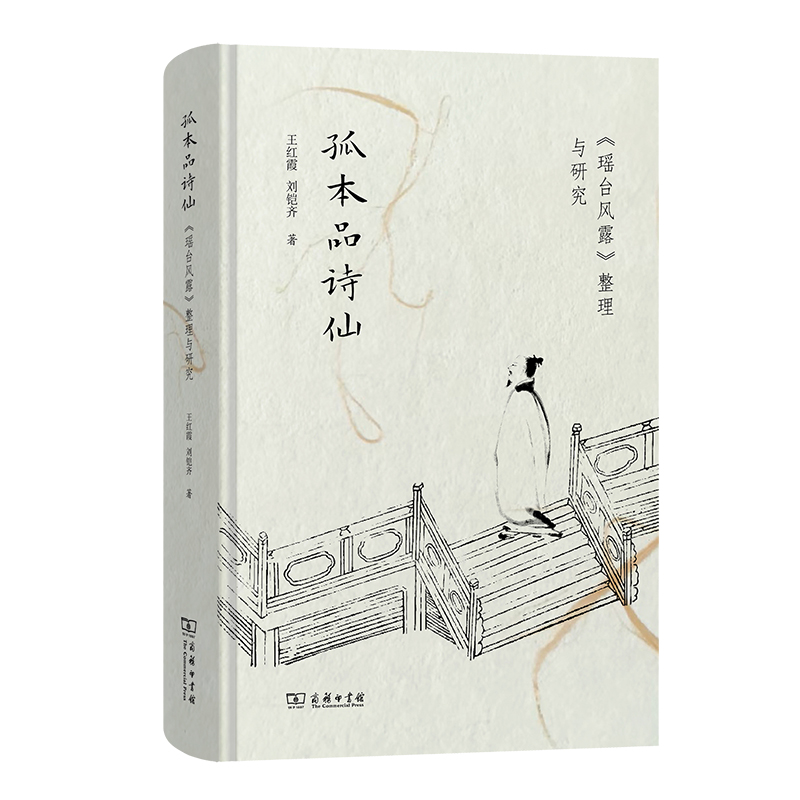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8.60
折扣购买: 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精装)
ISBN: 9787100228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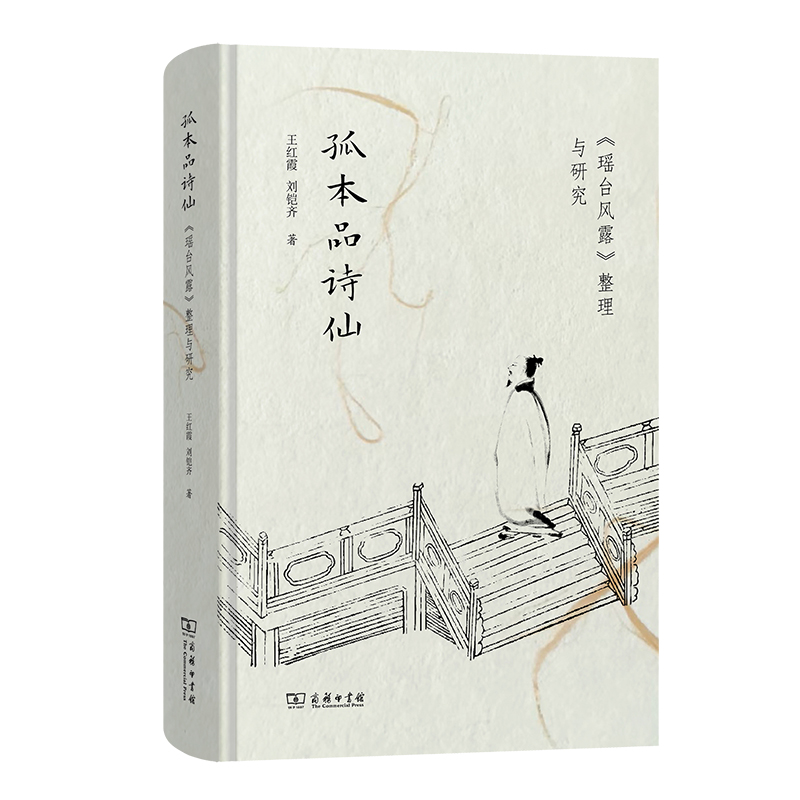
王红霞,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四川杜甫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和域外汉学。先后获四川省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四川省第15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2部:《权德舆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主编四川省委宣传部重点项目第一批历史文化名人《李白研究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中国国家图书馆、韩国国学振兴院等课题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陆所藏汉文古籍题跋整理与研究”的科研工作,目前承担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子课题、和1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刘铠齐,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主持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和杜甫研究中心课题两项,参与四川省区域和国别重点研究基地韩国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韩国诗话对李白的接受与传播研究”的科研工作。
《礼记·经解第二十六》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湿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可见,“温柔敦厚”是言以委婉的方式进行讽谏,讲求温和宽厚,即所谓“怨而不怒”。“诗教”一词,本来专指《诗经》的教化作用,后来泛指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 对于诗歌的社会功用,孔子早有言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所谓“怨”,是指怨刺时政,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节制地表达感情。正因为诗歌有节制情性、教忠育德的作用,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诗教。然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诗歌的教化功用,使其沦为人们日常抒情和娱乐的工具。于是,清代许多文人开始上溯诗歌的源头,主张恢复诗教传统。沈德潜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在《说诗晬语》中称:“(诗)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而诗教远矣。”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也是本着恢复诗教传统的目的来选诗的,《清诗别裁集》序云:“然而不嫌其少者,以牧斋、竹垞所选,备一代之掌故,而予惟取诗品之高也。不嫌其多者,以殷璠、高仲武只操一律以绳众人,而予唯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由此,足以见得他对诗教传统的重视。 《瑶台风露》的编选者鲍瑞骏和王鸿朗亦是如此,他们将诗教传统中“温柔敦厚”的思想情旨作为其重要的选诗标准之一。后人论及唐代最杰出的诗人时,多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而认为李诗的思想情旨有悖于诗教。实际上,李白的诗歌创作并非无关于人伦风教,他在《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中写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李白想效仿孔子,以诗文来反映王政得失,明是非而寓褒贬,垂教于后世。这不正应合了儒家诗教当中“兴观群怨”的宗旨吗。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的诗教传统其实已在李白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所谓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即是说反映王政兴废的文学作品许久都没有出现了,以诗文来恢复古道,舍我其谁!而李白的诗文复古之中,当然也包括了对诗教的恢复。 因此,为了呈现李白这一特点,《瑶台风露》在选诗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思想情旨较为“温柔敦厚”的篇目。上文提到的《东海有勇妇》《怨歌行》《去妇词》等诗为大多数选本所遗漏,而《瑶台风露》偏偏选入,这也体现出鲍瑞骏与王鸿朗二人对于诗教的重视。 解读现存唯一李白五言古诗选本,品味诗仙飘逸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创作技法。精品孤本:《瑶台风露》是已知现存唯一的李白五言古诗选本,未经刊刻,原本藏于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选诗共计179首,有批语近800条。 细致解读:原汁原味呈现《瑶台风露》孤本,广罗相关文献,详细注解、细致分析,展现李白五言古诗风貌,呈现清代诗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