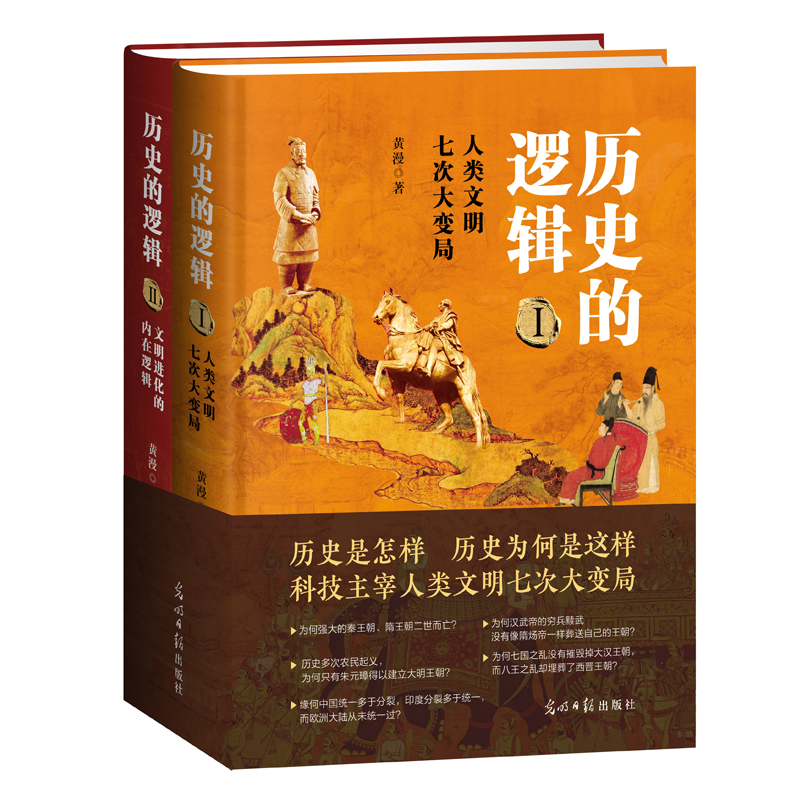
出版社: 光明日报
原售价: 238.00
折扣价: 147.60
折扣购买: 历史的逻辑(1-2)
ISBN: 9787519468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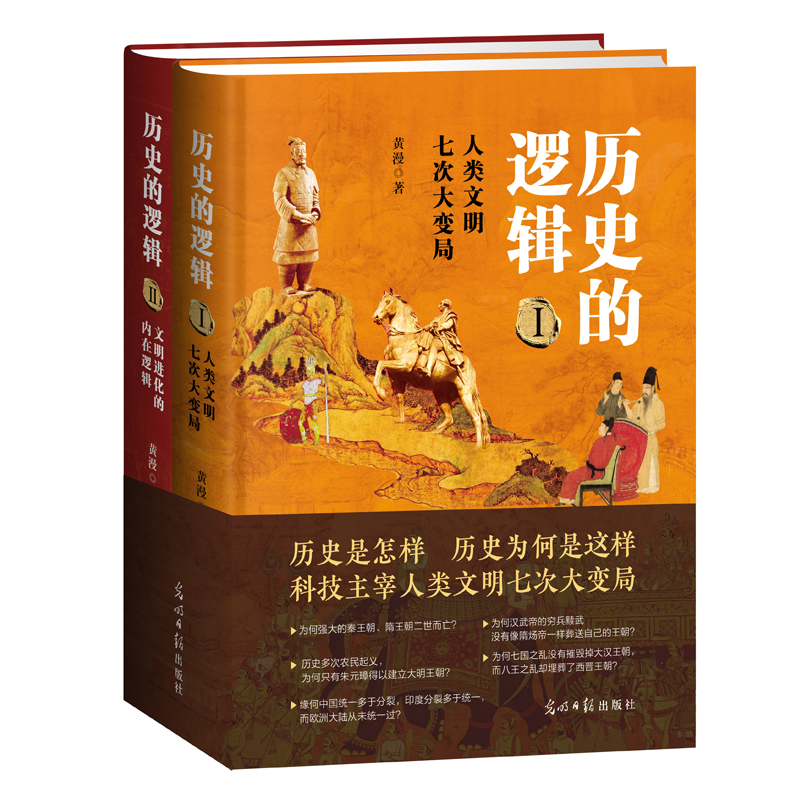
黄漫,湖南人,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学硕士。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红塔证券,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长期从事世界经济研究和金融投资管理工作。 2015年开始将过去在历史、经济上的研究整理出书,曾出版《文明简史:历史为什么是这样》。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遥远而神秘的太古宇宙中,太阳星云在什么时候游荡到今天的太阳系位置,逐渐聚集形成了太阳。太阳星云的一小部分,和星际物质不断地碰撞、结合,经过几亿年的时间,逐渐形成一颗小小的地核星子, 围着太阳年复一年默默地旋转。又花了几亿年时间,它在浩瀚渺茫的太空中缓慢地捕获熔融物质、塑性物质、固态物质、气体和液体,终于长成了一颗滚烫的岩石星体,那便是我们婴儿时期的地球。 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转动,地壳有了自东向西的漂移, 形成海洋和陆地、群山和深壑、高原和盆地。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岁月,多少个纪元,经历了多少陨石和彗星的撞击,掀开的地幔混杂着陨石碎块抛向无垠的轨道,才有了今天动人的月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大唐盛世中叩问苍天的才子们,又何曾想到当初映照月亮的,大抵只有滚烫的熔岩了。这些熔岩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分层,高密度的金属物质开始沉落富集在地核, 于是我们的地球有了一颗钢铁的心脏。在月球引力所形成的潮汐作用下,地球的外球发生了旋转,形成地极和磁极的移动——钢铁心脏开始搏动。这一刻, 还没有广寒宫的月亮,撕开了五指山上镇压孙大圣的六字真言,从此磁极为地球建造了一个美丽的保护罩,避开了地狱般的高能等离子体——太阳风。又过了多少个世纪,地壳慢慢平和,地表渐渐冷却,原核生物终于有了自己古老的家园。 从这种原核生物开始计算,地球上总共大约生存过10 亿个物种。今天的物种究竟还剩下多少,似乎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因为生物学家们还无法把地球上每个角落都做好严格的物种普查。据有些生物学家估计,现存的生物大约有870 万种。也就是说另外的9.9 亿多个物种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洪水、冰川等季候变迁而匆匆灭绝了,只留下不到1% 极少数幸存者得以艰难地生存下去。现今被我们认识和描述的物种大约有870 多万种,其中包括777 万种动物,29.8 万种植物,61.1 万种真菌,3.64 万种原生动物,2.75 万种藻类。 这些巨大的数字,无不令人震撼不已,我们甚至无法感受它真实的意义。如此浩大的生物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竭尽所能地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一亿年又一亿年,从原核生物到动物,从单细胞到腔肠动物,从蠕形动物到软体动物,从贝类动物到脊椎动物,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从灵长目到直立人、到智人,最终才有了我们现代人类。而这中间每一步的进化过程,看上去平淡无奇,却要耗费无数个万年。 人类是渺小的,我们只是生物界10 亿物种中的一分子。数以亿万计的物种死于非命,只为寻找这世间能穿越时空的生存方案。当你远赴太空,遥远地观察着地球生命几十亿年的脉络经纬,不禁会说,人类又是伟大的。我们是地球这台巨型计算机,用10 亿个物种进程并行计算,耗费了近40 亿年,才找到的那唯一穿越时空的解。 20 万年前非洲东部的直立人进化出了现代智人,跟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那茂密的树林里无数次花开花落,辽阔的草原上无数次日升月起。又这样过了14 万年漫长而平淡的岁月,人口越来越多,食物越来越少,智人们终于被迫走出非洲,“世界那么大,咱得去看看”。 于是他们用脚步探索着苍茫的世界,用血肉对抗着无情的自然。他们徒步干燥的沙漠,攀登陡峭的群山;他们横渡凶险的海域,跨越冷冽的冰川;他们蹚进泥泞的沼泽,出没野兽的大荒。 他们尝遍艰辛和苦难,他们历尽幽怨与悲伤;他们为每一口食物流尽了鲜血,为每一次死亡哭干了眼泪;他们掩埋了多少相濡以沫的亲故,失散了多少生死相随的宗族。 就这样他们四海漂泊、飞蓬柳絮,布满每一块海岛和大陆;他们辛勤劳作、胼手胝足,只为顽强地生存与延续,终于才有了今天人类社会璀璨繁星般的伟大文明。 然而生物进化在人类DNA 层面似乎已然停止,除了最后分化出不同肤色的种族外,今天的我们和20 万年前的智人所差无几。目前地球上有70 多亿人口,而任何两个异性之间,都能实现繁殖,并没有产生生殖隔离。拥有70 亿人口只有一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这无疑是巨大的奇迹。自然环境对个体人类基因的选择似乎已经失效,族群中的老弱病残依然能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娶妻婚配,每一个女人都有权生儿育女,而每一个孩子都有权生存,于是所有的基因都被接纳了。所有的遗传疾病都能在今天找到, 所有的基因缺陷都能在今天留存。什么自然选择,什么获得性遗传,什么用进废退,什么灾变理论,什么中性漂变,这所有的进化假说,通通失效了。这个驱动着自然界几十亿年的进程到底遭遇了什么?是失败了?抑或暂停了?还是永远地结束了? 生物进化学说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从达尔文时期以个体为基本进化单位,逐渐过渡到现代一致认为以物种为基本进化单位,基因的变异是以种群为单位积累。以个体生命的视界,我们看不到任何变异的积累,以及适应性;于是跳出个体生命的框架,以种群的视野,基因演化的路径就一目了然。但这一观点仍然是有局限的,因为发现不了基因演化有任何的方向性,种群似乎仅仅只是适应环境的随机漂变。于是我们应该跳出种群的框架,以生命的大视野,进化的方向终于划开了重重阴云一目了然——智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如果始终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对于生命来说生存和毁灭永远是旦夕之间。只有能改变环境的物种,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任它寒来暑往、潮升海退,我自立于不败之地。而这就是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所开创的世界。 我们的祖先活得卑微而伟大。当我们每天早上为了是吃西式三明治还是中式面点,而苦恼挣扎一番的时候,何曾能理解那些在蛮荒世界,仅仅为了一块过夜的腐肉,为了一颗青涩的果实,就要跟野兽厮斗、跟环境肉搏的先祖们的顽强意志。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如此考究地吃喝,如此优雅地生活,只是因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统治了地球。 不管承不承认,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的主宰。 地球已经被人类彻底驯服了,环境被大规模地改造。我们发明了钢筋水泥,建造了总面积达几十万平方千米的摩天大厦;我们砍伐森林制造出万能的工具,夷平丘陵耕种平坦的农田;我们铺设巨大的悬索吊桥跨过江河和沟壑,铺设颀长的地下隧道穿越崇山和海底……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改变地球的步伐?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根基已经如此深厚,即使偶尔肆虐的超级地震、台风和海啸使人类有所损失,对这个有着70 亿人口的社会来说,其影响似乎不值一提。 这个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物种、数以万亿计的生物个体,只是各自为战,被自然界困在自己小小的生态位上苦苦挣扎。而我们人类却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社会化,用每一个个人的智能,组建了规模庞大的群体智能,然后创造、扩展和统一了自己的生态位。我们分化了各种职业系统,解决环境和自然一个个的生存难题;分化出了政治管理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决策、神经系统;分化出了军事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肢体战斗系统;分化出了司法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免疫系统;分化出了生产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呼吸和饮食系统;分化出了工商管理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血液和体液循环系统。这个社会已然成为一个超级生命体,以我们个体无法感知的智能,悄然无声地驯服和打造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唯我独尊。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各种社会结构,以及附着在社会物理实体之上的所有精神、道德、文化知识被统称为文明。 文明是一个超级生命体。文明是地球上的主神。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遥远而神秘的太古宇宙中,太阳星云在什么时候游荡到今天的太阳系位置,逐渐聚集形成了太阳。太阳星云的一小部分,和星际物质不断地碰撞、结合,经过几亿年的时间,逐渐形成一颗小小的地核星子, 围着太阳年复一年默默地旋转。又花了几亿年时间,它在浩瀚渺茫的太空中缓慢地捕获熔融物质、塑性物质、固态物质、气体和液体,终于长成了一颗滚烫的岩石星体,那便是我们婴儿时期的地球。 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转动,地壳有了自东向西的漂移, 形成海洋和陆地、群山和深壑、高原和盆地。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岁月,多少个纪元,经历了多少陨石和彗星的撞击,掀开的地幔混杂着陨石碎块抛向无垠的轨道,才有了今天动人的月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大唐盛世中叩问苍天的才子们,又何曾想到当初映照月亮的,大抵只有滚烫的熔岩了。这些熔岩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分层,高密度的金属物质开始沉落富集在地核, 于是我们的地球有了一颗钢铁的心脏。在月球引力所形成的潮汐作用下,地球的外球发生了旋转,形成地极和磁极的移动——钢铁心脏开始搏动。这一刻, 还没有广寒宫的月亮,撕开了五指山上镇压孙大圣的六字真言,从此磁极为地球建造了一个美丽的保护罩,避开了地狱般的高能等离子体——太阳风。又过了多少个世纪,地壳慢慢平和,地表渐渐冷却,原核生物终于有了自己古老的家园。 从这种原核生物开始计算,地球上总共大约生存过10 亿个物种。今天的物种究竟还剩下多少,似乎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因为生物学家们还无法把地球上每个角落都做好严格的物种普查。据有些生物学家估计,现存的生物大约有870 万种。也就是说另外的9.9 亿多个物种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洪水、冰川等季候变迁而匆匆灭绝了,只留下不到1% 极少数幸存者得以艰难地生存下去。现今被我们认识和描述的物种大约有870 多万种,其中包括777 万种动物,29.8 万种植物,61.1 万种真菌,3.64 万种原生动物,2.75 万种藻类。 这些巨大的数字,无不令人震撼不已,我们甚至无法感受它真实的意义。如此浩大的生物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竭尽所能地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一亿年又一亿年,从原核生物到动物,从单细胞到腔肠动物,从蠕形动物到软体动物,从贝类动物到脊椎动物,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从灵长目到直立人、到智人,最终才有了我们现代人类。而这中间每一步的进化过程,看上去平淡无奇,却要耗费无数个万年。 人类是渺小的,我们只是生物界10 亿物种中的一分子。数以亿万计的物种死于非命,只为寻找这世间能穿越时空的生存方案。当你远赴太空,遥远地观察着地球生命几十亿年的脉络经纬,不禁会说,人类又是伟大的。我们是地球这台巨型计算机,用10 亿个物种进程并行计算,耗费了近40 亿年,才找到的那唯一穿越时空的解。 20 万年前非洲东部的直立人进化出了现代智人,跟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那茂密的树林里无数次花开花落,辽阔的草原上无数次日升月起。又这样过了14 万年漫长而平淡的岁月,人口越来越多,食物越来越少,智人们终于被迫走出非洲,“世界那么大,咱得去看看”。 于是他们用脚步探索着苍茫的世界,用血肉对抗着无情的自然。他们徒步干燥的沙漠,攀登陡峭的群山;他们横渡凶险的海域,跨越冷冽的冰川;他们蹚进泥泞的沼泽,出没野兽的大荒。 他们尝遍艰辛和苦难,他们历尽幽怨与悲伤;他们为每一口食物流尽了鲜血,为每一次死亡哭干了眼泪;他们掩埋了多少相濡以沫的亲故,失散了多少生死相随的宗族。 就这样他们四海漂泊、飞蓬柳絮,布满每一块海岛和大陆;他们辛勤劳作、胼手胝足,只为顽强地生存与延续,终于才有了今天人类社会璀璨繁星般的伟大文明。 然而生物进化在人类DNA 层面似乎已然停止,除了最后分化出不同肤色的种族外,今天的我们和20 万年前的智人所差无几。目前地球上有70 多亿人口,而任何两个异性之间,都能实现繁殖,并没有产生生殖隔离。拥有70 亿人口只有一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这无疑是巨大的奇迹。自然环境对个体人类基因的选择似乎已经失效,族群中的老弱病残依然能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娶妻婚配,每一个女人都有权生儿育女,而每一个孩子都有权生存,于是所有的基因都被接纳了。所有的遗传疾病都能在今天找到, 所有的基因缺陷都能在今天留存。什么自然选择,什么获得性遗传,什么用进废退,什么灾变理论,什么中性漂变,这所有的进化假说,通通失效了。这个驱动着自然界几十亿年的进程到底遭遇了什么?是失败了?抑或暂停了?还是永远地结束了? 生物进化学说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从达尔文时期以个体为基本进化单位,逐渐过渡到现代一致认为以物种为基本进化单位,基因的变异是以种群为单位积累。以个体生命的视界,我们看不到任何变异的积累,以及适应性;于是跳出个体生命的框架,以种群的视野,基因演化的路径就一目了然。但这一观点仍然是有局限的,因为发现不了基因演化有任何的方向性,种群似乎仅仅只是适应环境的随机漂变。于是我们应该跳出种群的框架,以生命的大视野,进化的方向终于划开了重重阴云一目了然——智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如果始终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对于生命来说生存和毁灭永远是旦夕之间。只有能改变环境的物种,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任它寒来暑往、潮升海退,我自立于不败之地。而这就是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所开创的世界。 我们的祖先活得卑微而伟大。当我们每天早上为了是吃西式三明治还是中式面点,而苦恼挣扎一番的时候,何曾能理解那些在蛮荒世界,仅仅为了一块过夜的腐肉,为了一颗青涩的果实,就要跟野兽厮斗、跟环境肉搏的先祖们的顽强意志。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考究地吃喝,如此优雅地生活,只是因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统治了地球。 不管承不承认,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的主宰。 地球已经被人类彻底驯服了,环境被大规模地改造。我们发明了钢筋水泥,建造了总面积达几十万平方千米的摩天大厦;我们砍伐森林制造出万能的工具,夷平丘陵耕种平坦的农田;我们铺设巨大的悬索吊桥跨过江河和沟壑,铺设颀长的地下隧道穿越崇山和海底……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改变地球的步伐?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根基已经如此深厚,即使偶尔肆虐的超级地震、台风和海啸使人类有所损失,对这个有着70 亿人口的社会来说,其影响似乎不值一提。 这个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物种、数以万亿计的生物个体,只是各自为战,被自然界困在自己小小的生态位上苦苦挣扎。而我们人类却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社会化,用每一个个人的智能,组建了规模庞大的群体智能,然后创造、扩展和统一了自己的生态位。我们分化了各种职业系统,解决环境和自然一个个的生存难题;分化出了政治管理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决策、神经系统;分化出了军事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肢体战斗系统;分化出了司法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免疫系统;分化出了生产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呼吸和饮食系统;分化出了工商管理系统,这是群体智能的血液和体液循环系统。这个社会已然成为一个超级生命体,以我们个体无法感知的智能,悄然无声地驯服和打造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唯我独尊。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各种社会结构,以及附着在社会物理实体之上的所有精神、道德、文化知识被统称为文明。 文明是一个超级生命体。文明是地球上的主神。 1 本书一套两册,内文采用纯质纸印刷,精装,装帧精美,适合阅读和收藏。 2作者将历史学穿插进了数理逻辑分析的范畴,综合了多种史学理论的论述,既有严密的逻辑性,又有严谨的专业性,见解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