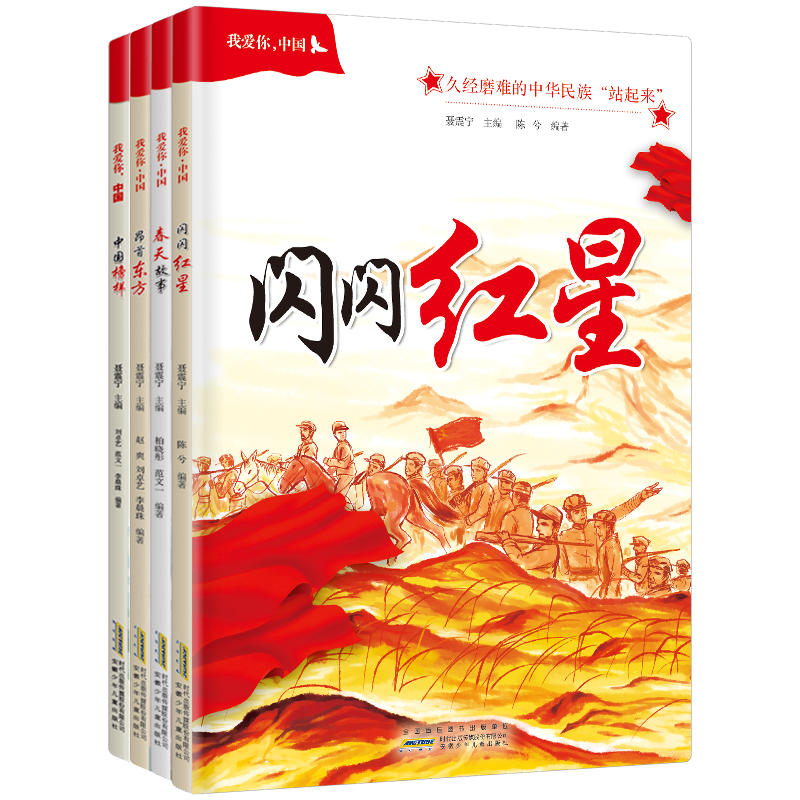
出版社: 安徽少儿
原售价: 100.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我爱你,中国系列(套装共4册)
ISBN: 9787539757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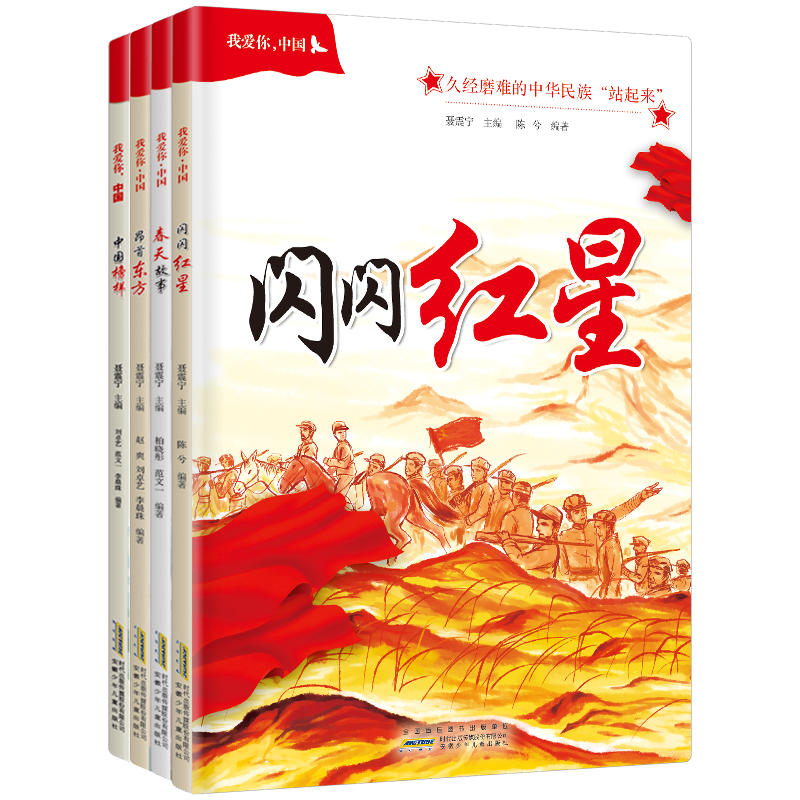
聂震宁,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中央党校法学理论研究生班。历任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文化局干部,《金城》文学编辑,漓江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委书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中国出版集团总裁、党组副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曾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首届庄重文文学奖等。代表作有《我的出版思维》《暗河》等;策划的图书曾获中国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或提名奖。
超级工程:“天眼”和“蛟龙” “上天他比天要高,下海他比海更大……”这句歌词唱的是神话英雄小哪吒——这部动画片曾是许多孩子的童年最爱,相信你也一定看过。可“上天”“下海”这些原本只存在于中国神话故事中的超级幻想,如今却真的以“超级工程”的形式实现了,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天眼”和“蛟龙”。 “天眼”工程坐落于贵州省喀斯特地貌区的洼地,其实是一台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选择建在喀斯特地貌区,是因为那里更符合“天眼”碗一样的外形,并且盆地地形易使水向下流走,不会对“天眼”造成腐蚀。“天眼”的球面口径长达500 米,整体约有30 个足球场大,在外形上的确很像一只“观察世界的眼睛”——“天眼”的“索网结构”可以根据天体的运动而调节、变化。 “天眼”系统的科学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接收到上百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观测范围可到达宇宙边缘,不仅可以用来寻找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还可以收集关于宇宙的更多信息,探索更广阔的外太空文明,同时也代表着当今世界科学界的最前沿。包括中国天文学家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的科学工作者,都为“天眼”的出现感到振奋,并对其寄予厚望。澳大利亚科学及工业研究院帕克斯(Parkes)望远镜科学主管乔治·霍布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天眼”甚至还能监测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发出的无线电波。对此中方的科学家也确认,搜寻地外文明,或者说外星人,的确是“天眼”的终极目标之一。 中国“天眼”与号称“地面最大的机器”的德国埃菲尔斯伯格100米口径望远镜相比,灵敏度提高了约10 倍;而与被评为人类20 世纪十大工程之首的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相比,灵敏度提高了一倍多。作为射电天文学界的重要突破,“天眼”对数据存储与计算的需要同样也是“天文级”的,其短期内计算性能要求至少高达每秒200 万亿次以上;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和科学任务的深入,其对计算性能和存储容量的需求还将爆炸式增长,说它是“超级工程”毫不夸张。 “三分陆地,七分海洋。”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以上,因此人类在仰天探索宇宙神奇的同时,还必须入海深潜,充分了解海洋的秘密,从而找到更多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空间。 于是,与“天眼”遥相呼应的另一项“超级工程”——“蛟龙”号应运而生。“蛟龙”号其实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深海潜水器,由1000 多人参与,历经6 年多才研制成功。它可以通过机械手下潜到几千米深的海底获取海水样本、抓取海洋生物信息,甚至直接在海里钻孔找矿物,然后带回到母船上研究。 “蛟龙”号长8.2 米、宽3 米、高3.4 米,它所使用的耐压结构、生命保障、远程水声通信、系统控制等关键技术难点都是中国人自己突破的,可谓是条地道的“中国龙”。 2012 年6 月,“蛟龙”号在地球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也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深下潜深度纪录。这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在全球99.8% 以上海洋深处作业的能力。而到达这个深度时,“蛟龙”号全身每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面积都承受着约达一辆坦克重量的压力。全世界都为它捏了一把汗,但“蛟龙”号最终经受住了考验。 除了开发海洋资源,“蛟龙”号还有一大功能,就是进行海底救援。它能运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入深海,在海山、洋脊和盆地等复杂海底进行科考。“蛟龙”号是科学家们的坐骑,也是他们的手,更是他们的安全保障。未来,“蛟龙”号世界级探索船将正式下潜,届时探索效果将大幅度提高,探测时间将大幅度增长。 从“深海进入”到“深海探测”,再到“深海开发”,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预示着我国在深海探测技术方面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个别领域领跑的水平,令人自豪。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两大夙愿,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下实现,何其有幸!当“天眼”深情、庄重地仰望星河,当“蛟龙”浪漫、自由地遨游海底,谁说中国人的神话故事只是远古幻想?谁说它们不会造福人间?驾驭它们的,唯有高科技! “敦煌女儿”——樊锦诗 “白天想的是敦煌,晚上梦到的还是敦煌。”50多年来,从青丝到白发,从少女到耄耋老人,樊锦诗为“敦煌母亲”交出了一份问心无愧的科研答卷。 樊锦诗,浙江省杭州市人,1938年出生于北京,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至今,樊锦诗已在敦煌研究院工作50余年,毕生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被誉为“敦煌女儿”。 “我今年80岁,能为敦煌做事,我无怨无悔!”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刚考上北大时,樊锦诗根本没想过自己将来会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这一去就是50多年。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 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虽然事先有些心理准备,但当地生活的艰苦程度还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在敦煌洗完头之后,头发都是黏的,因为水的碱性太高了。”但即便如此,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还是留了下来。“那个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青年人的主流价值观。”更何况,敦煌已经令她着迷。“越接触敦煌,越觉得它真是深不及底;越了解敦煌,也就越热爱敦煌。”于是,那年夏天,樊锦诗这个瘦弱的年轻女子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坐上了从北京到敦煌的火车。那一年,她25岁。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文物研究院。 樊锦诗见证了这一切。现在,在研究院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人们仍能看见一座以初到敦煌的她为原型的雕像,叫作《青春》。 来到气候恶劣的大西北,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工作的艰辛尚不必说,生活的“落差”更是连许多七尺男子汉都承受不住。单位里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信困难;电力设施不完善,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更要跑很远。“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但最终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一天天下来,敦煌石窟已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白天想的是敦煌,晚上梦到的还是敦煌。”50多年来,从青丝到白发,从少女到耄耋老人,樊锦诗为“敦煌母亲”交出了一份问心无愧的科研答卷。在考古研究方面,她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同时,由她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对百年敦煌石窟研究做出了集中展示。 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后,她带领团队更加积极地致力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为了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她费尽千辛万苦构建“数字敦煌”——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和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与此同时,她还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建设,探索科学保护石窟的理论与方法,为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用了一个词形容樊锦诗所做的一切:功德无量。 然而,作为一名女性和母亲,在致力于石窟保护和管理的同时,樊锦诗对家庭和孩子又何尝没有眷恋之情。她的丈夫彭金章曾说道:“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地守护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新,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回忆往事,樊锦诗说:“我至今仍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谈到敦煌,她又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本套书既是对当下中小学生学习的历史、地理、道德与法制等课本的解读和补充,又是一套紧紧围绕五四运动100 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念而撰写的献礼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