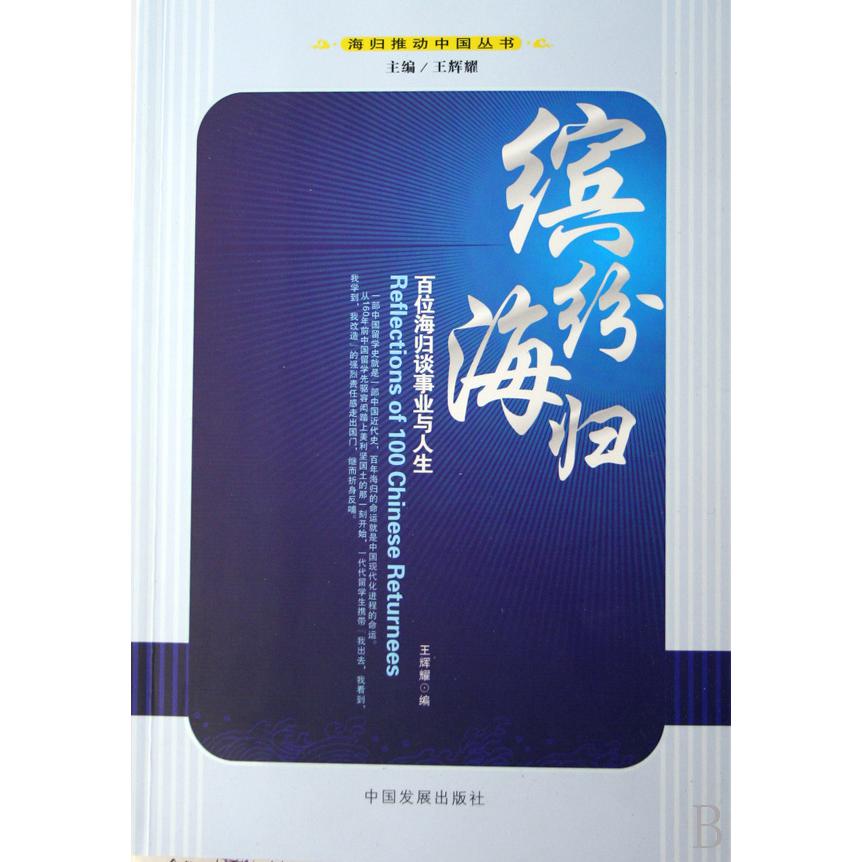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发展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9.20
折扣购买: 缤纷海归(百位海归谈事业与人生)/海归推动中国丛书
ISBN: 978780234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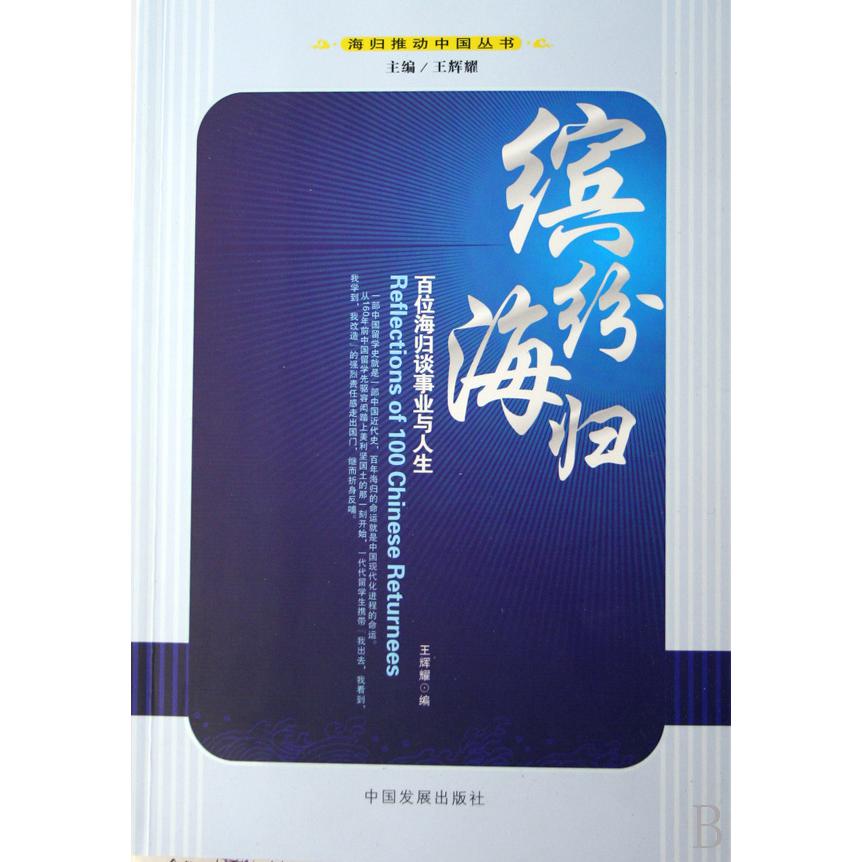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组特聘专家,国家多个部委课题研究组组长和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北京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以及多家地方政府顾问,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提交多项专题研究和政策性报告。分别于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商学院学习,获得MBA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著有《开放你的人生》、《国家战略》等多部畅销书。
我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没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个,我 排行第五。 1979年,我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第一次到了长沙,我的世界从 此开阔起来。我的同学,已经开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了,而我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没有任何课外书刊,借不到 ,也没钱买。 宿舍一位周刚同学的父亲,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我从他那儿 借到了《中国日报》。1986年初,在国防科大拿到硕士学位后,我不想再学 工科了,但是学校不让我走,要我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我是进入 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半年后,我申请了出国留学。 我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因为考试需要美元,而当时外汇管制严, 我当时一美元都搞不到。没办法,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说明缘 由。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有奖学金。按当时政策,一有工作,二有奖 学金,算自费公派出国,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1986年8月,我身揣 80美元,坐上了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飞机。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对万历十五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不感 兴趣,但我喜欢经济史和社会史。我的分析方式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史料便 是在这一视角下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让历史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 史料证明了还是证伪了我的观点,都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学者能体验到的最 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实在太 少了。 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养老问题,你会发现实际上很 多老人的晚年过得并不幸福。这是怎么回事?解决方案在哪里? 中国的孩子,小时候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没 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负担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 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在赡养父母上,可能会互相推诿。 做父母的,可能会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生存呢?觉得 自己是累赘,是负担,更不幸福。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家庭 都不幸福,而是说,要有勇气正视并非小面积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 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 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唯一养老途径。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 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交流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 有了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们未来的保障,他们已经通 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 己言听计从。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观念,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而逼 出来的。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凭空而来的。举例说,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没有 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 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 的是家族、宗族。或者说,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和信贷,后 代是这些金融证券的具体替代。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 ,是隐形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 县太爷,而是靠文化。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 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 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 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证明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 会脱节得太厉害了。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导什么 ,而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我们的教科 书,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书不从根 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经常被教科书 上的那些错误分析框架、错误理论蒙蔽了。 在美国生活21年,越来越发现,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都有自己的利 益诉求,都受到利益的驱动。美国人也不喜欢什么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们 知道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来拒绝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 识。 P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