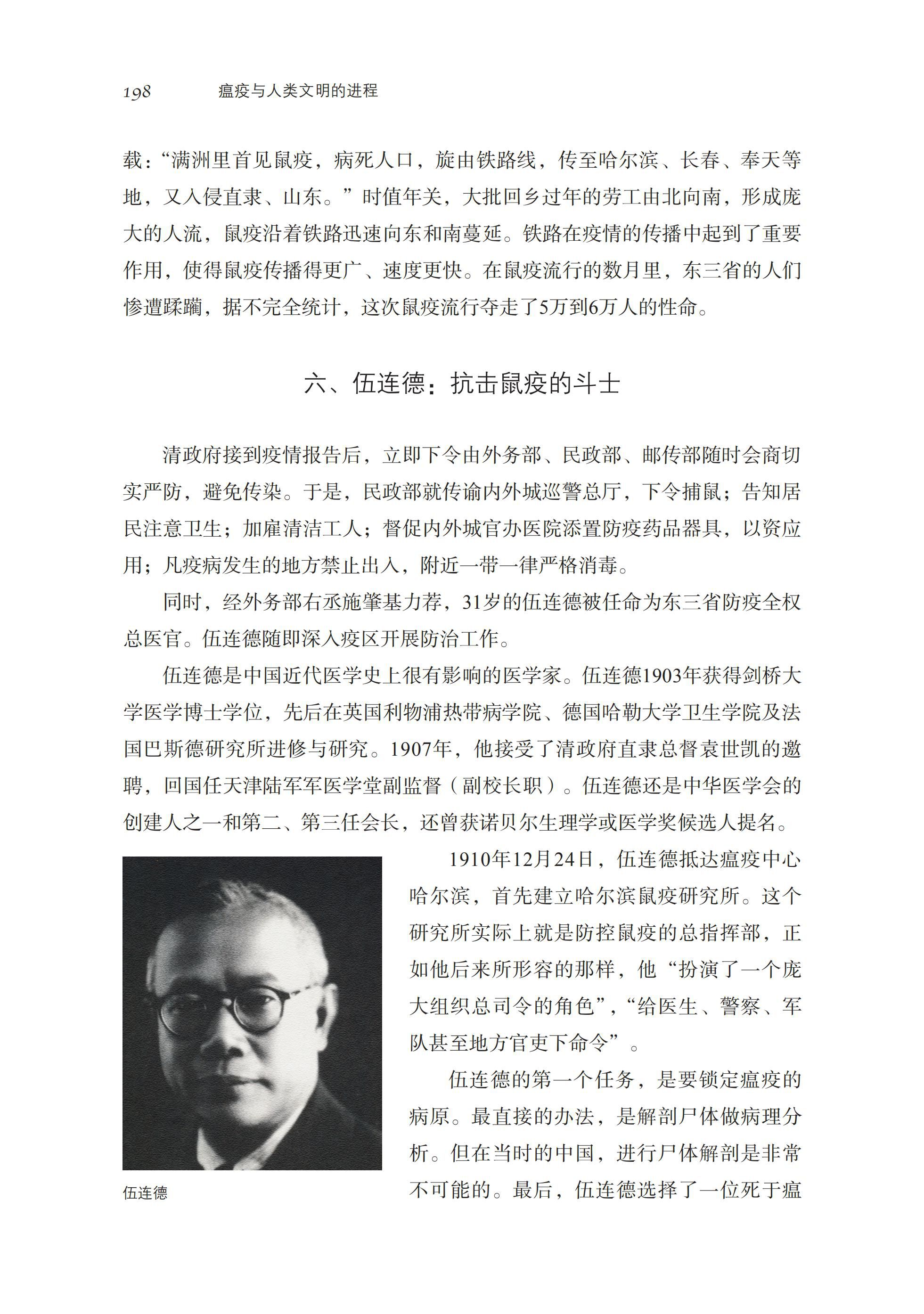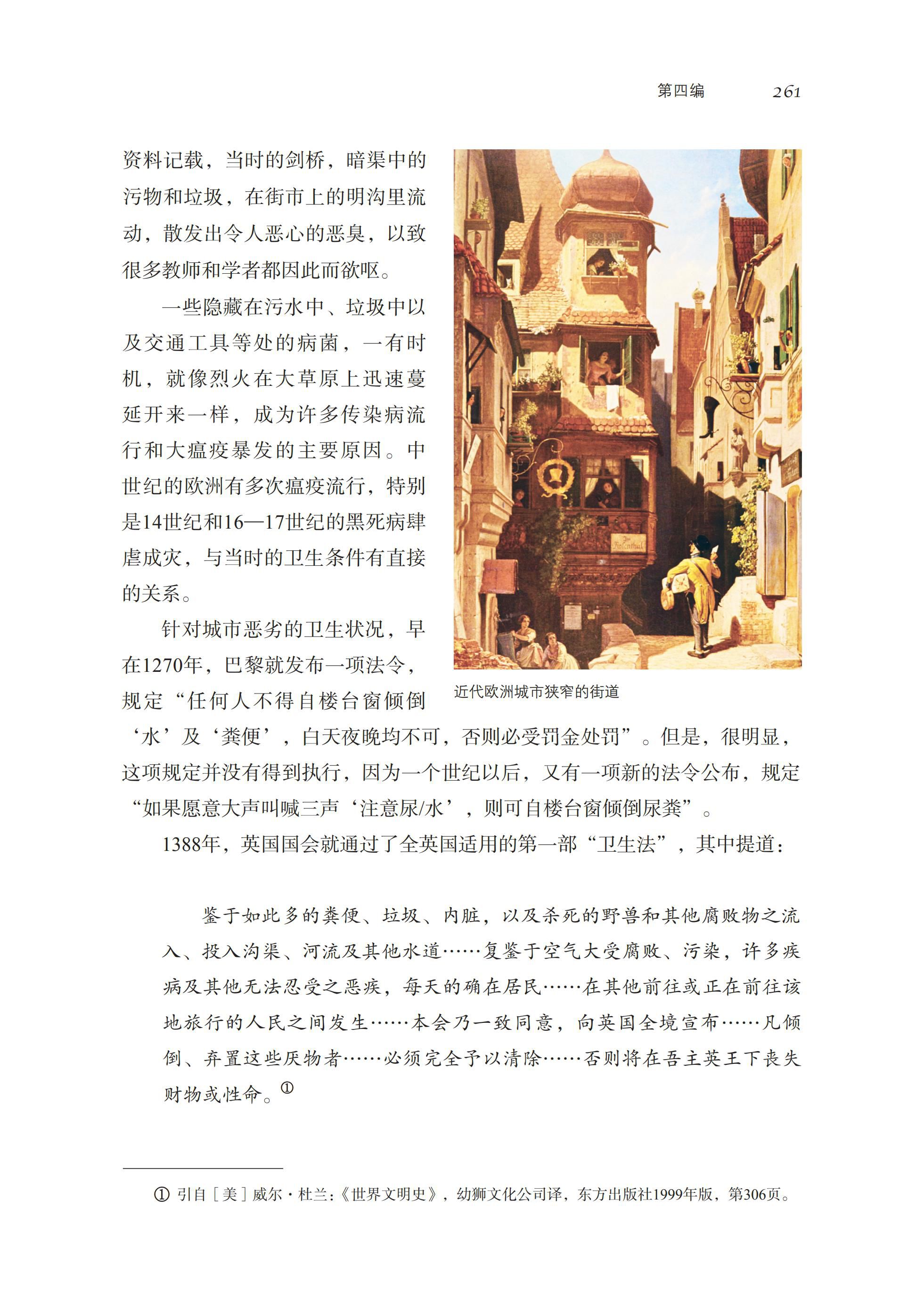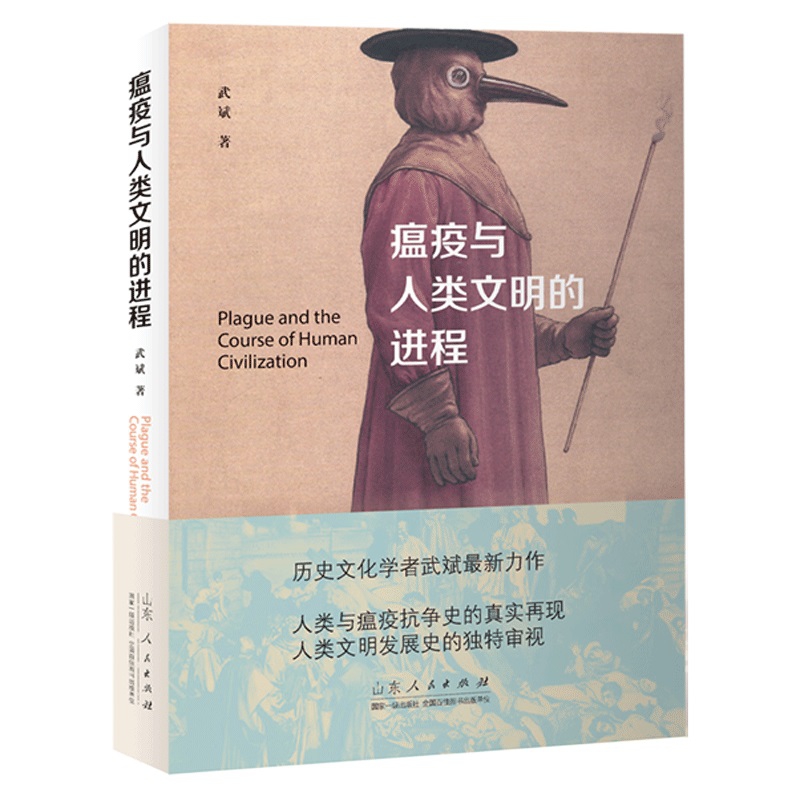
出版社: 山东人民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瘟疫与人类文明的进程
ISBN: 9787209126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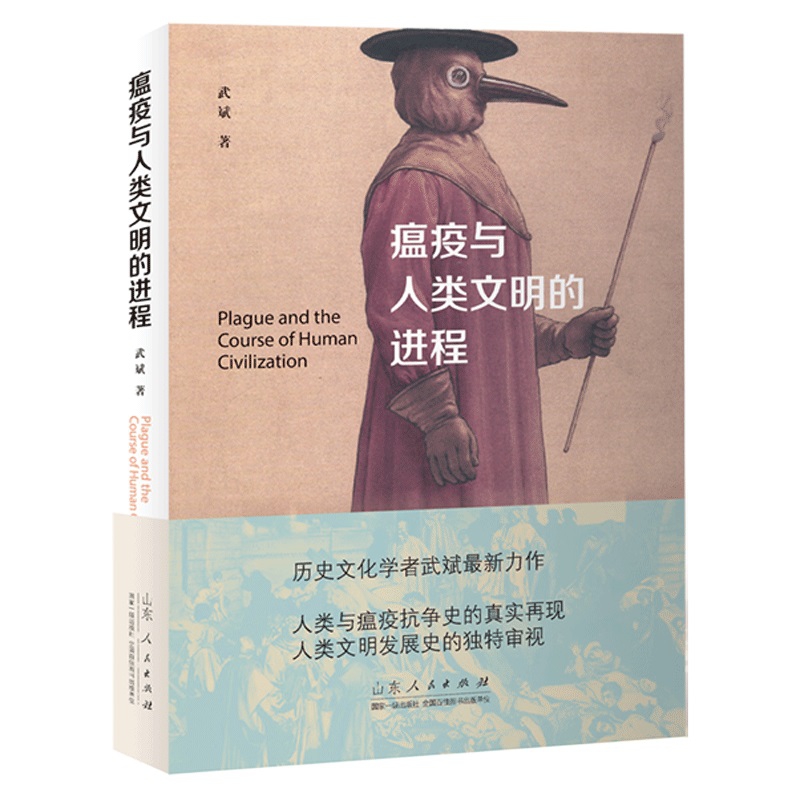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丝绸之路全史》《丝绸之路史话》《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其中,《丝绸之路全史》入选“2018年度30本中国好书”,《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
第1章 瘟疫与人类文明相伴生 一、瘟疫是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是时常出现的。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有瘟疫的记载。有的是小规模的、局部地区的,也有的是大规模暴发的、蔓延全国范围的,文献上叫“大疫”。三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仅这样的“大疫”就发生了几十回,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这样,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一直到现代,几次大的瘟疫暴发,都给人类文明以沉重的打击,甚至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走向。 那么,我们说的瘟疫指的是什么呢? 一般说来,瘟疫就是传染病。根据现代疾病细菌学说,传染病是微生物侵入宿主体内并在生长和繁殖时破坏宿主身体而造成的。传染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一个生物体传染到另一个生物体。有些疾病有很强的传染性,这意味着病人可以把疾病传染给许多新的受害者。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是人类生存的大敌。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染病都被称为瘟疫。“瘟疫”(Plague)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lege”和拉丁语“Plaga”,意思是“打击”或“冲击”,与“疫病”(Pest)、“时疫”(Pestilence)、“痘症”(Pox)等词语类似。“瘟疫”一词主要用于描述一系列毁灭性的流行性疾病。 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造成大的危险和危害的瘟疫主要有麻风病、鼠疫、天花、斑疹伤寒、梅毒、结核、霍乱、流感等,还有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艾滋病、埃博拉等等,都是危害很大、传染性很强的传染病。其中,尤以鼠疫最厉害。两千年以来,鼠疫在历史中有几次大的暴发,给人类的健康、生命以及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人类获得与瘟疫的抗争的阶段性胜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取得了新的平衡时,有些传染病被彻底消灭了,比如天花;有些传染病则成了一般性的地方性疾病或受到很大遏制的传染病,不再会造成大规模的泛滥,比如斑疹伤寒、肺结核等。因此,它们就不再作为瘟疫存在。 被称为瘟疫的传染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瘟疫都是突然间暴发的。美国学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说:“大自然手中还挥舞着另外一件可怕的武-器:传染性疾病。它可以像夜行军一样, 突然间向人类社会发动袭击。”当然,瘟疫也有一个潜伏期或者说酝酿期,但这时人们并没有感觉,也没有警惕。突然之间,瘟疫在很短的时间内暴发,并且迅速蔓延。瘟疫的强大危害在于它的传染性。病菌或病毒的迅速传播和症状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口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很快被感染。有的研究 者概括了瘟疫流传的几条规律或者说共同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感染;第二,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感染的患者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 二是传播的广泛性。许多大规模的瘟疫,从一个起源地暴发,很快就通过交通、人员往来、军队的转移等渠道,迅速传播到广大的地区,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蔓延的地方非常广。例如6世纪出现的查士丁尼瘟疫,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暴发,之后,从城市到乡村,蔓延到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地方。近代以来,交通日益发达,商业和人员往来逐渐增多,都给瘟疫的蔓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有人说,只要有一架飞机,就可以把瘟疫从一个地方传到地球的另一端。所以,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瘟疫都是全球性大流行。 三是瘟疫的高死亡率。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以百万、千万计。在古代,凡是瘟疫席卷的地方,大多十室九空,尸横遍野,土地荒芜,城市废弃,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社会经济因此停滞甚至倒退,甚至人类历史因此发生重大改变。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泛滥,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有些城市的死亡率甚至达到了70%。在17至18世纪,全世界都流行天花疾病,死于此病的人数,在欧洲达到50万人,在亚洲多达80万人。在瘟疫肆虐期间,并不是所有的死者都是由疾病致死,而是因为大量人口死亡使得那些免于被感染而可能存活的人,也会因为缺乏食物、饮用水和起码的照顾而死去。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们找到了对抗瘟疫的科学方法,以及现代医学和医疗技术、社会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大多数受感染的人能够被治愈,这种高死亡率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四是急性的和大面积传染的特征,造成了瘟疫的极大恐怖性。因为瘟疫往往是在没有任何征兆和预示的情况下突然降临的,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对它一无所知、束手无策,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等到人们面对大量的感染和死亡而行动起来的时候,它却已经形成燎原之势,难以控制,所以会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 突发性、蔓延的广泛性、高死亡率以及造成的社会恐慌,是瘟疫的主要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瘟疫将会给人类及其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毁灭性影响。 二、瘟疫与人类文明共生 瘟疫是人类的大灾难。但是,瘟疫的产生,也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滋生并引发了瘟疫。瘟疫的强烈传染性需要足够数量和足够拥挤、稠密的人口,因而它们首先是“群众性”疾病。这样才能使瘟疫的病菌得以一代一代地存活。实际上,许多传染性疾病都需要一定数量——比如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聚集作为它们流行泛滥的基本条件。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历史的晚近时代,瘟疫出现得越频繁,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所以,瘟疫的产生一开始就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瘟疫的大规模流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旧石器时代,人们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来维持生活。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自然认识的逐步加深,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便取代了采集和狩猎的地位,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由“采集食物”进化到“生产食物”,被称为“产食革命”,这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Will Durant,1885—1981)也说,“农耕是文化的第一个形式”。 “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从两个革命来看:从狩猎到农业的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与由农业到工业的现代过程。没有其他的革命曾有如这两次革命的绝对真实或 基本性的。” “农业革命”这个重大事件几乎同时在世界各地发生,是在大约一万年前。农业文明的起源对以后的文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种植业的出现,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开始由游猎的移动生活方 式向定居生活方式转变,形成人类的聚居。人类除利用天然洞穴居住外,开始营建房舍。在河谷、台地等水源便利之处,逐渐形成村落,出现了早期的社会 组织。这个时候,已经具备瘟疫传播所必需的人口密度的条件。在这个阶段,定居的生活方式、单调的饮食、密集的居住点、对地貌的改造,以及旅行和交流的新技术,所有这些对微生物生态学以及人类种群的结构和分布都有影响。长期存在于大自然的疾病在新环境中迅速传播。农业使我们与家畜密切接触;城市创造了细菌传播所必需的人口密度;贸易网络的扩张让地方性病原体肆无忌惮地传播到其他处女地,导致了“文明疾病池的汇聚”。 从农业社会开始聚集起稠密的人口,而在以后几千年的城市发展中,实现了更大规模、更加稠密的人口聚集。与狩猎的生活方式相比,农业社会人口的密集程度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而与农业的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社会的人口密度更是上百倍的增加。数量巨大的定居人群为病原体从个人到个人以及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提供了许多机会。随着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长,人类成为许多疾病的合适宿主,而这些疾病先前仅仅在大量野生动物中发现过。 瘟疫产生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连接永久定居点的道路交 通网络为传播传染病提供了新的机会。人类的跨地区迁徙,灌溉农业的出现,城市的兴起,以及商队与商船的活动、战争、朝圣等行为,都伴随着瘟疫从一个疾病圈向另一个疾病圈传播,而瘟疫也深刻影响着人口发展与新定居地的开拓。大规模的战争、商贸活动以及各民族的大迁徙,使得病菌也随着这样的人口流动从一个人群传播到另一个人群,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特别是世界贸易的发展,很容易使在某地发生的一场瘟疫迅速超出国界的范围,成为全人类的灾难。比如在古罗马时代,这样的世界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 有效地连接成为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更是把瘟疫的危害带到了全世界。欧洲殖民主义者登上美洲大陆,带去的天花等致命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空前的人口灭绝。因此,可以说,瘟疫是随着人类社会(“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的发展而发展的。 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是研究瘟疫必须注意的方面。人类一直是与动物共生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主要流行病,比如黑死病、疟疾、黄热病、肺结核等,都能感染动物。野生动物或家畜家禽常常以极大的密度群居生活,它们也成为直接或通过携带有病菌的昆虫向人类传播病菌等的源头。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改变持续地原体提供机会,使其从正常的动物宿主传到人类,或从人类传到其他动物。 畜牧业是与农业同时发展起来的。畜牧业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可以称之为革命的一件大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也不是一项偶然的发明,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驯养动物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许多野生动物被驯养成为家畜。驯养山羊、绵羊、猪、牛等家畜,改善了古代人的营养状况,但这些动物身上难免藏有病原体和寄生虫,成为许多传染病的传播载体。人类在与家畜的长期密切接触过程中,一些家畜身上携带的病菌转移到了人类身上,家畜的疾病也由此成为人类的疾病。人类通过食用动物或只是与动物接 触而被感染传染病。人类历史上流传的几种瘟疫几乎全来自驯养动物,或与人类共生性强的动物有关。比如麻疹来自牛瘟,肺结核来自牛,天花来自牛痘,流感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和狗,恶性疟疾来自禽鸟。这些原本寄生在动物身上的病菌转移到人身上后,经过适应和变异就发展成为典型的人类疾病。人口的增长和定居社会的兴起促进了这些疾病的传播,由此而造成了我们称之为瘟疫的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除了驯养动物和与人类共生的动物,还有野生动物。在工业社会以前,人和其他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基本上是各有各的领地,所以此前人畜共患的疾病多是与家畜或与人类共生的动物有关。但是,工业文明出现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大范围开发,迫使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大规模捕杀,不仅使许多野生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同时也拉近了人与它们的距离,这就增加了这些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向人类感染的危险性。如果是这样,人类面对的就又是一种从没有见过的可怕的病毒,又会经历一次没有经历过的恐怖的瘟疫。野生动物往往携带着多种可以传播给人类的病菌。有研究表明,20世纪后期至今出现的新兴传染病,比如艾滋病、埃博拉、莱姆病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来自野生动物,而不是驯化物种。来自野外的病原体进化和人畜共患疾病,在新兴传染病的动态机制中比以前占了更大的比重。一系列新的来源于野生动物的传染病的不断出现,表明动物传染病库 是人类新传染病潜在的原因。美国学者凯尔·哈珀说:“疾病史上最主要的戏剧性事件,是野生宿主身上不断出现的新细菌,找到不断扩大、容易相互感染的人类群体。” 总之,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头上就存在孕育和滋生瘟疫的条件。驯养家畜,大规模聚居,建构永久的村落、城镇,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文明,这些带来的代价之一就是新的疾病。人类行为和技术的改变,几千年的狩猎、觅食、烹饪,以及动植物的驯化和永久居住地的形成,改变了人类和微生物的关系,导致了人类疾病模式的重大转变,给致病的微生物媒介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瘟疫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一部分,瘟疫困境下的人生境遇境遇催生人性的极端表现。人性是脆弱的,也是坚强的;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是怯懦的,也是勇敢的。但终归是勇敢战胜了怯懦,伟大遮蔽了渺小。因此,才有了人性的光辉,才有了文明的进步。阅读本书,让我们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为当前及今后面临的种种未知挑战汲取经验教训,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