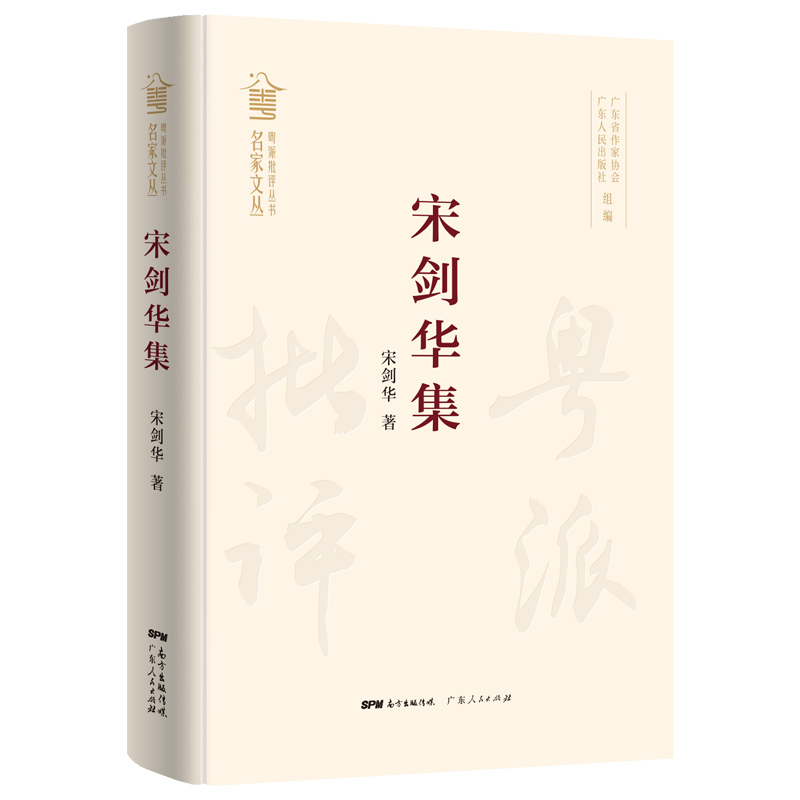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1.92
折扣购买: 宋剑华集(粤派批评丛书?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144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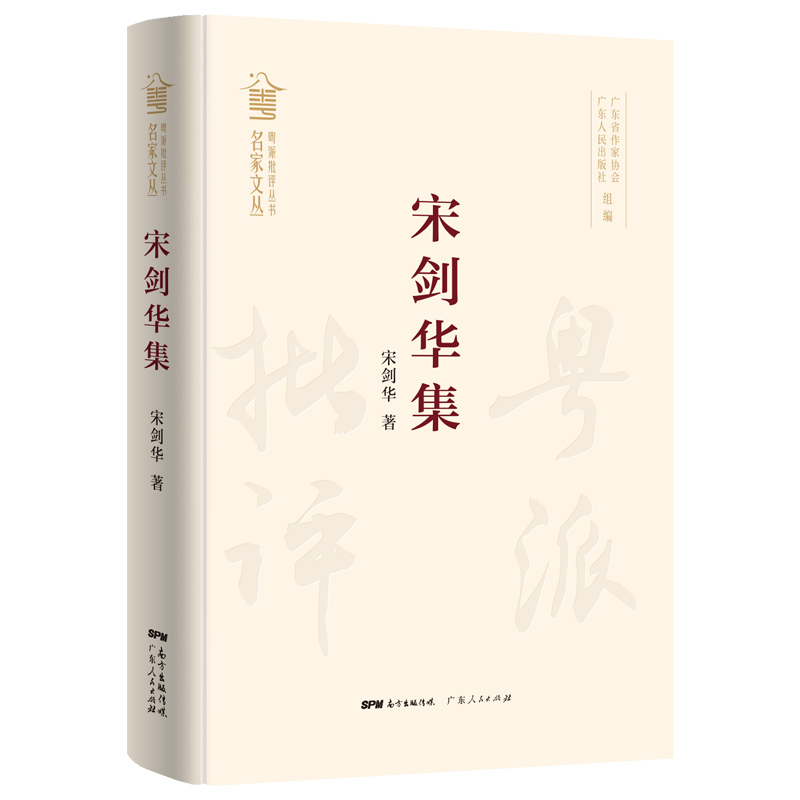
宋剑华,男,1954年12月25日出生,辽宁丹东人。1981年7月,毕业于四川涪陵师范专科学校(现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7月,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现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从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话剧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海南省重点学科责任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9月至2008年2月,作为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课程一学期。2018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出版学术著作有:《胡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红色经典”的真实与传奇》《围城中的巨人:理解鲁迅的寂寞与悲哀》等13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后期资助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省社科项目2项;曾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第一章?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坚守 早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陈独秀就曾公开声言,《新青年》杂志发动文学革命的思想宗旨,就是要用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陈独秀与胡适都把文学革命定性为“反传统”,这一论断几乎得到了后来学界的一致认同。比如李泽厚在总结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时,便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性语气这样写道:“《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陆续发表了易白沙、高一涵、胡适、吴虞、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则更是标新立异,他不仅认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是“反传统”,而且还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 。对于上述种种“反传统”说,我个人始终都不敢苟同。 若要弄清楚“五四”以来,新文学究竟是彻底地“反传统”,还是“批判”与“承续”并存,我们首先要去厘清一个最基本的名词概念 — 即什么是“传统”。所谓“传统”者,《新华词典》里早已有过明确的释义:“过去传下来具有一定特点的某种思想、作风、信仰、风俗、习惯等。” 如果按照《新华词典》的定义或表述,那么我们将直接面临着两大难题:其一,既然“传统”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与过去,那么“反传统”无疑就是在反我们民族的历史与过去;由于我们与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否定传统也就意味着同时否定了我们自己。试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传统我们又是“谁”?其二,“传统”中确有“精华”与“糟粕”两种成分,但是我们依据何种价值尺度去加以区分?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倡导科学理性精神,可另一方面却又以民间庸俗等同于儒学礼教,完全歪曲了孔子作《论语》而正“民风”的原初本意,这难道就是知识精英们所理解的科学理性吗?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真实的历史倾向性:即先驱者们绝非是在全面地扬弃传统文化(他们不可能做到),只不过是打着“西化”的旗号去重新负载传统(实际情形则是如此);无论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还是鲁迅、郭沫若、巴金,在他们那种思想启蒙的激烈言辞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意图。比如“西化派”的领军人物胡适就曾明确地指出,“五四”以来对于传统儒学的猛烈攻击完全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救行为,而不是简单地以“西化”去替代传统。故他非常自信地向世人宣称:这场“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因此,重新认识与理解“五四”反传统的历史成因以及文学表现,科学地评价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意义与运作模式,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学进城与新文学培育期的文化背景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发生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延续;经过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两代知识精英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这两次思想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又与儒学进城有着十分密切的逻辑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巨大变革归功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直接移植,我个人对此说法却并不赞同。因为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还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他们都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从旧垒中来” ,对于传统文化的沉重负载,使他们的灵魂深处充满了“毒气和鬼气” 。尽管那时候“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故梁启超后来曾无限感慨地回忆道:“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 — 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梁启超的追述的确值得我们后人去认真思考,但他们能够把“新学”搞得令全国上下热血沸腾,并构成了“五四”知识精英救亡图存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我所要展开论述的一个全新概念:儒学进城与思想启蒙的历史真相。 儒学进城是指近代中国由于大量乡绅和学子进城,最终导致以现代大都市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转型。众所周知,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思想重镇是新兴的城市上海而不是古老的皇城北京;后来帝制被废学人又联袂北上,这才形成了以北大为中心的启蒙阵营。目前国内学人仍抱有这样一种偏见,他们认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租界出现了精英文化真空的情形,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精英文化对平民文化控制角色的中国绅士在租界不存在,不是说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社会集团不存在。” 这种说法完全有违客观事实,因为法国汉学家白吉尔就曾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她根据历史资料考证告诉我们,晚清时代“在这个城市(上海)社会里,居领导地位的是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阶层” 。租界文化当然也不能例外,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其早期身份无疑都是属于乡绅阶层,他们都是以上海租界为栖身之地,并以报刊杂志或办班讲学等途径去发动思想启蒙运动,同样也扮演着“精英文化对平民文化”进行控制的社会角色。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乡绅”概念去做一简单解释。所谓“乡绅”者,即“乡间的绅士” 也,专指“乡里中的官吏或读书人” 。如果按照这些权威定义去推演,康有为与梁启超等晚清学人,毫无疑问都是些开明“乡绅”而已。因为他们在科考中举之后,都没有直接进入仕途,而是兴教办学造福乡梓,向青年学子传授儒家思想。比如,康有为在广州开办“长兴学舍”,纳梁启超等人为徒;吴稚晖到同乡家里做塾师,为其子讲授“四书五经”要义等。我个人认为康有为等开明“乡绅”最终将他们思想传播的阵地由乡间转向了大都市,甚至于还转移到了国外去讲授“国学”(章太炎先生在东京办学讲经便是如此),这都是对儒学进城乃至其现代转型的很好注解。